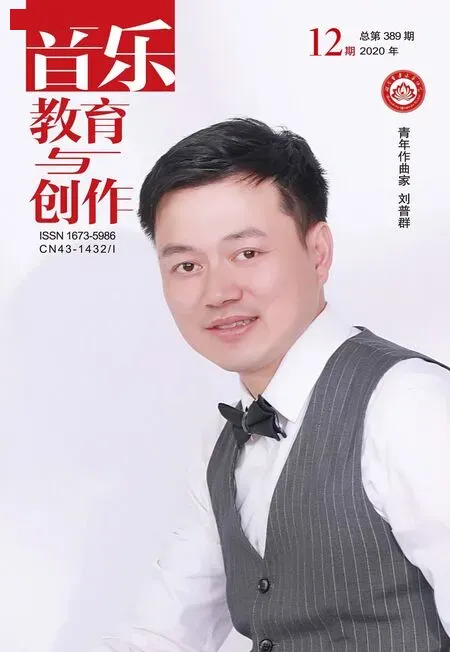浅谈胡琴演奏在“戏乐” 对话艺术中的呈现与延伸
□ 蔡 霞
胡琴,是我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弓弦乐器家族。 近年来通过当代作曲家、 胡琴演奏家、教育家的不懈努力,胡琴演奏以丰富多样的表演形式呈现震撼人心的舞台艺术效果, 逐步成为传统音乐和现代创作融合的典范,深受观众和演奏者的喜爱。 而戏曲音乐是戏曲艺术的重要元素,是中华民族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之一,相同的剧本,各剧种都能排演,唯独音乐不可相互替代,能起到区分各个剧种的识别作用。众所周知,戏曲乐队中担负领奏和主弦演奏的乐器通常为胡琴,它在剧目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京胡、 板胡、 高胡、 坠胡、 大筒等多种地域风格、 形制、音色各异的胡琴乐器在各自地域戏曲艺术中散发着无穷魅力。
中国戏曲艺术源远流长,它以唱、 念、 做、 打为基本表现手段,融“歌、 舞、 乐” 为一体。 民间有句俗话: 戏曲就是“戏” 一半,“曲” 一半,观众是来“听”戏,不是来“看” 戏的。 随着时代变迁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任何艺术存在都需要土壤与空间。 面对观众审美品味与审美需求的不断提高,戏曲艺术家们不断优化和创新戏曲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有两种创新戏曲门类尤为观众所喜爱: 一是“戏歌”,二是“戏舞”。 “戏歌” 是戏曲与歌曲相结合,不仅为传统戏曲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也丰富、 提升了歌曲创作的艺术内涵,拓宽实现了歌曲创作的多元化之路。 无论是早期风靡大江南北的《故乡是北京》 《前门情思大碗茶》 ,以流行唱法为主的《情怨》 《北京一夜》 《卷珠帘》,还是新时期委婉与大气相融合的《梨花颂》《中国脊梁》《天下乡亲》 等戏歌作品,几乎曲曲经典动人、 百听不厌,营造无人不为之陶醉的艺术效果;“戏舞” 则是戏曲与舞蹈相结合,精美绝伦的舞蹈融合极具特色的戏曲设计,将传统戏曲中水袖舞、扇子舞、 剑舞、 霓裳羽衣舞等传统戏曲符号加以形、 神、 韵、 味兼并的舞蹈化呈现,意蕴深厚,带给观众美轮美奂的视觉享受。群舞《俏花旦》 《夜深沉》 流动的舞姿,舞剧《粉墨春秋》 瑰丽、精彩的多维呈现,更是令人们惊叹不已。
一、 “戏乐” 对话的艺术特质
随着“戏歌” 与“戏舞” 的推陈出新,中国戏曲艺术增添了许多新的色彩,而“戏乐” 对话的表现形式则非常少见。 如何将中国戏曲与器乐演奏巧妙融合起来,需要每一位戏曲人和音乐人深入研究、 探索。 笔者是一名在湖南艺术职业学院任教二十多年的胡琴教师,从小在湖南花鼓戏剧团成长,除了对自身胡琴专业的不懈追求之外,会时常关注、 思考戏曲艺术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在我看来,中国戏曲之美,古老精致,百世流芳,戏歌、 戏舞、戏乐“三花齐放” 是现代戏曲艺术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
“戏乐” 主要指戏曲与器乐演奏相结合。 打破固有的传统模式,以开放的观念拓宽器乐表演的文化视野,在赋予乐器演奏技法本身及其运用的基础上融入新视角,以地域风格、 民族风格、 群体风格为艺术特征,借鉴韵美的戏曲艺术元素和典雅的舞美意境烘托,将“中国戏曲” 与“器乐演奏” 融合交织,多元化延伸拓展器乐演奏艺术,构建独特的音乐语言,或缠绵悱恻、 或高亢激越、 或轻盈流转、 或悲怆凄美、 或清丽舒展,诠释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意蕴,营造精美别致、 气韵传神、撼人心弦的视听效果。 2020 年疫情期间,广东民族乐团推出了“国乐为你鼓与呼” 系列线上音乐会,被誉为“南国鼓王” 的国家一级演奏员陈佐辉司鼓演奏了潮州大锣鼓代表名作《关公过五关》。 这首乐曲根据戏曲“美须出千里走单骑、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 的情节谱写而成,演奏者“槌起时威风凛凛、 槌落处挥斥方遒”,曲牌套用完美,音乐形象鲜明,锣鼓配置有序,气势壮观雄伟,是一首叙事性的大型锣鼓音乐。 作品推介旨在讴歌抗疫战役中涌现的当代英雄们,鼓舞了士气,享誉海内外。
二、 “戏乐” 对话中的胡琴功能
戏曲音乐对胡琴演奏技巧和风格早已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借鉴戏曲音乐素材创作的经典二胡曲目历来有之,如《秦腔主题随想曲》 《湘江乐》 《豫乡行》《迷胡调》 《长城随想》 《黄梅戏变奏曲》 《西秦王爷》 等,这些优秀乐曲大量汲取剧种与地域不同的戏曲音乐风格和音调内涵,加以独到的演奏技法丰富胡琴民族化,使音乐旋律更优美、 更灵动,风格韵味更浓郁、 更传神。而胡琴演奏在戏曲伴奏乐队中又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伴随着南曲北戏的传播,在戏曲艺术的流变、 发展中,在不断汲取传统声腔语韵精华的同时,发挥其近似人声、 曲韵悠长的特点,具备“戏乐” 发展中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如京剧曲牌《夜深沉》 被广泛运用,是经过历代京胡琴师、作曲家们不断改编创造,使京胡独奏、 合奏、 重奏版本成为各大乐团音乐会保留节目,常演不衰,更有京胡与舞蹈交融惊艳动人,大堂鼓与京胡对奏荡气回肠; 又如,近几年移植经典京剧《智取威虎山》 唱段改编的胡琴四重奏《打虎上山》 独树一帜,以三把二胡轮流主奏,配合一把中胡低音衬托,将风雨交加的林海与人物角色的英雄气概展现得酣畅淋漓,令人身临其境,成为了当代最受欢迎的胡琴重奏曲。 可见,戏曲与胡琴二者之间有着重要关联且密不可分,延伸、 拓展胡琴演奏的音乐表现力,进一步与戏曲元素相融相促,实现对“传统之根”的“复接”,将积极推动戏曲艺术与民族器乐的传承发展。
三、 “戏乐” 对话中的胡琴创新融合
时代向前发展,科技高新前行,带来了物质生活与文化享受的现代化。 胡琴演奏作为戏曲音乐的重要演奏乐器,演奏者不仅要遵循胡琴演奏艺术的发展规律,充分了解尊重广大观众的审美趣味, 还要积淀戏曲艺术理论知识、深入熟悉戏曲声腔、 领会胡琴音乐的审美规律,不断创新思维,创作作品、 推进技法,拓展艺术呈现形式和传播形式,为胡琴演奏艺术多元化发展输入新鲜动力;而对于中国戏曲艺术来说,提倡多从胡琴演奏艺术的角度来进行创新融合,为传统戏曲艺术创编新颖的表演形式,弥补戏曲艺术创新发展中遭遇的局限性,进而为“戏乐”对话的呈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如何继承与创新,甚为关键。对于此,笔者不仅仅是亲历其中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同时又是努力探索的实践者和创新者。 我在中国音乐学院二胡硕士研修期间,导师宋飞教授曾不断激发我的创新意识、 培养我的创新能力,甚至鼓励我要“胆大妄为”,要有艺术思维和胆识,勇于超越老师。得益于这位当代胡琴演奏家、 教育家宋飞导师的引导与鼓励,我富有创意地将硕士毕业音乐会《戏与乐的对话——弓弦雅韵》 融八种胡琴演奏和六种戏曲元素为一体,将声、 光、 电设计巧妙结合到舞美之中,营造出典雅的场景和幽美的意境,于2017 年5 月开创了湖南文艺工作者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的先河,上演了“戏雅流芳、 南腔北调、弦韵馨声” 三个篇章,移植改编、演绎了中胡与曲笛《昆曲牡丹亭——惊梦》、 京胡与高胡《梨花颂——蝶恋》 等十首作品,被专家称赞为“中国培养地方高级艺术人才的典型案例”。 2018 年,笔者受邀参加以“戏乐共生、 源远流长” 为主题的中国弓弦艺术节,于《戏韵曲腔——胡琴专场音乐会》 中演绎由湖南花鼓戏声腔改编的大筒独奏曲《金堤柳林披薄纱》,受到观众与专家的一致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戏曲学院举办的“戏曲、 曲艺、 音乐多视域中的民族弓弦艺术” 专题研讨会上,我荣幸地与来自胡琴演奏戏剧戏曲学、 戏曲影视学等专家、 学者根据自身专业、 学术思考和艺术实践等,由点到面,深度细致地就戏曲音乐发展,胡琴艺术史中的戏乐关系,戏曲音乐中弓弦乐的文化归属与发展以及当代戏曲音乐和民族音乐创作等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具有高度、 深度和广度的对话与研讨。 这也是通过中国弓弦艺术节首次提出将戏曲、 曲艺与音乐三个艺术领域融合在同一个视域当中的想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近期,本人还创作、 编导了一首“戏乐” 对话节目——胡琴与剑舞《霞飞剑影》。 作品借鉴了中央民族乐团新创曲目《象王行》的曲风和结构,形式上大胆创新,加入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身段表演“剑舞”,旋律以二胡演奏为主,独具匠心地将“湖南的胡琴——大筒” 植入,作为主旋律发展和乐曲的高潮部分演绎,形成具有湖湘地域特色的现代音乐和灵动多元的舞台表演,以期在气韵上达成人剑合一、 人琴合一、剑琴合一,呈现出侠骨飞仙、 刀光剑影的视听效果。 这首“戏乐”原创节目的编创过程由湖南卫视《我的纪录片》 栏目播出,有专家观看后兴奋地说: “作品很好,是传统与现代、 古典与时尚的对接,散发出戏曲人独特的情致韵味与青春风采”。
中国戏曲艺术是一种色彩斑斓的精美艺术,宛如一幅秀丽的山水长卷。 创新思维是实现戏曲艺术与器乐演奏对话的前提,唯美融合是提升戏乐对话呈现魅力的保障,将情感与乐感相统一则是戏曲艺术与器乐演奏传承与发展的关键。 胡琴演奏者更要基于联想、 想象、 总结和体悟,延伸艺术幻想,创设情感意境,努力做到景与情、 动与静、 远与近的结合,提升作品的立体感和空间感,使“戏乐” 对话更富有诗情画意。 此外,胡琴演奏者还需要深入解读作品,借助娴熟的演奏技巧保持胡琴演奏的情感张力和情感传递能力,实现以音发情,提升胡琴演奏的魅力,引领观众进入“戏乐” 对话构建的情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