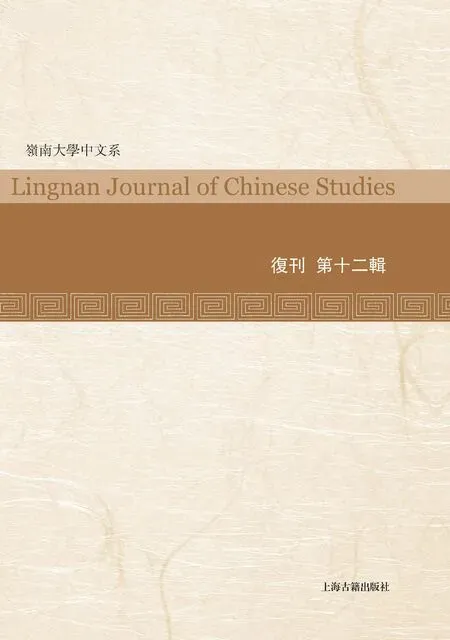同志文學的翻譯、再版與重譯:一個叙事建構的視角
李 波
一、引 言
同性戀一直以來是一個敏感話題,甚至是社會禁忌;同志文學的境遇亦然。雖然,西方翻譯研究學界近年來對同志文學的翻譯給予越來越多關注,相關研究在中文語境下並没有得到相應的重視。同志文學的書寫和翻譯始終是在文化和意識形態衝突語境下進行。貝克在《翻譯與衝突——叙事性闡釋》一書中指出,“同一組事件透過不同的方式建構,可以得到立場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叙事,其結果對於衝突各方均有重要意義”①有關貝克此書的内容,本文參考了該書的中文譯本《翻譯與衝突——叙事性闡釋》,主譯者為趙文靜,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2006,p.107);同時,通過建構策略(framing strategies),“譯者、出版商、編輯以及參與到整個翻譯出版過程的相關人員,強調、弱化或改變原文中叙事的某些方面”(2006,p.105)。基於此,本文試圖探討同志文學的奠基之作Maurice的中文翻譯。透過Maurice(莫瑞斯)的中譯,我們可以考察譯者和出版商如何共謀,在譯入語文化和意識形態語境下,(重新)建構出被強化的同性戀主題;而讀者對譯作的不滿,迫使譯者和出版社再版時,不得不做出回應,對譯作進行重新建構,呈現出與社會接受語境的互動建構策略。
二、文獻回顧
何為同志文學?紀大偉(2017)、朱偉誠(2005)、弗朗·馬丁(Fran Martin)(2003)、矛鋒(1996)、伯恩·馮(Byrne Fone)(1998,Preface)、麥科勒姆和圖卡嫩(Mccallum and Tuhkanen)(2014)、貝鄂(Baer)(2016)等人從不同角度對同志文學進行過界定②更多有關同志/女性平權運動與文學書寫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可以參考Mccallum和Tuhkanen為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ay and Lesbian Literature寫的序言(Mccallum&Tuhkanen,2014,pp.112)。,也許可以用一個工作定義來界定同志文學,無論作者的性傾向如何,如果文學文本本身主題涉及同性情欲,就可以作為同志文學而成為研究客體。近年來,學界對同志文學的翻譯給予越來越多關注(Baer,2016;Baer and Kaindl,2018;Harvey,2000,2003;Linder,2014;Mazzei,2007;Mira,1999等)。哈維(Harvey)分析了在法語和英語之間翻譯“同性戀主題”的文學作品過程中所發生的翻譯轉移(translation shifts),強調翻譯文本成為“對抗意識形態定位之間的交界面”(2003,p.43)。以上研究,多側重從原語與譯入語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意識形態語境下對同性戀的不同態度入手,探討同志文學作品在翻譯過程中的審查、改寫、主題強化與弱化等,但總體而言,正如貝鄂也指出,“翻譯中無處不在的歸化處理表明大衆對同志題材文學的猶豫和矛盾”(2016,
p.160)。
相較而言,同志文學的翻譯在中文語境下並没有得到相應的重視和研究。對同志文學翻譯的討論,散見於中文文獻中,如余靜和周韻妮(2018)、段薇(2012)、謝宏橋(2015)、孫小雅(2015)等。孫小雅以美國黑人作家艾麗斯·沃克(Alice Walker)的長篇書信體小説The Color of Purple及其三個中文譯本作為研究對象,她指出,“在譯者主體性及譯者不可掌控的文化和社會因素的影響下,該書在引入中國的過程中,不得不參照中國的現實情況而將同性戀的描寫做出一定的改變”(同上,頁ⅲ—ⅳ)。余靜和周韻妮(2018)以小説Brokeback Mountain的中文翻譯為例,考察譯者在處理小説同性戀内容時的翻譯策略,如加强、壓制、亦或干預,而影響翻譯策略的因素包括“對同性戀性描寫的嚴格審查制度、譯者對同性戀群體的認知、以及譯者對婚姻的態度”等(2018:1)。
簡言之,無論是文學生產還是翻譯接受,對待同性戀的社會容忍度不同,畢竟不同的文化、社會、宗教等背景,左右著文學作品的生產和傳播。而作為敏感題材的同志文學,更會受到文化價值和宗教信條的干預。本文的研究對象是福斯特的Maurice,而這部小説的西班牙語譯文,也有學者 從 不同角度 進 行研究(Valdeón 2009;Lázaro 2019;etc)。Valdeón主要利用翻譯研究的重要概念(如交際翻譯、譯者作為文化協調員、翻譯能力等),從文本、文化及文學三個層面上對這部作品的英語和西班牙語版本做了比較,但研究的重點並非討論作品的同性戀主題在翻譯中的呈現。Lázaro的研究則指出,小説的西班牙語翻譯於1973年出版,雖然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實行獨裁統治的時期(1939—1975)已接近末期,但是“當時的審查制度非常嚴厲”(Lázaro 2019:1)①審查與翻譯之間的關係,已經有很多西方學者做了深入探討與研究(e.g.Seruya and Moniz,2008;Woods,2012;Chuilleanáin et al,2009;Billiani,2007),而學者張南峰(2008)和譚載喜(2015)也討論過中國語境下審查與翻譯之間的糾纏。。作者利用審查辦公室的檔案資料,研究小説中同性戀的主題如何經歷傳統恐同觀的審查,展示這部小説的西班牙語譯本在送審過程中的情形,特别是審查者對譯文的意見和標注,其中不但有對正文内容的標注,還有對“引言”的標注(Lázaro 2019:6);原版小説正文之前Furbank在引言中強調了作者對同性戀的正面描寫以及對當時社會不接受同性戀的批判,西班牙語譯者的完整呈現,也被審查者標出。Lázaro(2019:10)指出,“譯者没有對原文内容進行弱化處理,或者删除審查者可能會認為是不道德的部分,即譯文整體是準確、忠實於原作的”,但在當時審查嚴格的環境下,審查者還是給譯文開了綠燈。
同志文學的翻譯和接受呈現出社會衝突語境的特徵,所以在不同語境下,會出現原文同志主題強化或弱化的處理策略。另外,譯者作為翻譯主體,其自我身份認同也會影響翻譯的決策,如譯者刻意避免翻譯同志題材作品可能導致對自身的社會輿論與政治、宗教打壓,採取回避、弱化同志主題的策略等。當然,也有譯者(包括出版社、編輯等)操縱同志文學的翻譯,實現政治目的等。
三、Maurice的 中 譯
Maurice是英國著名作家E·M·福斯特(E.M.Forster)於1913年寫下的頗具自傳色彩的同名小説,講述了在20世紀初等級觀念非常嚴格、保守的英國發生的一段同性愛情故事。大衛·李維特(David Leavitt)在引言中將這部作品視為現代同志文學的奠基之作(Forster 1972)。囿於當時英國的社會環境,作者決定小説要在自己過世之後纔能出版,因此,英文原版小説在1971年由The Provost and Scholars of King's College,Cambridge正式出版,而中文譯本也説明是基於這個版本翻譯的②根據本文作者考證,目前所見中文譯本版本包括文潔若(2002,北京)、文潔若(2002,臺北)、文潔若(2009,上海)和文潔若(2016,上海),以及李斯毅(2019,新北市)。。在1971年的Cambridge版本中,還附有一篇《結尾的札記》,日期是1960年9月。在2002年的中國大陸中文譯本中,增加了費爾班克(P.N.Furbank)的《導言》①實際上,1971年Edward Arnold經由Cambridge出版的版本,並没有收録這篇導言。文潔若譯本後面顯示基於這個版本翻譯,而這個導言其實出現在1972年Penguin Books的版本中。、文潔若的《譯後記》以及文潔若的丈夫、著名作家和譯者蕭乾先生的一篇短文《唉,同性戀》。臺灣譯本也出版於2002年,同樣是文潔若的翻譯,只是題目更改為《墨利斯的情人》,封面標明是“電影《墨利斯的情人》原著小説”②《墨利斯的情人》(Maurice)是一部1987年的英國電影,故事改編自英國著名作家E·M·福斯特於1913年寫下的頗具自傳色彩的同名小説Maurice。,而封底的導語也未有提及“同性戀情”,反而強調“墨利斯原欲抽離性别上的錯亂,符合社會大衆的要求,但他的身心始終無法平靜、安頓下來……書中人物不僅背負社會歧視的壓力,也多了分對英國階級制度的越界掙扎”。臺灣版本中並没有收録費爾班克的《導言》,而且把福斯特的《結尾的札記》放在了譯者文潔若的《譯後記》之後③這明顯是一個排版錯誤,福斯特的《結尾札記》是原著一個不可分割的部份。。這個版本與同年北京版本的最大區别是没有收録蕭乾的短文,原因留在後文揭曉。
原作除了故事本身講述同性戀的内容,作者福斯特的結尾札記也討論了20世紀上半葉英國社會對同性戀的社會態度開始發生改變,至少已經不再是19世紀末將同性戀列為刑事罪的時代。而在中文翻譯版本中,從整個翻譯出版來看,是一個重新建構叙事(reframing the narrative)的系統過程。中文版封面指出,這是“一部探討社會價值與愛情衝突的經典文學作品”,而封底的導語(blurb)引用了《紐約時報》的評論,之後開宗明義地指出,“這是一部描寫同性戀情的小説”,最後説明“蕭乾先生去世後,其妻文潔若以全新的譯本來紀念中英兩位作家之間彌足珍貴的友誼”。在封面内頁的作者簡介最後寫到,“作者在書中肯定了同性戀,走在時代之前”。文潔若的《譯後記》則集中回顧蕭乾與該書作者的交往和友誼,同時指出,“福斯特生前,只有少數朋友知道他是個同性戀者……蕭乾在1943年初讀此稿時,就已經知道了福斯特的這段隱私”(福斯特,2002,頁285)。
小説原文中,有諸多互文性指涉的成分,這些互文性内容與外圍社會以及在文本内部,透過相互指涉,建構起一個同性戀的叙事話語。互文性在主題建構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卻對譯者提出了挑戰④有關翻譯與互文性研究,參見Venuti(2009)、Klimovich(2014)、Li(2017)以及范司水(2016)。。巴赫金在討論文本和語境的界限問題時指出,“文本的每一個詞語(每一個符號)都引導人走出文本的範圍。任何的理解都要把該文本與其他文本聯繫起來”(1998:379)。法國符號學家克莉斯蒂娃(Kristeva)則將巴赫金的這種思想引申,並且以互文性(intertextuality)這個術語進行了總結(Kristeva 1986:35-37)。互文性概念的提出,打破了文本的封閉狀態,將意義呈現出一種開放的姿態。在文學翻譯過程中,在距離比較大的語言和文化之間,可以採用保留原文的互文性指涉,而加上注釋的方法來保證信息的傳遞。這就是我們常看到的,在很多翻譯中,譯者會採取腳注、尾注、或者是術語表(glossary)的形式,來彌補因為直譯而導致的對某些互文性文化成分的理解障礙。
互文性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同志文學,作者通過運用互文性内容,進一步加強文學文本的主題。有時,互文性是向讀者表達寫作目的的。互文性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有利於了解一類文化環境中特定的群體和此群體中個體的身份。同志文學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國詩人劉遵的一首詩中寫道:“剪袖恩雖重,殘桃愛未終。”實際上,這是互文性的典型特徵和用途,因為“斷袖”、“分桃”在歷史上用來表達同性愛情,所以讀者很快就能理解這一指涉意義。
在小説《莫瑞斯》中,柏拉圖(Plato)的著作《會飲篇》(The Symposium)屢次被提起。同時還提到了同性戀藝術家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聖經中的索多瑪城(Sodomite City),以及因同性戀被判入獄的英國作家奥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所有這些互文性描寫有助於加強文學作品中“同性愛情”的主題,但是同時也給譯者的翻譯工作加大難度。大多數情況下,因為原文讀者熟悉文章的文化背景,所以他們能將文中的這些元素和例子與同性戀聯繫到一起。然而,將原文翻譯為中文,考慮到目標讀者的文化差異,和中文讀者對西方文化缺乏了解,那麽是否還能將這些互文性的效果準確傳達給讀者?對於目標讀者來説,他們是否能從翻譯文中獲得原文對等的含義?
貝克指出,“翻譯對於叙事的建構可以運用任何語言和非語言資源:從副語言手段(如語調、印刷格式等)、視覺資源(如色彩和意象等)以及各種語言手段(如時態轉换、符碼轉换以及使用諱飾語等)”(2006,p.107)。在具體操作層面上,貝克主要討論了用於調節叙事的四種策略:時空建構(temporal and spatial framing)、選擇性建構(selective appropriation of textual material)、通過標示加以建構(framing by labeling)以及對參與者的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 of participants)。其中,通過標示加以建構是指在翻譯時透過對名稱或個别詞彙的變動達到重新建構叙事内容的目的,尤其在翻譯書名、電影名及其他事物名稱時都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對原文進行干涉,以重新建構叙事;對參與者的重新定位,是指在翻譯出版過程中,參與者之間的關係、參與者與讀者或聽者的關係均可以被重新定位(ibid.,p.132),具體操作層面可以是在文本或話語内(ibid.,p.135),更加可以透過副文本評論(repositioning in paratextual commentary)(ibid.,p.133),“前言、序言、腳注、詞彙表以及封面設計及導語(當然,很多時候封面設計和導語並非譯者所能控制),透過這些渠道,譯者可以重新定位自己、譯文讀者以及該時空涉及到的其他參與者”(ibid.)。本文將以貝克的叙事建構為分析框架,討論Maurice在翻譯、再版、重譯中的建構策略和主題呈現。
小説的中文譯本,經由譯者、出版商的通力合作,對小説的同性戀主題進行的重新建構(reframing),最直接的策略就是透過譯本的腳注來實現
(Baker,2006,p.133)。
首先,小説初稿完成於1914年,迫於社會現實,直到作者去世後的1971年纔正式出版,這是因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國,同性戀不但被污名化,而且是不合法的。作者的這種擔心,是因為有前車之鑑,也就是英國文學史上著名的王爾德案。在小説第9章最後,當克萊夫(Clive)向莫瑞斯耳語“我愛你”時,莫瑞斯卻意外地回應到,“德拉姆,你是個英國人,我也是。不要説荒謬的話。你並没有傷害我的感情,因為我曉得你是言不由衷。然而,你要知道,這是惟一絶對被禁忌的話題。他是列在大學要覽裏的最嚴重的犯罪行為。你千萬不要再説了。德拉姆!這確實是一種可鄙的非分之想……”(福斯特,2002,頁58)。莫瑞斯的反應來自他對社會現實的屈服,不僅僅是對社會成見的迴避,更多是對法律條文的恐懼。當莫瑞斯決定尋求心理醫生的治療時,他先是用“漫不經心的語氣”問自己唯一熟悉的年輕醫生喬伊特(Jowitt):“我説,你在這一帶巡回治療的時候,會不會碰上奥斯卡·王爾德那樣的難以啟齒的病例呢?”(同上,頁168)在得到否定回答之後,他不得已向家庭醫生巴裏大夫(Dr.Barry)求助:“我是奥斯卡·王爾德那種難以啟齒的人。”(同上,頁171)譯者在首次提及王爾德時,加了一個腳注指出:“奥斯卡·王爾德(1854—1900)是愛爾蘭詩人、小説家、戲劇家。1895年他被控和青年艾爾弗雷德·道格拉斯搞同性戀,被判入獄服勞役兩年。”(同上,頁168)
其次,對古希臘同性戀盛行的互文指涉也有助於對原文主題的建構。小説第7章結尾部分,“這個學期即將結束的時候,他們接觸到一個更敏感的問題”(同上,頁50),在翻譯課上,學生把希臘文口譯成英文,“康沃利斯先生卻用低沉平穩的聲調説:‘省略。這一段涉及希臘人那難以啟齒的罪惡’。”(同上,頁51)克萊夫認為老師虚偽,且不應該省略,“希臘人,也就是説,絶大多數希臘人都有那樣一種傾向”(同上,頁50)。之後,克萊夫問莫瑞斯:“你讀過《會飲篇》嗎?”(同上)“莫瑞斯没讀過。他不曾補充説,自己倒是探索過馬提雅爾。”(同上)中文譯本中,對“罪惡”加注腳“指同性戀”。古希臘的同性戀傳統,學者多有研究(Dover 1978;Hubbard 2003;Davidson 2007;etc.)。雖然《會飲篇》的注腳没有提及同性戀,但《會飲篇》對男同性戀的贊美和馬提雅爾(Martial)對同性戀的指涉都服務於作者的寫作動機和意圖①有關《會飲篇》參見David Decosta Leitao撰寫的Plato and the Philosophical Dialogue,載McCallum and Tuhkanen(2014,pp.39-40);有關Martial參見Roman Prose and Poetry,作者Thomas K.Hubbard,載McCallum and Tuhkanen(2014,pp.7980)。。
再其次,對《聖經》所多瑪城(Sodomite)的互文指涉。小説多處有提到《聖經》内容,而最特别的是對所多瑪的提及。小説第12章中,克萊夫是個虔誠教徒,“有著接近神、使神感到滿意的強烈願望。不過,年少時,他就領悟到自己因來自所多瑪的另一種欲望而備受磨難”(福斯特,2002,頁69)。第32章中,巴裏大夫在與莫瑞斯有關後者的王爾德不恥交談後,他(巴裏大夫)相信,“惟有最墮落的人纔能瞥視所多瑪”(同上,頁173)。譯者在首次提及所多瑪時,加腳注解釋,克萊夫感到的“‘另一種欲望’指同性戀傾向”(同上,頁69)。
除了以上英國歷史、古希臘和《聖經》對同性戀的互文指涉之外,小説中還有其他多處對同性戀的互文指涉。比如第21章提及哈莫狄奥斯(Harmodius)和阿裏斯托基頓(Aristogeiton)的故事以及第邦神聖隊(the Theban Band),譯者注腳解釋,前者是“一對同性戀者”,而後者“是一對對同性戀者組成的軍隊”。莫瑞斯初訪克萊夫時,後者正在找《悲愴交響曲》中的《進行曲》(同上,頁32)(指涉柴可夫斯基與侄子的關係);莫瑞斯向巴裏醫生求診時,室内描寫提及“壁爐架上立著梅迪契的維納斯銅像”,而腳注裏解釋梅迪契是意大利雕刻家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的贊助人,後者是同性戀藝術家。除了小説主體本身,作者福斯特在1960年寫的札記裏,提到更多同性戀人物和事件,如福斯特的師友和《沃爾芬登報告》等,譯者不遺餘力地在注腳中解釋注明各人的同性戀身份和報告關於成年同性戀性行為非刑事化的訴求。
不得不指出,上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對同性戀議題依然非常敏感。1993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與三島由紀夫的同志小説《假面的告白》同名的翻譯小説集,收録有義大利、德國、愛爾蘭、美國、阿根廷等國家的作品。然而,這本翻譯集的副標題是《變態心理小説》,封面導言將同性戀病態化,“這裏展現的是種種病態的心理和病態的人格。但正如展覽疾病是為了防止疾病一樣,認識並正視這些病態恰是治療疾病的前提和條件”(王向遠、亓華,1993,封面頁)。文潔若在大陸2002譯本最後附加了一篇蕭乾先生早年寫的《唉,同性戀》,主要是因為蕭乾在這篇文章中談到他與福斯特的交往。文章中,蕭乾將同性戀類比於愛滋病,“正如愛滋病,它在中國没有在西方那麽嚴重”(2002,頁289),而且,“異性戀纔是正常的,同性戀屬於變態。我不贊成去鼓勵。在美國某些州裏,同性戀可以登記結婚。這種婚禮,我決不會去參加”(同上,頁292)。可以想象,上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在行政管理和道德審查上出現了鬆動,這在某種程度上打開了譯介的門,當然不能否認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恐同言論和態度。雖然蕭乾提出《莫瑞斯》“是一本健康的書”(同上,頁291),但是,這篇早期的文章收録在文潔若2002年的大陸譯本中,蕭乾將同性戀病態化的態度,卻引起網民的反感(肖渾,2017)①該文作者考證,蕭乾的這篇文章是1992年發表在《南方周末》上。對於2002年北京的中文簡體版,肖渾指出:“短評欄出現最多的就是對蕭乾後記的吐槽,甚至有讀者是以一副義憤填膺的語氣,批評蕭乾的後記反人類。”參見https://www.douban.com/note/625013614/,2019年7月8日最後登入網頁。,以至於譯文2009和2016年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再版時,不得不放棄附録蕭乾的這篇文章。同樣,前文提到2002年臺灣版譯文也没有收録蕭乾的這篇短文,出版社已經意識到蕭文可能引起了讀者的不滿,可謂明智之舉。
2009和2016年上海譯文再版時另一個顯著的變化,則是體現在對homosexuality的翻譯和對“同性戀/愛”的選擇上。英文原文中,只有少數位置出現了homosexuality這個詞彙(見Forster,1971,p.158、184,以及作者的《結尾的札記》中),在2002年版的中譯文中,被翻譯成“同性戀”;同一版本中,譯者所加的腳注,也統一使用“同性戀”這個譯法。然而,上海譯文出版社的版本中,無論是譯文還是譯者腳注中,全部替换成了“同性愛”,這也是除了删除蕭乾短文之外,新版本最大的改動之處。張北川指出,“80年代末,隨著國内性學的發展,同性戀一詞更多地被能更準確反映出性愛定向内涵的同性愛一詞替代”(1994,頁44),而秦士德為張北川的《同性愛》寫的序言同時指出,“據作者談,戀字太俗,常為君子所不齒,故選用愛字為題,以示對同性愛者的深切同情和人格尊重”(同上,序壹)。文潔若在譯作2002年由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後,曾經寄送樣本給與蕭乾長期通信的張北川,隨信指出:“最近我譯了一本以同性戀情(你主張用同性愛,但編者不同意,所以改了)為題材的小説,Forster著,後面附了蕭乾的《唉,同性戀》。”(肖渾,2017)也就是説,譯作最早完成時,文潔若曾經按照張北川的主張使用“同性愛”,但卻被編輯否決;於是,譯文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再版時,全篇將“同性戀”改為“同性愛”,也回應了蕭乾對張北川所做研究的認同。
除了文潔若譯本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的翻譯與再版,2019年4月,臺灣的聯經出版社也出版了由李斯毅翻譯的最新版本。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文潔若譯本2016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再版,還是2019年李斯毅的譯文由聯經出版社出版,都與2002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和臺北的圓神出版社不同;相對來説,上海譯文和臺灣聯經都是更為主流的出版社,這也説明這部作品更加被中國大陸和臺灣接受和認同。根據統計,在文潔若(2002年)譯本中所有腳注中,共有多達11處是解釋與同性戀有關的内容;在李斯毅(2019年)譯本中,也還有11處注釋是與同性戀有關。當然,二者之間對注釋的内容並非一致。比如在文潔若(2002年)譯本中,有專門解釋英國小説家奥斯卡·王爾德的同性戀戀情,而李斯毅(2019年)譯本中,並未就這一點做解釋。所以,雖然李斯毅的譯本在2019年出版,但是譯者還是通過腳注或章節尾注的方式,對文本中的一些互文性内容加以解釋,從而間接向讀者傳達了小説所隱含的同性戀主題。另外,李斯毅的新譯文,並没有收録Furbank的導言,而是採用了臺灣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紀大偉寫的一篇導讀。紀大偉是《同志文學史》的作者,而這篇題為《回顧同志經典》的導讀,將小説與許多經典同志文學作品和電影作品放在一起討論,建構了Maurice作為同志文學經典的歷史地位。
總觀中文譯本的翻譯和出版策略,無論是封底的導語、譯文大量有關同性戀互文性符號的腳注、譯者後記對作者同性戀身份的解釋,通過這些副文本的操作,小説對同性戀主題的描寫被重新建構(reframed),雖然這些腳注會影響閲讀流暢性,但對傳達作者整個叙事建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對同志文學的(預期)讀者而言,有積極的作用。某種意義上來説,種種建構的策略,使得原文隱含的同性戀主題,在中文譯本中更加突出和明顯,按照哈維的説法,屬於“同性戀主題被強化”的翻譯(gayed translation)。這得益於21世紀初中國大陸對同性戀話題的包容度越來越大,相對於上世紀末期社會對同性戀的態度,有很大的變化。同時,中國大陸譯文讀者對譯作的不滿,迫使譯者和出版社再版時,不得不做出回應,對譯作進行重新建構。
四、結 語
通過以上對Maurice中文翻譯的文本細讀顯示,無論是封面設計、導語、譯者前言、注釋等副文本手段,促成了“譯者重新定位自己、譯文讀者以及該時空涉及到的其他參與者”(Baker,2006,p.133)。由此可見,翻譯一定不單單是語言的轉换。主流文化意識會影響翻譯過程,譯者和其他翻譯主體也扮演重要角色。中文語境下的同志文學翻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作為現代意義上同志文學奠基之作的Maurice在譯入中文語境時,因為21世紀初相對寬鬆的接受語境,譯者透過腳注等副文本闡釋原文中隱含的同性戀指涉,使得譯入語讀者有機會全面深入了解原文傳達的主題;同時,譯者透過附加相關副文本,更加強化了對譯文在新語境下的叙事建構。當然,蕭乾的文章寫於上世紀90年代,雖然擁抱逐漸開放的社會氛圍,卻依然流露出對同性戀的不認同或病態化認知。很明顯,這個副文本並没有很好地服務於譯文的接受,反而引致網絡社交媒體質疑與圍剿;譯者和出版社在重新出版中文譯本時,不得不拔刃斷臂,重新建構一個為譯入語文化所認同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