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庄子·天下》篇
□马 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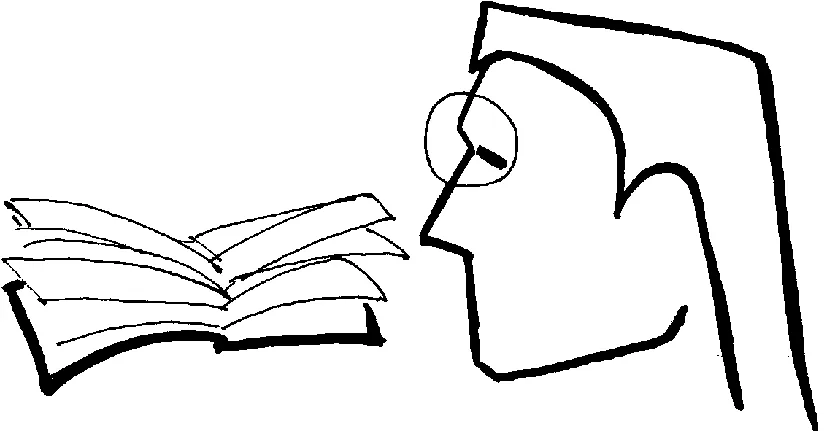
《庄子·天下》评述了先秦各家学说,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学术史。作者从道术和方术的角度,对包括墨家、儒家、法家和名家在内的各家学说进行了评价,认为它们的学说都属于道术一端的“方术”,“寡能备于天地之美”。作者认为道家学说最能体现道的普遍性与整体性,道家思想能代表真正的道术,是“内圣外王”之道。
自晋郭象为《庄子》作注以来,学术界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对《天下》篇进行研究:其一、关于《天下》篇的作者与时代问题;其二、关于《天下》篇的主旨问题。关于作者问题,分歧仍在,至今没有定论。有学者认为《天下》篇的作者是庄子本人,如王夫之、胡文英、梁启超等人从文风的角度进行了论证,认为此文“浩博贯综”“微言深至”、文体丰茂,故为庄子自作;也有学者认为《天下》篇的作者是庄子后学,如林云铭认为文章将庄子与同为道家的关、老分别评述,“庄叟断无毁人自誉至此”,故为后人所作。当代学者刘笑敢提出,《天下》篇的作者出自庄子后学“黄老派”,因为黄老道家对儒墨法诸家不仅不排斥,甚至融合兼收诸家观点,表现出包容并蓄的学术倾向。刘的观点具有启发性,值得进一步论证、分析。
关于《天下》篇的主旨,主流的观点认为在于阐发“内圣外王”之道。结合《天下》篇文本本身和《庄子》全书来看,“内圣外王”确实是贯穿《庄子》全书的一条线索,这个出自《天下》篇的道家术语,如今却被广泛运用于儒家学说,儒学甚至被概括为“内圣外王”之学。现在,我们回到“内圣外王”的出处——《庄子·天下》,看看道家的“内圣外王”是个怎样的面貌。《天下》篇按照文章内容,可分为七个部分。从开篇至“道术将为天下裂”为总纲,余下段落分论从墨子到惠施六门学派。
文章的开始作者就提出古之道术“无乎不在”,认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一”有本源性、整体性的含义。《庄子·天地》有言:“通于一而万事毕”,结合《天下》篇来看,“一”可以是道的别称。圣、王皆源于道,道是“内圣外王”的根本。作者继而划分出七类人:天人、神人、至人,他们不离于“宗、精、真”,距离古之道术最为接近,是道家理想的状态;圣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能预见万物的变化,上承天人、神人、至人,下又与现实联系紧密,是较为特殊的一种状态;君子、百官、民,生活在仁、义、法、礼之中,是人的现实生存状态。这七类构成了道家眼中人的全部生存状态,结合开篇作者提出的:道术是关于人生和宇宙本源最高的学问,它“无乎不在”,上至天人,下至民,古之道术无所不在,所以有天地之纯、古人之大礼的说法。
总纲的最后,是“一”向“裂”的转折,即道术分裂为方术。百家之说“皆有所长”,但“譬如耳鼻口目,皆有所明,不能相通”,作者认为诸家学说都是偏于道术一端的方术,且各家“往而不返”,最终导致“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结局,内圣外王之道也因此抑郁不发。在作者看来,“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与道术的分裂有很大关系。综合上文来看,《天下》篇所列出的七种人中,天人、神人、至人不离天地之本,取天地精华,代表的是内在修养,君子、百官奉行仁义、礼法,是外在的经世之术,前者是内圣,后者为外王,圣人贯通二者。由此观之,以道术为根本的“内圣外王”,是具有普遍性和整体性的,这是道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所在。下文对各家之说的评述,也从侧面反映了道家所主张的“内圣外王”的具体内容。
首先,对于墨家学说,作者肯定了他们的出发点,却否定了他们的救世方法,认为其主张“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作者认为墨子学说太过严苛,脱离实际,难以实行。“内圣外王”最主要的是要符合人的实际需求,虽不提倡纵欲享乐,但墨家“必以自苦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的自苦方式对普通人来说又是另一个极端,走向了“兼爱”的反面,因此很难实际地推行这种主张。墨家虽能独行此道,但算不上真正的“内圣外王”之道:“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与墨家类似,宋钘、尹文“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主张“禁攻寝兵”、“情欲寡浅”,为世间的太平安宁而奔走不息、上下说教,但这类行为仍然是“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作者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是不懂“道”的表现。他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部放在别人的身上,因此“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站在作者的角度来看,齐同是非、消除取舍之心,顺应万物,先成就“内圣”,“外王”才可能得以实现。
再看彭蒙、田骈、慎到一派:他们崇尚“不教”之教,认为事物经由人的主观选择,必定会有所遗漏,所以“道则无遗者矣”,顺着道就不会有遗漏。他们的道是以外物为基础的,因此他们的“去己”是被动、迫不得已的。他们树立了一个客观标准,即“万物皆有所可,皆有不可”,于是“泠汰于物,以为道理。”彭蒙、田骈、慎到放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人“至于若无知之物”,认为“无知”、“无用知”是保全道的途径,他们的学说被认为是“死人之理”也就无足为怪了。虽然他们“齐万物以为首”,让人联想到庄子的“齐物”,但他们的“齐物”是不得已而为之,与庄子的“齐物”不同:庄子认为万物都是浑然一体的,并且在不断地相互转化,因此要齐而观之。反观彭蒙、田骈、慎到,他们“决然无主”,认为万物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于是去除人的主观性,正是所谓的“弃知去己”。再看庄子的“无己”:庄子的无己是要突破世俗的束缚,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人生观,最终成就“逍遥游”。二者如此大相径庭,这也是作者在段末说“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的缘由。
接着,作者的视角转向了道家。老聃、关尹“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作者认为他们的道虽未至极,但对其仍多有称赞。关尹的“在己无居,形物自著”,表明关尹不偏执己见,使有形之物各自彰显。老聃“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是以退为进的智慧。作者肯定了他们的道的观点和谦下的处世态度,老聃、关尹把握了自然的天道,因此他们也最接近道,所以作者称他们为“古之博大真人”。庄周与老聃、关尹相比,更进一步。他“寂漠无形,变化无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在作者看来,庄周的学说虽然“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奇特瑰玮,但无伤道理。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但不为老子所限,庄子的道术“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包罗万物,其理不竭。作者对道家学说做了高度的评价,道术的普遍性也从中显露了出来。
文章的最后,作者评述了惠施之学。首先,作者没有提惠施“闻其风而说之”,而说“惠施多方”,从墨子到庄周,虽然各家之说有异,但都不离“古之道术”。可见在作者眼中,惠施之“术”与古之道术是有区别的。作者在段首指出,惠施“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直接对惠施之学进行了批评。中间叙述惠施的“历物十事”和“辩者二十一事”,认为惠施的学说是“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是逞口舌之快的诡辩之术,在作者看来就是浪费生命。最后以“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的感叹结束全文,无不透露出作者对于惠施之才的惋惜。虽然作者对以惠施为代表的名家学说进行了详细评述,但并没有意识到名家在中国传统学术上的贡献。名家学说中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悖论在科学、逻辑学方面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这些正是包括庄子在内的中国传统学术所欠缺的。
从道术与方术、内圣外王的角度看,《庄子·天下》不仅是一篇关于先秦诸子思想的学术史。作者通过“道术”的视角,评述了百家之学,围绕“内圣外王”之道,认为庄周之学“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面对自然天道(“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做到了内圣;在外王(“应于化而解于物”)方面,“芒乎昧乎,未之尽者”,将庄子自由和真实的一面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庄子的未尽之言和在《庄子》书中无尽的道理都留待后人去体悟和发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