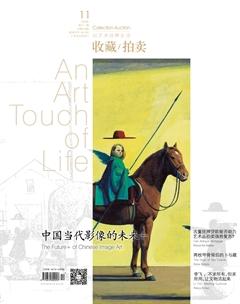城市废墟的内在召唤
张梓华



画中话,老广州的旧楼
亮灰色调与粗放的笔触,整体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岁月流逝的气息。黄德华把拆下来的建筑废料,化成了一种大笔触的肌理,这种看似凌乱的肌理穿插在不规整的建筑中间反而显得出乎意料的协调。( 谢砚文)
时间深处的灰烬
《陈寅恪故居》画出岁月的纹理,画出时间深处的灰烬,只是这时间的叶片至今还在隐隐燃烧,摇曳不定。在斑驳的画面里,唯有大师门前的那张空着的藤椅以发光的线条缓慢地释放出风雨之后的沉静之美和书卷之气,那份生命的沉香仿佛是先生还在纷乱的人世讲述着他的《柳如是别传》。( 黄礼孩)
废墟对应的心灵结构与美学
城市废墟不只关乎其外观,我们不能忽略“古老废墟的结构”跟“人类心灵潜意识”的对应关系。关于建筑跟心灵结构的对应关系,心理学家荣格曾提到“我们必须发现一幢建筑,并对它加以解释:它的上面楼层建造于19世纪,地面楼层则可以溯及16世纪,如果再小心检查其石工技法,我们会发现,其实它是从第二世纪一幢塔楼改建而成的。走到地窖,我们发现罗马时期的地基牆,在地窖下面,还有一层填土的洞穴,在这一层,我们发现了石工工具,接下来是更下层里面的冰河期动物遗迹。几乎就像是我们心灵的结构。”简言之,这些被历史所遗忘,潜藏在黑暗之中的废墟,似乎就像是我们潜意识的原型或共同体。
菲比· 克拉克在《廢墟的美学》里说:“废墟是美学的、艺术的、历史的、政治的、旅行的图像,同时质疑着时间、空间、记忆、还有形式、建筑或它的缺席、它的毁坏或它的自我否定。”在黄德华的绘画中,最常出现的图像是在拆迁中的老楼,即美学的概念“废墟”。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模型”,废墟与现代性和工业化带来的普遍焦虑紧密相关,人们对永恒、不朽和文化根源的乡愁变得极为迫切。
这些在文明进程中被淘汰的废墟,仿佛是现代社会中的“剩余物”,难以被今天的资本所吸纳利用(如果没被空间活化的话)。而黄德华则是让这些在文明进程中的剩余物,透过绘画让它们显现在我们面前。
没有肖像的广州城市追忆
黄德华自幼在广州成长。随着城市的疯狂扩张,城市中心向新城转移,昔日的广州旧城逐渐换新衣,而黄德华大大小小目睹着这些实体空间与想象空间拆解与重构的过程。这些被拆除的建筑所呈现的某种“空缺”状态,这种虚无般的缺席状态触及黄德华的记忆和感怀,出于对广州老建筑的感情,她从事艺术创作伊始,便以建筑和建筑材料作为主要的视觉图像之一,但她画的城市没有人,只有建筑,一些被遗弃的旧建筑景观和一些正在拆除的建筑图景。
不管是描绘海珠地界,还是《冼村》《越秀南》,整个画面阴郁、暗沉,充满了建筑废墟,在作品上我们可以窥见鬼魅般的混沌,而这种混沌,似乎使观者身临在这个承载记忆与历史的空间。换言之,尽管她是大量观察这些建筑物的外表,没有实地描绘里面的空间;但这些建筑物却呈现某种危楼状态,让观者如临其境般目睹这场混沌。
它们既不是圆明园,也不是古罗马或是庞贝古城的遗址,它们只是在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与繁华都市仅一墙之隔的各种废墟。这些废墟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会消失,或者继续完工,或者转换身份,或者摧毁。但作为一种城市建筑的异样的种类,这类废墟永远存在城市发展的历程中,它不断消失,又不断涌现,构成了我们的城市表情不易觉察的局部和瞬间。现代城市中的每一片废墟都有着其独特的故事,也反映和承载着不为大众所知的城市另一面。
特别是《冼村》系列,让我想起娄烨前几年那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其拍摄背景很大一部分就取材于广州冼村。冼村——21世纪初期广州CBD最后一个旧改项目,位于珠江新城中轴线上,如若俯瞰这个历史悠久的古村,我们会看到它破旧低矮的房屋群被高楼大厦包围压迫,成为一个“百废待兴”的城中村。早期村里会出租一些屋子给外来人口住,他们很多都是对面大楼里的白领务工人员,在城中村享受着比对面低廉的生活物价和房价。几年之后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村民看到了商机,于是又将自己居住的房子加盖成二层甚至是四层小楼,除了留出自住,剩下的纷纷租出,这些房子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握手楼”,走在街头小巷,抬头暗无天日,好像井底之蛙一样。终究这些格格不入的建筑要被高速发展的摩天大楼所取代,这也是村民心之所向。他们早就想离开这些破壁残垣,被城市垃圾包围的家园。可是很多社会问题伴随而来,逐渐演变成了各种矛盾、冲突。像冼村一样的城中村在广州还有很多,他们都是改革开放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大时代变迁的产物。无论在娄烨的电影里,还是在黄德华的绘画里,他们都如出一撤地呈现了这些城中村雾蒙蒙的环境夹杂着阵阵喘息。
尽管黄德华在作品中试图避免讨论过硬的政治问题,但她选择的废墟本身却彰显出我们对过去城中村历史的认同以及想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废墟事实上也是现代性的产物,因为现代社会不断加剧的进步,所以把淘汰的事物远远抛在后头。但黄德华却一片片地拾起这些被抛在历史后头的碎片。我们可以从这些碎片中感受到这些建筑的岁月,它们也曾经是那个时代的“现代”。而我们所属的这个“最新的现代都市”(大楼、钢筋水泥等等),未来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废墟(不可抗拒的衰败)。按黄德华的话说就是“它们就像老人,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注定被淘汰”。
历史幽灵的召唤
本雅明在他的著作《拱廊计划》中以废墟和破碎性为基础的寓言式哲学解释了现代社会的支离破碎的状态和废墟本质,并提出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救赎需从其中去挖掘。他将现代性概念视为“废墟化的进程”,同时强调了废墟及其中的游荡者的形象,正是在这些游荡者形象中,现代社会得以辩证地呈现出来。如今在面临紧迫的环境问题的当下,黄德华就好似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或“拾荒者”形象的化身,把存在于现代都市中的废墟的一部分一一拾起,再将这些碎片拼接,以形象化的、美学的形式创造另一种感官体验,借由这感官体验试图去捕捉尚存的记忆、唤醒现代社会里尚未被大众自觉意识的一处暗涌的废墟。在黄德华的笔下,被描绘的并非只是一座座被遗弃的建筑、景观、日常居所,更是属于一座城市被遗忘的时光。
黄德华的作品不是悦人眼目的,它是扎心的。换句话说,她的审美其实是在于追求力量。建造有些时候是要破坏的,即使破坏的话,其实也是需要一种力量。所以,她的建筑不是庸常意义上的,看起来很美好,看起来很阳光,看起来很舒服。她的作品并不是让人舒服的,而是要刺痛,就是要刺激,要让观者感觉到痛。
概而言之,如果以废墟作为创作,单纯回顾过去并停留在既定的框架里,或许只是一种物哀;更重要的是透过作品开启我们新的感性逻辑,让我们从“当下回望”,进而思辨未来。“对世界进行寓言式的批判辩证,使得从过去所堆叠的残片废墟中醒悟而来,开启未来的启蒙。”黄德华就像透过绘画堆叠残余的废墟,而这些废墟直指我们内心的深层结构,同时创造性地勾起我们思考自己的记忆、想象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