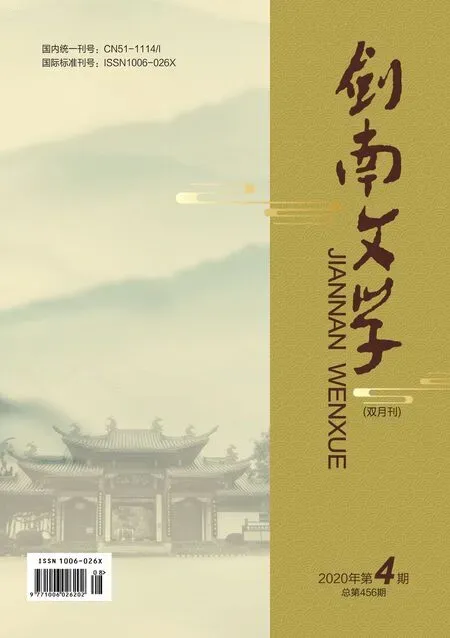王朗记
□阿贝尔
田瑛来平武,我陪他去王朗。
我与《花城》缘起朱燕玲,但田瑛却是主编。我跟田瑛不熟,不过,他是多大个人物我是晓得的——有二十年吧,他的名字总是因为 《花城》这本杂志和王蒙、毕飞宇、苏童、格非、残雪、阿来等连在一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吧,在《花城》上第一次看见田瑛,以为是女的,没敢想以后会认识。
八月的一个午后,在山里风味大酒店见到,田瑛不记得我们以前见过了。他从陈霁的沃尔沃里出来,挎着个真皮公文包,整个人也像公文包的皮革显出某种陈旧而有些磨损的痕迹。这痕迹是一位大佬而非文人所有的。我言及我们在广州和肇庆见过,同桌喝过酒,有朱燕玲、习习和张鸿在座。我准确地说出了时间——2011 年8 月,试着去唤醒他的记忆,他完全无动于衷。田瑛阅人无数,想必见过的人在脑壳里乱码柴窖的,像我这样的小人物早被覆盖了。
实话讲,在我决定来吃这顿“工作餐”时,我只想表达我对田瑛的谢意。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在诗人蒋雪峰五十岁生日午宴后给朱燕玲打过电话的,借酒壮胆,话似乎说得流利一些。朱燕玲告诉我《鹿耳韭》留用,田瑛很喜欢,准备发头条。
一餐饭没吃完,我就决定陪田瑛进山了,我觉得我们有话要说。需要加注的是,见面第一餐,我和他都滴酒未沾。
田瑛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老大哥。不是亲生大哥,也不是江胡上的大哥,是那种彼此都父母早亡、年龄相差较大、什么都得靠的大哥。这种感觉首先是身体的——他那么壮,那么多肉,又那么稳重,坐在哪里都很有定力,不安静的也安静了。
陈霁是个有时间感的人,什么事都喜欢有计划有安排,当他就去王朗的吃住征求田瑛的意见时,田瑛说他完全听他的,“吃什么看什么,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起”。他说的另一句话使我特别震动——“就是这阵掉头回去,我也不觉有什么,只要我们能在一起。”
田瑛坐副驾室,我坐后排他背后。路上,他问我一些事——想起了才问,更多的时候是沉默。他没有表现出对平武自然、历史、人文有多大兴趣,想必在他的感觉中,那些原本厚重、浓郁甚至悲情的东西都变得稀薄了,他穿越它们,犹如穿越夺补河两岸洁净的空气。车过白马寨时,我勉强地向他讲起白马十八寨、白马土司什么的,都是有头无尾,因为我不敢保证他在听。
话题转移到当地头上插白鸡毛的白马人——很容易谈起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已经过了好几个白马人的寨子,到了以前白马人生活的核心区白马路——我谈到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基因测试和早期人类迁徙。我依然不确定他是否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结果被订餐、住宿这样最现实的话题打断,没有了下文。
经过木座时下过一阵雨,到白马路又在下,且越下越大。原计划先到扒西家转一圈,再到刀解家的白马部落住下,但因为雨——也因为田瑛在颠簸中睡着了,我和陈霁临时决定直接到白马部落。
实话讲,扒西家没必要去,说是古寨,其实去年遭受洪灾后老房子都拆光了,新建了劣质的民宿,且正在治理溪沟,寨里一片狼藉。我见证了扒西家从无人问津的老寨子到天友打造、再到今日翻新的全过程。十几年里,想必扒西家人的内心——价值观、审美观什么的,也跟房子一样都翻新过了。
田瑛醒了,车从通往九寨沟的刚升为国道247 的公路拐上去王朗自然保护区的便道,视线离这条叫夺补河的已全然没有河样的河流更近了。“可惜这河了!”田瑛突然冒了一句,不像是在说梦话。“是啊,我写了《夺补河之死》。”我说。我写的时候还没修高速,夺补河还没死硬,只是毁于早期的伐木和后来的修水电站;而今高速路开工已有三年,夺补河算是死硬了。
我们没有就人与自然的话题继续下去。祥述家到刀解家一段高速路已经成型,桥墩竖立河床,预制桥板也都铺上,盘旋在河上,河流完全被忽略了。事实上,河流也没了,河岸、植被全毁,河水渗入地下,原来的河流变成了一个施工现场。
白马部落在公路的左手边——夺补河右岸,我几次路过看见,感觉并不咋样,想听真话的话——有点像牛圈,圈起一大片草滩,方便晚归的牛羊。
田瑛对山门上“白马部落”四个字感兴趣,专门停车拍照。他说了这四个字是陈霁兄的书名,想必他的兴趣更多在对友谊的纪念上。
“这个民宿用了你的书名,你任何时候来住他们都不该收你钱。”我跟陈霁开玩笑说。“人家先有白马部落。”陈霁说了句老实话。
入住。雨一直下,不大不小。不见我和陈霁都熟悉的女主人,见到的两三个人都是不认得的帮工。下午五点的样子,气温从三十四五度降至十七八度,我换了长裤长袖衫还感觉凉。提着行李站在客栈天井的片刻,我突然生出一种置身在某部电影的外景里的感觉。帮田瑛送行李箱上楼,这种感觉越见明晰和强烈。
一院木楼,雨淅淅沥沥,客栈寂静无声,偶尔看见有人从虚掩的门里探出半边脸来。
放下行李,我没立即下楼回自己房间——田瑛取了本 《生还》给我,特别提到书中的那篇《大太阳》。我们谈了什么? 天在下雨,有种夏日傍晚不多见的晦暗。但已不是新鲜的晦暗了,晦暗蒙了苔藓或者旧血,也混杂了矿粉般的时间粉末。我提到我年初写完的中篇 《黑白河纪事》。他叫我先看他的《大太阳》。我直觉到了,大太阳,就像立秋后这几日秋老虎一般的毒太阳。
吃晚饭还有一段时间。雨住了。我把椅子搬到外面,开始读 《大太阳》——大太阳挂在时间源头的苍穹,映照的却是后来的一个广场。在海拔2500 米的岷山深腹,我不愿走进人类历史,哪怕只是象征和借喻,我想清静一会儿,坐在雨后的客栈的天井,把自己和别的事物切断,甚至把自己和欲望切断。
然而,这样的时间很短暂,同行的人很快聚在一起,一些话题又展开在了嘴边。
其中一个是关于田瑛的。他自己展开在自己的嘴边,像一朵怪异的野花。这样的一朵野花,对于我则是似曾相识的。湘西出土匪,田瑛身上着实有些匪性,而今老矣,但血液中还有沉疴,脸上还有刀疤。但他的匪性不是诉诸暴力的,而是一种审美,更多是对自我独立的维护。他讲了自己很多,我听了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我觉得我们有着本质的一致,那就是对某些现实存在的清醒认识和拒绝——不是决绝。
其实,什么都不用说,一样的人走到一起是感觉得到的。思想、观念只是硬翘翘钢筋一样的东西,心才是第一位的,审美才是第一位的。两股水合在一起不排斥、不污染。我觉得是这样,爱和恨——不恨,也绝不做同类。
说话间,雨突然大起来——很大,雨声唤起了我对诸多印象深刻的夏天的记忆。我感觉到安全,有瓢泼桶倒的雨水阻断我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一些雨水溅到了我头上、身上,我有种受洗的喜悦。这一路走来,身上裹挟了尘埃和脏污,挨肉的居多,挨心的也有,倘若能像个孩子跑进雨中淋个透是最好不过的。
雨水伴着冰冷、伴着夏日的寒意和傍晚的暗淡,像篝火簇拥着我们凌乱无序的交谈。我们都穿得单薄,冷是真的,但我们并不想点一堆篝火,围着唱歌跳舞。冷寂才是我们需要的氛围,因为我们的理想和美学从来都是生长在灰烬中,一旦点燃篝火,什么都忘了,只能回到过去。
其间,男主人过来小坐了会儿。他是听人说陈霁来了才过来的。男主人是女主人的父亲,我熟,但也仅限于“面熟”。他的到来打断了田瑛的自述,即使在男主人与陈霁热烈的寒暄中,我也能觉出田瑛的沉默。用陈霁的话说,男主人是平武白马人当中两个最聪明的人之一——另一个是官至某市市委书记的马某。
晚饭时,田瑛见我们桌上摆的是火锅而背后一对小夫妻桌上摆的则是腊肉,便抬起他的胖身,缓步过去“借”了块腊肉。他表现得颇有绅士风度,下箸前征求女客的意见,说是“借”。女客长得说不上多美,却有几分古灵精怪,跟田瑛讲话目光直勾勾的,或许是蜂蜜酒的效果,脸颊颇有几分酡红。忽看见田瑛过去,误以为是冲着那美人。
看得出,这顿饭吃得不合口味,好在主人补上了田瑛喜欢的腊肉和腊排。“入乡随俗,凡事都不要问我。”这是田瑛多次表明的态度。他很配合,平常不喝酒、喝酒只喝茅台的他居然喝了两碗白马人自酿的青稞蜂蜜酒。
咂酒虽也带个酒字,但到了田瑛的嘴里和血液里压根不是酒,“只是甜水”——他的原话。实话讲,两碗咂酒下肚,我是有一点酒意的,说话也不分大小了,感觉和田瑛又亲近了半步。这亲近有酒精的过,但更多还是我们吐出的话语,它们的频率和分贝总是很接近,颜色也很接近,意义和“在一起”没有半点不容。文学在我们的话语中不是风花雪月,而是陈年旧血和喷发之后凝固的岩层,里面包裹着无法探究的化石——那些瞬间停止呼吸的生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爱和悲恸。
屋外。雨一直下着,落进岷山之夜,在我的想象中像洒在路面的不连贯的沥青。
人间最好的氛围总是脱不了世俗——声色犬马,那种带一点肉色的人间烟火味儿,即便在偏远的岷山之夜也少不了。我感觉到的这一点点自然来自那对小夫妻——男的已喝得满脸通红,只是沉默或傻笑;女的还没喝到位,嘴巴利索,脑壳清醒,一说一笑,娇声中透出穆桂英的豪气。
杯盘狼藉之后,我们没有在这暖色而孤单的气氛中久留,坐了片刻便冒雨回房间了。透过只能听见声音的雨幕,我想着田瑛的 “大太阳”,它镶嵌在瓦蓝的天顶,吐着轻易便可以点燃树木、煤炭的毒焰。这里曾是白马部落,“大太阳” 普照的也是部落,酋长领着整个部落走在迁徙的路上,像领着一群牲畜。
次日早起。想着六月的大太阳。捧起《生还》,出客栈。客栈寂静无声,客主都还在梦中。天晴了,河谷间的天空瓦蓝,静泊着几丝豹纹云,空气潮湿而冷冽,穿着单衣和凉鞋的我忍不住发抖。这一刻,白马部落再次成为一部电影的外景。走出山门,我一边跺脚一边瞭望青天上的花云,感觉自己成了电影中一个很文艺的配角。
日线刚移到右岸山脊,要下到河滩尚需一两个时辰。我取消散步,一个人回到昨晚吃饭的炉边,但炉子没升火,依然冷。我读了几页《大太阳》,却借不来文字中的热力——新老酋长都是吝啬鬼,空气都是隔绝的。
我去到前院的饭堂,一个女人刚把炉子的火烧旺。她躬身往炉膛塞柴,露出肥滚滚的后腰。我坐下来,立即感觉到了暖和——但还只是不冷,说不上热烈。
把茶杯和手机放旁边桌上,继续读 《大太阳》——远古的大太阳,一个部族的生存环境恶化了,老酋长死后,在新酋长的带领下开始逃亡。田瑛小说中的大太阳有着蛮荒时代的紫外线,在我读来却是湘西的大太阳,逃亡之路途经的也是湘西的山水溶洞,就像当地苗人和土家人经历的那样。
饭堂很大,除了一个藏式火炉,就是两张餐桌。我感觉到久违的自由——一边吸取热量一边游弋在小说多重象征中的自由。小说文字的密度虽说很大,但因为是想象而非现实,透着梦幻的日晕,并未给予我压迫感。
女人端来巨大的锑锅放在炉灶上,用铁瓢搅过锅里的大米盖了锅盖走了。不一会儿,我便听见锅里沸腾的声音,锅盖被蒸汽托起的声音。米汤潽了,洒在铁板做的灶台上,发出烫伤的哧溜声。这声音没有惊动我,我反倒在小说中更安静。只有片刻,女人过来看火,衣兜里的手机放着藏歌,让我不适。
不知不觉,火炉变得炽热,我的脚脸明显感觉到了它的热辐射。我本能地往后退了退,本能地拿过杯子喝了口茶,继续埋头在书里。
现实是清晰的,但现实免不了俗,且体味太重。想象呢? 想象又总是模糊,没有足够的物质相对应,就像梦醒后对梦的追记,相较于真相缺失得太多。然而我喜欢带着象征意味儿的想象表述,它像颜料,像沥青,覆盖了现实——现实是人类没想周全便开闸放出的洪水。
在我一人偎炉读书的约莫一个时辰里,我忘记了很多,或者说放下了很多。从前窗看出去,日线移到了右岸西边,右岸整座山都被朝阳在水绿之上镀了一层薄金。但它不是我拿得起的,我们之间一直都有距离,就是被裹挟、被紫外线刺痛,彼此也无法进入。
陆续有吃饭的人进来,围炉。先是烤火。有人坐在我坐的板凳的另一头。他们闹闹嚷嚷,带着外地口音。在我的感觉中,他们都是从世俗的染缸中跑出的,一身地沟油和泔水味儿;从动作到语言都是油滑的,见过世面,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但却不懂得美。他们越聚越多,开始围桌吃饭,每个人都是一副热爱生活的样子。
去王朗的路上。我们谈论最多的是大熊猫——会不会撞见一只。7月21 日,我从王朗回来的次日,有人幸运地在珍宝桥到大草坪之间的路边撞见一只出来喝水的大熊猫。我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好运。
从豹子沟开始,我们进入了原始林区,道路两旁原始灌丛的无序之序让这个湘西汉子很是惊讶,问灌木的名字,我答之高山红柳。显然,湘西的山里是没有这种柳的。
从豹子沟到牧羊场,更远到珍宝桥,早先都是原始森林,冷杉、红松、刺柏、雪松成林,1953 年森工局进来,砍得只剩灌木。
牧羊场往前不远,过去有个熊猫馆,1999 年秋天,我最后一次参观熊猫馆,还与大熊猫拍过一张照。熊猫馆拆除后,就是路过,连具体位置也不记得了。我对珍宝桥的印象一直停留在1986 年夏天第一次进王朗所见,一个二十出头天天写诗的小伙子,午饭后独自从牧羊场往原始森林走,走十里路,便要过珍宝桥,到达被1976 年大地震撕裂的山下——撕裂的裸山,倒挂的红松和刺柏从此定格在了脑壳里。沿路剥下最好的红桦树皮,幻想着给一个莫须有的女孩写封情书。
现在,我们正经过这段路,海拔接近三千米的林荫道,车缓缓前行,偶尔有戴胜鸟在路上跳跳,不等靠近便钻进树林了。路还是原来的路,林子还是原来的林子,路下穿过灌丛的溪流还是那么清澈、激越,但我总觉得少了什么——一个人的清寂,还有恐惧。
我个人是很喜欢大草坪的,每次到来都能获得一种脱离苦海的自由感。关乎身体,也关乎灵魂。大草坪的所有高原野生花卉都能与我的灵魂相照应,同时也像是从我的灵魂分派出的。
大草坪的细节很迷人,不只每棵站立或者倒伏、活着或者死亡的大木,也包括路边灌丛和草坪的每一朵小花,杜鹃和报春,龙胆和翠雀,以及开在溪间湿地的叫不出名的花。
大草坪的大环境很美,草坪外围的冷杉林和远处的砾石山,砾石滩下方的草甸区,背阴处未完全融化的积雪,更远处的雪山,颇有层次地自成一个世界。
对于大草坪的记忆可以追溯到1999 年的那个秋日。我一下车首先注意到的不是具体的大草坪,而是路边冷杉林投下的一绺阳光,和阳光正好照着的一朵野菊。我直觉到了它的神性。然后是不经意抬头,看见了雪山,我视这一抬头为从未有过的与神对视。以后再来,神躲藏了,有时踏雪,有时踏青。阿来和舒婷曾经来到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阿来忙着拍照,架起脚架,有种欲将冷杉、砾石滩和雪山嵌入镜头的架势。舒婷表现得则很淡漠,仅仅转了一圈,回去也不见著一字一句。我喜欢舒婷的态度,或许某个夜里,大草坪会出现在她的梦境。
我记得在大草坪留下身影的还有来自宁夏的阿舍。她走步道下到溪边,转到溪水的拐弯处,蹲下,掬起溪水,视线却落在远方的雪线。
我和田瑛沿步道逆时针转了一圈。上个月,我陪人刚转过。这次,因为点地梅和龙胆都开过了,我陪得更为专心。
田瑛一心想遇见大熊猫,没想到在大草坪还真遇见了,且不是一只,是四五只,它们就在过了木桥的草坪上。田瑛克制住激动,走拢去,大熊猫一动不动,他小心地把自己略显笨重的身躯放在它们中间。我按下快门,为他留下难忘的一瞬。
离开大熊猫,平静下来发了朋友圈,才被人留言告之那些大熊猫是假的——田瑛当然知道是塑像,但他是当真地在零距离接触。
沿步道绕到右方,那雪溪怎么都无法回避,且是和一些人事合在一起的。上个月,我还下到溪边,拍了点地梅和龙胆。除了阿舍,这条溪水让我记起的还有范晓波、吴佳俊和胡弦,且伴随着他们在空若的开阔地显得弱小的吆喝。
大太阳。紫外线极强。但我并未产生有毒的意识,觉得即使受一点伤,也是干干净净的,就像失恋。这样的大太阳因为没有人类事务的参与显得很纯粹,完全不同于那个被动物血浸染的大太阳。
我们在步道穿过两棵高大红松的位置稍作停留,仰望树巅。田瑛提起了我们昨晚搁下的话题——发生在松潘的“咸丰番变”。那也是个大太阳,悬挂在与我们脚下的大草坪相同海拔的高原,因为众多人的死亡染上了乌鸦的黑色。一年半的围城与守城,两次破城,死者阻塞了岷江。太阳没有防疫,失去了免疫力,被乌鸦和秃鹫冲撞。
当然,我们的谈话最终回到了功利的文本——一部某天我会动笔的小说。虚构与纪实——纠缠小说家一辈子的问题。纪实——真实到不放过大太阳底下发生的每个细节;虚构——想象到微距、微观世界的最深层,并灌满纯物质的浓汤。
我们的交谈如同打了个盹,很快便回到了大草坪——对于我是一种已经产生审美疲劳的氧吧,对于田瑛或许是一个尚能产生爱、尚能把略显衰老和笨重的身体里那个少年释放出来的飞地。
田瑛很喜欢大草坪,让我频频为他拍照便是例证——和一棵精神抖擞的红松,和一棵倒伏的冷杉,和一条穿过灌木丛的林荫道,和一只戴胜鸟……
我每次到大草坪,感觉到的都是一种对人的世界的成功逃离。人的世界包括人居世界和被人居格式化的世界。为什么逃离,我想是一种洁身自好的要求,一种对古朴灵魂的挽救。大草坪随处可见比我们人的生命悠久得多的野生花卉,包括纤弱的灌条,都是我们危在旦夕的灵魂的映照。还有自由——逃离了人类生活规则的自由,一种仅仅承载自身灵魂的云彩般的漂泊……
快到步道尽头时,我一个人走了,丢下田瑛独自品尝陌生——我相信他对王朗乃至整座岷山都有一种陌生感,而品尝陌生会是很奇妙的感觉——没有我在他面前晃悠,他会对这个大熊猫、扭角羚、雪豹、蓝马鸡和各种报春的栖息地生出更多的想象。
离开大草坪,我们不是继续往前去道路的终点竹根岔,而是折返回去,在珍宝桥进了另一条沟——大窝凼。
岷山最深腹完全保留了初创的样子,每一棵树每一株花草都不曾有人的东西参与,未受到人的惊扰,对于我们的瞳孔和肌肤都是原版,没有一点翻转的痕迹。草甸、雪线以下的砾石滩和天空也都是原版的,几乎看不出时间的刷痕。
从竹根岔翻山过去便是黄龙寺,和大窝凼一山之隔的则是九寨沟。岷山深腹的这几处精华段落是“尤物”“天使”和“伊甸园”也不可比拟的,只有在剔除欲望、保留纯洁之爱的时候,人体的某些部位和线条才可以与之媲美。
在王朗,我一直想问田瑛,如果只允许他到王朗做一件事,他最希望做的是什么。但我没有问。或许我能猜到他的答案。如果有人这样问我,我的回答很明确——死在王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