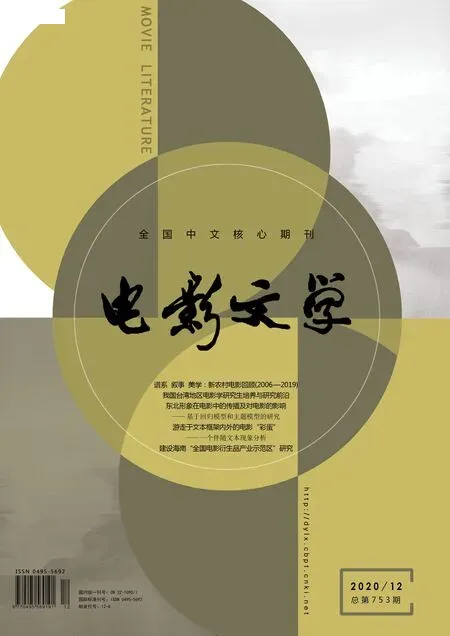跨媒体环境下电影美学再认识
杨丽娟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谈及电影美学,首先应触及的是电影的本体,电影诞生百余年,学术界周期性的爆发电影本体的大辩论已成为常态,其核心问题是“电影是什么”。而电影史上之所以有电影的“照相性”“戏剧性”“文学性”“绘画性”等本体的争论,原因就在于电影的综合性使得它自身无法确立自己“电影性”存在。
一、电影本体再认识
(一)纪实美学的再认识
“电影是什么”这一问题,在数字技术越发强大的今天再一次受到了质问。从《火车进站》《水浇园丁》等开始,追求纪录性的真实当然是传统电影艺术的美学追求。安德烈·巴赞在其著作《摄影影像的本体论》中强调“摄影的客观性赋予影像以令人信服的、任何绘画作品都无法具有的力量”。克拉考尔在《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中提到电影是展示现实本身的唯一的艺术。他还提到,电影是照相的外延,跟我们的周围世界存在近亲性。即便随着技术的进步,电影在原有画面上进行了低水平、浅层次的特效制作,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物质世界的复原”的本体论观点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公认的美学典范。然而,随着电影技术的更新和进步,电影不仅可以利用成熟的技巧再现现实,还可以增强真实。如:“拉长某些转瞬即逝的过程、放大某些肉眼难以辨识的细小事物、扩大某些细碎的声音”等。电影美学不再追求生活本质的写实性审美,而是在追求奇观化、时尚性的审美意象下,构成了一种“超真实主义”。数字技术和摄影技术的跨界结合,给影像开拓了更广阔的表现空间。因此,照相写实主义(photorealism)和之后发展起来的虚拟现实美学成为并存的电影美学观念。
(二)虚拟现实美学
数字技术进入电影创作导致了巴赞和克拉考尔影像本体论的瓦解和更新,当代电影已经不同于纪实美学提倡的“现实的渐近线”,也并不满足于卡拉考尔的“物质世界的复原”,而是基于数字技术,构筑产生“现实效果”的影像,形成“虚拟现实美学”。
虚拟现实包含两个层面:“混合的真实”和“虚拟的真实”。“混合的真实”是指现实与拟像共同交织,其“实现方式是外部世界的现实逻辑与拟仿事物的想象逻辑相接合”,如《阿凡达》中,真人角色和CG人物,真实场景和虚拟场景的融汇等。虚拟现实的另一个层面是纯粹“虚拟的真实”。以虚拟现实技术构筑的“仿真”影像,与现实甚至毫无关联。学者陈犀禾说“虚拟现实是指在视觉表象上具有客观世界物质现实的外观,但实际上却是人工合成的,它是关于现实的全新版本,一个假现实,一个虚拟的现实”。在打破二维空间营造三维立体空间的3D电影以及VR电影中,观众可以获得更逼真、更震撼的视听奇观,甚至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多感官的综合体验,带来更沉浸式的欣赏状态。
(三)工业美学
工业美学研究是将工业产品和美学原理相结合的研究角度。工业产品追求的是实用性,因此,工业美学关注工业产品实用性中的审美性。然而,工业产品的审美性和艺术品的审美性有诸多不同,艺术品通常体现的是艺术家自身更私人化、个性化的审美体验。工业产品追求标准化和流程化。因此,个人与集体,个性化与标准化成了二者截然不同的身份标签。
在关于“电影是什么”的本体论辩论中,关于电影的“商品性”也常常受到来自各地学者的关注。通常“商品”的概念对应营销环节,而工业产品的概念对应生产环节,两个概念的指涉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法国电影理论家马塞尔·马尔丹曾说,“电影是一项企业,也是一门艺术”。1995年,著名电影理论家、翻译家邵牧君提出“电影工业”的概念,并提出“电影首先是一门工业,其次才是一门艺术”。可以说,艺术创作和工业生产、艺术性和商业性成为电影发展中挥之不去的矛盾。邵牧君先生提出的“电影工业”的概念在当时中国电影界引起轩然大波。其提出的现实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面对电视媒介的冲击,市场逐渐萎靡。从这里可以看出电影纳入“工业产品”行列是电影商品化的必然诉求。作为工业范畴,其发展又与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电影工业美学包含“技术层面”以及“内容层面”。
从技术层面来看,“工业美学”思维主导的电影,除在技术上追求逼真之外,更要追求视觉冲击力。如以好莱坞为典型代表的高概念电影是电影工业美学标准下的典范。从内容层面来看,“工业美学”思维要求利用当今的大数据和新媒体环境了解观众的“共鸣度”和“接受度”,转换“导演中心制” 思维,以“制片人中心制”协调电影内容生产、运作、管理等诸多层面。某种程度上来说,“工业美学”倡导弱化感性的、个人的体验,应以理性的、规范化的、流程化的工作方式寻求艺术美学和商业美学的平衡。置身于商品化和消费主义浪潮裹挟下的电影,以工业美学标准来形塑自身,无论是重工业大片还是中小成本类型片,都是电影在多元消费文化中的必然选择。
二、跨媒体影像美学
(一)屏幕美学
从公共开放式的电影银幕到家庭共享式的电视荧屏,再到个人化的电脑屏幕以及近身性的手机屏幕,屏幕的每次变迁都带来电影的革新。多屏幕共生的时代,电影冲出影院的静态银幕,流入各种大大小小的屏幕中,观众甚至可以轻松地在城市LED 显示屏、展览馆、博物馆、新媒体艺术馆和影像艺术展等寻觅到电影影像的踪影。尤其是电影在电视机、电脑、手机等终端的显示更新了电影影像的话语形态,成为电影跨媒体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细分来看,电影、电视与电脑、手机以及VR 眼镜微缩屏幕相比,类型截然不同。电影与电视屏幕单纯作用于人的视觉来呈现和显示,具有单一视点的固定性,而电脑之后的屏幕,已经成为人直接交互操作的界面。“图形用户界面”技术革命性地带来了屏幕显示中的多重并置视窗。上下前后并置界面的多视点性形成了单一视点所不具有的主导性和多重性。“在《计算机屏幕的考古学》中,列维·马诺维奇认为:电影的古典银幕(在一个平面上的三度透视空间)被一个动力屏幕所替代,那里多重的、互动的影像在时间中展开。”以往的观众变身为网络空间的“游牧者”,在马赛克式的多元界面窗口中,在数据流的迷雾之中,观众以个人经验构建属于自身的影像叙事。在以虚拟现实技术主导的眼镜微缩界面中,“可触摸”“可参与”“可反馈”的技术支撑形态促使“使用者”成为影像的一部分。可以说,电影欣赏屏幕的跃迁带来了革命性意义,一方面它改变了电影媒介与人的关系;另一方面它改变了影像创作观念,更新了电影文本形态。也难怪一些理论家试图用“屏幕学”来取代之前的“电影学”术语。展望未来屏幕,人机交互的界面实体或许将被“虚拟存在”替代,社会从“有屏”时代进入“无屏”时代,这一切,让我们拭目以待。
(二)互动美学
“美学”其本质内涵是“感觉学”,因此,针对电影的美学研究归根结底要回到对感觉的分析和感受的拓展上。在观影越来越追求娱乐消遣的趋向下,观众已不再满足于“一对多”的被动欣赏,而是渴望在电影塑造的奇观景象中寻求更多的体验和参与,电影的互动美学观念应运而生。在此观念下,或许写一个电影开头,一个电影文本就能持续不断地写下去。这一切得益于电影的跨媒体拓展,同时也得益于前文所述的计算机屏幕显示技术,更由于“粉丝经济”带来的“参与式文化”。
电影融合了游戏的互动性,以影像叙事美学为根基,借助游戏的自由操纵和反馈机制完成互动电影的多元融合。逻辑清晰的故事讲述让位于灵活、多线的情节铺陈,如《头号嫌疑人》《黑镜·潘达斯奈基》《全明星探案》等。从技术角度来看,交互性是屏幕技术开发的重要指标。在多通道人机界面中,观众以主观视角操作视窗、唤醒图标、进入代表不同路径的窗框。每个个体都可以制造一部带有自身主体性的电影。除此之外,就传统影片观影来看,观众也在操纵、篡改电影本身,如在网站、论坛、博客和自媒体等的展示窗口中,以及近几年流行的“弹幕”中,主观视角的互动沟通由此产生。当然每个人成为潜在电影人的“制造”得益于亨利·詹金斯所说的“参与式文化”。似乎“观众”这一称谓在互动美学下也显得不合时宜,而应被“用户”取而代之。而且“问一部电影有多长”这样类似的问题似乎已经毫无意义,因为“用户”决定时间长度、顺序和轨道。“用户”主动参与进入多条岔道、多条出口和多个结局的时空世界中,制造更个人化的时空,形成更个人化的情感。吉尔·德勒兹在《电影Ⅱ:时间—影像》提到的未来的电影“构成了一张信息表,一个不透明的表面,题写‘数据’,信息取代了自然”。具有“可写”性的“数据”取代单纯“可看”的信息应是互动美学观念所倡导的。
(三)后现代美学
20世纪80 年代,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称呼当今社会的文化已经步入后现代文化阶段,他认为“表意的链条断裂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只能是一堆支离破碎、形式独特而互不相关的意符”。面对大量电子信息流的包裹,人们无时无刻不处在信息的爆炸式包围中,人与机(移动终端)的互动合体成为现实。统一、稳定的时间感让位于碎片式、主体身份丧失的流动状态。在电影领域,“后现代”表现为“后电影”时代与“后电影”理论的兴起。经典电影理论主要讨论电影是什么的话题,追求“大理论”,“后电影”则把电影当作一种媒介,更深层探讨电影与其他媒介间的勾连关系,研究电影的跨媒体互动。
在“后现代”文化下,“后电影”较多地追求张扬、奇观化的视觉铺排,情节松散、注重感官体验,呈现出稀释内涵、消解深度的“后现代美学”特征。在影像材质上,手持移动终端、监控设备等影像充斥在影片中,营造出粗粝、质朴甚至混乱的影像现实感。在跨媒体呈现上,数码影像的可编写性促使不同媒介间的借用和混用成为常态。电影理论家斯蒂芬·沙维罗在著作《后电影情感》中,将这种现象称为“后连贯性”。列夫·马诺维奇将“后现代美学”的表征称为“数据库逻辑”,人们借助自身主体性经验从数据库中采集、编写自己的叙述,重新激活、重组赋予原有影像新内涵。可以说,在“后现代美学”观念主导下,没有哪一部电影可以带给观众全新的新奇感,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是在与其他电影的对照中来读解。而随着生命支持系统和植入技术的融合,在媒介成为人体一部分的时候,电影学者帕特里夏·品斯特所提到的“神经-影像”,银幕如同大脑或将成为现实。可以说数字技术充斥的当今,后现代美学观念从很多角度重建了电影理论研究。
三、跨媒体消费美学
(一)社交美学
“社交美学”指的是将作为“感觉学”的美学概念与电影作为媒介的社交性特征相融合,从人际关系视角,关注电影与受众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现实世界中人际关系角度看,电影成为人与人之间日常沟通、交流的重要谈资,成为个体确立集体归属感的重要媒介,甚至有些时候,看电影是年轻人谈恋爱和社交的幌子,在这种社交现实下,许多艺术品质并不精雕细琢的电影,却借助话题性收获票房以及下载量。
从虚拟世界的社交性来看,社交媒体平台形成了不同的社群部落,用户以自媒体身份主动担当起信息的传播者,从电影数据中抽出信息比特和片段,分享、转发,同时也制作各类数据汇入海量的数据流中。用户作为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者,在关于电影信息的一出一进中,生成一种介于人与虚拟社会生活之间的新型媒介社交关系,有时这种虚拟社交关系融入现实,又生成日常生活的社交。可以说,以社交美学视角关注电影是媒介交融的必然。从内容层面看它倡导电影在保证艺术品质的基础上进行话题生产,从营销层面它关注电影如何通过社交营销占领市场。
(二)沉浸美学
随着电影技术的更新、虚拟现实设备的诞生,观众所获得的体验已经不仅仅是《火车进站》放映时火车“冲出了银幕”的观感,而变成了“火车径直冲向了我们”,电影的沉浸式审美愈演愈烈。
1956年,被称为电影发展史上第一套真正意义上的虚拟现实设备诞生。从这时开始,杜比全景声听觉、3D电影、全息360度环幕电影、沉浸式影院设备等在虚拟与真实之间提供了跨越式的沉浸体验。随着VR、AR、AI等技术的升温,立体眼镜、头戴式显示设备进入电影领域,它将体验者与环境完全隔离开,加上影像的“拟真”播放系统,体验者无干扰地完全沉浸于虚拟空间中,而更高级的体感背心、嗅觉模拟器、体感手套等带给体验者更可感可触的“超真实”体验。除了VR影像外,影院装置中的吹风设备、振动座椅系统甚至气味制造装置等也将电影从单纯的视听感受中解放出来,进入“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的全感官艺术中,观众也越来越多地沉浸到日常现实中无法亲历的体验中。沉浸美学以追求感官的极致体验作为关注角度,基于感官至上的逻辑,它打通了人的所有感觉通道。罗伊·阿斯科特将沉浸性界定为“进入一个整体,由此消解主体与背景”,沉浸性会让观众浑然忘我地沉浸在影像的世界中,达成角色和体验者的统一。未来,虚拟屏幕、全息投影技术的更广泛应用,“距离消失”的沉浸审美中,人与电影作品将会达到更深层次的交融。
(三)休闲美学
休闲美学是生活美学的一个分支,将电影研究纳入休闲美学范畴,它以电影休闲如何走向美的休闲,以电影为休闲内容的人、电影休闲环境、休闲方式为研究内容。
首先,把欣赏电影作为休闲方式,它关注传统美学所倡导的电影视听体验,作为生活中实际的休闲内容,电影视听内容的打造应以追求审美为最高层次和境界,以促进休闲主体获得精神升华为己任。休闲美学倡导以“美的休闲”为目的,因此,迎合个别休闲主体低级趣味的电影视听内容是违背“美的休闲”旨趣的。在此基础上,电影休闲美学还关注电影如何提高休闲者休闲品位,拉动审美层次的提升问题。其次,影片中的相关元素通过“电影衍生品”这一形式,从“拟像”世界进入日常生活,这构成了第二层面的电影休闲。电影衍生品的出现与发展,是电影以视听为主的休闲美学走向日常休闲审美的切入点,因为“休闲美学要超越传统美学局限于视听的感官机制,而将全身心体验和践履的涉身机制融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在电影赋予某种物品或者地点美学意义的基础上,从拟像世界到现实世界的移情和共感是推动“电影衍生品”休闲的动力机制。如《捉妖记》中的胡巴、好莱坞电影中的擎天柱、钢铁侠、美国队长等从镜像世界延伸到真实世界中,享誉全球的迪士尼乐园成为全球瞩目的日常休闲地,这些都实现了观众从视听审美体验向全身心感知体验的扩展,在当今中国电影打造“IP”电影的现实下,只有以休闲美学的内涵作为内在指向的电影衍生品,才能真正融入人们日常休闲的现实世界中。
跨媒体环境下的媒介关系正颠覆着传统电影的一切规则,而且电影作为“技术的、经济的、美学的、社会的”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产物,以多重视角审视电影美学,升级电影自身的美学体系对重构电影理论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