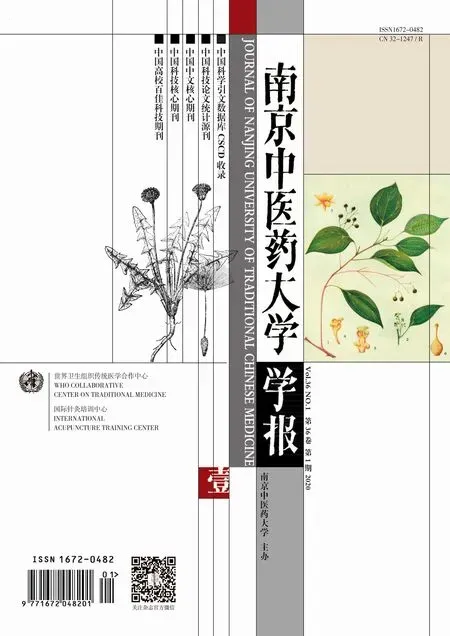《黄帝内经》毫针刺法基本体系探讨
颜纯淳,张永臣,毛逸斐,贾红玲
(1.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5;2.山东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5;3.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 济南 250355;4.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山东 济南 250001)
石器时代的砭石疗法是毫针刺法的起源,《后汉书·赵壹传》就有:“古者以砭石为针”[1]的记载。继石器时代之后,人类文明进入青铜器和铁器时代,铜、铁等金属的使用不仅代替了原有的石质生产工具,医疗器具方面,砭石的地位也逐步被以九针为代表的各种金属针具所替代,以九针为代表的金属针开始在临床广泛应用。大约在秦汉时期,毫针疗法的应用逐渐成为主流,成为九针疗法中最为常用的一种针具。针具的变革改变了针刺操作的手法术式,扩展了针灸临床应用的适宜范围,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针灸流派,进而推动了古代针灸学科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嬗变与创新。笔者对中国古代毫针刺法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认为《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奠定了中国古代毫针刺法的基本体系,在中国古代针灸学科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就研究中的些许思考,略述己见,望就正于大方之家。
《内经》汇编先秦两汉时期医学著作,非一人一时所成,详细阐述了针灸疗法的临床应用,包括单纯针刺、灸法、放血疗法和火针等都具备良好的临床效果[2]。尤其是针刺疗法,《内经》中各种针具的刺法论述纷呈,这其中毫针疗法的应用最为广泛,且形成了针灸学科毫针刺法的基本体系,成为后世论述针刺操作之圭臬。就其内容而言涵盖了毫针刺法的先决条件、基本术式、终极目标、补泻机制、禁忌事宜及其他六类。
1 毫针刺法的先决条件
毫针刺法的先决条件是在先秦两汉时期对针刺理论与临床实践的总结背景下,形成的毫针应用必须遵循的标准与原则。包括先诊脉、分虚实、明经络、别阴阳、重体质、知血气、合四时、必治神、辨标本、审寒热、度气候,共计11项。
1.1 先诊脉
《灵枢·九针十二原》提出:“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也。”(本文所引《灵枢》原文均出自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版《灵枢经》)诊脉是针刺操作前必不可少的步骤,有助于对疾病进行辨证诊断而开展针对性施治。《内经》时期的脉诊并不只是独取寸口,《灵枢·终始》《灵枢·禁服》等篇将人迎与寸口脉的比例作为诊断与治疗的依据。《灵枢·邪气藏府病形》根据脉之急缓、大小、滑涩确定不同的针刺操作原则。《内经》众多篇章中都蕴含有诊脉的论述,诊脉可决定针灸的方法、补泻、取穴,检验针刺的效果,判断针灸的禁忌,对针灸临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强调脉诊的目的,在于以中医的方法与理论,分析诊断病情,因人、因证选穴施以针灸,提高临床疗效[4]。
1.2 分虚实
虚实是人体病变的不同状态,是区分体内邪正盛衰关系的基本要素,更是决定针灸补泻的重要前提。如《灵枢·九针十二原》曰:“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灵枢·经脉》云:“盛则泻之,虚则补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分清病证之虚实,才不会导致虚虚实实之误。
1.3 明经络
经络是针刺起效的物质基础,经络理论是毫针疗法的理论基础。如《灵枢·本输》言:“必通十二经络之所终始,络脉之所别处,五输之所留,六腑之所与合,四时之所出入,五脏之所溜处,阔数之度,浅深之状,高下所至。”《灵枢·刺节真邪》曰:“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实虚,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而下之”,针灸临床首先需要了解和把握经络、腧穴的状态。明代马莳《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注《灵枢·经脉》曰:“此篇言十二经之脉,故以经脉名篇。实学者习医之第一要义,不可不究心熟玩也。后世能言不识十二经络,开口动手便错,而于此懵然,惜哉……凡《内经》全书之经络,皆自此而推之耳。”[5]由此可知明晰经络的重要性。
1.4 别阴阳
别析阴阳、调和阴阳、从引阴阳均为针刺操作过程中必须遵守的法则。《灵枢·根结》曰:“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调阴与阳,精气乃光,合形与气,使神内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本文所引《素问》原文均出自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版《黄帝内经素问》)张志聪注曰:“此言用针者,当取法乎阴阳也。夫阴阳气血,外内左右,交相贯通,故善用针者,从阴引阳分之邪,从阳引阴分之气。”[6]故《素问·标本病传论》总结道:“凡刺之方,必别阴阳。”
1.5 重体质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云:“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则血气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约毕也。”《灵枢·根结》《灵枢·逆顺肥瘦》针对布衣、大人以及肥人、瘦人、常人、壮士、婴儿的针刺原则均有论述,体现了《内经》因人制宜、辨体施针,注重根据体质差异而施治的原则。《灵枢·终始》有言:“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气。”《内经》深入细致地论述了体质差别与针灸施治之间的对应关系,对体质的辨识有助于预判疾病的进程及发病的倾向,从而针对性地把握针刺操作的原则和禁忌,进而规避不良反应,提高临床疗效。
1.6 知血气
血与气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的重要保障,因此也是疾病治疗过程中的重要切入点。《灵枢·官能》曰:“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出入之合,谋伐有过。”《吴医汇讲·摄身杂话》曰:“周身气血,无不贯通。故古人用针通其外,由外及内,以和气血……至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盖指本来原通,而今塞者言,或在内,或在外,一通则不痛,宜十二经络藏府,各随其处而通之”[7],亦体现了针灸对于通调气血的作用。
1.7 合四时
《灵枢·终始》曰:“春气在毫毛,夏气在皮肤,秋气在分肉,冬气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时为齐。”《内经》中以四时为原则的刺法众多,总的原则就是要做到因时制宜。《灵枢·四时气》曰:“四时之气,各有所在,灸刺之道,得气穴为定”,认为具体疾病的临床治疗方法,应根据四时变化的情况而适当调整。因时制宜是针灸临床常用的治疗原则,是将自然界节气、时令的变化规律,与机体的机能状态相结合,从而选择对应防治疾病方法的一种措施。
1.8 必治神
《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凡刺之真,必先治神”,《灵枢·九针十二原》言:“粗守形,上守神”,《灵枢·本神》曰:“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灵枢·官能》提到:“用针之要,无忘其神”,还有《素问·诊要经终论》所言“刺针必肃”等均为针刺治神的描述。后世窦汉卿有“凡刺者,使本神朝而后入;既刺也,使本神定而气随;神不朝而勿刺,神已定而可施”[8]的论述;张景岳提出“针以治神为首务”[9]的观点。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中亦是如此[10]。能否治神是判断医生针灸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治神是针刺过程中必须一以贯之的内容,治神是否得当可直接影响临床疗效。
1.9 辨标本
《灵枢·卫气》曰:“能知六经标本者,可以无惑于天下。”《素问·标本病传论》云:“病有标本,刺有逆从。”《素问·至真要大论》言:“知标与本,用之不殆。”《内经》中的标本,既是经络理论的组成部分,也体现了疾病治疗过程中的主次关系。标本理论既可以指导辨证诊断,又可以指导临床取穴,还可以指导新穴运用[11]。辨清标本,分清主次,掌握取穴、配穴之道,是临床针刺过程中提高疗效的关键。
1.10 审寒热
《灵枢·官能》曰:“审于本末,察其寒热,得邪所在,万刺不殆,知官九针,刺道毕矣。”审察本末寒热,方能得邪所在;得邪之所在,方能万刺不殆。在临证时,详察寒热、虚实的不同,是针灸处方配穴的重要条件。
1.11 度气候
《素问·八正神明论》云:“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天地乃大宇宙,人身为小宇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与人体之气相呼应。中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称其为天人相应,并将此观点贯彻于中医的诊疗始终。因此气候变化不仅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同时也能影响到针灸的临床治疗。因此,针刺之时也应当审度天地人体之气。
上述11项为毫针刺法的先决条件,被《内经》反复强调,多次被提及,突出了其在针刺操作过程中的重要性,也被后世医家所继承与发扬。
2 毫针刺法的基本术式
针刺过程中的揣穴、进针的角度与深度、行针手法、留针时间以及出针方法,同样对针刺效果有影响,《内经》对毫针刺法的基本术式进行了全面归纳。
2.1 揣穴
《灵枢·九针十二原》提出:“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对针刺左右手的操作进行了分工。《灵枢·刺节真邪》云:“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实虚,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而下之。”对揣穴的基本操作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内经》认为揣穴可起到探明穴位、辨别虚实、辅助补泻的作用。《难经·七十八难》提出:“当刺之时,先以左手压按所针荥俞之处,弹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气之来,如动脉之状,顺针而刺之”[12],强调了揣穴之左手(押手)的重要性,认为“知为针者,信其左;不知为针者,信其右。”[12]窦汉卿《标幽赋》指出:“左手重而多按,欲令气散,右手轻而徐入,不痛之因”[13],徐凤《金针赋》认为:“按之在前,使气在后,按之在后,使气在前,运气走至疼痛之所。”[13]可见通过揣穴可以探查腧穴的情况,确定穴位的深浅和具体位置,以达到无痛进针的目的,还可以疏通经络,调控针感,从而达到气至病所的目标[14]。
2.2 进针
持针是进针的前提,“持针之道,坚者为宝”是《灵枢·九针十二原》对持针的首要要求,也是持针法的总则。《内经》关于进针中针刺的角度、深度以及具体刺法的论述主要见于《灵枢·官针》。如五刺中的输刺,十二刺中的恢刺、齐刺、扬刺、直针刺、输刺、浮刺、傍针刺等对针刺的角度都有具体要求,涵盖了现代高等教育针灸教材中直刺、斜刺、平刺的内容。进针深度方面,针刺深浅有其基本规律,同时还需根据刺法、病证、腧穴、体质、季节等因素综合判断。总体的原则按《素问·刺要论》所言:“病有浮沉,刺有浅深,各至其理,无过其道”。
2.3 行针
行针的目的在于产生、调整针感,或使针感向某一方向传导扩散。可分为基本手法和辅助手法。基本手法即提插与捻转,《内经》中并未明确提出。《灵枢·官能》中伸、推、切而转之、微旋而徐推之为提插捻转等行针基本手法的雏形。行针辅助手法的论述见于《灵枢·邪客》:“辅针导气,邪得淫泆,真气得居”,通过《素问·离合真邪论》所述“扪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门,以闭其神”的方法,辅助导气,以驱邪扶正。
2.4 留针
留针是针刺过程中的又一重要环节,尽管《内经》中并没有明确记载留针时间的长短,但《内经》提出了留针与否的原则。如《灵枢·九针十二原》云:“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素问·离合真邪论》有“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的论述,说明决定是否留针的基本原则在于气至与否。另外,《内经》中不留针或短留针的情况有婴幼儿、老人、瘦弱者、生活优越者、脑力劳动者,以及性格外向、病情轻、病位浅、病程短、实证、热证、感传好、得气快者;留针时间较长的情况有肥胖者、青壮年、强健者、体力劳动者,以及性格内向、病情重、病位深、病程长、虚证、寒证、无感传、得气慢或不得气者。留针与否以及留针时间的久暂,要根据患病的季节、部位、病邪性质、邪正盛衰、脉象、年龄、体质、补泻手法等因素,在辨证论治的原则指导下来确定,以提高针灸疗效[15]。
2.5 出针
出针是针刺操作的最后环节。《内经》论出针以“谷气至”为准则,《灵枢·终始》认为:“三刺则谷气至,谷气至而止。所谓谷气至者,已补而实,已泻而虚,故以知谷气至也。”只有谷气至后出针,针刺操作方可结束。如《类经》所言:“邪气去而谷气至,然后可以出针。”[9]
此外,《灵枢·官针》对于针法操作论述尤详,其中五刺、九刺、十二刺三类26种刺法,系统总结了当时的针法,为后世针法奠定了基础。《灵枢·官针》根据所刺部位的不同即有对应不同的刺法之分。刺皮法如毛刺、直针刺、半刺;刺脉法如络刺、赞刺、豹纹刺;刺肉法如分刺、合谷刺、浮刺;刺筋法如恢刺、关刺;刺骨法如短刺、输刺。《灵枢·官针》还记载了透穴刺法的雏形合谷刺,烧针刺法的焠刺,排脓放血的大泻刺,以及特定穴取穴中的输刺,交叉取穴的巨刺,循经取穴的远道刺,近部取穴的经刺,前后配穴的偶刺等。
3 毫针刺法的终极目标
针刺操作的终极目标就是得气,《内经》得气的内涵包括得气、气至、候气、守气、针游于巷五个方面。
3.1 得气
得气的论述主要见于《灵枢·小针解》《灵枢·终始》《素问·离合真邪论》三篇。《灵枢·小针解》曰:“空中之机清静以微者,针以得气,密意守气勿失也。”得气指针刺后观察与静候腧穴中气机的微小变化,并须审慎把握的一个时机。《灵枢·终始》提到:“令志在针,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气至乃休。男内女外,坚拒勿出,谨守勿内,是谓得气。”得气是神志专一,精神内守,把精神集中在针刺上,直至气至病所,从而使正气充盛不出,邪气外散不入的一种状态。《素问·离合真邪论》在论述补泻时,将“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候呼引针,呼尽乃去,大气皆出,故命曰泻”与“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知日暮,其气以至,适而自护,候吸引针,气不得出,各在其处,推阖其门,令神气存,大气留止,故命曰补”并见。可知得气是针刺操作达到补泻效果的先决条件。
3.2 气至
《灵枢·九针十二原》提出:“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气至是针刺有效的前提条件。《内经》多处论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谷气至而止”,“凡刺之道,气调而止”,体现《内经》对气至的强调,故气至对于针刺起效非常重要。
3.3 候气
候气见于《灵枢·卫气行》和《素问·离合真邪论》,认为针刺要候其时、候其所在,须候邪气来而泻之、真气来而补之。候气的具体操作是“静以久留”,待针下真气至、邪气来而施行补泻之法,成为《内经》针刺扶正祛邪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如《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言:“知其往来,要与之期,粗之暗乎,妙哉工独有之。”
3.4 守气
守气两见于《灵枢·小针解》:“上守机者,知守气也。……空中之机,清静以微者,针以得气,密意守气勿失也。”前者与候气意思相近,后者指得气后慎守经气而勿失也。《素问·宝命全形论》曰:“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深浅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论述了守气的方法与意义。针灸临床中进针强调得气,而忽视守气的现象时有发生,是导致治疗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
3.5 针游于巷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云:“刺此者,必中气穴,无中肉节。中气穴则针游于巷,中肉节则皮肤痛。”对针刺“中气穴”后的感受进行了描述。“针游于巷”强调的是医者的感觉,并非指患者在受针后所产生的上下传导的放散感[16],更确切地说是从医者的角度形容刺中腧穴时手下的一种顺通空余之感[17],亦属于得气的范畴。
4 毫针刺法的补泻机制
针刺补泻是毫针刺法的核心内容,《灵枢·九针十二原》提出:“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补泻之时,以针为之。”《内经》通过针刺的补泻操作达到补虚泻实的目的,从而开展疾病治疗。关于具体的补泻手法,《内经》明确提出迎随、徐疾、呼吸、开阖、深浅、导气法、方员等7种补泻手法。其中深浅补泻后世发展为烧山火、透天凉等复式补泻手法,导气法后世阐发为平补平泻,方员补泻中包含了提插、捻转补泻的雏形[18]。
4.1 迎随补泻
迎随补泻首见于《灵枢》开篇《九针十二原》,可见地位之重要。“迎之随之,以意和之”,并非对迎随补泻的具体描述,而是对针刺补泻时机的高度概括,也被认为是针刺补泻的总则。《灵枢·终始》曰:“泻者迎之,补者随之,知迎知随,气可令和”,迎随在《内经》中仅作为针刺调气补虚泻实的原则来解释,类似的含义如《玉龙赋》:“伤寒无汗,攻复溜宜泻,伤寒有汗,取合谷当随”[13],此处“随”即指“补”。关于以针向与经脉循行方向的逆顺来确定补与泻的具体操作,则主要见于宋元之后《济生拔萃》《标幽赋》《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针灸大成》等书,属于对《内经》迎随补泻操作规范的细化。
4.2 徐疾补泻
徐疾补泻的论述亦首见于《灵枢·九针十二原》:“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关于徐疾补泻的认识,《内经》中出现不同的观点,分别记述在《灵枢·小针解》及《素问·针解篇》中,后世医家有从前者,有从后者,亦有认为两者皆对者,由此引发了的一系列争辩。徐疾在《内经》中主要有三种用法,一指气行的快慢或脉的徐疾,一指出针的快慢,一指留针时间的长短。其具体含义应与《内经》上下文相参[19]。
4.3 呼吸补泻
呼吸补泻在《内经》中的论述主要见于《素问·八正神明论》《素问·离合真邪论》《素问·调经论》三篇。基本操作是以患者吸气时入针(针与气俱内),呼气时出针(针与气俱出)为泻;呼气时入针(气出针入),吸气时出针(气入针出)为补。后世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临床实践,对呼吸补泻做出了各自的阐释。特别是元明时期,高武、李梴、杨继洲等在呼吸调息方法的主被动性以及结合呼吸调和阴阳的应用上提出各自观点。高武主张病人自然呼吸;李梴主张自然呼吸与使然呼吸的灵活应用;杨继洲则从调和阴阳的角度来分析呼吸补泻的机理,根据病证的阴阳、寒热、虚实而施行相应的呼吸补泻法[20]。
4.4 开阖补泻
《素问·离合真邪论》《素问·调经论》在论述呼吸补泻的同时亦兼有开阖补泻的描述,以出针时“摇大其道”为泻,“闭塞其门”为补。此外《素问·刺志论》有“入实者,左手开针空也;入虚者,左手闭针孔也”,《素问·针解》亦有“邪胜则虚之者,出针勿按。徐而疾则实者,徐出针而疾按之。疾而徐则虚者,疾出针而徐按之”的相似论述。后世《针经指南·直言补泻手法》亦遵从经旨有“随吸出针,乃闭其穴”及“随吹气一口而徐出其针,则不闭其穴,命之曰泻”的开阖补泻论述[8]。
4.5 深浅补泻
深浅补泻的论述见于《灵枢·终始》:“一方实,深取之……一方虚,浅刺之……脉实者,深刺之,以泄其气;脉虚者,浅刺之,使精气无得出,以养其脉,独出其邪气。”此外本篇及《灵枢·官针》均有关于“三刺至谷气”“三刺则谷气出”的论述,为后世“烧山火”“透天凉”天地人三部操作补泻之源。
4.6 导气法
导气法的最早描述见《灵枢·五乱》:“徐入徐出,谓之导气。补泻无形,谓之同精。是非有余不足也,乱气之相逆也”,为现代平补平泻手法的起源,后世李东垣、徐凤、杨继洲等均有其自身的理解与阐释。
4.7 方员补泻
方员补泻在《内经》中有两处不同论述,分别见于《灵枢·官能》《素问·八正神明论》。前者认为泻必用员、补必用方,后者认为泻必用方、补必用员。应当辨明《灵枢·官能》立论在先,《素问·八正神明论》阐发在后,不可将后者与前者混合不分,甚至颠倒主次[21]。另外,从两篇的论述可知方员补泻实际为一种复式补泻,其中包含了徐疾、开阖、呼吸补泻。同时从“切而转之”“伸而迎之”“微旋而徐推之”等描述可知其中还蕴含着捻转、提插及迎随补泻。
5 毫针刺法的禁忌事宜
针刺禁忌在《内经》中有系统的论述,且占据较多篇幅,足见其对针刺禁忌的重视。《灵枢》《素问》中分别有16篇及12篇涉及针刺禁忌,尤其是《灵枢·五禁》《素问·刺要论》《素问·刺禁论》三篇为针刺禁忌的专论[22]。内容涵盖施术部位、患者体质、病情性质、针灸时间等多个方面,基本构建了针灸禁忌的理论体系,至今仍然对针灸临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凡刺之”在《内经》中多次出现,且其后有真、要、理、法、道、方、术、属、禁、害等字。如“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经络之所终始”“凡刺之理,经脉为始”“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气”“凡刺之要,九针最妙”“凡刺之道,毕于终始”“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凡刺之要,官针最妙,九针之宜,各有所为”“凡刺之道,气调而止”等,论述了针刺要治神守气,以经络理论为理论依据;针刺前要对经络进行诊察以明确病位、病性,以选择对应的针具和操作方法;针刺要遵循天时、把握进针和出针时机,以气调为目的[23]。
综上,尽管现代毫针针具较《内经》时期已有不同之处,但《内经》对毫针刺法的先决条件、基本术式、终极目标、补泻机制、禁忌事宜等的论述,构成了以中医药高等院校《针灸学》《刺法灸法学》教材为代表的,当今针灸学科毫针刺法体系的基本轮廓。涵盖了毫针刺法的基本原则、基本操作、基本目标、基本补泻、基本禁忌等多方面内容,是中国古代针灸学科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学必正脉,作为针灸经典著作,《内经》关于毫针刺法的论述成为后世论述针刺操作之圭臬,亦有待于后人进一步传承、发扬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