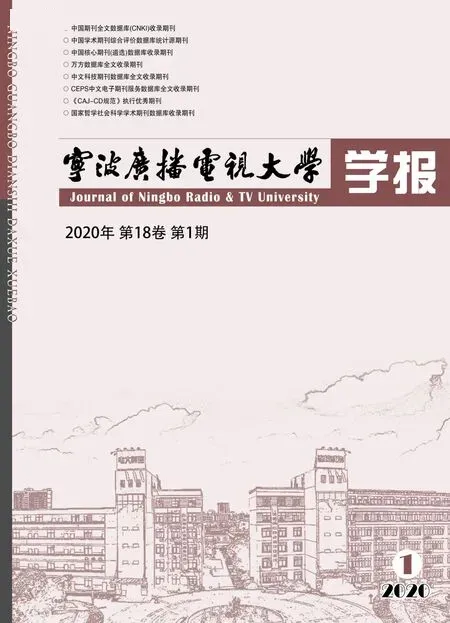梦幻与迷醉的交响
——艾德娜形象中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
汤路平
(南京市红山初级中学,江苏 南京 210000)
引言
凯特·萧邦的力作《觉醒》出版至今,已有评论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富有见地的分析。《觉醒》讲述了一位中产阶级女性自我意识、性意识和自由意识觉醒的故事。细读文本,艾德娜的性格跃然纸上。性格决定命运,而行为表现人物性格。尼采笔下的两种相悖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在艾德娜的性格血液中流淌。艾德娜追求自我存在的过程是这两种精神相互交织、相互斗争的外显。由大海、草原和尚奈尔岛所构筑的梦幻世界促其觉醒以挣开枷锁,进入“迷醉”的酒神状态。在追求本真存在的途中,她对人生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知晓这些幻想在现实世界难以实现后,她勇敢地沉入大海,拥抱梦幻,实现永生。
一、“日神精神”——虚幻的梦境
日神阿波罗是光明之神,它的光辉使万物呈现美的外观,他“统治了我们内在世界的美丽梦幻”。[1]日神精神的冲动创造了一个光明灿烂的梦幻世界。梦境的内容并不是理性的、真实的,而是非理性的、虚幻的。在现实中实现不了的愿望在梦中能得到满足。因而主体用梦境来实现自己潜在的愿望。
大海与尚奈尔岛作为《觉醒》中两个重要的意象,在艾德娜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两种元素胶合在一起,紧密不分地编织着艾德娜的梦。“大海是《觉醒》中的最重要的意象;小说中所有的重要事件都与大海相连,每一次都在大海中经历,直到最后的融入。”[2]夜晚劳伯特邀请艾德娜一起游泳,在矛盾心理的左右下,艾德娜最终接受了他的邀请。“大海的回响呼唤着她的灵魂。大海的抚触好柔,它温柔地紧紧拥抱她的身躯。”[3]16这是艾德娜觉醒的第一步,她的思绪如脱缰的马儿自由地驰骋于天地间。在艾德娜心中,大海代表着自由的乌托邦,大海的广阔迷人唤起了她对少女时代大草原的回忆。格蓝岛上克里奥妇女们谈话中的放荡不羁唤醒了艾德娜的自我意识,她那矜持的外罩也松开了。而与劳伯特在尚奈尔岛的徜徉则是艾德娜在自由的梦幻中的一次真正的探险。尚奈尔岛的别致浪漫,金蛇盘旋不禁让人想起伊甸园。在那里,艾德娜如夏娃一样,获得了智慧。“艾德娜觉得好像自己正被载离长久以来束缚着她的停泊港。栓索终于松了,就在前一天晚上,神秘的鬼魂出现时断了,现在她终于得以自由漂流,任意扬起帆来前往任何想去的地方”。[3]42艾德娜完全把妻子、母亲的身份抛之不顾,只愿与劳伯特一起编织童话般的梦。她“心想这么慵倦的小岛一定每天都是安息日”。[3]44当她问劳伯特她睡了几年时,劳伯特回答道:“你睡了整整一百年,我被留在这里保护你,让你能好好睡觉。我已经在这棚下看了一百年的书,唯一无法抵抗的恶魔就是没有办法让一只烤熟的鸡不会越变越干。”[3]46劳伯特既是艾德娜的守护者,又是她心灵的倾听者。艾德娜希望她能自由地和心爱的劳伯特在梦幻天堂里幸福地生活。但在现实中,劳伯特不愿投入到这份无果的爱情中,他选择逃离。即使是虚幻的,尚奈尔岛美好的梦让艾德娜思考“为什么今年夏天和生命中的其他夏天都不一样。她只知道自己——目前的自己——和以前的自己有所不同,却还没想到自己正以不同的眼光看周遭的事情,正重新发现内心里那足以改变外在环境并使之增色的崭新情境”。[3]50“这个夏天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又在穿越那片绿色草原,同样无所事事、漫无目的,不加思索又没人引导地走着。”[3]20艾德娜被自己带入了幻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乐此不疲,认为她假想的新世界单纯而美好。沉浸在浪漫而虚幻的梦中,艾德娜决定“要远远地游出去,游到别的女人从来不曾游过的地方”。[3]34在抚触好柔的海水中,她无拘无束,绽放生命的张力。游泳象征着她欲挣脱羁绊,跨越边界。她的这一行为为她之后逃离家庭、丈夫和孩子埋下了伏笔。
没有幻想的人生是多么的索然无味。重要的是,艾德娜开始领悟到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也逐渐开始挣开强压在她身上的枷锁。大海召唤了艾德娜的心灵,激起了她对自身价值的思考。艾德娜开始聚精会神于梦境,体验生存的快乐。但日神精神毕竟是超现实甚至具有虚幻意味的。劳伯特不愿沉溺于日神的梦幻表象,因为他深切地感到作为庞特里耶太太的艾德娜与他的心心相印只是在尚奈尔岛的童话世界中熠熠生辉,而在现实中必将阴暗惨白。梦在现实与表象的世界中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作为一种存在生活在现实社会不能一味地生活在虚幻世界而脱离常规。如果失重,带来的必然是人生悲剧。艾德娜一生都追求不可触及之物。少女时代痴迷的三位情人、大草原、大海、尚奈尔岛,甚至劳伯特都只属于艾德娜自设的梦幻天堂。对梦幻世界的追求而忽视现实对个人的约束也预示着艾德娜自杀的必然性。
二、“酒神精神”——放纵的迷醉
梦境中的一切异常美好却虚无缥缈。艾德娜愿意沉浸在自己编织的梦中,不愿再沦为丈夫的附属品和孩子的看护人。在广阔的大海、葱郁的草原和神秘的尚奈尔岛构成的梦境中,其情欲、创造欲和独立意识进一步升级,进入“醉境”。它是“梦境”的延伸,是更自由、更本真的境界,是非理性的激情,即“酒神精神”。这种精神也在艾德娜的性格血液中流淌。在“酒神精神”的作用下,艾德娜化为酒神狄奥尼索斯,摈弃了束缚其身心发展的理性、家庭和社会,解放了自己,张扬了个性。艾德娜在寻找本真存在的孤独的心灵之旅时将“酒神精神”释放到了极致。在“醉”中,艾德娜触及存在,感悟到生命的真谛。
对于“醉”的本质,尼采提供了一个简短的回答:“醉的本质是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4]在尼采看来,这个世界是一个无形的生命之“力”构成的世界。这种“力”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力,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是生命世界的绝对命令,是一种不容抗拒的意志,即使生命本身也不能抗拒这种强大的内在于生命的意志。因而醉境中的艾德娜敢于公然反抗社会道德规范,公然显示隐藏在无意识深处的生命本能和独特个性。梦境的美好激发了艾德娜潜在的生命意志。从此她不再沉静,不再安于现状。浑浑噩噩地生活了二十八年,顺顺从从地做了艾德娜·庞特里耶后,大海把她从桎梏个性的生活中唤醒。“她开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完全跟着感觉走”,[3]71她拒绝再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从取消每周二的接待日到摔婚戒、砸花瓶、搬新居都显示了艾德娜冲破传统规则和家庭樊笼的勇气。在艾德娜的“酒神精神”淹没理性审慎的过程中,她从根本上叛离了封建伦理,打破樊笼,僭越界限。在这方面,她的“酒神精神”代表了一种冲破旧秩序,追求真实自我和新生活的积极向上的因素。但不容讳言,艾德娜在劳伯特离她而去,与厄络宾之间没有爱情的肌肤之亲被打上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烙印。
“醉”的本质除了力的提高,还表现为“充溢之感”。这一点在艾德娜身上,体现为在“放纵”的迷醉中达到个性的张扬。艾德娜并非像奉行酒神崇拜的西方信徒那样通过苦行、酒精、吸毒或狂舞来追求迷醉,而是通过对音乐的热爱和绘画的追求,达到个性的张扬。芮芝的音乐激发她走进了艺术的世界。艾德娜“任由音符贯穿她整个人,像一缕温热的光辉照亮了她灵魂深处个个阴暗的角落,这是她愉悦快乐的序曲”。[3]100芮芝的钢琴曲坚定了她反叛的决心,因而她再也无法回避灵魂深处的自我。在《权力意志》中,尼采激情满怀地宣称:“艺术,无非就是艺术!它乃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壮举,是生命的诱惑者,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5]艺术能调节人的性情,给人以审美享受,给人以安慰。
“艺术家,其中包括诗人,凡是有成就的几乎都是传统的反叛者和新思想的开拓者。”[6]芮芝以极大的勇气去追逐自己热爱的艺术以获得对本真自我的认识。芮芝身上的“酒神精神”让艾德娜看到了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她把时间都花在了学习绘画上,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代表自己身份的艺术家,对孩子弃之不顾,对丈夫毫不关心,靠卖画来支撑自己的生活,实现了精神上和经济上的独立。艺术状态就是生命力充溢的状态,是酒神强力得到充分表现的状态,是个性达到张扬的状态。艺术的人生才不是贫瘠的、苍白的。艾德娜的丈夫庞特里耶认为“身为一家之主又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女人,不为全家的舒适费心,反而把时间浪费在画室里,简直太荒唐。”[3]71但是艾德娜立刻反驳道:“我喜欢画画,不要干扰我,你把我弄得心好烦。”[3]71艾德娜通过追求艺术来构建自己的身份,虽然会背离传统,但在这一过程中,她的个性得到张扬,她的生命丰盈而充溢,这也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明证。
艾德娜酒神式的“放纵”恰恰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即使这一行为是毁灭性的,她却真切地感受到了“自我”。作为上流社会的女性,艾德娜具有追求个性自由的愿望和要求。这种愿望伴随着艾德娜的觉醒日益强烈,与内心深处强烈的生命激情融为一体,合成艾德娜式的酒神精神。
三、“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交响——孤独的死亡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认为希腊悲剧便是日神的梦与酒神的醉的最高形式的融合。“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彼此并行又公开决裂,互相刺激而不断获得新生。作为个体的人总是受这两种本能冲动的支配。日神状态是酒神状态向外在世界的流溢,酒神状态借助日神美化的形象世界使生命感受到激发。日神与酒神并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本能,它们都是对生命意志的肯定,共同赋予人生以存在的意义。
艾德娜梦幻世界里大海的光照亮了路程,“她的内心似乎有种曙光初现,一方面照亮她眼前的路,”[3]16启发她在现实中追寻本真的自我。“另一方面又禁止她走上这条路。”[3]16“海浪拍打海岸的此起彼伏的节奏,像是陪伴着她寻找自我意识的历程,陪伴在她的一系列的反抗中,揭示了每一次经历的不同精神状态。”[7]回忆往事,“她还听到水波潺潺,还有帆布拍打的声音,看得到反照在水面的月光,也感觉得到那阵阵柔和温暖的南风。一股微微的欲念缓缓流经她的躯体,几乎教她把持不住手中的画笔,双眼灼热了起来”。[3]72即使当艾德娜作画时,海水依然在她耳畔低吟,梦幻天堂依然清晰可见。在艾德娜眼中,梦幻与现实的界限如此模糊。“过去对她而言毫无意义,并不能给她任何教训;未来则是一团神秘,她也无意去参透。唯有目前才是真实的,才是真正属于她的,足以折磨她,带给她锥心的痛苦:她已经失去原来拥有的,却又得不到那狂热而刚刚苏醒的自我所渴求的。”[3]56艾德娜愿意只争朝夕,活在当下。但是在尚奈尔岛上劳伯特为她哼唱的《哦,但愿你了解》却一直萦绕在她的心中。尤其是“艾德娜工作的时候,不时会低声唱着《哦,但愿你了解》那首小曲子”。[3]72
“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在艾德娜身上释放艺术的强力。两者存在着对立与冲突,但又相结合,并在“酒神精神”的宣泄中得到了升华。艾德娜如同萧邦笔下的其他女性,虽然都表现了强烈的欲望、沉醉、迷狂、放纵等“酒神精神”,但最终却又获得了“理智”的回归。艾德娜如同尼采一样是时代的早生儿。她觉醒得太早了,除了芮芝,大部分女性都还在沉睡。她注定是寻梦,筑梦路上的独行者。觉醒后直面痛苦,承担痛苦,并在痛苦中赎清自己对孩子的罪恶,由此获得了精神上的解脱。艾德娜的死亡是“酒神精神”发挥到极致的表现,而她的死是为了追求像日神那样美丽的梦幻。既然她的生活不能达到她所期望的标准,而自杀能实现她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愿望。
艾德娜一生都追求虚无缥缈的不可触及之物,这些是她自我编织的梦之网的组成部分。艾德娜在梦幻中徜徉,把深藏于内心的生命力绽放出来,形成一种坚韧的生存态势。她经历了如尼采笔下人类精神的三种变形。骆驼——具有担当重荷的精神;狮子——为创造自由而生反抗精神;婴儿——创造新的价值。艾德娜赤露着身子,“她觉得自己像是个初生的婴儿,正张大着眼睛看这个似曾相识的世界”。[3]147尼采认为婴儿之所以能狮子所不能,就在于他是天真而善忘的,婴儿代表的是一个新的开始,一种神圣的肯定,在这种神圣的对新生的肯定之下,精神就有了自己的意志。所以,艾德娜如同婴儿一样拥抱大海。死亡亦是另一段人生历程的开始。死亡的是肉体,不朽的是精神、意志和灵魂。艾德娜搬出丈夫的豪宅,精心设计用于安身立命的鸽子屋。然而狭小的空间不能完全使她身心得到解放。朋友的不解、爱人的遁去、家庭的束缚促进她离开尘世,拥抱大海。在鸽子屋里,艾德娜获得的只是暂时的象征独立和自己的精神家园。只有真正地回归大海,这种暂时性才会变为永恒性。她的死亡是孤独的,因为她的内心、她所追求的梦以及她为梦所做出的负隅顽抗鲜被人理解。但她的行为却是勇敢的,她决意挣脱社会的束缚,成为一名勇敢的“艺术家”,徜徉在艺术的梦境中。性格血液中流淌着“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艾德娜热爱生命,可并不畏惧死亡。在生命状态的消散中,艾德娜通过自我否定而肯定生命的本质,最终迈入了自由的天堂。
结语
艾德娜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虚无缥缈的不可触及之物,活在自我编织的“梦境”中。梦境的美好促其性意识、自由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激起了潜在的“酒神精神”。觉醒后,她毅然反叛社会,张扬个性,彰显生命的价值。爱人的遁去、友人的不解、家庭的负担让她无力再挺身奋斗。她选择死亡,重归自己的乌托邦,达到永生的恒态。萧邦笔下的艾德娜超越了道德和社会成规,冲破了理性的樊笼,执着于内心本真的渴求,最终品尝到了自我存在的甜蜜,可视为“酒神精神”的象征。艾德娜性格中充斥的“酒神精神”即是人性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以理性为其平衡。
尽管萧邦和尼采之间未必有明显的相互影响,但他们对人类追求自我存在价值的礼赞却因时代的相同而相似。尼采的哲学具有明显的反理性特征,“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是其中的核心概念。梦与醉从表象的冲突到内在融合的演变,正是对生命的礼赞与肯定。理性因其压抑生命本能的特性而造成人这一生命体生命力的缺失。尼采希望人类摆脱理性的桎梏,找回生命本真的状态,弘扬生命的力量,而艾德娜身上流淌的两种精神砸碎了一切对生命的束缚,也正是人性中不容忽视的非理性力量的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