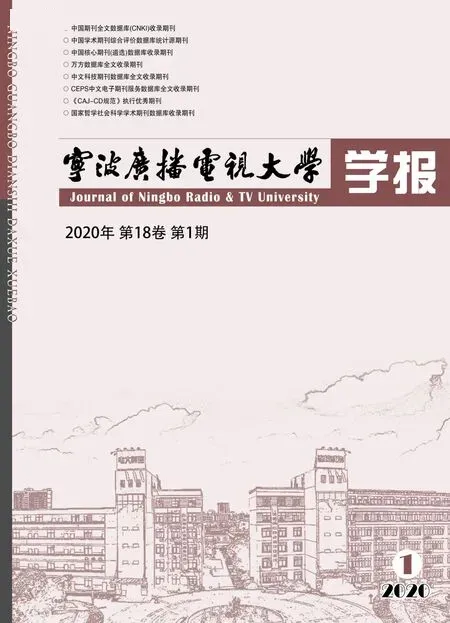近三十五年《诗源辩体》研究述评
冯圆圆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晚明复古派诗论家许学夷撰著的《诗源辩体》,历经当代近三十五年的重视和研究后,逐渐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中的价值和地位。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标点版《诗源辩体》出版以前,虽已有学者关注这部著作,但标点版通行后的九十年代至今,对许学夷及《诗源辩体》的深入研究才开始逐渐增多。截止2018年底,两岸对许学夷《诗源辩体》的研究论文达60 余篇。方锡球的《许学夷诗学思想研究》是目前可见到的唯一一本专门研究许学夷及其诗论的论著。这些研究成果大多聚焦许学夷主要诗学思想及成就,也对许学夷的历代诗评及其诗学思想在晚明及以后的接受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一、关于许学夷生平与《诗源辨体》版本研究
(一)对许学夷生平与交游的研究
许学夷(1563-1633),江阴县人,晚明诗人、诗论家。今留存在世的著作有《伯清诗稿》《诗源辩体》,其诗作亦收录于《江阴诗粹》《江上诗抄》等。关于许学夷其人其事,研究者多了解自《诗源辩体》所收录的《许伯清传》,该传记由明代晋陵恽应翼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撰写,约 1380字,其中云“许学夷,字伯清,先世汴梁人”,又说“不理生产,杜门绝轨,惟文史是紬”,[1]432-433对许学夷的家世和履历都作了清晰的考述。汪泓在其论文[2]中还谈到崇祯以后的《江阴县志》及《澄江诗选》一类作品中,也皆有许学夷小传。汪泓的这篇文章,当是目前唯一一篇以论述许学夷生平为主的论文,对许学夷的精神世界和撰写《诗源辩体》以外的文学活动分别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析,由此勾勒出一位个性强烈、有中正之识、终身致力于诗学的学者形象。
此外,许学夷还与晚明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有着密切的交游关系,对此学者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如台湾学者谢明阳在其论文中提到:“杜门绝轨、谓世无足与言的许学夷,竟然与大旅行家徐霞客一同泛舟游山,甚至相思契阔、相见绸缪,可以想见二人情谊之深。”[3]田柳对许学夷与徐霞客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也进行了专门的考察。[4]这些研究无疑对进一步了解许学夷的生平及其交游情况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二)对《诗源辩体》版本的研究
《许伯清传》言许学夷为撰《诗源辩体》“历四十年,十二易稿,业乃成”,[1]433描述了许学夷著《诗源辩体》所付出的功力和心血。实际上,“历四十年,十二易稿”并非由见证了《诗源辩体》初刻的恽应翼所书,而是出自全权负责《诗源辩体》再刻的许学夷女婿陈所学之手。这件事陈所学自己在《许伯清传》末尾作了交代:“诗源小论,初刻于万历壬子……将复刻,而恽先生已殁。”[1]434可知《诗源辩体》有两个版本。其中,初刻本为十六卷本(刻于1613年),再刻本为三十八卷本(刻于 1642年)。
对这两个明代版本的刻印情况进行详细研究的有谢明阳,其在论文中考察了《诗源辩体》在当时由传抄进而两度刊行的传播情形,认为《诗源辩体》十六卷本在付梓前受到过徐霞客的传书,且其刊行属于家刻;而三十八卷本由陈所学父子刊行[3]。除这两个版本,汪祚民在其论文[5]中还关注到《诗源辩体》的另一个本子,即十六卷本变为三十八卷本前的稿本,汪祚民通过将之与明代两个版本进行对比,认为稿本在我们研究十六卷本向三十八卷本的演变中起到了权威的参考作用,又因其与三十八卷本之间存在部分出入,因此不仅可用以校正陈所学刻本及其系列版本中的舛讹,在“寻绎许学夷诗学理论的发展脉络”方面也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二、对许学夷《诗源辩体》诗学思想的总体研究
《诗源辩体》是一部诗学专著,学者对它的研究便主要着眼于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价值意义的诗学思想,因此达到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约有25 篇论文,仅次于对其历代诗评的研究。对这部分的研究,主要有《诗源辩体》诗学思想的来源、内容及成就几个方面。
(一)许学夷《诗源辩体》的理论根源
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几乎是明清众诗论家的理论标杆。就明代而言,复古派的诗学观点沿袭了严羽的“标举盛唐”之说,提倡“性灵”的公安派其主张与《沧浪诗话》也有一定的因袭关系。身处明代复古与反复古运动中的许学夷,以毕生精力撰写的《诗源辩体》,其理论来源必定是多元复杂的。朱金城、朱易安在论文中一语破的,认为包括许学夷在内的明代各大家论诗的分歧以及发生分歧的原因之一正是《沧浪诗话》的影响。论文分别从许氏的源流、正变和标举盛唐之说详细分析了许氏对《沧浪诗话》的继承和发展,尤其肯定了许氏对《沧浪诗话》的大量注解和较为客观的新见。[6]与本文见地深刻相得益彰的是汪泓[7]对《诗源辩体》理论根源的全盘考索,其考察得出历代诗论对《诗源辩体》的影响大致有四个方面:对南朝诗学的接受;对朱熹《诗集传》的接受;受《沧浪诗话》的影响;对明代诗学论争的融通。论文还关注到与许学夷处同时代而非主流的诗论家对许学夷的影响,不可谓不全面。此外,汪泓另一篇论文,虽其重点在于论述《诗源辩体》产生的创作和批评背景,[8]但就其研究结果来看,几乎是对许学夷诗学理论渊源的简要提炼和分析,因此将之归为一类,不再赘述。
许伯清诗学思想所受历代影响的程度,与其在著作中征引前人诗论的多寡和态度休戚相关。据汪泓统计,许氏在《辩体》中引胡应麟语近九十则,居所引之首;征引或批评王世贞语达六十条;单是引用严羽《沧浪诗话》就共有三十三则,而遑论对其诗学的大量阐发与补正。故汪泓总结许伯清诗歌理论根源时认为,其中最核心最直接的影响还应当是来自于《沧浪诗话》《艺苑卮言》和《诗薮》。[7]
(二)许学夷《诗源辩体》诗学思想的内容和成就
恽应翼言《辩体》“其书虽论述古人,而源流、正变、消长、盛衰,阐泄祥明,褒者得其髓,贬者砭其骨,宏博精诣,集诗学之大成”,[1]433该评论可以说高度概括了许学夷诗学思想的全部内容及其成就。其中“源流、正变”既是其诗史观,又包含了他的诗体观;“宏博精诣”既归纳了他对历代诗歌审美标准的兼容并包,又总结了他识高见广的诗歌批评思想,因而称《诗源辨体》“集诗学之大成”诚为不过。
1.诗歌辩体观
许氏将古今诗歌的源流、正变概述为:“统而论之,以三百篇为源,汉、魏、六朝、唐人为流,至元和而其派各出。析而论之:古诗以汉魏为正,太康、元嘉、永明为变,至梁陈而古诗尽亡;律诗以初、盛唐为正,大历、元和、开成为变,至唐末而律诗尽敝。”[1]1“寻源流”和“考正变”正是《诗源辩体》一书题旨,因此受到研究者的重点条析。如汪泓[9]将许氏的诗史观与同属明代复古派的胡应麟“格以代降”相较,肯定了许氏主张的会通与适变相结合的“通变”诗史观。方锡球[10]则把许氏这种“正变兼得”的成就追究为他对诗歌发展的自律和他律的整体把握,即许氏发现了对文学规范产生作用的内外动因。
许学夷既然认识到了诗体的流变,又对三百篇、汉魏古诗、盛唐律诗推崇至极,他在《辩体》中就会有意识地向后世学者强调辨别诗歌体制的重要性。目前对许学夷“体制为先”观念的研究也表现出一定的深度。方锡球[10]认为许学夷的诗歌本体论同时包含“情兴”与“诗体”两重本体,也即对“体制为先”的观点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汪泓对此提出质疑,并提出了“体制为先”是许学夷论诗的最基本的观念的论断。[11]其论文对“体制为先”的源流作了较为详细的爬梳,又具体分析了许氏所论“体制为先”的内涵,其立论深刻,必然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影响。如任竞泽在其论文中就基本沿袭了这一观点,但任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关注到许氏的“诗先定其正变,而后论其深浅”的观念较“先体制而后工拙”的传统命题更具有文体理论革新意义,[12]这种判断无疑进一步提升了《诗源辩体》整个理论体系的价值和意义。
2.诗歌审美观
明代格调派注重以体格声调论诗,同时也在不断寻求新的审美标准。至晚明许学夷,其论诗所持的审美尺度也显示出了融汇各家之长的水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汪泓、方锡球对许氏唐诗审美观的研究成果为代表。汪泓[9]在论及《诗源辩体》兼容并包的审美标准时,重点阐述了许氏的“兴趣”“诗而入神”等深受严羽影响的唐诗审美理论。方锡球补充并深入探究了汪文提及的“入神”说,其以“文化整合”为理论依据,认为许学夷对历代审美文化的融合,最终是为了“建构他的以‘入神’为标志的诗歌终极理想形态”,[13]这样的论断不仅与许学夷的儒家“中和”观相符合,同时也与明末诗学思想处于融合期的历史状况不相违背。
囿于许学夷复古派的诗论家身份及其“标举盛唐”的诗学思想,学界对许氏诗歌审美观的探讨便主要是在他唐诗观的基础上展开的。
3.诗歌批评思想
许伯清对历代诗论家的批评多有散见于《辩体》全书,但主要集中在第三十五卷。与前人相比,许学夷的批评观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从而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如汪泓认为许氏有着自觉的批评意识,主要表现于他要求论诗者应具“中正之识”“识理势之自然”,以及具备宏观的批评视角。[9]方锡球专门论述了许氏的元批评,认为其对历代诗学思想评判的核心理念是“诗道”,并总体表现出“通方广恕,好远兼爱”的批评取向。[14]陈广宏对《辩体》卷三十五的“言诗”体系进行了条分缕析,阐述了许氏“言诗”传统的范围与知识谱系。[15]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成果皆以突出许氏论诗的客观性为题旨。
以上对许学夷诗学思想研究的综述,皆取目前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另有几篇论文,或因无法取得,如谢明阳硕士论文《许学夷〈诗源辩体〉研究》、汪群红(汪泓)的博士论文《许学夷〈诗源辩体〉研究》等,暂付阙如;或因内容缺乏创见,不出以上之右,故不论及。
三、对许学夷《诗源辨体》中历代诗观的研究
《诗源辩体》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前三十三卷及后集纂要两卷论历代诗歌诗人。《诗源辩体》卷十一:“……盖三百篇、汉、魏、盛唐,各极其至,即穷予之力而阐扬之,有弗能尽;梁陈以后,体实相因,而格日益卑,予何所致其辩乎?”[1]137许氏对历代诗歌格调高下的评价直接影响其论述的详略。有鉴于此,为了准确把握许学夷的诗学成就,研究者也大多是从许学夷的汉魏、盛唐诗学观,或是陶渊明、李杜诗评进行研究的,少部分则关注许学夷的宋诗观、明诗观等。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分的研究成果已达半数之多,其中仅对许学夷唐诗接受的研究就有15 篇左右。
(一)许学夷《诗源辩体》中的汉魏六朝诗学观
《辩体》以两卷篇幅论汉魏之诗,所持观点依旧是复古派主张的“古诗法汉魏”,但许氏在这一问题上显然也有超越前人的地方。陈斌通过分析许学夷对胡应麟等人尊汉贬魏诗史价值观的批评,认为许氏在把握汉魏诗歌嬗变的问题上比起前人而言表现得更为客观中性。[16]有学者主要还以许学夷的曹植批评为研究对象,试图从点至面深入揭示许氏的汉魏诗观。如杨贵环通过分析许氏对曹植诗歌体制等的具体批评,得出许氏在正变之辩方面有异于前人的创见。[17]
在明代,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以杨慎为代表的六朝派则以六朝为“诗之高者”,在许学夷看来,这些都是昧于正变者。陈斌的另一篇论文较为清楚地阐述了许氏的六朝诗观,认为许学夷通过梳理汉魏六朝诗歌的源流正变,把握住了汉魏六朝五言由古入律的大方向,“明确了汉魏至六朝的‘正变’‘渐变’性质”。[18]为了说明许学夷对诗史的清晰认知,作者还详细论述了他对陶渊明的批评。事实上,以复古派正变观审视陶诗,其理应归为变体诗,但许学夷却对陶诗评价甚高,这无疑成为评判许氏诗学思想超越明代诸家的最好论据。因此,当前学者对许学夷六朝诗观的研究,也多是在把握其对陶渊明评价的基础上展开的,如谢明阳《〈诗源辩体〉论陶诗》[19]一文,周至地论述了许学夷的陶诗学,论文不仅发现许、陶二人在人格志趣上有极为相似之处,同时能谨循《诗源辩体》的论诗体系,依照许氏对陶诗的鉴赏观、诗史观、辩体观、创作观等展开全面完整的论述。该文是迄今研究许学夷陶诗观中体系较为完备、阐述较为详尽的论作。
以许学夷汉魏诗观及其六朝诗观为焦点的相关探讨已然分别取得一定成果,但仅有少数学者能对许氏汉魏六朝诗观进行整体性观照,其余论说则难免失之偏颇。
(二)许学夷《诗源辩体》中的唐诗观
《诗源辩体》以二十一卷篇幅论唐代诗歌,这足以可证许学夷“标举盛唐”的诗学眼光。作为明复古派的后继者,许学夷的唐诗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诗论个性,也是他诗史意识的典型表现。在这一部分的探讨中,方锡球先生的成果较为丰硕,其著作也几乎是以许学夷的唐诗观作为重点研究对象,阐释可谓透彻。如他分析许氏的初唐诗观,论述了许氏对初唐诗歌审美特征的揭示;[20]144分析许学夷对唐诗发展方向问题的独到见解,即他以“兴趣”论盛唐诸公,而以“意兴”论杜甫之诗。[20]175在另一章中,方锡球先生还专门论述了许学夷的李杜诗观,既分析了李杜诗歌各自之“变”的深层内涵,又区分出李杜高于盛唐诸公的根本原因,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许学夷唐代诗歌的审美标准。查清华[21]对许氏的唐诗观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许学夷主要是在辩体的基础上揭开唐诗发展的因革关系。基于此,当许学夷在论唐诗正变观时,能“就时论诗,以为代各有诗”,逐一突破了“唐无五言古”及前人对元和、晚唐诗人的苛刻评价,而一反七子派伸正绌变的态度。与此观点声气相通的是台湾学者陈英杰在论文[22]中所持的看法,他在分析许学夷杜诗学的基础上,也认为许氏对复古派诗学传统有革新之处。
总体而言,在许学夷唐诗观的研究中,关注许学夷杜诗批评的成果较多,且能从唐诗审美观、唐诗辩体观、唐诗批评思想等多角度对许氏的唐诗学进行梳理论证,可见相关探讨已趋于成熟。
(三)许学夷《诗源辩体》中的宋、明诗观
《辩体》以后集纂要两卷论宋、元、明诗。与汉魏、盛唐相较,宋及以后的诗歌尽管“未可以世次定盛衰”,不过是各随唐以前诗歌质性而仿制罢了,但主张“通方广恕,好远兼爱”的许学夷仍能从客观立场上对其作出扼要肯綮的评价。由于对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较少,且目前只见对许学夷宋、明诗观的研究,故归一处而论之。
许学夷对宋诗的评价,又是一次站在复古派和公安派之间的理论调和。复古派倡导“诗必盛唐”,于宋诗的价值自然不能认识;公安派则反过来申宋贬唐,二者由此各执一端,留给了许学夷“中和”诗学观再次得以发挥的空间。方锡球认为许学夷对宋诗认识的成就就在于他发现宋诗的“‘美处’即‘恶处’”,即他认为正是“变”才让宋诗另辟出异于唐诗的天地,而宋诗的这种“变”来源于宋人“以才学为诗”的特质,由此走出了以唐诗规范衡量宋诗的桎梏。同时许学夷给予公安派的回应是,宋人并非仅凭才力就能写出佳作,而要“以识为主,以才力辅之”。尽管方锡球最后对许学夷宋诗观的局限性提出了批判,但对其“颇具理论家客观冷静的理性素养”[23]进行了肯定。
汪泓则较为详尽地论述了许学夷的明诗观。他总结了许学夷评论明诗的几项原则,一是选择诗集时,要重视全集和作者的自选集;二是要持“中正之识”;三是要区别学古和拟古。在选择品评对象时,则强调重视转变诗风的人物。在批评明诗的成就方面,汪泓认为许学夷也有着客观的评价,因而主张他的批评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和评价明代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4]
四、对许学夷《诗源辩体》在晚明及以后的接受的研究
以“历四十年,十二易稿”的心血和功力写就的《诗源辩体》,在晚明及清代的接受情况却不容乐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有谢明阳和汪泓。谢明阳在其论文中深入细密地考证了《辩体》在晚明不受重视的各方原因。通过分析时人李维桢、邹迪光和夏树芳所撰的《诗源辩体序》,认为前二人所作之序皆与许学夷著书之意不合,故许氏宁愿放弃二人作序可能带来的宣传效果,也未采纳;而后者由于文坛地位不及前二者,尽管对《诗源辩体》作出了正确评价,但也不能为《诗源辩体》的传播起到明显的作用。故作者总结《辩体》之所以未能见重于晚明的原因有四,一是定本梓行太迟;二是许学夷在当时的声名未显;三是许学夷负气多傲的性格使然;四是《辩体》未能迎合晚明诗学发展的趋势。[3]汪泓则重点考证了《辩体》在清代的接受情况及其原因。如其所述,由于“诗选”的散佚,导致《辩体》的不完整降低了其影响力;许学夷在《辩体》中所引用李维桢、邹迪光等人书目皆属于清代禁书,这影响了《辩体》在清中后期的流传;而许氏的诗人地位未能树立,也对《辩体》的传播产生了负面影响。[25]
统而论之,许学夷及《诗源辩体》之所以未能受后世学者看重,与许氏财力有限、名望不足、个性多傲及其诗学思想在明清时期皆不合时宜等内外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
以上对截止2018年底有关《诗源辩体》的研究进行了大致的述评,但由于部分论文未能亲见,因此在论述上难免不够全面。就目前而言,对许学夷及《诗源辩体》的研究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仍有可探讨的空间。首先,尽管许学夷诗学思想主要受到南宋严羽、明代诸家的影响,但学者在对许学夷诗学思想价值进行挖掘时,多少忽略了许氏对宋以前诗论家的批评与接受,其“集诗学之大成”的历史地位在研究成果中是片面和局限的。其次,缺乏对许学夷汉魏六朝诗学观的整体性观照。《诗源辩体》卷一:“古诗以汉魏为正,太康、元嘉、永明为变,至梁陈而古诗尽亡。”[1]1可见在许学夷看来,汉魏六朝诗歌已自成阶段性的体系,但研究者多关注其汉魏诗观,具体论述时亦只是详论汉魏、略述六朝,这就不能更好地反映许学夷通变的诗史观。最后,至今关于《诗源辩体》的研究著作只有方锡球所著的《许学夷诗学思想研究》,该书尽管对许学夷的生平、诗学思想、唐代诗学观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但因其基本是以论文集的形式呈现,因此无论是从著作的数量和体系上看,都是不够完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