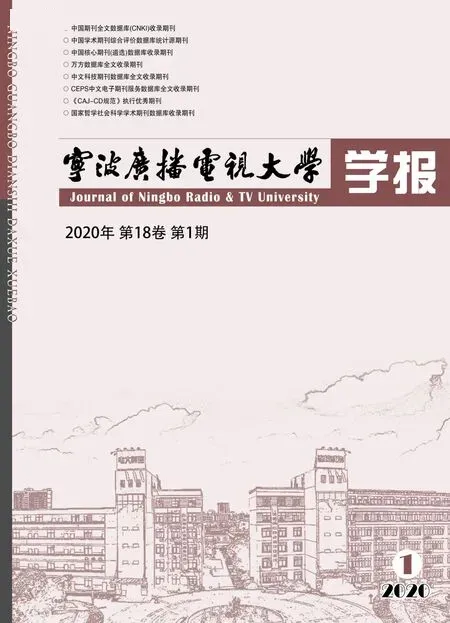CISG期前违约制度“减损原则”探究
刘凯全
(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上海 201600)
一、问题的提出
期前违约(anticipatory breach)又称预期违约,起源于英国1853年霍彻斯特诉德·拉·图尔案(Hochster v.De la Tour),①后被美国统一商法典(UCC)继受改良,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各国合同法的重要内容。CISG 借鉴了英美法系的期前违约制度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
CISG根据程度不同分别在Article71和Article72规定了两种期前违约,分别为“预期非根本违约”与“预期根本违约”。“预期非根本违约”并不导致合同无效,只是给了被违约方中止自己的履行的权利,该权利仅持续到履行期到来(之后被违约方只能寻求其他救济),同时被违约方有即时通知相对方,让其提供担保的义务,担保的种类和形式并无特别规定。[1]320-323“预期根本违约”给予了被违约方更多的救济,但同时其构成条件比“预期非根本违约”更为严苛。要求相对人的不履行具有“高度可能性”,其违约是根本违约,将导致合同消灭,同时被违约方的通知义务被降低,特殊情况下可以无需通知相对人提供担保而直接主张相对人“预期根本违约”。[1]324-325
CISG 在Article77 规定了“减损原则”,该原则要求遭受损害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措施减少损害,而如果受损害方没有采取如此措施,那么违约方可以请求减少本可以被避免的损害的赔偿。[1]356
然而在期前违约情况下,债权人是否有减损的义务,实践中却存在争议,并无统一观点,造成法律适用的困难。CISG 中的预期违约制度基本继受自英美法系,因此英美法系的判例与学说研究应有借鉴意义。因此为解决这一难题,本文试做粗浅分析,以求抛砖引玉。
二、期前违约的理论基础
期前违约早已被各国民法所采纳,即便是传统的并没有期前违约制度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亦通过类似的手段承认期前债权人的利益保护[2]而达到类似的效果。诚如坎贝尔大法官(Lord Campbell)所言:“如果一个买方坚称‘我到期也不会履行合同的’,那么卖方还需要履行或者是提议履行吗?假设按照合同原告需要送一艘船到港口装运货物,如果他已经知道港口不会有货物,难道他还必须去一趟港口然后空手而归吗?如果这是法的话,那这法将毫无意义。”②但是期前违约对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却并非没有疑问。期前违约制度之核心就在于“违约”的事实出现在合同履行期之前。然而问题在于,履行期既未届至,债务人本就可以不履行其债务,债务人还没有履行合同的义务,而既然“违约”之时债务人还未有履行合同的义务,又何来违反合同义务而构成“违约”一说呢?对于这一逻辑上的悖论诚如塞缪尔·斯图嘉(Samuel Stoljar)所言:“期前违约仅有‘违约’之名而无违约之实(it can never consist of an actual nonperformance)。”亦如在前述的Hochster v.De La Tour 案中,被告辩称的那样“期前违约不是违约,只是可能违约的‘证据’,因此是不能诉的”。虽然法院最终判决被告败诉,可是该判决并非没有争议。例如随后在Frost v.Knight③案中低一级的法院事实上拒绝遵循先例(Hochster v.De La Tour),该法院认为合同不能在履行期前被打破,这只是“可能的违约”(possible breach)。
债权人的期前利益需要得到保护,但是如何在法学理论上构建期前违约的理论基础,使得期前违约有其理论依据亦有其重要意义。以下笔者将列举两种代表学说并逐一检讨之。
(一)要约承诺说(offer-and-acceptance approach)
此说认为,期前违约的实质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以“要约——承诺”的方式新达成了一个合同。债务人明示(明确表示将不会履行)或者默示(以自己的行为表示将不会履行)发出要约,要约的内容为希望合意解除旧合同,并愿意给予债权人救济的权利,债权人若对其要约予以承诺即合同成立生效,旧合同消灭,债权人即时获得请求救济的权利,而债权人若不予承诺则原合同继续存在,债权人可以在履行期届满后请求一般的违约责任。
许多的判例采取了这种观点。在Bardley v.H Newsom Sons & Co④一案中,法官伦勃里(Lord Wrenbury)说:“毁约方发出要约,内容是解除合同,如果解除,你可以起诉我因我拒绝履行而产生的损害赔偿。另一方可能承诺,可能拒绝要约。如果承诺那么就达成一致,合同解除,但是有起诉对方损害赔偿的权利。”同样,在上述Hochster v.De La Tour 和Frost v.Knight 中终审的法院也都认为受害人可以选择维持合同关系。而 Johnstone v.Milling Co.⑤案中,法院更是明确认为在期前违约情况下双方同意消灭合同并订立新合同,新合同内容为前合同的消灭,和给予债权人损害赔偿的权利。[3]64-65尽管要约承诺说几已成为英美法系的通说,但是其并非无可指摘。要约承诺说的拟制地过于明显(striking artificiality)。
1.要约承诺说的“要约”并不能附条件
如前所述,期前违约将会让债权人处在一个可以选择的地位,他可以选择让合同继续,也可以选择让合同消灭,“要约承诺说”认为债权人通过承诺与否即可以达到让合同继续或消灭的效果。问题在于,要约与承诺成立合同需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要约人或承诺人无法单独决定合同的命运。然而很明显,在期前违约的情况下,债权人在此时所处的是一种优势的地位,他并不需要借助于债务人,就可以单独决定合同的命运。这在债务人的要约附上一定条件时尤为明显。
以一个案例加以说明:2019年11 月1 日甲与乙达成了一个汤臣一品房屋的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房屋价金为2 亿元,甲于2019年12 月31 日将房屋交付给乙,乙在12 月1 日突然反悔,不想再购买甲的房屋,但却相中了甲房间中的一幅名画想要买下,于是乙郑重明确声称自己将断然不会支付给甲购房费,但是若甲同意解除合同,乙将高价购买甲的画作为补偿,甲拒绝,其后将房屋卖给了丙并办理了登记手续,乙嗣后起诉要求甲履行房屋买卖合同。若以“要约承诺说”加以分析,乙的要约附上了条件,而甲断然拒绝了这个要约,由此新合同并未成立,乙并未构成期前违约。但很明显乙的行为构成了期前违约,因为他明确表示自己将不会履行,完全符合明示期前违约的情形,没有一个法院会让这样一个债务人受到如此的优待。同样,要约在受要约人作出承诺之前是可以撤销的,那么债务人关于期前违约的“要约”也一定可以撤销吗?CISG article72 条第2项的“if time allows”即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时间不允许,被违约人可以在不通知违约人的情况下便解除合同。[4]
2.要约承诺说的“要约”并不能撤销
甲与乙达成了建造一栋房屋的合同,合同约定由甲提供建造房屋所需的劳动力和建筑材料。乙严肃认真地声明他将不会支付价金,甲听闻后便赶忙寻找是否有其他人需要建造房屋,恰巧丙也想建造一栋房屋,于是甲与丙达成了建造房屋的合同。乙事后后悔,于是又要求甲为他建造房屋。理性的人站在甲的位置上,当乙严肃认真地声明他届期将不会履行合同义务时会做什么呢?很明显如果他听说丙在寻找一个建造者,那么他就很可能很快地采取行动,和丙签订了新合同,即便没有承诺乙的“要约”。那么乙可以撤销“要约”,让甲回到原来的合同中吗?即便以最优待“要约人”的方式处理,即通常情况下享有撤销权,但是一旦受约人基于此拒绝履行而实质地改变了他的地位,这种撤除权便不复存在,[5]473仍然与要约无形式拘束力在承诺前可以自由撤销的原则相违背。
3.要约承诺并未达成一致
事实上很多时候要约和承诺并未达成一致,从当事人角度而言,若是双方可以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债权人愿意解除合同,债务人愿意给予适当的补偿,债务人所给予的补偿被债权人欣然接受,如此皆大欢喜,又怎么会产生“讼争”?之所以产生讼争恰恰是因为双方对于是否解除合同,解除合同后的损害赔偿问题争执不下,无法达成合意。如此一来,既然被起诉到法院的案件都是没有达成合意的案件,法院又如何用要约承诺来解释它们呢?
4.小结
“要约承诺说”中的“要约”不能附条件,且该要约在承诺作出前亦未必能撤销,与要约无形式拘束力相违背,此外甚至很多时候要约承诺根本就没有达成一致。当然可以构建“特殊”要约规则以使其解决上述的矛盾,但是如果那样“要约承诺说”的人为性将更加明显。其危害在于将破坏一般的意思表示“要约——承诺”规则,造成体系上的“畸变”拆东墙补西墙,实在得不偿失。
(二)义务违反说
要约承诺说存在诸多不足已如上述,义务违反说试图通过证明即便履行期尚未届至,当事人间仍然存在某种“义务”,而正是对于该种义务的违反,导致期前违约法律效果的发生。
1.义务来源于信赖
有些学者对这种隐性义务提出质疑:“它怎样构成了一个对任何现实的法律权利的违反?”[3]64-65实施中的合同本来不给予合同实际内容的权利或利益,直到履行期到达,债权人才有要求履行的权利,因此在履行期到来之前他并不受有损害,因此没有损害赔偿的基础。救济必须基于权利(the legal remedy must be founded on some present legal right),无权利即无救济。“要约承诺说”试图通过“约定解除”的方式,构建消灭合同和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但需要检讨的是,合同订立后,履行期届满前,合同当事人真的没有任何的权利义务吗?如果有,其是否可以作为救济所基于的“权利”呢?
义务从何而来?在大陆法系国家被誉为法学史上的重大发现之一——缔约过失理论,通过对“信赖”的保护甚至已将当事人的义务延伸至合同订立之前,“从事契约缔结之人,是从契约外的消极义务范畴,进入了契约上的积极义务范畴。”[6]举轻以明重,合同订立之后当事人既已经离开消极范畴,进入积极范畴,彼此之间更应该存在某种义务,因为合同订立之后当事人理应比缔约之前对彼此的关系更加“信赖”。
2.义务的内容为“维持合同关系”
当然,严格上来说,履行义务不能被期前违约所违反,被违反的只可能是当下的义务。当下的合同义务并不仅限于当事人自觉地预见并予以同意的那些义务。[5]450除了明定的履行义务外,合同之间尚存在内容为“维持合同关系”的义务亦即“将要履行的义务”。“期前违约”这个词隐藏了期前违约的实质,明示的或暗示的拒绝履行违背了“将要履行的义务或承诺”(it only breaks a duty or promise to perform)如果要约人履行的承诺被受要约人接受,那么那个承诺将不再被违反或者毁约。因为一个合同一旦订立,就会有这样的结果:双方都被联系在一起,进入一个熟悉的交流,每一方都有默示的权利让这个合同继续下去,直到合同被最终完成。被承诺人有权利让合同继续下去直到履行期[7]355-369(即所谓的“合同维持”义务),那么债务人造成的损害就基于对更长的合同关系的拒绝。事实上,在 Hochster 案中坎贝尔大法官(Lord Campbell)就已经提及了相互之间的关系(a relation constituted between parties)“因为他们默示保证在此期间不会做任何有损合同关系的事”。可见期前违约损害的就是一种对双方都不会为有损合同履行行为的“信赖”,违反的是“合同维持”义务。
3.小结
“义务违反说”相较“要约承诺说”更为妥适,“合同维持”义务因信赖而生,损害因“合同维持”义务的违反而导致。通过确立“合同维持”的义务,提供期前违约的基础,避免了过度的拟制和对体系的破坏。
三、以“义务违反说”解释“减损规则”
期前违约可以减少被违约方甚至是违约方的损失,对提高经济效用有着显著的功效,然而恰恰是由于这一点,使得其在损害赔偿的计算上存在困扰。其中备受争议的一点就是被违约方是否需要承担“减损义务”,即“减损规则”(rule on mitigation of loss)是否有其适用的空间。运用“义务违反说”可以很好地统合期前违约背景下“减损原则”的适用。笔者以为,“减损规则”的实质就是“维持合同”义务的违反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
(一)判例的类型
损害赔偿的计算中关于债权人是否需要承担“减损义务”现有的判例大致存在三种判例。第一类认为债权人没有减损义务,第二类认为债权人对于减损拥有一定自由度,第三类认为债权人有减损义务。
1.一些判例认为债权人没有减损义务
罗珀诉约翰逊一案(Roper v.Johnson)⑥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该案中原告被告达成了一项分期供货的合同,被告将在5 月、6 月、7 月、8 月四个月分期向原告运送煤炭,但是被告在 5 月就表示自己将不会履行合同,在 6 月初买方开始对卖方的声明采取行动(寻找其他卖家)。在5 月至8月间,煤炭价格持续上涨。双方诉至法院,原告要求按照合同约定,以5 月、6 月、7 月、8 月的煤炭价格分别计算损失,而被告则声称原告在 6月即已采取行动,应以原告采取行动的时间计算损失。最终原告的诉请得到了支持,即认为原告没有减损义务。
2.一些判例认为被违约人有一定的自由度
维克诉本杰明案中⑦(Novick v Benjamin)法官认为,“合同消灭的期前违约案件中,违约的损害应当以履行期计算”,但何时采取措施应当给原告“少量的自由度”(some slightly latitude)。该案中减损原则(rule on mitigation of loss)没有适用,因为原告理性地没有在其他地方购买。
3.一些判例认为被违约人负有减损义务
哈兹斯诉德蓝土瓦和德拉瓜湾投资公司案(Hazis v Transvaal & Delagoa Bay Investment Co Ltd.)⑧中法院认为由于债权人没有采取减损原则而导致的损害,不能被主张。
(二)判例总结分析
期前违约背景下,被违约人有减损义务抑或无减损义务,各方观点不一。但运用“义务违反说”可以很好地统合“减损义务”的适用。义务违反说的背景下,损害的原因不再是当事人之间意思自治的结果,而是由于债务人对“合同维持”的违反,损害的发生需要与义务的违反存在因果关系。债权人的减损义务取决于个案判断,原因在于减损义务只是计算的方法。而其实质在于因果关系,即若损害的产生是由于债权人的“不作为”而非债务人的期前违约,则债权人负有减损义务,若损害的产生并非由于债权人的“不作为”而是由于债务人的期前违约,则债权人不具有减损义务。不能概括地认为债权人有或没有减损义务,即这并非是一个全有抑或全无的问题。以典型的两类合同:买卖合同与雇佣合同为例,减损义务对于各自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
1.买卖合同中的减损义务
以莱诉帕特森一案为例(Leigh v.Paterson)。⑨该案中原告和被告达成了关于油脂买卖的合同,约定被告在12 月时向买方交付动物油脂,但被告在11 月时明确表明他将不会履行合同。油脂的价格在缔约时仅为65 先令每英担,但在11 月涨到了75 先令每英担,而到12 月则涨到了81 先令每英担。法院支持了买方的诉请,理由在于给买方强加减损义务将会违背基本的合同规则。这意味着剥夺买方被合同赋予的利益(合同缔结时价格和起诉时的市场价的差额),更糟糕的是,部分利益将会转给了卖方,因为他可以以更高的价格转卖。从因果关系分析,买方的损失确是由卖方的期前违约造成的,理性的买方没有理由会在履行期前就进入市场寻找替代卖家,因为价格比合同成立时的价格更高。
2.雇佣合同中的减损义务
而雇佣合同则经常存在认为卖方负有减损义务的情况。假设2019年5 月1 日甲与乙签订雇佣合同,乙 2019年 10 月 1 日至 2021年 10 月 1 日需要每日为甲家中打扫卫生、处理内务,月薪3000元。甲于2019年9 月1 日反悔,向乙表示自己不再需要其打扫卫生。2019年6 月1 日,乙另寻一处类似工作,月薪3000 元,但乙无端拒绝了该工作。这种情况下应有减损原则适用的空间,乙应当尽快寻找工作,否则乙可以无端拒绝理性之人应当接受之工作,因乙无端拒绝造成的损害却由甲承担,在布雷斯诉卡尔德案中(Brace v.Calder)⑩法官有相似见解“他也不能要求比通常损害更多的损害,如果他被提供了一个相似的不可拒绝的工作”。这当然一个人在失去工作后,能否找到工作?多久能够找到工作?新的工作是否和旧工作条件一样?都存在疑问,因此并不意味着乙一定可以迅速找到工作,只是类似工作的可能性和可取性将成为损害赔偿的标尺(yard stick)。
(三)小结
“在买卖中,我们不需要减损规则,因为我们可以用市场价格计算损害赔偿。”[7]355-369而雇佣合同等劳务合同中,由于劳动的市场价格并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存在不确定因素,因此用以所谓的“减损义务”来限制债权人(通常是劳工)滥用期前违约救济的行为,而“减损义务”实质仍然在于“合同维持”义务的违反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对于“减损义务”难题的解决更加凸显出义务违反说的说明力。
四、结语
期前违约制度旨在保护履行期届至前债权人的利益,要约承诺说拟制债务人的要约与债权人的合意解除合同,提供损害赔偿请求权来给期前违约提供制度基础,但效果并不理想。义务违反说认为,期前违约的制度基础在于债务人违背了因信赖而生的当事人间的“合同维持义务”,相比之下义务违反说更具有说服力。应用义务违反说分析解释判例结果可以更好地解决期前违约债权人是否具有“减损义务”这一难题。期前违约的债权人是否负有“减损义务”需要个案判断,判断的基准在于“合同维持”的义务违反与损害发生的因果关系。
【注释】
①Hochster v de la Tour,[1843-60]All ER Rep 12.
②Cort v Ambergate,Nottingham and Boston and Eastern Junction Rly,(1851)17 QB 127.
③Frost v Knight,[1861-73]All ER Rep 221.
④[1919]AC 16(HL)at 52.
⑤Johnstone v.Milling Co.,L.R.11Q.B.Div.460.
⑥Roper v Johnson,(1873)LR 8 CP 167,28 LT 296.
⑦Novick v Benjamin 1972(2)SA 842(AD).
⑧Hazis v Transvaal & Delagoa Bay Investment Co Ltd.1939 AD 372.
⑨Leigh v.Paterson.(1818)8 Taunt,540.
⑩Brace v Calder and Others,[1895-99]All ER Rep 1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