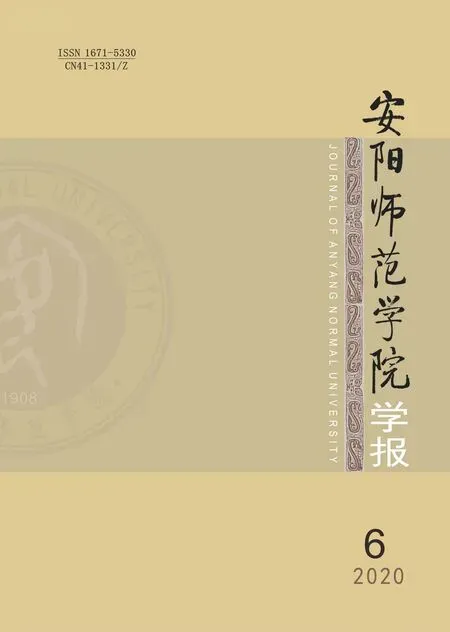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研究
王明前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下简称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开辟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被中共中央誉为“模范区”。学术界对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政策的研究已经取得诸多成果,特别是减租减息对边区土地关系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各社会阶层群众的角色及作用,均做了可贵的探索。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对减租减息政策本身的发展脉络和相关规律关注不足。首先,现有研究往往忽视对晋察冀边区建政前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与土地制度相关的地租和高利贷形态的背景分析,其对社会和经济效果的评价缺乏明确的相关对照。其次,现有研究对减租减息政策本身关注不足,流于一般叙述,缺乏必要的科学归纳,未能把握政策实践本身的发展脉络和相关规律。最后,由于缺乏对抗战前社会经济状况的背景分析,现有研究对减租减息社会效果的评价普遍偏离历史环境自身的有限规定,从而得出与历史文本差异较大的结论。
笔者在分析抗战前减租减息政策的基础上,首先确定减租减息政策的时代必要性,进而分析其具体执行过程中正规化和科学性有机统一的发展脉络,最后对减租减息政策的社会经济效果做针对性总结,以期增加学术界对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的学术认知。
一、减租减息前晋察冀边区农村封建地租高利贷剥削状况
抗战前,晋察冀边区范围内的华北地区,封建地租和高利贷剥削沉重而苛刻。以晋察冀边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冀中区为例,冀中区尽管商品经济较发达,但是也没有因此发展出先进的农村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相反呈现出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特征。冀中“平津附近,封建势力大,土地集中,有种有1000顷土地的大地主,种有几百顷者很多。这些大地主同时又经商,又做官,年丰下乡,年荒入京。而晋县(今晋州市)到高阳过去为产棉区,系日本资本家之原料市场,中国华北四大银行组织有棉业合作社,鼓励产棉”。冀中现代工业系买办性质的纺织业,“棉纱皆系购自日方,没有独立工业,所以被日本资本家压迫得很厉害”。总之,“冀中是在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官僚三种势力统治之下,封建势力最强大”[1](P100)。
冀中各地封建地租剥削形态呈现地区差异。平汉线一带,“地主较少,富农经济比较发展,土地多用富农方式经营,雇工有达数十名者”。租佃关系以“客家地”为主要形式,剥削较重,一般钱租多于物租。津浦线一带,租佃关系以“二房子”式为最普遍,剥削尤重。商业方面,平汉线一带“与城市关系密切,家庭手工业、副业比较发达,亦有少数工业。普遍利润率最高者不过1分多”。津浦路一带“工商业发展均差,但利润率较高,平均在三分左右”[1](P711)。大清河以北,“由于大清、永定二河每年泛滥,当地地主豪商乘人之危,贱价收买土地,故土地非常集中,有二十万亩以上的大地主”。大河以南,“耕种集约,农业中资本主义有一些发展”,但“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盛行,农村破产相当严重”。[2](P158-159)具体而言,地租分为死租(定额租)和活租两种。死租“租额多是十分之六至十分之八”。活租分为两类:其一,“地主除了土地外不投任何资本”,有“大种地”“对半客家”“对分收”“分种地”等不同名称,租额50%-80%不等。其二,“地主除了土地外还有供给肥料、牲口、种子、马力、工具等”,有“小种地”“带把”“客家”“倒插股”“伙种地”“锅火地”等名称。如“带把”,即“有的地主出一个小孩或雇工帮助雇工生产,佃主还要从佃户所得中分去一半”。地主大致分为一般地主和经营地主两类,区别在于经营地主“除去封建剥削的地租外尚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投资部分”。由于“水车肥料投资很多,贫苦农民种不起,佃户就多系中农或中农以上的成分”,因此富农佃户就呈现两种类型:“一种是没有自耕地,租种地主的地而雇长工经营的资本主义的富农。另一种是富裕中农或富农除自耕地外,还租地主一部分地也是雇长工来经营的”。[3](P132-133)
冀热察区封建地租和高利贷剥削也呈现地区差异。冀东各地土地占有极不平衡,长城两侧山地村庄,土地集中,地主、富农占有一半左右土地。热河土地占有更加集中,长城内山边即平原地区,土地占有比较分散,宝坻、玉田地区,土地很集中。封建地租的主要形式是粮租,其次是钱租和粮租的另一形式半种地。粮租租额各地不一,山坡地大约占20%,平原地高至66%,一般多在40%-50%。在白河区有层层转租现象,经五次之多东家的层层剥削,某些地区佃户实际上有永佃权,但白河地区佃农流动性大。半种地多为平坦土地,“牛粮籽种由佃户出,出粪者要柴草,一般是地佃各分五成,花销一般归佃户”。钱租,多分布在口里,都是上打租,租率比粮租轻些。额外剥削,如利息谷,一是因初租土地向地主借粮而交利息谷,另外是因借钱交押租钱,而出利息谷者,性质上属于借贷关系。再如伪满境内的“申报租”,即“地主荒山上佃农开荒,当年要出租,地主要将开荒地向政府报告,从这里边转移负担与佃农”。高利贷剥削,主要是钱利和借粮两种,前者“一般为年利三分或月利二分。地主、富农借钱只要二分或二分半,一般的有抵押品、契约、保人,到期不纳利,利坐利,到期不纳本没收抵押品。此外还有还粮利者,有的借一百元还一石谷,有年还6斗玉米者”。后者,“一般是春借秋还,一斗还半斗,利率五分。吃坐者是借粮还钱,借时便‘现加利’,秋后粮价贱时还钱,有2斗还1斗者”。[2](P750-753)
平北租佃形式分为定租和活租两种。活租又具体分为四种形式:其一为伙种地,“地主只出土地,另外什么都不供给,而秋后按成分粮,分粮的成数多少也不一样”。其二是“招佃户”,又称大伴种、里伴种,即“地主除供给土地外,还供给佃户牛力、粮食、籽种、肥料的一部或全部。粮食有的按五分行息,有的歇息,秋收后从大堆中扣出籽种秸草归地主,然后两家分粮”,或对半分,或倒四六分。其三为“里插股、倒插股”,即“地主把他自己家的劳动力给佃户再入上个股份,分粮多分股,这实际上也是活租伴种地的变异”。其四为“两头用”,即“年景好时算当佃户,年景坏时算当长工”。平北的地租形态也分为货币(钱租)、实物租(粮租)、劳役地租三种形态,但“抗战以来由于物价昂贵,伪币跌价,钱租减少,粮租增多”,因此“以劳力顶地租的剥削形式现在很少了”。总之,平北定租“一般全在百分之四十以上,最高的有占产量全部还倒贴本的”。活租“全是百分之四十、五十的,倒三七地主占百分之七十”。此外,正租之外的额外剥削也十分苛重。如“押地钱”,除了每年要交租外,在种之前先押上一部分钱,不种地时再给佃户退回;“跑山租”即“所有权转移了,可是原主还要收租”。此外还有“上打租”“二当家”“带差租”等等,名目繁多。高利贷剥削也十分残酷,如“大加一”,即借一元每月利息一角;“加五利”即借一斗还斗半;“斗头米”即借一斗米还一斗半或一斗三;“斗米三谷”即借一斗米秋天还三斗谷;“作价米”即粮贵时往出借米作成钱,秋后粮贱还钱折成粮。“驴打滚”“利上利”即利钱作成本,本还行利来回滚;“死三分”即年利三分;“活三分”即月利三分;“现扣利”“七顶十”“八顶十”即借钱先从本钱里扣下利,用七元就算十元,或放八元就算十元;“放钱吃租”即“放出钱债要收粮利”。[3](P63-68)
晋察冀边区抗战前的封建剥削也十分严重,正租之外如杂租,“系指在地租额之外另要些各种物品,如肉类、酒类等”。再如“小租”,也是佃户于正租额以外对庄头的纳款。“送工”属于无偿劳动,佃户于每年之内,给地主无代价地服务几天。“太粮”则是高利贷的一种,即“佃户约定为地主佃耕时向地主预借米粮若干,到次年秋时加五或加倍偿还”[4](P89)。此外,在华北还存在中间人剥削,如“二东家”,即承种地主土地,然后将土地分租给农民,从中渔利。“当头制”即地主豪绅利用农民惧怕衙门的心理,给农民代交赋税,代交时即进行欺骗,冒称增加附加,借以剥削。“假甲制”即军阀时代,农民惧怕出田赋,立定契约,将自己土地归属地主富农,而自己出租,此办法等于地主富农没收了贫农的土地。“钱粮地”即“高利贷者贷款给农民往往以土地作抵押,农民贫困,无力按期还息,便变本生息,几度轮转,农民土地为高利贷者所有”。[2](P141-142)
总之,以封建地租和高利贷作为主要剥削收入来源的封建地主经济仍然居于主体地位。因此,晋察冀边区农村社会存在着强烈的减租减息要求,边区党和政府执行减租减息政策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减租减息政策的正规化与科学化
(一)减租减息政策的正规化
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政策作为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首先明确二五减租原则。1940年2月1日修正公布的边区减租减息条例规定, “出租人之土地收入,不论租、佃、伴种,一律照原租额减收百分之二十五”“地租不得超过耕地之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二五减租后,地租仍超过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应减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具体租佃形式为“出租人对于佃户耕作上必需之农具、种籽、肥料、牲畜完全供给,佃户只出劳力者,二五减租后地主所得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二分之一,超过者应减为二分之一”。另规定:“出租人不得预收地租,并不得收取押租”“耕地之土地税由承租人代付者,应于地租内扣除之。耕地之合理摊派,以村合理负担行之”。其次,条例充分保障佃权即耕作生产权利,规定:“出租人未得租户、佃户、伴种户之同意,不得将耕地收回转租转佃转伴种他人”,应“依定期限租用耕地之契约与依不定期限租用耕地之契约,如承租人继续耕作,出租人均不得解除契约”,如果“出租人于能维持生活之前提下,于不能保持耕地原有性质及效能前提下,于不能不增加雇工耕作前提下,均不得以收回耕地自耕权为借口而解除契约”[3](P20-21)。这一条例的颁布标志着边区减租减息政策初步实现正规化。
1942年3月20日,边区政府根据1940年2月条例执行情况做出诸多修正。如伴种地正产物之分配,“地主所得以耕地正产物及柴草收获总额十分之六为最高额”;地租交付可“经双方同意,得将现金地租一部或全部改为实物地租”;出租人供给种籽粮食,“约定有利息者,每月增收不得超过原借点千分之八点四”。土地租佃契约之缔结,“出租人如因契约期满或因其他原因收回土地者,必须自耕三年始允任意出租于他人。如在三年以内出租者,原承租人有依原定契约之租额租用之优先权”。但是“租佃户累世经营之土地,非租佃户自愿放弃使用权者,地主不得夺佃”[1](P31-32)。条例施行细则还规定:减租方面,出租人对耕地施行改良,出租人于契约终止收回耕种时,“须先清付出租人之特别改良费,但以其未失效能部分之价值为限”。减息方面,“清理多年旧债,应按年利率一分一本一满利计算清价,其已付利息超过原本者,停利还本,其已付利息超过原本二倍者,本利皆停付”“质地揭借钱,欠息在二年以上者,准按减租减息条例减息后债权人一年应得利息之二倍,分期清偿另换新约;债权人不得因欠息关系处置所质土地”。[3](P34-35)新条例的公布,标志着减租减息政策进一步正规化。
(二)减租减息政策的逐渐科学化
在正规化的基础上,减租减息政策逐渐科学化,主要表现在边区领导层对各种土地关系的科学分析上。
1942年11月7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针对典地回赎问题规定,典地是“地无租钱无息,活买活卖的土地买卖关系”,当地是“指地押契押钱的银钱借贷关系”,两者性质不同,因此“典当地回赎问题,实际只是典地回赎问题,不能牵涉当地,当地应按借贷关系处理”。处理典地回赎“必须坚持保障地主土地所有权,保障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原则”。因此,“出典人赎回之土地,不能自耕,再行出租、出佃、出典、出卖者,土地使用人有优先承租承佃承典承买权”“出典人回赎之土地,不能出租出佃致承典人失去土地使用权,并因粮价高涨,收回典价亦无以为生者,出典人于原典价之处可予承典人增补一部”“出典人回赎之土地不许自耕者,出典人应将赎回之土地,租或佃与原承典人耕种,另订租佃契约”。[3](P170-171)
1942年12月4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指示处理典地回赎问题,要求出典人于典约期满回赎时,或“出典人生活无困难,赎回土地并非自耕,租佃户得依原租佃条件,继续租佃至契约期满”,或“出典人租佃户生活皆无问题,但出典人赎回土地确系自耕者,则出典人得依典约规定赎回土地”;或“出典人租佃户同样困难,出典人得依典约规定赎回土地,但租佃户得根据租佃契约的规定,向原承典人要求赔偿因出典人赎回土地所遭受之损失”。关于购买租佃优先权,规定“将所典之土地出租出佃之承典人,无购买租佃该项土地的优先权,该优先权属于租佃户”。[3](P172)
为进一步保障佃权,1943年2月4日公布的租佃债息条例规定,“土地之租佃,经一律缔结书面契约,契约期满,出租出佃人得收回其土地。但在抗战期间,出租出佃人收回土地致承租承典人无法生活者,应减收一部或暂时不收,并另定新约”。为奖励生产,“承租承佃人得自由在租佃之土地上,施行土地特别改良,出租出佃人不得因土地改良而要求加租”。对典地与抵押权问题,本着保障佃权的原则规定:“出租出佃人出典耕地时,出租承佃人有依同等条件承典之优先权”“出典人将赎回之典地出租出典时,原土地使用人有依同等条件承租承佃之优先权”“在租佃关系存续中,出租出佃人将其土地抵押于人,因清偿债务而土地所有权转移者,承租承佃人仍得就其土地继续租佃至契约期满”。[3](P37-41)
边区政府还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确定具体政策。1943年10月18日,晋察冀分局指示减租工作,总结了各地区减租工作的地区类型。其一是彻底执行减租政策的地区,“实行了二五减租,排除了一切超经济剥削,充分发动了广大基本群众”,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其二是基本执行减租减息的地区,“虽然实行了二五减租,排除了超经济剥削,但在个别落后村庄许多是明减暗不减及其他减得不彻底的现象仍然存在,基本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其三是初步执行减租减息的地区,特别是“只开始执行或停滞在开始执行的阶段,基本群众也处在初步发动的时期”。其四是尚未实行减租减息的地区。其五是曾经实行减租减息,但因环境变化,群众利益得而复失。由于边区大部地区属于第二种情况,因此为执行中央十月一日指示,坚决贯彻减租减息,分局要求北岳区减租的重点“应置于大部基本上业已执行但尚未彻底执行的地区,要求其由基本上执行减租变为彻底执行减租”,特别是“纠正明减暗不减及其他减得还不彻底的现象,应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过去已彻底减租的地区,主要是巩固群众既得利益。在过去曾减过租、但地区变质的敌区,“应即逐步进行恢复基本群众的既得利益”。在新开辟地区,“应即有计划地逐步实行减租,首先做到初步减租”,至少应准备实行减租的条件。平北等初步减租地区,应进一步深入执行减租,冀中区“应把对敌斗争放到最主要的位置,一切服从对敌斗争的要求”。在过去已减租、至今仍为游击区的地区,“继续深入巩固群众的既得利益”。在已变质的地区,“应在条件具备时恢复之”。冀东区,在准备创造成为根据地或游击区者,“必须认真地实行减租,不能因这些地区民族矛盾比较尖锐,统一战线具备一切不同条件而不去发动群众”。在冀东的伪满地区、冀中的新开辟区,以及群众既得利益得而复失的地区,减租“应多采取调节协商的统一战线的方式”。[5](P871-874)
1943年10月28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指示减租工作,总的重点放在限制高额地租与废除超经济剥削方面。具体而言,北岳区“放在基本实行了的地区,逐村逐户地检查,求得彻底实行”。冀中区“重点放在游击根据地,保障或恢复减租的既得利益,基本实行的求得彻底实行”。冀热边“重点放在山地的中心区与已恢复了的平原基本地区”,平北继续推行与深入贯彻。在减租具体政策的掌握上,指示首先要求合理确定减租的租额,“凡未实行二五减租或明减暗不减,减的不彻底者,须一律按二五减租”。工作开辟较晚的游击区,“减租成数可由十分之一至二五,最高租额可略高于三七五”。钱租“因粮价高涨,过低者可适当提高,改实物半实物租,如改实物应将减租后租额之一半按订约时粮价折粮,其最高额不得超过法定最高租额之半数”。为防止地主逃避税收,指示要求“地主不要地租令佃户白种代拿统累税或对敌负担者,应视同出典,双方须订契约并定年限”。为促进生产,指示要求:“应提倡地主与佃户实行订租制与订较长期契约”。本着“不算旧账,互相让步”的精神,妥善解决清理欠租与逃租的问题,“凡应减租未减或减后仍超过最高额及本会民地字第一号布告中规定停交日之欠租,须一律取消,地主不得再要,并给佃户以执据”,且“因未减租佃户已交应减之租,地主应依法退还”。原则上游击地区,“佃户替地主已交的统累税,与减租后仍超过法定最高租额的超过部分,或因灾应减免未减免多交之租一般均不退。佃户生活特别穷苦者可酌退一部或全部。因生产量下降超过法定最高租额的超过部分应一律不退”。为保障佃权,维护农民的生产权利,鼓励永佃权契约,指示要求:“凡取得永佃权之土地,地主不得巧借名目违法收地”。其他契约也尽力保障佃权,“在抗战期间,契约期满地主如依约收地,应依如下原则处理:地主生活优于佃户,不收地仍能自给,而佃户因收地无法生活者,应暂时不收”,如果“地主与佃户生活均能自给,佃户不因收地而无法生活者,得允许地主收回一部或全部,如双方生活均困难,得允许地主收回一部或全部”,或者“佃户生活优于地主者,得允许地主收回一部或全部”。关于典当地债息问题,指示要求典当地“应规定年限,未约定年限者,依三年后出典人始得回赎之习惯。出典人因赎地典地致承典人无法生活者,应改订租佃关系,将地租给承典人”,对那些“未依法减息之抵押地,应依法减息清理,债权人因未依法减息而取得抵押地所有权者,应依法纠正之”。为恢复农村借贷关系活跃金融,指示要求土地典当或借贷“用白银者,在白银禁止流通之地区得以边币按法定比值回赎典当地或还债付息,因边币跌价承典人或债权人损失过巨影响其生活者,得由出典人或债务人酌增一部边币或实物”。在白银与边币同时为流通货币地区,“其约定以白银回赎或还付债息者,仍应依其约定,无此约定者,得依上项之原则处理。伪钞流通地区亦得依上项原则处理”[3](P80-85)。
三、减租减息后边区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
减租减息斗争引起边区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体而言,封建地主阶级受到严重削弱,资本主义因素得到鼓励,中农小商品经济成为边区经济发展的主流,并为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根据北岳区党委1942年秋对6个分区28县88村的调查,减租减息后的农村社会阶级变化呈现出如下特点:在敌寇严重压榨的地区是各方面向贫农看齐;在我根据地及各种政策能够贯彻之游击区是两头向中间挤;“在无人区则经过敌人的无人政策,全体下降,阶级关系的变化最为剧烈。但在恢复之后,其变化又会逐渐与巩固区看齐”[6](P613)。而各劳动阶级向上变化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党的民主民生政策的执行,排除了土地关系、债务关系上的超经济剥削和重利盘剥,废除了苛捐杂税,减轻了基本群众的负担,使贫农中农的生活大大改善,租地多的上升最大”。[6](P628)总之,“敌我两个力量,两种制度的斗争,是决定各阶级阶层变化的第一个基本因素”。[6](P631)
上述北岳区28县88村调查表明,减租减息引起社会阶级关系的显著变化。首先,土地关系是“由集中走向分散”。其次,从典当关系来看,抗战以来,当出土地的多是地主、富农,当入者则主要是中农、贫农。据1942年阜平县8区调查,1至8月共当出土地1008亩,佃户承当822亩,占81.55%。另据北岳区24村调查,1937至1942年共当出土地834.57亩,地主、富农当出599.04亩,占71.8%。当入土地1019.87亩,地主、富农仅当入90.2亩,而中家、贫农则当入929.67亩,占90%以上。最后,从土地买卖关系来看,抗战以来卖地者多为地主、富农,买地者则多为中农、贫农甚至佃农。据1942年阜平县调查,1至8月卖出土地620亩,佃农承买492亩,占79.36%。另据北岳区1943年对巩固区24村的调查,中农买入土地54.1%,贫农买入土地30.39%,而地主、富农仅分别买入1.59%、5.16%。但出卖土地的地主占36.13%,富农占29.06%,中农以下合计只卖出土地34.81%。总之,上述调查表明,地主经济在逐渐削弱和下降,而富农经济则呈上升趋势,加之不少中农已经发展为富裕中农,中农已从1937年占总户数的35.42%上升到1942年的42.31%。贫农、雇农经济地位也迅速上升,土地占有从19.10%增至20.12%。最可喜的变化是新富农经济的显著增长,一方面“由于减租减息,减弱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之后,地主阶级感到坐吃地租已比不上转业或直接参加生产过程更为有利,因此有一部分地主自动转化为富农的经营,或者自己用雇工经营一部分土地成为经营地主”;另一方面,“由于深入的减租减息及合理的负担政策,贫农中农经济发展上升为新富农,这种富农的发展将不再踏旧资本主义的覆辙,他们将要成为一种新型的富农,即吴满有式的富农,这种富农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将获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3](P52-56)
减租减息也引起冀中区社会生产关系向有利于广大贫雇农、中转化。根据第八分区9县统计,1944年春冀中区全面贯彻减租减息后,彻底减租村庄1310个,初步减租930个,只有敌占区及附近的550个村尚未减租。9县36区,共计解决租佃地29839.62亩,退粮53633.1斗,退租钱30797元,认差地转为正当租当关系43931.6亩,当地续约80923.6亩,佃户取得永佃权土地1193.8亩,贫农、抗属收回被迫出卖出当土地所有权土地12895.8亩,返还使用权的土地15632.5亩。农村阶级关系也发生积极变化,据新乐县8村统计,减租前地主37户,占有土地4504亩,减租后减少到21户,土地减少到1699亩;富农由226户、占有土地11094.7亩减少到201户、7041.5亩;中农由减租前的792户、占有土地17404.8亩,增加到1234户、19601.9亩;贫农户数由减租前的806户下降为减租后的688户,但拥有的土地由5240.2亩增加到7594.2亩。[7](P448-449)
综上所述,抗战前,晋察冀边区农村封建地主经济仍然居于主体地位,晋察冀边区农村社会存在着强烈的减租减息要求,边区党和政府执行减租减息政策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减租减息斗争引起边区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封建地主阶级受到严重削弱,资本主义因素得到鼓励,中农小商品经济成为边区经济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