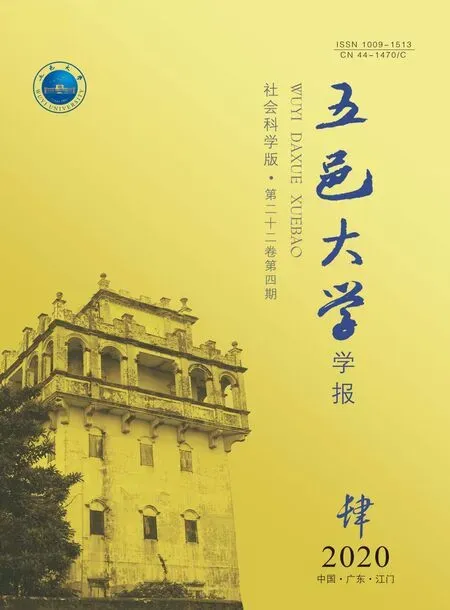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释家传记之书写策略
杨朝蕾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魏晋南北朝释家传记在叙事写人过程中,并非单调乏味的平铺直叙,而是灵巧高妙地运用多种书写策略。既节约篇幅,简省文字,又使行文灵活多变,摇曳生姿,多角度、立体化地呈现传主的神韵风采,提升传记的文学品味。其不仅采用传统史传常用的附传法、带叙法,还采用不少别具特色的书法,如旁衬法、心影法等,使之在传统史传外另树一帜,尤其值得关注。然而,学界对其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兹不妨略作抉发,以稍呈魏晋南北朝释家传记书写策略之多姿多彩。
一、附传法与带叙法
附传法与带叙法是传统史传常用之法。所谓附传法,清代吴见思认为,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项梁、项伯、范增,是附传。盖纪其始,并叙其终者,附传法也”[1],意谓在《项羽本纪》中,传主是项羽,而涉及到的其他人物,均附于其中,就是附传法。梁启超亦曾以《史记·孟荀列传》为例,指出“一人为主,旁人附录”,意谓孟子荀子为传主,而其他相关的邹子、田骈、慎到等一二十人,“个人详略不同,此种专以一二人较伟大的人物为主,此外都是附录。”[2]综合二者之言,可见,附见法就是在史传中附记与传主相关之人的事迹,不再为其单独列传。
然而,《史记》等史书在史传题目上往往不见传中附见人物的名字,如《项羽本纪》,仅看题目只知其为项羽传,根本不可能知道传内附传哪些人。这是魏晋南北朝释家传记与其迥异之处。慧皎《高僧传》运用附传法最多,并且其在章节题目上均不仅注明正传传主法号,亦明确注明附传高僧之法号。以下是《高僧传》卷四“义解一”之部分条目:
义解一 正传十四人 附见二十二人
晋洛阳朱士行 竺叔兰 无罗叉
晋豫章山康僧渊 康法畅 支敏度
晋高邑竺法雅 毗浮 昙相 昙习
晋中山康法朗 令韶
晋燉煌竺法乘 竺法行 竺法存
晋剡东仰山竺法潜 竺法友 竺法蕴 康法识 竺法济
……
这是《高僧传》所用附传法的直观呈现,从题目上很容易明确哪些是正传,哪些是附传。在行文中,附传多附于正传之文末,当然亦有个别系于文中,此类往往与正传传主有密切联系,才顺势带出。其用笔亦有详略之分,通常情况下,正传挥墨泼毫,大笔书写,附传则惜墨如金,点到为止。如《晋燉煌竺法乘附竺法行、竺法存》,在竺法乘传叙述结束后,末尾加一句:“乘同学竺法行、竺法存,并山栖履操,知名当世矣”[3]155,即将竺法行、竺法存之事迹一语带过,用语简省。再如《宋京师白马寺释道饶附道综、超明、明慧》,全文如下:
释僧饶,建康人。出家,止白马寺。善尺牍及杂技,而偏以音声著称,擅名于宋武文之世。响调优游,和雅哀亮,与道综齐肩。综善三《本起》及《大挐》。每清焚一举,辄道俗倾心。寺有般若台,饶常绕台焚转,以拟供养。行路闻者,莫不息驾踟蹰,弹指称佛。宋大明二年卒,年八十六。
时同寺复有超明、明慧,少俱为梵呗。长斋时转呗,亦有名当世。[3]499
在此短短的传记中,正传一人,附传三人,四人皆擅长音声梵呗,可谓为以类相系。正传道饶与附传道综齐名,均以音声著称宋世,所以二者笔墨相当,不分上下。而附传中的超明、明慧亦与道饶同寺,又同擅长梵呗,用语则极简。由此可见,慧皎在人物书写时,颇明轻重,何处详何处略,了然于胸中。
除了附传法,魏晋南北朝释家传记亦时常运用“带叙法”进行叙事。“带叙法”是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宋齐书带叙法》中提出的史传书写策略,谓“其人不必立传,而其事有附见于某人传内者,即于某人传内叙其履历以毕之,而下文仍叙某人之事”。又举《刘道规传》为例,进一步阐释:“攻徐道覆时,使刘遵为将,攻破道覆,即带叙遵淮西人,官至淮南太守,义熙十年卒。下文又重叙道规事,以完本传,是刘遵带叙在《刘道规传》内也”[4]。意谓在正传中带叙与其相关的他人事迹,之后又接着叙述正传人物之事。之所以运用带叙法,“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为立传则其人又有事可传,有此带叙法,则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因带叙之人之地位与作用尚轻,事迹又简,不足以支撑起一篇独立的传记,而其与正传人物又有密切关联,所以正传中带叙其事迹。
魏晋南北朝释家传记中以带叙之法传人叙事者,比较典型的如《比丘尼传·冯尼传》载:
冯尼者,本姓冯,高昌人也。时人敬重,因以姓为号。年三十出家,住高昌都朗中寺。菜蔬一食,戒行精苦,烧六指供养,皆悉至掌。诵《大般涅槃经》,三日一遍。时有法惠法师,精进迈群,为高昌益国尼依止师。冯后忽谓法惠言:“阿阇梨未好,冯是阇梨善知识,阇梨可往龟兹国金花寺,帐下直月阁,当得胜法。”法惠闻而从之,往至彼寺,见直月。直月欢喜,以蒲萄酒一升与之令饮。法惠惊愕:“我来觅胜法,翻然饮我非法之物。”不肯饮。直月推背,急令出去。法惠退思:“我既远来,未达此意,恐不宜违。”即顿饮之,醉吐迷闷,无所复识。直月便自他行。法惠酒醒,自知犯戒,追大惭愧,自搥其身,悔责所行,欲自害命。因此思惟,得第三果。直月还,问曰:“已得耶?”答曰:“然。”因还高昌,未至二百里,初无音信,冯呼尼众远出迎候。先知之迹,皆此类也,高昌诸尼莫不师奉。年九十六,梁天监三年卒。[5]189
之所以要将《冯尼传》全文录于上,在于惟如此,才能发现此传记以大部分篇幅带叙法惠事迹,直接叙述冯尼者则寥寥。而法惠之事,不过为突出冯尼之先知先觉特点。在宝唱编撰的另一部传记《名僧传》中,收有《法惠传》,内有类似记载,只不过叙述之角度由冯尼转为法惠。在同一作者编撰的两本书中,叙述同一事件,却因主角的转换而改变写法,由此可见正传与带叙之不同。
魏晋南北朝释家传记中的带叙法与附传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各自为营,区别的标志在于题目标注法号的,属于附传法,未标注法号又叙述其事迹及生平的为带叙法。有时二者又融合为一,既为附传法,又为带叙法,意即既在题目中标明其属附传,又将其在正传中带叙,而不将其单独置于正传末。如《高僧传·释玄高附慧崇、昙曜》,就题目言,玄高为正传,慧崇与昙曜为附传。就正文言,将昙曜之事迹附于文末,是附传法无疑,而慧崇之事则夹叙在正文中,又带上带叙特征。因慧崇与玄高共同赴死,所以在叙述玄高之死时捎带叙出。另外,在叙述玄高事迹的过程中,又带叙昙弘、昙无毗、樊僧印、昙绍、玄畅、法达之事迹。如其带叙玄绍曰:“高学徒之中,游刃六门者,百有余人。有玄绍者,秦州陇西人。学究诸禅,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净,倍异于常。每得非世华香,以献三宝。灵异如绍者,又十一人。绍后入堂术山禅蜕而逝”[3]410,之后继续叙述玄高之事。很显然,玄绍之人不足以独立一传,而其事迹又有得传,颇具传奇色彩,因此慧皎将其置于其师父玄高传中,捎带叙出,既传其人,又节省篇章,同时借玄绍之神异事迹衬托其师玄高灵异本领之高超。其他如释玄畅者,在《高僧传》中另有正传,而在《玄高传》中带叙其得知师父玄高罹难的消息后,从距离魏都六百里的云中扬鞭而返,泣闻玄高预言之事,可以补其正传之不足。樊僧印在《名僧传》中亦有正传,其文曰:
僧印,姓樊氏,金城榆中人,释玄高弟子。性腹清纯,意怀笃至,与之久处者,未尝见慢忤之色。下接庸隶,必出矜爱之言。振恤贫餧,有求无逆,心道聪利。修大乘观,所得境界,为禅学之宗。……后还长安大寺,年六十余卒。[6]
而《高僧传·释玄高》带叙之事,却在此正传中不见。其文曰:
时西海有樊僧印,亦从高受学。志狭量褊,得少为足,便谓已得罗汉,顿尽禅门。高乃密以神力,令印于定中,备见十方无极世界,诸佛所说法门不同。印于一夏寻其所见,永不能尽,方知定水无底,大生愧惧。[3]411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在《高僧传·释玄高》中带叙的僧印事迹,是为了烘托其师玄高的神力无穷与教化之功,而在其正传《名僧传·僧印》中,则全是对其品德道行的正面书写。二者亦呈互补之势,结合起来看,更有助于多角度、立体化地理解僧印之品性与人格。而在《高僧传·释玄高》中将附传与带叙结合起来运用,使其行文更复杂,更曲折,也更具有文学性。
二、旁衬法
在谈及“记人之文”的做法时,梁启超提出“旁衬法”,“记一人的事,有时不能专记本人,须兼记他人来做旁衬。因为一人的动作必定加在他人身上,所以不必专写本人,而写因本人动作所发生的事,或别人对于他有什么动作,可以烘托出本人人格。”[7]魏晋南北朝释家传记多处运用旁衬法,以突出传主某方面之特质。“旁衬”又分“正衬”与“反衬”。“正衬”即正面衬托,作为“旁衬”之人的帝王、太子、重臣、名士等,通过供养、征请、致敬、拜师等方式,以显示传主之品行高尚、才学卓越。《高僧传·释僧镜》载:
后入关陇,寻师受法,累载方还。停止京师,大阐经论,司空东海徐湛之,重其风素,请为一门之师。后东返姑苏,复专当法匠。台寺沙门道流,请停岁许。又东适上虞徐山,学徒随往百有余人。化洽三吴,声驰上国。陈郡谢灵运,以德音致欵。宋世祖藉其风素,敕出京师,止定林下寺。[3]293
对僧镜之事迹只以寥寥数语,概括而言,却通过徐湛之请为一门之师、沙门道流请停岁许、谢灵运以德音致欵、宋世祖敕出京师等旁衬之人之举措,烘托其风素过人,德业超众。
更有甚者,攻城略地只为得高僧之辅佐。《高僧传·释道安》载:
时苻坚素闻安名,每云:“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后遣苻丕难攻襄阳,安与朱序俱获于坚,坚谓仆射权翼曰:“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翼曰:“谁耶?”坚曰:“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3]181
此处,苻坚不惜以十万之师攻取襄阳,以获道安,其对道安之推扬可谓到达极致。而苻坚此举,亦在无形中提升了道安之身份,其价值与此可见一斑。《高僧传·昙无谶》有一更极端之例:
时魏虏拓跋焘闻谶有道术,遣使迎请,且告(蒙)逊曰:“若不遣谶,便即加兵。”逊既事谶日久,未忍听去。后又遣伪太常高平公李顺,策拜蒙逊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凉州、西域诸军事,太傅骠骑大将军、凉州牧、凉王,加九锡之礼。又命逊曰:“闻彼有昙摩谶法师,博通多识,罗什之流,秘咒神验,澄公之匹,朕思欲讲道,可驰驿送之。”……逊既吝谶不遣,又迫魏之强。至逊义和三年三月,谶固请西行,更寻《涅槃后分》,逊忿其欲去,乃密图害谶,伪以资粮发遣,厚赠宝货。……比发,逊果遣刺客于路害之。……至四月,逊寝疾而亡。[3]79
昙无谶明解咒术,所向皆验,为得到他,拓跋焘不惜任何代价,而蒙逊既不愿遣无谶归魏,又惧怕魏之进攻,所以密谋害无谶。无谶已预料此事,流涕告知诸弟子“谶业对将至,众圣不能救矣”,后果然被蒙逊派刺客害杀,而蒙逊“常白日见鬼,以剑击逊”,于同年四月亦亡。昙无谶因道术而被崇,亦因道术而亡身。此事例亦用旁衬之法,不明写无谶道术之高明,而通过写拓跋焘与蒙逊之争,已见其高明。
“旁衬”之中亦有“反衬”之法,即从反面衬托,以突出传主某方面特点。《比丘尼传·道馨尼传》载,竺道馨“雅能清谈,尤善《小品》,贵在理通,不事辞辩,一州道学所共师宗”,然而却因此遭人妒忌而罹祸。其文曰:
晋太和中,有女人杨令辩,笃信黄老,专行服气。先时人物亦多敬事,及馨道王,其术寝亡。令辩假结同姓,数相去来,内怀妒嫉,司行毒害。后窃疑毒药内馨食中,诸治不愈。弟子问:“往谁家得病?”答曰:“我其知主,皆籍业缘,汝无问也。设道有益,我尚不说,况无益耶?”不言而终。[5]25
道馨之德行,受人尊敬,而使原本为人敬事的黄老之徒杨令辩不为人重视,从而生发嫉妒之心,最终对其下毒手。而道馨知己为其所害,将其归结为宿业有报,至死不言其名,不起嗔恨,以免冤冤相报,不得终了。如此,以杨令辩之所为反面烘托出道馨修为之高深。
亦有“正衬”与“反衬”结合而用者,如释法慧“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阁不下三十余年。王侯税驾,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颙,以信解兼深,特与相接。时有慕德希礼,或因颙介意,时一见者。”[3]472此乃先用“反衬”之法,通过叙述王侯驾到却不得见法慧,只能拜房而返,从反面衬托法慧德行与时风相悖,不喜交游,不攀缘富贵。再用“正衬”之法,指出唯独隐士周颙“以信解兼深,特与相接”,愈发衬托其交游之慎。而那些慕德希礼之人,通过周颙介绍,才得以与法慧相见,则进一步突出其对周颙的信任与对来者的审慎。
在对志节清高、拒不礼敬王者的释僧远进行书写时,《高僧传·释僧远》亦采用正衬与反衬相结合的写法。其文曰:
宋明践祚,请远为师,竟不能致。其后山居逸迹之宾,傲世陵云之士,莫不崇踵山门,展敬禅室。庐山何点、汝南周颙、齐郡明僧绍、濮阳吴苞、吴国张融,皆投身接足,咨其戒范。后宋建平王景素,谓栖玄寺是先王经始,既等是人外,欲请远居之。殷勤再三,遂不下山。齐太祖将升位,入山寻远,远固辞老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礼,咨访委悉。及登禅,复銮驾临幸,将诣远房,房阁狭小,不容舆盖。太祖欲见远,远持操不动。太祖遣问卧起,然后转跸而去,远曾不屑焉。至于寝疾,文惠、文宣伏膺师礼,数往参候,时贵卿士,往还不绝。[3]319
对于君主王侯、达官贵人,僧远不屑与之结交,宋明帝请僧远为师而不能致,齐太祖躬自降礼,入山寻访,僧远以老疾相辞,持操不动,对照其语“我剃头沙门,本出家求道,何关于帝王”,可谓言行合一,品行清高。此乃以帝王为旁衬,从反面衬托其不慕权势,业行高远。至于隐士高人,何点、周颙之流,对僧远皆投身接足,咨其戒范,时贵卿士文惠、文宣之俦,对僧远伏膺师礼,则从正面烘托其德行清俨,令人敬重。二者结合,僧远之品行高洁、风容秀整之特征跃然纸上。
“旁衬”书法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是对比。只将二者并置,不言其正反与褒贬,而对比之功效自著。释慧永与释慧远同为道安弟子,后慧永停庐山西林寺,慧远止庐山东林寺。慧永“贞素自然,清心剋己,言常含笑,语不伤物”[3]232,慧远“神韵严肃,容止方棱,凡预瞻睹,莫不心形战栗”[3]215,可见二者虽同门师兄弟,同山修行,却性格迥异。《高僧传·释慧永》载:
后镇南将军何无忌作镇浔阳,陶爰集虎溪,请永及慧远,远既久持名望,亦雅足才力,从者百余,皆端整有风序,及高言华论,举动可观。永怗然独往,率尔后至,纳衣草屣,执杖提钵,而神气自若,清散无矜,众咸重其贞素,翻更多之。远少所推先,而挹永高行,身执卑恭,以希冥福。[3]233
在赴何无忌之邀约时,慧永与慧远风格迥异。慧远久持名望,弟子众多,声势煊赫,而慧永孤身赴会,神气自若,清散无矜,二者形成鲜明对比。慧皎虽未明论得失,却将这一事件载于慧永本传,又言“众咸重其贞素,翻更多之”,言慧远之变化,“少所推先,而挹永高行,身执卑恭,以希冥福”,其褒贬之意已内蕴其中。
三、心影法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曾夫子自道:“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8]也就是说,司马迁有意识在《管晏列传》中不全篇累牍地载其作品,而是“论其轶事”,一语道出传记文学之精髓:传写非常之事,树立非常之人。鲁迅先生曾对名人传记的写法亦有精辟论述:
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9]
鲁迅先生批评那些名人传记,只一味铺张其特点,而忽略其生活细节,将其喻为删夷枝叶,自然得不到花果。梁启超亦曾指出:
社会既产一伟大的天才,其言论行事,恒足以供千百年后辈之感发兴奋,然非有严密之传记以写起心影,则感兴之力亦不大。[10]
书写传主之“心影”,是传记的灵魂,是传记产生感兴之力的根本。“心影”之所在,恰蕴含在生活轶事中。所以,优秀的人物传记,绝不是仅关注传主一生之大事,而应以笔墨点染于生活细节中。
魏晋南北朝释家传记颇多“心影”书法,以此对传主传神写照,图影摹形,以突出其个性特征与人格魅力。《高僧传》中,数百位高僧同而不同,各有所长,妙通医法的于法开,“明六度一除四魔之病,调九候以疗风寒之疾”[3]168,曾经乞食于某家,恰逢妇人在草危急,众治不验,举家遑扰,法开出手相助,“主人正宰羊,欲为淫祀,开令先取少肉为羹,进竟,因气针之,须臾羊膜裹儿而出”[3]168。法开以其精湛之医术,使妇人顺利生产,此一细节,足以彰显其慈悲之心,高超医术。能救眼疾的单道开,“时秦公石韬就开治目,著药小痛,韬甚惮之,而终得其效”。石韬因用道开眼药而微有痛感,心里害怕,合乎情理而细微传神,最终目愈,而愈发可见道开医术之高超。尤长巧思的释慧要,“山中无刻漏,乃于泉水中立十二叶芙蓉,因流波转,以定十二时,晷景无差焉。亦尝作木鸢,飞数百步”[3]238,手制芙蓉日晷以计时,尝作木鸢而能飞,其心灵手巧可见一斑。擅长目测的释僧祐,“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等,并请祐经始,准画仪则”[3]440,其目测功力不可谓不深。多才多艺的释僧饶,“善尺牍及杂技,而偏以音声著称,擅名于宋武文之世。响调优游,和雅哀亮,与道综并肩”[3]499,擅长书法的释昙迁,“工正书,常布施题经”[3]501,无一不是各具所长,技艺精良。
就个性特征言,释家传记之僧尼亦环肥燕瘦、各领千秋。既有“神韵严肃,容止方棱,凡所瞻睹,莫不心形战栗”[3]215如慧远者,《高僧传·释慧远》载:
曾有沙门持竹如意,欲以奉献,入山信宿,竟不敢陈,窃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义法师,强正少惮,将欲造山,谓远弟子慧宝曰:“诸君庸才,望风推服,今试观我如何。”至山,值远讲《法华》,每欲难问,辄心悸汗流,竟不敢语。出谓慧宝曰:“此公定可讶。”[3]215
慧远之威严通过两件小事予以说明,一则为沙门欲献竹如意而不敢,一则为素无忌惮之慧义每欲问难而心悸汗流,通过正面旁衬之法现其“心影”。
又有“妙辩不穷,应变无尽,而任性放荡,亟越仪法。得意便行,不以为碍”如僧宗者,《高僧传·释僧宗》载:“守检专节者,咸有是非之论。文惠太子将欲以罪摈徒遂,通梦有感,于是改意归焉”[3]328。慧义因为个性突出而遭墨守成规者非议,文惠太子甚至要将其摒除缁林,通过反面旁衬之法现其“心影”。由此可见,“心影”书法可与其他书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多法合用,能够更充分细致地表现人物之形神特点。
将人物置于激烈的戏剧冲突中,以彰显其某方面之特质,亦为释家传记典型的“写心”之法。众所周知,魏晋风度的内涵之一即在于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每临大事有静气。谢安在得知淝水之战大获全胜时,仅以“小儿辈遂已破贼”一言以带之,尚且有几分做作,喜怒不形于色,全凭克己之功。嵇康“临刑东市,神色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则超脱了对死亡的恐惧,为其点染上一缕诗性的光芒,平添几分视死如归的悲壮意味。在面对死亡威胁的严峻时刻,最能考验一个人的真正定力与修为功夫。魏晋南北朝释家传记中不乏此类精彩书写,既有时代对名士风度无限推崇的烙印,又无疑凝聚为传主一生的高光时刻。“形长八尺,风神俊爽”而又“冲默有远量”的高僧释慧持,就曾经面临这样的生死考验。《高僧传·释慧持》载:
持避难憩陴县中寺。(谯)纵有从子道福,凶悖尤甚,将兵往陴,有所讨戮,还过入寺,人马浴血,众僧大怖,一时惊走。持在房前盥洗,神色无忤,道福直至持边,持弹指漉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门谓左右曰:“大人故与众异。”[3]230
在此事之前,蜀人谯纵已攻杀刺史毛璩与高僧慧俨,致使“举邑纷扰,白黑危惧”,在这种情况下,慧持由龙渊精舍避难陴县中寺。谯纵之从子道福将兵往陴,大肆屠戮,面对强暴之徒的屠刀,“众僧大怖,一时惊走”。而慧持却依然淡定自若,神色无忤,盥洗如旧,即使道福至其身边,亦无惧色,反令道福愧悔流汗。在生死关头,慧持以其深厚的修持功夫令暴徒汗颜,亦使自己全生远害,表现出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名士风度。
亦有出于道义救人而不顾己之安危者,《高僧传·释僧导》载:
高祖旋旆东归,留子桂阳公义真镇关中,临别谓导曰:“儿年小留镇,愿法师时能顾怀。”义真后为西虏勃勃赫连所逼,出自关南。中途扰败,丑虏乘凶追弃骑将及,导率弟子数百人遏于中路,谓追骑曰:“刘公以次子见托,贫道今当以死送之,会不可得,不烦相追。”群寇骇其神气,遂回锋而反。义真走窜于草,会其中兵段宏,卒以获免,盖由导之力也。[3]281
刘裕留儿子刘义真镇守关中,委托僧导多加顾怀,在刘义真兵败被追之际,僧导率众僧将敌兵阻遏在路,声称要以死相送,其神气令敌兵震惊,从而回锋而反,使刘义真得以逃脱。僧导本身“气干雄勇,神机秀发,形止方雅,举动无忤”, 在此危机时刻,气势逼人,不战而屈人之兵,表现出其有勇有义之特点。
面对劫匪,谈笑若常之奇女子亦有之。慧湛“神貌超远,精操殊特,渊情旷达,济物为务,恶衣蔬食,乐在其中”,就有这样的遇劫经历。《比丘尼传·慧湛尼传》载:
尝荷衣山行,逢群劫,欲举刃向湛,手不能胜,因求湛所负衣。湛欢笑而与曰:“君意望甚重,所获殊轻。”复解其衣内新裙与之。劫即辞谢,并以还湛,湛舍之而去。[3]21
面对劫匪的屠刀,慧湛不仅没有恐惧,反而悲悯心大发,设身处地为劫匪着想,笑其想得到的太多,所得到的太少,自觉只送其一件外衣太少,又将衣内新裙一并送入。如此反让劫匪有了愧意,表现出谦谦君子之德,不仅辞谢,还将衣与裙一并还给慧湛。由此可见慧湛之德风不仅救己命于危难之时,还能够化干戈为玉帛。
细微之处见精神,是释家传记“心影”书法之要。求那跋陀罗“自幼以来,蔬食终身,常执持香炉,未尝辍手。每食竟,辄分食飞鸟,乃集受取食”[3]134,通过蔬食、香炉、与鸟分食等细节突出其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特点,暗示其佛缘深厚。释智顺“尝有夜盗顺者,净人追而擒之,顺留盗宿于房内,明旦遗以钱绢,喻而遣之,其仁洽笃恕如此”[3]335,通过留盗宿、赠钱绢等细节,表明其仁厚宽容之菩萨心肠。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品鉴亦常通过静观默察其不经意之举而加深对人物之了解。《高僧传·释昙翼》载:“经游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为设中食,躬自瞻奉。见翼于饭中得一粒谷,先取食之,璩密以敬异,知必不孤信施。得后饷米千斛,翼受而分施。”[3]198毛璩对昙翼的敬重之情,即建立在对其进食时不浪费一粒谷的细微观察中,由此而知其人必不浪费信众的布施。后昙翼果然妥善处理所接受的千斛饷米之布施,将其一一分施出去。
多种书写策略的灵活运用,不仅使魏晋南北朝释家传记之章节更加凝练、行文更加多姿,还彰显了其以简省笔墨传人物风神的品格,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