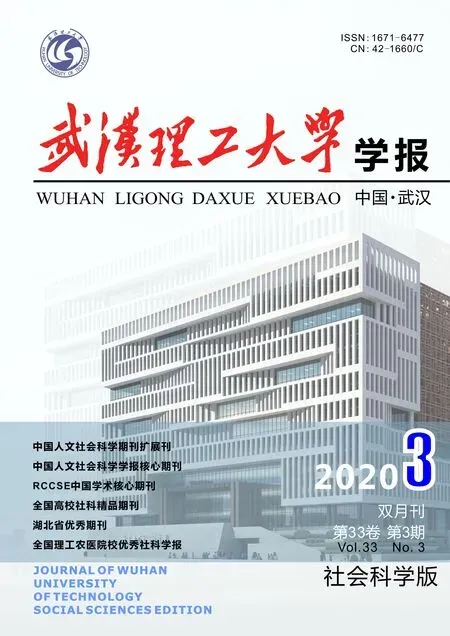独立性和依存性:克罗齐艺术与道德关系思想重释*
郭玉生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克罗齐的艺术与道德关系思想不仅对康德以来的艺术自律观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分析,而且为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奠定了坚实的美学基础。他立足于自己的精神哲学体系的框架强调艺术活动与道德活动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灵活动,艺术独立于道德,同时艺术与道德互为前提、彼此依存,在人性的基础上实现了艺术的独立性与艺术家的道德责任的统一。
一
克罗齐建立了自己的精神哲学体系并以此为前提阐述了艺术活动与道德活动。克罗齐受到了黑格尔的绝对的、普遍的精神是世界万物的本体的观点影响,认为只有精神才是绝对真实的存在,精神创造了一切事物,也创造了一切历史,但克罗齐同时又提出了不同于黑格尔的观点。黑格尔对于精神的理解具有超验性、实体性特征,强调外在于人的绝对理念对于世界和人的支配作用;克罗齐对于精神的理解与人的心灵密切联系,使精神具有了内在性、个体性特征。克罗齐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支配历史的是人的心灵,哲学的任务只是研究内在于人与人的生活的心灵活动。克罗齐把心灵活动分为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两类,其中认识活动不仅在实践活动之先,而且独立于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以认识活动为基础而包含认识活动。认识活动始于直觉活动,止于逻辑活动;实践活动始于经济活动,止于道德活动。直觉活动、逻辑活动、经济活动、道德活动各有其相应的正反价值,即美丑、真伪、利害与善恶。直觉活动、逻辑活动、经济活动、道德活动之间基于克罗齐所说的“差异辩证法”只存在差异,不存在对立,都是后者包含和超越前者,前者独立于后者并成为后者的基础,正如克罗齐所言:“概念不能离开表现而独立,效用不能离开概念和表现而独立,道德不能离开概念、表现与效用而独立。”[1]59四阶段心灵活动前后相继,循环相生,不断发展。克罗齐由此超越了康德把认识、情感、意志罗列并举、机械划分各自职能范围的哲学思想。
克罗齐精神哲学意在揭橥人类心灵活动的形式与规律。心灵活动的发展包含直觉活动、逻辑活动、经济活动和道德活动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又对应产生了美学、逻辑学、经济学和伦理学四种科学。克罗齐将康德认识论中的感性认识改造为直觉活动。直觉把握个别事物,产生的是形象化的意象,对于直觉的研究产生了美学;以直觉为基础形成了概念,概念关注个别事物之间的关系,对于直觉具有规范作用。以概念为研究对象产生了逻辑学;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两种价值属于实践活动的追求目标和发展方向的价值,与心灵活动的一般性法则直接关联;伦理学侧重于研究善和自由,而所有的道德感最终都通向宇宙的和谐感,人由此可以体察、认识心灵的整体性,从而实现自由。可以说,上述克罗齐精神哲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奠定了克罗齐的艺术与道德关系观点的理论基础。
在克罗齐看来,直觉活动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处于人类心灵活动的起始阶段。直觉凭借想象进行认识,是一种心灵赋形的创造活动,即心灵赋予杂乱无序的质料、物质、印象以形式。克罗齐说:“物质,在脱去形式而只是抽象概念时,就只是机械的和被动的东西,只是心灵所领受的,而不是心灵所创造的东西。”[1]10在此基础上,克罗齐认为,直觉即表现,直觉与心灵赋形活动产生的具体形象无法分开。克罗齐从他对于直觉的理解出发,提出艺术即直觉即表现。艺术是心灵赋形的创造活动,当人们以直觉的形式认识对象时,艺术创造活动就得以实现。在艺术创造活动中,直觉来源于情感,并且情感还使直觉具有了连贯性与整体性,所以艺术表现与情感的表现具有同一性。情感在艺术创造活动中获得了形式,呈现为具体的意象。情感的表现由此完成,产生了美的价值。
克罗齐对于道德本质也立足于精神哲学体系提出了他的理解:“心灵起意志要实现它自己,实现它的真正的自我,即含在经验的有限的心灵之中的普遍性。”[1]58道德来自于意志,而西方哲学对于意志的理解通常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把意志看作“宇宙的基本,事物的本原,真正的实在”[1]47;另一种观点是把意志看作“心灵的力,心灵,或一般活动”[1]47。克罗齐不赞同这两种关于意志的观点,重新界定了意志的内涵,即“与对事物取纯粹的认识性的观照有别的那种心灵活动,它所产生的不是知识而是行动。”[1]47克罗齐强调意志属于心灵活动中的实践活动。意志区分为经济的意志与道德的意志两种形式。经济的意志可以称为个别的意志,道德的意志可以称为普遍的意志。道德的意志作为普遍的意志以理性的目的也就是“善的”目的作为自身的目的,道德的意志所产生的行动是善的行动。这意味着,克罗齐主张道德的意志追求“善的”目的,与康德道德哲学中的善良意志一脉相承。在康德这里,善良意志的产生以纯粹理性为基础,即理性“真正的使命,并不是去产生完成其他意图的工具,而是去产生在其自身就是善良的意志”[2]。
综上所述,克罗齐认为,艺术与道德有着本质的差异。艺术属于心灵活动的认识阶段,本质上是一种直觉活动,是情感的成功表现;道德属于心灵活动的实践阶段,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来源于意志,具有理性的目的。
二
克罗齐把艺术看成是“一种完全特殊的直觉”[1]17,而直觉活动是唯一能够独立存在的活动。直觉不受概念或逻辑的作用,独立于经济与道德实践。克罗齐在此基础上认为艺术具有独立性。
克罗齐首先批判了艺术的内容需要经过选择的观点。他说:“在诸印象及感受品之中加以选择,就无异于说这些印象与感受品已经是表现品,否则在混整的东西之中如何有选择呢?选择就是起意志:起意志要这个不要那个;这个和那个就必须摆在我们面前,已表现了的。实践在认识之后,并不在前;表现是自然流露。”[1]50克罗齐认为,不能从道德的标准对艺术的内容进行选择和评价,唯有形式即情感直觉才能使诗人成为诗人,“这就完成了艺术独立的原理,也是‘为艺术而艺术’一语的正确意义”[1]51。克罗齐驳斥了主张艺术的内容必须引发人们的道德同情的观点。他强调,这种观点把题材与表现混为一谈。题材对于艺术表现的性质并没有决定性作用,不能引发人们道德同情的题材完全可以获得美的表现。
在克罗齐的精神哲学体系中,认识活动先于实践活动并且独立于实践活动而存在。基于此,艺术活动就先于经济活动与道德活动,独立于一切实践的价值。因而克罗齐得出了以下结论:“对某艺术作品所下的审美判断,与作者作为实践者的道德是毫不相干的,它和预防艺术被用去做坏事(这也就违反艺术纯为认识观照的本质)的措施也是毫不相干的。”[1]105艺术并不是来源于意志、来源于实践活动,因而艺术活动不是道德活动,具有独立性。如果从道德角度理解人格的内涵,那么“风格即人格”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克罗齐说:“善良的意志能造就一个诚实的人,却不见得能造就一个艺术家。”[1]176由于艺术活动与道德活动之间具有本质的差异,道德评判的标准就不适用于艺术活动。即使在艺术活动中产生的审美意象显示了一个在道德方面可以进行褒贬的行为,但人们也不应按照道德评判的标准对审美意象本身进行褒贬。正如人类世界不会存在针对审美意象进行法律审判的条文,也不会存在针对审美意象进行道德审判的法庭。倘若有人认为莎士比亚《李尔王》中考狄利娅具有道德性,如同主张一个正方形具有道德性而一个三角形不具有道德性一样。审美意象只能以是否成功的表现来评判,批评家应该采取美学的观点衡量艺术。因而克罗齐强调,批评家评判艺术作品的题旨的根据不在于艺术家对于题旨的选择,而在于艺术家如何处理所选择的题旨,即艺术家是否成功表现了所选择的题旨。即使艺术家选择了道德品格低下的题旨,在作品中没有抒发纯洁的道德情感,批评家也没有理由指责艺术家,而是应该关注并改变产生丑恶的世界。艺术家的直觉来自于印象,来自于触动心灵的事物,因此只要世界上存在丑恶现象,批评家就无法制止艺术家选择对于道德品格低下的题旨的表现,而且如果艺术家成功表现了道德品格低下的题旨,同样可以认为创造了完美的艺术。因此,克罗齐反对艺术预先存有道德教育的目的。他说:“勉强把教育职责加给艺术,既是一个预求预计的目的,就不复纯是认识的事实,而是认识的事实变成实践行动的根据;所以它不是理智主义而是教训主义与实用主义。”[1]79在克罗齐看来,艺术家不应该因为道德说教的需要而损害艺术自身具有的独立性:“审美意识完全没有必要从道德意识中汲取什么廉耻心,审美意识中包含着这种情感,即审美的廉耻、审美的忌讳和审美的贞操。审美意识明白什么时候沉默是最好的表现形式。相反,当一个艺术家违背了审美的羞耻心,违背了审美意识,让与审美目的无关的东西混杂到艺术中来,那么,即令没有比他的目的更高尚、更值得褒奖的了,从艺术的观点来看他还是虚伪的,从道德的观点来看他还是有罪的,因为他玩忽了艺术家的职守。”[1]261传统的艺术观念非常重视艺术的道德教育作用,强调艺术应该引导人爱道德,恨罪恶,敦风化俗,引人向善。克罗齐认为这是艺术无法完成的职责,就像几何学不能承担道德教化的任务。
克罗齐反对艺术作为道德教育工具还表现在他对艺术传达提出的观点。在克罗齐看来,直觉作为心灵的赋形活动只在内心完成,不需要外在媒介的传达。因而人直觉到一个意象,便已在内心完成了一件艺术作品。关于人们一般所说的“传达”,也就是在具体作品中借助于物质媒介显示意象的过程,克罗齐认为需要意志参与,因而属于实践活动而不属于艺术活动。他进一步强调,通过传达活动而产生的各种艺术作品以字母、音节、声音、颜色、线条等物质材料的组合为基础,因而这样的艺术作品属于物理事实而非呈现直觉意象的艺术。克罗齐由此强调艺术是独立于包括道德活动在内的实践活动的心灵自由活动。
可以认为,克罗齐阐述的艺术独立性的观点是对19世纪以来“为艺术而艺术”文艺思潮的理论辩护。在传统社会,艺术一直依附于政治、道德、宗教等,缺乏独立性。克罗齐以他的精神哲学体系为基础,评析了美学史上艺术与道德关系的各种理论,区分了直觉活动与道德活动,为艺术划定价值领域,确定艺术在精神活动中的地位。在克罗齐看来,如果艺术不是独立于道德以及一切实践的价值,那么它就会受制于其他心灵活动的原则,由此艺术与其他心灵活动没有实质的差异:“依赖于道德、快感或哲学的艺术,就是道德、快感和哲学,而不是艺术。”[1]206所以克罗齐强调:“艺术就其为艺术而言,是离效用、道德以及一切实践的价值而独立的。如果没有这种独立性,艺术的内在价值就无从说起,美学的科学也就无从思议,因为这科学要有审美事实的独立性为它的必要条件。”[1]104克罗齐的观点既反映了19世纪以来西方艺术自律的发展趋向,也为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提供了坚实的美学基础。
三
克罗齐认为,艺术与道德作为人的心灵活动的两种基本形式,具有内在的联系。虽然艺术独立于一切实践的价值,艺术活动不同于道德活动,但艺术对于道德同时具有依存性。在克罗齐这里,独立性与依存性可以看作一对相依相伴的关系概念。他说:“任何一个特殊的形式和概念,一方面是独立的,另一方面又是依存的;或既是独立的,又是依存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心灵,乃至现实界,要么就会是一系列并列的绝对存在者,要么就会(其实是一回事)是一系列并列的空无。”[1]207因此,艺术作为心灵活动的基本形式,它一方面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其他形式,具有独立性,另一方面又与其他心灵活动的形式存在密切联系。克罗齐认为直觉活动、逻辑活动、经济活动与道德活动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它们在整体中只是被理想地区分开来,但实际上它们与整体是不可区分的。这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就是直觉活动、逻辑活动、经济活动与道德活动的综合,艺术的独立性和依存性就是以这个综合为前提。艺术不仅以逻辑活动、经济活动与道德活动等心灵活动为前提,同时艺术也是逻辑活动、经济活动与道德活动等心灵活动的前提。由此可以推论,艺术与道德之间互为前提、彼此依存。一方面,缺乏了直觉表现,具有辨别和评判功能的概念就无从形成;缺乏了具有辨别和评判功能的概念,行动就无从产生;缺乏了行动,评判行动好坏、善恶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无从存在。另一方面,虽然一个人善于运用概念进行辨别和评判,思维具有逻辑性,富有批判精神,履行各种道德责任,品德高尚,但是他的心灵仍然倾向于追求诗意,对于心灵活动的对象包括道德活动提出了美的要求。
人类通过直觉活动与逻辑活动认识世界,但人类还要通过实践活动改变世界。因而直觉活动经过逻辑活动而与实践活动领域产生联系。实践活动不仅包含了直觉活动、逻辑活动等认识活动的内容,而且能够激发直觉活动、逻辑活动等认识活动的内容而形成新的直觉、新的情感、新的艺术。这样一来,实践活动为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或内容,从而制约着艺术活动。道德活动为“更崇高、更完美、更复杂、更成熟的艺术”提供了素材,道德活动提供的素材经过心灵的赋形活动,成为了直觉的意象,如果离开了道德活动等实践活动,艺术就会丧失现实生活的基础而题材贫乏,内容空虚。所以,克罗齐强调,诗人创造的每一个诗句,诗人的所有幻想都是以现实生活的场景为基础,揭示了整个人类的情感、愿望与命运。
克罗齐通过论述艺术的独立性与依存性具体内涵,揭示了艺术与道德之间既相互独立又互为前提的关系。艺术由此既不能依附于道德,也不能脱离道德的制约。艺术作为直觉活动虽然不以道德教化为直接目的,但艺术家的生活包含着道德活动领域,承担着一定的道德责任,因而艺术活动应该符合时代的道德要求。克罗齐指出:“把艺术同仅仅是引起快感的东西区分开(艺术有时和这种东西相混淆),给艺术一个更有价值的地位:这种学说毕竟也有其正确的一面,因为,从艺术在道德范畴之外这点来看,艺术家当然是既不在道德的这一面也不在那一面;然而艺术家既是在道德王国里,那么他只要是人,就不能逃避做人的责任,就必须把艺术本身——现在和将来都不是道德——看作是一项要执行的使命,一个教士的职责。”[1]177克罗齐强调,艺术活动虽然不同于道德活动,具有独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进行创作可以摆脱道德的规范而随心所欲。艺术家倘若对于道德缺乏体认,就没有创作的资格。他说:“为发展审美再造用的工具争较大的自由,这本是很好的。”[1]105但是,“在任何情形下,艺术独立那一个最高的原则,那一个美学的基础,总不能援引来为虎作伥。一个艺术家在外射他的想象时,如果像不道德的投机者,逢迎读者的不健康的趣味,或是像小贩子在公共场所出卖淫画淫像,都不能援引这最高原则来洗刷罪状,维护自由。”[1]105在克罗齐看来,艺术家外射自己的想象即通过物质媒介传达直觉属于实践活动,必须考虑道德原则的制约和伦理效用。
不过克罗齐所主张的艺术家的道德意识与直觉活动密切结合,所以艺术家的道德责任不是体现在外射活动或传达活动中流露道德倾向,而是体现在直觉意象的成功表现。在此,克罗齐进一步提出了艺术真诚说。他认为,“真诚”作为艺术家的道德责任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从伦理学方面而言,“真诚”是指不欺骗人。克罗齐认为“真诚”这个内涵与艺术家没有关联。因为艺术家本来就没有欺骗任何人,他只要赋予其内心的印象、情感以形式,创造美的价值,就是已经履行了艺术家的责任。二是从美学方面而言,“真诚”是指艺术家应该使自己的直觉表现真切完美。显然,“真诚”这个内涵与一般道德准则无关。因而克罗齐认为,即使艺术家在现实生活中没有遵循一般道德准则,但他在艺术活动中完美表现了自己的直觉,维护了艺术的独立性,那么这个艺术家仍然具有道德特性。
克罗齐把“人性”作为统一艺术的独立性与艺术家的道德责任的基础。他说:“不论是什么诗,其基础是人性,而正因为人性是在道德上实现的,任何诗的基础也就都是道德意识。”[3]10在克罗齐看来,道德的基础在于人性,艺术的基础也在于人性,因而“人性”成为了把艺术与道德相互联系起来的纽带。“人性”在拉丁文中的原意是指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情感和理性。克罗齐从“人性”的拉丁文原意出发,认为人性的实现不能离开实践活动特别是道德活动。人在实践活动中以自己经历或者同情他人的方式分享思想与行动的世界,体会世事变迁,体认美德与罪恶。艺术灵感的产生就是因为艺术家在实践活动特别是道德活动中体会到应当景仰与向往的情感,即:“是由于他感受到应当如此,是由于他看到这种现象就仰慕备至,并且渴望去追求这种现象。”[3]11克罗齐认为,艺术活动并非空虚的灵魂与愚顽的思维能够完成的。那些大谈特谈所谓纯粹的艺术,高喊“为艺术而艺术”口号的艺术家,往往会封闭心灵,对于波澜壮阔的生活和起伏变化的思想毫不顾及,由此不可能创造真正的艺术作品。
当然,克罗齐并不是说一个人只要品德高尚就能够成为艺术家。相反,形象与情感的表现更是一个人成为艺术家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是说,艺术需要才华。但是,克罗齐强调的是,对于艺术而言,固然不能离开才华,人性也是不可或缺。因而他说:“一个纯诗人、纯艺术家、制造纯粹的美的人,一旦缺乏人性,也同样会失去其本身这种形象,而成为一种漫画式的人物。”[3]11克罗齐指出,人性作为艺术与道德联系的纽带不是指抽象的思想和品德,而是指在实践活动中人所体验到的情感。直觉因为表达了这种情感而获得了连贯性与整体性,产生了不同于道德的审美意象,使艺术具有了独立性,同时情感来自于实践活动,艺术必然会与道德联系。克罗齐强调“人性”并不是要求艺术家应该成为道德的楷模或者英雄人物,艺术家在生活中可能犯罪,也可能失去心灵的纯洁而受到社会的谴责。但艺术家应该借助于自己经历或同情他人主动参与思想与行动的世界,感知表现对象,获得人生中诸如是非、善恶、纯真的丰富体验。由此,衡量艺术家是否道德的标准,不在于艺术家外在的行为,而在于艺术家精神创造的结果。艺术家在艺术活动中遵循的道德不是压抑人性的抽象道德教条,而是激发人的生命力的情感。因此追求感官快乐、沉湎声色而在思想方面怀疑悲观、不信上帝的现代艺术却能“把生活更有力地引导到某种更健康、更深刻的道德,这种道德将是内容更高尚的某种艺术之母”[1]220。
可以说,艺术的自律是现代社会出现的艺术发展趋向。因此,把艺术的自律看作艺术的抽象本质或美学的普遍概念是不妥当的。克罗齐关于艺术与道德的关系的思想充分揭示了艺术从在传统社会中整合在宗教与形而上学世界观中,到从科学、道德、宗教中区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分化与去分化的复杂关系导致了艺术与道德之间彼此独立又彼此依存的复杂关系,所以,艺术的自律是相对而言的,并不存在完全对立或泾渭分明的真善美不同的价值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