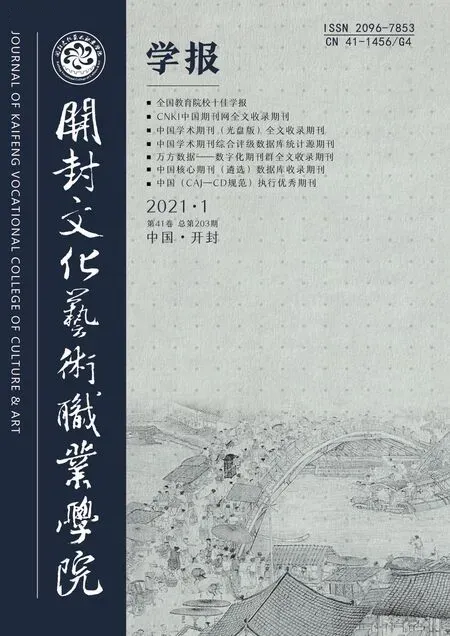伍尔夫作品译介及对残雪文学创作的影响研究
王明珠 王 春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是20 世纪英国意识流代表作家之一。她自20 世纪20 年代被引入中国文坛至今,以多元的作家形象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接受。伍尔夫前瞻的女性主义思想,对中国当代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残雪是受伍尔夫影响的当代女作家之一。残雪自1985 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黄泥街》《黑暗地母的礼物》和《山上的小屋》等。其作品注重对精神与灵魂的探讨,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的高度评价。
笔者尝试从文学创作手法、文学思想、女性主义三个方面对伍尔夫与残雪两位作家进行比较,以考察伍尔夫作品在我国的译介对残雪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以及残雪文学思想中对伍尔夫的接受。
一、伍尔夫作品在中国译介的史脉描述
伍尔夫作品在国内的译介已有近百年的历程,最早可追溯至诗人徐志摩发表的《关于女子》的演讲,这是国内文坛首次介绍伍尔夫的名作《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 s Own)。伍尔夫作品在中国最初的译介不是以意识流小说开始的,而是着重于介绍她的女性思想。随着译介语境背景的变化,伍尔夫作品译介的文化身份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概括来讲,伍尔夫作品的译介历程大体可以分为译介发端期、译介停滞期和译介活跃期[1]。
(一)译介发端期
徐志摩之后,赵景深成为20 世纪20 年代译介伍尔夫作品的重要学者之一。在《二十年来的英国小说》一文中,赵景深评论了包括伍尔夫在内的英国创作意识流小说的几位代表作家。20 世纪30 年代,伍尔夫的小说和论文得到初步译介。其中,叶公超开创了中国伍尔夫作品译介先河,其翻译的《墙上一点痕迹》刊载于《新月》杂志第四卷第一期;彭生荃评论《弗勒虚》的内容刊载于《人世间》杂志;范存忠翻译了伍尔夫的著名论文《班乃脱先生与白朗夫人》,并刊登在《文艺月刊》第6 册第3 期;石璞翻译的伍尔夫戏作《狒拉西》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到了20 世纪40 年代,伍尔夫两篇论文得到翻译,即《论现代英国小说——‘材料主义’的倾向及其前途》(冯亦代译)和《将倾的塔》(高殿森译)。此时还出现了谢庆翻译的《到灯塔去》节译本。此外,王还翻译了伍尔夫女性主义代表作《一间自己的屋子》,并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二)译介停滞期
20 世纪40 年代末,受到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文坛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翻译活动处于停滞状态。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新时期文学之前,伍尔夫作品的汉译寥寥无几。只有朱虹翻译的《班奈特先生和博朗太太》和袁可嘉关于伍尔夫数部意识流小说的评介。这便是此阶段伍尔夫作品所有的译介情况。
(三)译介活跃期
20 世纪80 年代末,恰逢改革开放时期,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外国文学翻译呈回暖趋势。从1980 年开始,伍尔夫的小说、论文等作品得到广泛译介和出版。1981—1983 年,伍尔夫的意识流代表作均被引入国内。首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刊载了大量西方现代主义文选作品,其中就收录了伍尔夫的两部作品,分别为《墙上的斑点》(文美惠译)和《达洛维夫人》(郭旭译)。随后,赵少伟重译了伍尔夫的论文《现代小说》。舒心翻译了伍尔夫的短篇小说《邱园记事》。同年,又出现了《墙上的斑点》的节译本,以及刘象愚和文美惠两位译者的不同译本。吴钧燮翻译了伍尔夫的意识流长篇小说《海浪》。瞿世镜是新时期译介伍尔夫的重要人物,不仅翻译了诸多伍尔夫的作品,如《到灯塔去》等,还出版了伍尔夫研究的相关著作《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
进入新世纪,伍尔夫在我国的译介和研究呈纵深发展趋势。这期间出版了不少伍尔夫的文集,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的《吴尔夫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伍尔夫文集》等。
由以上分析可知,百年来伍尔夫作品在我国的译介出现了两个高潮。20 世纪20—40 年代虽是伍尔夫作品译介的第一个高潮,但是总体上对伍尔夫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存在不足;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国内伍尔夫作品译介活动空前活跃,不仅伍尔夫的作品得到了全面译介和出版,而且其意识流实验技巧、小说理论、女性主义思想等均得到深入研究。
二、伍尔夫作品译介对残雪文学创作的影响
伍尔夫对当代女作家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少女作家与伍尔夫都有一种特殊而深厚的情感联系[1],残雪便是其中一例。
(一)伍尔夫的“意识流”与残雪的“自动写作”
1.伍尔夫的“意识流”
伍尔夫不仅是西方“意识流”派的代表作家,更是这一流派的主要阐释者。传统小说情节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发展,但读者往往会质疑现实生活是否真的如此。其原因在于,传统小说注重描写外在世界而忽略了内心世界。意识流写作则与传统小说创作手法大相径庭,作家在创作小说时十分注重人物心理描写,小说情节更是随着人物的意识活动而展开。
伍尔夫的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就记录了主人公内心意识流动的过程。小说开头便聚焦主人公“我”的内心世界。“我”看到墙上的斑点,起初,“我”假设那斑点是一枚钉子,由钉子又联想到挂在上面的肖像画。随后,“我”依旧不明白那斑点是什么,由此联想到了充满偶然性的人生与宇宙。接着又假设那斑点是玫瑰花瓣、木板裂纹等许多事物,引起了“我”关于生命与世界的无限遐想。最后,“我”发觉原来那斑点是一只蜗牛,至此主人公停止联想,全文结束。由此可以看到,整篇小说的情节是跳跃多变的,随着主人公的意识流动而发展。
2.残雪的“自动写作”
残雪是这样定义“自动写作”理念的,即“笔比自己先行”[2],下笔前不需要理性构思,而是将下意识涌现出来的语言记录下来。这与西方“意识流”的文学创作理念十分契合。
这样的写作理念使小说故事情节缺乏紧密的逻辑联系,人物对话也彼此不连贯。以残雪短篇小说《山上的小屋》为例:
“抽屉永生永世也清理不好,哼。”妈妈说,朝我露出一个虚伪的笑容。
“所有人的耳朵都出了毛病。”我憋着一口气说下去……
“每次你来我房里找东西,总把我吓得直哆嗦。”妈妈小心翼翼地盯着我。
“这是一种病。”
“他们帮你重新清理了抽屉,你不在的时候。”小妹告诉我,目光直勾勾的,左边的那只眼变成了绿色。
“我听见了狼嗥”我故意吓唬她……[3]
从以上小说片段可以看出,“我”和家人们似乎思维紊乱,每个人都在自说自话,且彼此间的对话缺乏紧密的逻辑和联系。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山上的小屋》中,而且残雪其他作品中的人物语言都有这样的特点。正因为残雪遵循的是“自动写作”的理念,这样的潜意识记录往往呈现出碎片化的意象,缺乏明显的逻辑。
由此可见,两位女作家的写作方式存在共性和差异性。残雪的写作方式是反传统、反理性的,强调只记录潜意识的想法,这与伍尔夫注重心灵写作的精神主义相契合。也可以说残雪的文本创作实践中,融入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以及西方“意识流”。二者的差异性在于,残雪的“潜意识”体现在不同人物紊乱的思维、缺乏逻辑的对话上,使得创作出的人物往往是自我裂变的,是对立统一的存在;而伍尔夫“意识流”小说的故事情节,往往随着主人公内心意识的不断变化而展开。
(二)“双性同体”的叙事手法比较分析
1.伍尔夫与“双性同体”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阐述了“双性同体”的理论思想。她指出,虽然人在生理上分为两性,但是大脑却没有性别之分。她认为,大脑的完整性体现在将两性结合起来[4]。在其长篇小说《奥兰多》中,描述了主人公奥兰多跨越几个世纪的性别转变过程,完整的双性人格使其发挥了最大的人生价值。这篇小说体现了伍尔夫对“双性同体”理论的推崇,以及对两性共同解放的追求,引领了当代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方向。
2.残雪与“双性同体”
残雪小说创作是指向自我的,深入灵魂世界。残雪笔下的人物颠覆传统的性别角色,无论男女都是由自我裂变而来,分别代表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自我的某一个侧面,他们是对立统一的存在,具有“双性同体”结构。以小说《公牛》中的夫妻对话内容为例:
“花瓣变得真惨白。夜里,你有没有发现这屋里涨起水来?我的头一定在雨水里泡过一夜了,你看,到现在发根还往外渗水呢。”
“以后决不再在半夜吃饼干。我的板牙上有四个小蛀洞,两个已经通到牙根……”
“一种奇怪的紫色,那发生在多少年以前。你记不记得那件事?那扇玻璃门上爬满了苍蝇,从门洞里伸出头来。树叶在头顶哗啦啦地响,氨的臭气熏得人发昏。”
“你看,”他朝着我龇出他的黑牙,“这里面就像一些田鼠洞。”[5]
从夫妻俩的对话可以看到,他们虽然处在同一个空间,却在自说自话,似乎活在两个世界。其实,妻子与丈夫是自我人格的两个裂变。夫妻的对话中,妻子关心的是外面“被雨水泡过的花瓣”和“奇怪的紫色”,象征着“灵”的世界,而丈夫关注的是牙齿的疼痛,意指“肉”的苦痛遭遇,二者呈现出两性的对应。
由上述分析可知,伍尔夫与残雪的“双性同体”叙事方式皆指向女性主义。《奥兰多》打破了性别认识的单一性和局限性,寻求男女两性的解放和平等,残雪的“双性同体”是一种超越性别文化的叙事方式,追求女性人格的独立。但同时,两位作家亦有区别,伍尔夫的“两性”是和谐共存的,因而主人公奥兰多的性别转换是循序渐进、十分平和的;而残雪创作的“两性”,相互矛盾,充满斗争却又相互依存。因此,与伍尔夫相比,残雪多了一份独特的自信[6]。
(三)女性主义观念的比较分析
1.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观念
伍尔夫有着非常清醒、自觉的女性意识,对后世女权主义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女性主义代表作《一间自己的屋子》《妇女与写作》中的观点深深影响了我国当代女作家的文学创作。王建香曾指出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立场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成为自己。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在政治、经济、婚姻、教育等方面受到了全方位的压迫。女性长期处于从属的地位,现实生活受到诸多限制。伍尔夫敏锐地察觉到女性的不公平遭遇,指出女性首先要成为自己。二是女性要想争取社会地位,前提就是要获得经济地位。女性若想成为自己,必要前提是要实现经济独立。三是克服女性的自我贬义。这就需要回答拥有了自己的“房间”后,女性要如何建立自信这一问题。伍尔夫指出,首先,女性树立自信就必须改变妄自菲薄的态度;其次,女性要建立完善的自我价值观[7]。
2.残雪的女性主义观念
残雪是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作家,她尤其尊崇西方的女性主义,对中国的女权主义和女性写作颇具微词,尤其批判我国女性文学作品中女性对男性审美的迎合现象,而对西方女性主义寻求的平等十分推崇。残雪的写作目标是实现彻底的个性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8]。这与伍尔夫“成为自己”的女性立场不谋而合。这一点在其小说作品中都得以体现。
残雪小说中的女性,不再是男权文化下的女性形象,她们自信张扬,拥有自己的个性化语言[9]。例如,残雪在长篇小说《五香街》中创造了一个女人主导的世界,所有的女性尽情地展现自己真实的一面,毫不避讳地谈论有关性的话题。不仅如此,她们在日常对话中也自信张扬,宣扬着女性在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作用,打破了女性从属男性的思维。
总的来说,伍尔夫强调女性经济与人格的独立,拒绝做男权社会的附属品;残雪注重重塑自由与个性的女性形象,找回男权文化下被剥夺的话语权。残雪视女性文学创作为颠覆传统、解构权威、重新审视两性关系的重要途径,并且主张在更深层次上实现两性的交融。这是对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一种继承与发展。
结语
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其“意识流”小说家、女性主义文化先驱的身份被中国文坛广泛接受,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作家残雪亦认可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有对西方文学经典的接受和吸收。残雪擅长潜意识写作,其作品中女性解放的主题,无一不让人联想到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虽然残雪与伍尔夫在文学创作和思想上存在共性与差异性,但从残雪丰富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其在创作手法和文学思想上亦有自己的个性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