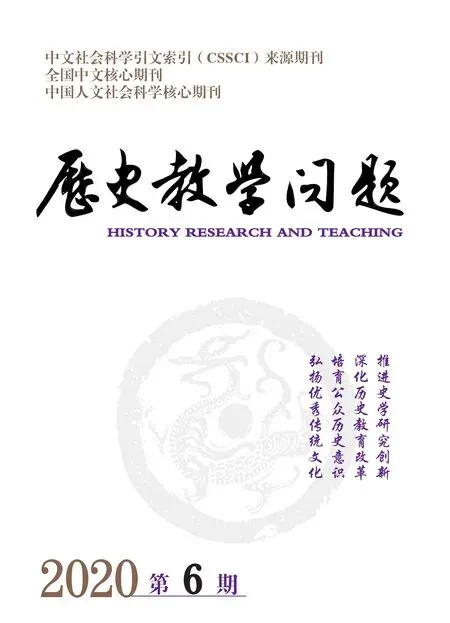森鸥外与明治日本的“黄祸论”
李 凯 航
1903 年,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森鸥外(1862—1922)作为第二军医部部长即将奔赴中国战场。然而在临行前,他特意举行了两场有关反对西洋“人种主义”的演讲,即《人种哲学梗概》和《黄祸论梗概》。由此可知,对于当时甚嚣尘上的“人种论”与“黄祸论”问题,森鸥外展示了特别的关心。在他看来,“人种论”已经成为“时代趋势吃紧的问题了”。①森鷗外「人種哲学梗概広告文」『鷗外全集』第38 巻、岩波書店、1974 年、625 頁。森鸥外对人种问题的关心,可以追溯其1884—1888 在德国留学的经历,②小堀桂一郎『若き日の森鷗外』、東京大学出版会、1969 年、185—293 頁。以及当时喧闹一时的话题:田口卯吉(1855—1905)的“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和姉崎正治(1874—1949)的“洋学无用论”。③林正子「日清·日露両戦役間の日本におけるドイツ思想·文化受容の一面 総合雑誌『太陽』掲載の樗牛·嘲風·鷗外の言説を中心に」、『日本研究』1996 年12 月、149—183 頁。而他所谓的“时代趋势吃紧的问题”,无疑是指日本经历过义和团事变,初次成为白种人的同盟国后,又在日俄战争中不得不与白种人帝国发生的战争。④飯倉章『黄禍論と日本人 欧米は何を嘲笑し、恐れたのか』、中央公論新社、2013 年、115—144 頁、廣部泉『人種戦争という寓話 黄禍論とアジア主義』、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7 年、31—41 頁。在此期间内,俄国大力宣扬的“黄祸论”,对日本政府的战争借款以及战后的条约改正运动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⑤有关日俄战争时期战争借款问题,参见板谷敏彦『日露戦争、資金調達の戦い高橋是清と欧米バンカーたち』、新潮社、2012 年。
在日本,有关黄祸论的研究非常之多。⑥有关日语学界的黄祸论研究史整理,参见李凯航:《明治日本的黄祸论与人种论》,《史林》2020 年第2 期。另,本文部分内容可参见李凱航『明治末期における黄禍論批判』(同志社大学博士论文,2018 年)的序章与第一章。然而,对于森鸥外与欧洲人种/黄祸论之关系的研究却并不多见。⑦有关中文学界对森鸥外与黄祸论关系的考察,可参见罗福惠:《“黄祸论”与日中两国的民族主义》,《学术月刊》2008 年第5 期;袁咏红:《“黄祸”论刺激下的日本人种、民族优胜论》,《世界民族》2009 年第3 期;许赛锋:《“黄祸论”与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外交:以人种意识为视点》,《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4 期。据查,最早注意森鸥外的是平川祐弘。平川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将当时的“黄白人种冲突”理解为“东西方文化冲突”。比如,他认为,森鸥外是以“知性的诚实处理黄祸论的具有代表性的明治知识人”,其批判“着眼于历史的相对性”,具有“现实主义的改良主义倾向”。①平川祐弘『和魂洋才の系譜 内と外からの明治日本』、河出書房新社、1971 年、137—154 頁。
此后,历史学家桥川文三也认为森鸥外是“考察‘黄祸论’历史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冷峻地指出人种哲学具有空想性与粗糙性”。但在桥川看来,森鸥外的黄祸论批判显得过于情绪化,只不过是“意气用事”而已。②橋川文三『黄禍物語』、筑摩書房、1976 年、28—37 頁。与此相反,野村幸一郎认为,森鸥外的“黄祸论”批判是基于“现实主义政治的路线”,处理的是“彻底的形而下问题”。 野村指出,“(森鸥外所谓的)人种的表象是一个国家经济军事实力的综合”。③野村幸一郎「アジアへのまなざし鷗外·天心の黄禍論批判」、『文学』2007 年3 月、103—118 頁。
虽然关于森鸥外的人种/黄祸论批判究竟是客观的政治评论,还是一时的感情用事,桥川与野村有着不同的评价,但二者都认为森鸥外的人种/黄祸论批判源自于当时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
此外,廖育卿认为森鸥外对德国有一种“纠结的心理因素”,所以在《人种哲学梗概》和《黄祸论梗概》中“几乎看不到他个人的意见”。这两篇讲稿不过是森鸥外的“梗概”系列作品,仅仅是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而已。④廖育卿「明治期の「黄禍論」言説に見た森鷗外 講演『人種哲学梗概』と『黄禍論梗概』を中心に」、『熊本大学社会文化研究』2009 年3 月、233—248 頁。
最后一种意见多见于森鸥外的传记作品中,他们把这两篇人种/黄祸论的讲稿视为日俄战争前,森鸥外所具有的浓厚的民族主义气氛的象征,强调这不过是为了鼓舞军队士气而已。⑤小堀桂一郎『森鷗外 日本はまだ普請中だ』、ミネルヴァ書房、2013 年、286—289 頁、山崎國紀『評伝森鷗外』、大修館書店、2007 年、240—242 頁、延芳晴『鷗外と日清·日露戦争』、平凡社、2008 年、151—153 頁、小林一夫『森鷗外論 現象と精神』、星雲社、2009 年、20—22 頁。
然而事实上,以上四种类型的研究都只强调了森鸥外人种/黄祸论批判的一个侧面,忽视了他对人种问题的多层次关心。所谓“人种”之概念原本就是具有科学、政治、文化、精神等诸多要素,⑥有关近代日语文献中“人种”概念的特殊性,参见家坂和子『日本人の人種観』、弘文堂、1980 年、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岩波書店、2001 年、54—77 頁、與那覇潤「近代日本における「人種」観念の変容 坪井正五郎の「人類学」との関わりを中心に」、『民族学研究』2003 年6 月、85—97 頁。如果只强调森鸥外人种/黄祸论批判的一个方面,会窄化研究视野。因此,本文将广泛搜罗森鸥外与人种/黄祸相关的言论,明确其各个时期不同的问题意识,特别是通过考察先行研究中被忽略的《卫生新篇》,指出虽然从两篇人种/黄祸论的讲稿来看,森鸥外具有某种程度的“反人种主义”倾向,但是基于自然科学的“人种卫生学”理论,森鸥外反而是一个彻底的“人种主义者”。
一、明治日本人种/黄祸论的兴起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是以“文明开化”为口号,以西方近代国家体制为目标而进行的一次政治、经济、文化变革。这次变革最终的成果体现为,在被称“文明与野蛮”的对决的甲午战争中,日本一举击败腐败、落后的清王朝,成为远东地区的第一大国。这使得日本人也产生了“文明国家”的自我认识。⑦中村尚美「日本帝国主義と黄禍論」、『社会科学討究』1996 年3 月、781—811 頁。然而,日本的崛起却被西方人认为是阻碍他们在远东地区展开殖民活动的重大事件,故以遏制日本为目的的“黄祸论”逐渐兴盛起来。
比如,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就致信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称“为了对抗日本,保护欧洲的利益,欧洲各国应该联合起来抵挡数量巨大的黄种人。”不仅如此,德皇还命令画师克纳科弗斯(Knackfuss)创作《黄祸图》在欧洲各国政要名流之间传阅,要求各国一致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因为德皇不遗余力的宣传,“黄祸”作为西方人对黄种人的歧视话语在欧洲社会流行开来。在日本方面,文部省大臣西园寺公望(1894—1940)于翌年将“黄祸”的相关消息详细地上奏明治天皇。⑧有关德皇威廉二世与“黄祸图”之关系,参考飯倉章『イエロー·ペリルの神話 帝国日本と“黄禍”の逆説』、彩流社、2004年、95—98 頁。此后由德皇主导的“三国干涉”,也可以说是这种黄祸思想的具体外交结果。①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日本外交史辞典編纂委員会編『新版·日本外交史辞典』、山川出版社、1992 年、276—277 頁。
尽管如此,正如“卧薪尝胆论”在甲午战争后流行开来一样,日本帝国为了复仇选择了忍耐。②有关三国干涉后“卧薪尝胆”的言论,大谷正『日清戦争 近代日本初の対外戦争の実像』、中央公論、2014 年、222 頁。随即,在日本知识分子中,围绕着如何消解强加在日本头上的“黄祸”之恶名,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意见。即“大亚细亚主义”“文明开化论”以及“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
首先是“大亚细亚主义”,其主旨在于强调黄种人之间的相互团结,把西方人歧视亚洲人的“黄祸”转化为动员黄种人抵抗西方人的“白祸”。比如,当时东邦协会的副会长近卫笃麿(1863—1904)就因为恐惧西方人“分割支那”而抛出了“支那保全论”。在《太阳》杂志上,他撰文《同人种同盟 附支那问题研究之必要》称,“东洋之前途难免沦为人种优劣竞争之舞台。吾等最后之命运不过黄白人种之竞争。于此竞争中,日本人与支那人同属黄种人,共为白人种之仇敌”。因此,他呼吁“如今所有的黄种人都应谋求同人种保护之策略”。③近衛篤麿「同人種同盟 附支那問題の研究の必要」、『太陽』1898 年1 月、1—3 頁。
然而,在明治政府看来,以上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呼声无疑是助长了“黄祸论”的泛滥。因此,明治政府对与中国结盟的外交策略十分警惕。事实上,帝国政府已然决议“严防黄祸论再燃”。在帝国议会发布的《与俄交涉失败后对清韩两国之政策》中就明文规定,“与俄国作战中,日清两国相合乃西洋诸国之大忌。其危害之处在于,西洋诸国刺激黄祸论之兴起,再次遭至德法等国干涉”。由此表明,“日清两国相合”对明治帝国政府来说仍然是最为敏感的外交辞令。④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原書房、1965 年、219 頁。
明治帝国政府的顾虑是,“黄祸论”会给日本的战争借款与条约改正带来不利影响。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1854—1936)受命前往英国募集战争借款。他谈到,“日俄战争乃白种人与黄种人之战争。而俄国与英国皇室为亲戚关系。因此作为白人帝国的英国对日本战争借款或多或少有不情愿之处”。不仅如此,英国一度对日本的战争表示“局外中立”,这让高桥是清非常不满。⑤大島清『高橋是清 財政家の数奇な生涯』、中公新書、1999 年、53—59 頁。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军费预算已高达29000 万日元的规模。但是随着战争的严峻形势,其实际开支已超过198612万日元。战争借款对日本的战争局势而言,可以说是起着生死攸关的决定性作用。⑥山室信一『日露戦争の世紀 連鎖視点から見る日本と世界』、岩波書店、2005 年、125 頁。
因此,明治政府积极地从国内与海外两方面抑制“黄祸论”,为战争借款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在国内,明治政府强调新闻与宗教自由,加大对外国人,特别是俄罗斯人的安全保障,努力宣扬自己是文明国家的对外形象。⑦飯倉章『黄禍論と日本人 欧米は何を嘲笑し、恐れたのか』、130—132 頁。在海外,明治政府向欧美舆论界派出末松谦澄(1855—1920)、金子坚太郎(1853—1942)等游说人员,诱导像《泰晤士报》《时代》等知名西方媒体对日本进行有利的报道。⑧松村正義『日露戦争と金子堅太郎 広報外交の研究』、新有堂、1980 年、同『ポーツマスへの道 黄禍論とヨーロッパの』、原書房、1987 年。总之,是以“文明开化”的国家形象向西方展示日本努力西洋化的决心,而与落后的、野蛮的、亚细亚诸国保持距离。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1838—1922)还宣称“露骨之人种言论有伤诸国之感情。此种于国家间友谊不利之言论乃政治家所警惕之事,也绝非帝国政府之所为”。⑨山県有朋「対支政策意見書」、『明治百年史叢書』第16 卷、原書房、1966 年、11 頁。他认为,尽管日本被侮辱为“黄祸”,也不应该用人种竞争论来挑起日本与西方的对立。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有学者认为作为第二军医部部长的森鸥外,“不论其主观的动机为何”,“只要他身处明治政府内部,就只能将亚细亚作为他者来对待,而与列强共进退,走向脱亚论的道路”。⑩野村幸一郎「アジアへのまなざし鷗外·天心の黄禍論批判」。这样的意见强调森鸥外言论活动的客观限制,值得参考。但是,森鸥外最终是否就“走向脱亚论的道路”,仍然需要更为详细的考察。
在对抗西方“黄祸论”的策略中,除了以上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文明开化论”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以外,明治时代以文明史论名震一时的田口卯吉提出的“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可以说是对“黄祸论”非常独特的反应。1904 年,随着日俄战争的白热化,田口卯吉为了消解“黄祸论”给日本带来的外交压力,出版了《破黄祸论 一名日本人的真相》一书。该书认为,“与其说日本人是黄祸,不如说在历史上被匈奴、鞑靼人以及蒙古人种征服过的俄罗斯人才是真正的黄祸。他们身上有着野蛮的蒙古人血统。如果说黄祸是指鞑靼人入侵的话,那么现在俄罗斯占领满洲地区,破坏世界和平,才是世界的黄祸”。田口卯吉强调历史上俄罗斯人与蒙古人的混血关系,指责俄罗斯才是真正的黄祸。此外,他还从语言学的角度进一步区分日本人与匈奴人、蒙古人、鞑靼人在人种上的区别。“从语法上来说,拉丁语、希腊语、梵语与欧洲诸国语言相去甚远,而与我日语类似”。“西洋的语言学家自称为雅利安人种,却把我人种贬低为图兰人种,实则本末倒置,谬误至极”。“现如今梵语的语法仍然无暇地保留在我日语中,我们其实比欧洲人更加接近雅利安人种”。“把日本人贬斥为黄祸实为不解事实真相,无稽之谈”。①田口卯吉『破黄禍論 一名日本人種の真相』、経済雑誌社、1904 年。
虽然田口卯吉论说的本意旨在借“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以提高日本人的自尊心,然而,田口卯吉以上的论说却遭到了日本大多数学者的激烈批判。语言学家新村出(1876—1967)抨击道,“田口卯吉君的学说在科学上毫无价值,在问学上也毫无道义”,“他的谬误是根本上的谬误,是整体上的谬误,而非一时一处的谬误”。②新村出「田口博士の言語に関する所論を読む」『新村出全集』第1 卷、筑摩書房、1971 年、104 頁。前总理大臣大隈重信(1838—1922)也在公开演讲中质疑:“雅利安人的血统就那么高贵吗?我深表怀疑。不论怎么说,我们日本人绝不是雅利安人种。”③大隈重信「東亜の平和を論ずる」『大隈伯演説集』、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07 年、111 頁。就连原本把田口卯吉视为文明史论的开拓者、东西两洋兼通的大学者的森鸥外也斥责道:“田口卯吉君的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浅薄无知,其语言学上的立论毫无根据。做为学者,不应下此轻率之言。”④森鷗外「鼎軒先生」『鷗外全集』第26 卷、421 頁。以上学者们对田口卯吉的批判,一方面是与语言学与人种学的争论有关,另一方面,也有着对大和民族自信心的维护。
如上所述,三国干涉以后,日本对人种/黄祸论的批判分为即“大亚细亚主义”“文明开化论”以及“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森鸥外在直接批判“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的同时,因为身处军务高官的角色,也不可能公开赞成“大亚细亚主义”。因此森鸥外很可能只剩下追随政府“文明开化”这一条路可以选择。然而,实际上,森鸥外对人种论的研究与批判,经历了更为复杂的纠结与动摇。
二、日俄战争与《黄祸论梗概》
甲午战争以后,清朝孱弱的国力已经暴露于世界。西洋列强所谓“黄祸论”的矛头也已经直指新兴帝国日本。而且,经历过三国干涉、义和团事变等,西洋列强对帝国日本的警戒不减反增,在日俄战争之前达到了顶点。森鸥外的演讲《黄祸论梗概》,⑤森鷗外「黄禍論梗概」『鷗外全集』第25 巻、1971 年、537—568 頁。相关引用皆出于此处,以下不赘述。正是在此危机时刻。
虽然森鸥外的演讲正值日俄战争爆发之际,但他在演讲开头就表明“对黄祸论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从十年前就开始搜集各种资料”。因此,我们对森鸥外的人种/黄祸论研究,也必须追溯这十年期间的各种历史情况。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镇压义和团运动首次成为列强的日本军人的体验。1900年,日本为了镇压义和团,加入了八国联军。一般而言,日本成为西方的同盟国,理应对西洋人抱有信任感,但是,森鸥外却呼吁对西洋人保持警惕。他在一篇针对义和团运动的演讲《北清事变之观察》中强调,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兵主要是通过书籍、洋人教官、留学生以及旅行者与西洋进行间接的接触。但是,在北京的战场上,上至军官下至兵卒,都可以与西洋人进行直接的接触。面对道德败坏的西洋军人,日本人已经推崇过甚,现在正是日本人打破对西洋人无限崇拜的最好时机。⑥森鷗外「北清事件の一面の観察」『鷗外全集』第34 巻、216—220 頁。
众所周知,在八国联军中,特别是德国与俄国军队,在北京战场犯下抢劫、纵火、强奸等大规模的暴行。但是由于日本人是第一次与西方列强同盟,日本政府视之为“开国以来之首”的重大事件,强调“野蛮之行为有损帝国之威严”,勒令日本士兵“果敢奋斗以示各国军队”,“以身作则,严守军令军规”等等。结果,由于日本兵在北京战场上亲眼目睹了西洋兵的种种暴行,以往理想化了的西洋人形象随即坍塌。日本报纸也对战场的暴行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特别是俄罗斯人残酷地杀戮与掠夺的形象被广泛地宣传。由此,“恐怖的俄罗斯人”形象随即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得以形成。①小林一美『義和団戦争と明治国家』、汲古書院、2008 年、340—352、357 頁。比如,当时伏病卧床的中江兆民(1847—1901)就记载道:“新闻报纸上时常刊登恐惧俄罗斯的文章”,“尤其是政府过度地恐惧俄国人”。“西洋人的物质学术,虽然让人钦佩,但是西洋人的义理却并不足畏,实则远远劣于我国”。②中江兆民『一年有半 続一年有半』、岩波書店、1955 年、89—91 頁。在中江看来,西洋人的道德其实并不如他们自身所宣传的那么高尚,所谓文明,也仅仅是物质之术而已。
在《黄祸论梗概》中,森鸥外同样对西洋人的道德持批判态度。
最近新出“黄祸”一语。殊不知在北瑷珲,俄国人驱赶五千清国人,残杀于黑龙江畔,又蚕食南边的旅顺、大连,强行租界辽阳,可谓是忤逆人道,破坏国际法,骇人听闻。
“人道”“国际法”原本是西洋人的理论,森鸥外却借此来批判俄国人对中国人的暴行,打破白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此外,就黄祸论而言,森鸥外认为不过是日俄战争的宣传而已。“战争于我不利,白人的黄祸论则会处于萌芽状态。而我军若是高奏凯歌,白人则会借此打压我军胜利果实。”“我们胜利了,就会成为黄祸;而我们失败了,则成为了野蛮人。”③森鷗外「黄禍」『鷗外全集』第19 巻、161 頁。森鸥外可谓是一语道破了黄祸论的双重标准。他认为,不论日本在战争中胜利与否,“黄祸论”都会抑制日本的外交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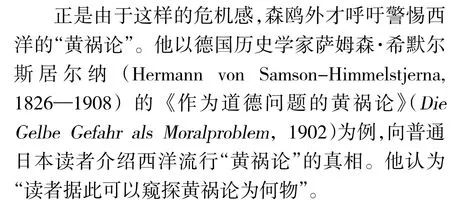
根据希默尔斯居尔纳的描述,“黄祸论”可以分为“和平的黄祸”与“战争的黄祸”。所谓“和平的黄祸”是指,“黄种人将会妨碍白种人的商业与工业”。而所谓“战争的黄祸”则是指,“黄白两人种迟早将会爆发大战争”。森鸥外对此分别批判道,“论者(指希默尔斯居尔纳)所谓的和平的黄祸乃由于西洋人自身道德问题的错误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而“战争的黄祸是因为西洋人妄自于支那划分势力范围,行使错误政策所致”,“因此西洋人迟早会被逐出支那”,此“两点之错误皆在西洋自身”。换言之,在森鸥外看来,希默尔斯居尔纳的“黄祸论”是在推卸西洋人的责任,欲转嫁至日本人身上而已。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希默尔斯居尔纳与森鸥外对黄祸论的关注点其实有所不同。相对于“战争的黄祸”, 希默尔斯居尔纳更强调“和平的黄祸”。正如希默尔斯居尔纳所说的“黄祸论”起源于“对面包的嫉妒”,“欧罗巴人把东亚看成是自己的商品决战场”。
然而,随着日本帝国的膨胀,日本与西洋列强争夺中国的竞争越发激烈。作为战争的直接参与者,相比于希默尔斯居尔纳,森鸥外更为关注的是“战争的黄祸论”。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西洋、日本、中国三者关系的评论来分析。
希默尔斯居尔纳的《作为道德问题的黄祸论》一书,其主要内容是从精神、道德、宗教等九个方面全面比较日本与中国。其主要态度是,赞美中国而贬低日本。例如,希默尔斯居尔纳认为日本人没有思想的力量,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而中国人沉着冷静,特别是官僚阶级高深、单纯,具有理论思维;日本人是恶俗的唯物论者,而中国立宗教,尚慕古风,崇拜祖先;日本商人信用低劣,而中国人富于宗教精神等。总而言之,希默尔斯居尔纳有意地“区分同为黄色人种的支那人与日本人”,“抬举支那人而责难日本人”。
而在森鸥外看来,希默尔斯居尔纳批判日本的原因不外乎日本是“西洋人的当面之敌”而已。他指出,日本人虽然与白人并肩作战,与同为黄色人种的“支那”为敌,甚至跻身于英国的同盟国,但是一般的白色人种一直把我们与其他黄种人混为一谈,带有厌恶的警戒之情。这里森鸥外明确地否定日本人作为“名誉白人”的自我陶醉之情,指出他们与白人的斗争其实不可避免。因为对于西洋人而言,相对于支那,日本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正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森鸥外才得出结论,“即使并不情愿,我们日本人也必须站在白人的对立面”。换言之,森鸥外并不认可政府的外交政策,而是认为黄白人种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政府应该早做准备。
三、《人种哲学梗概》与雅利安人种优越论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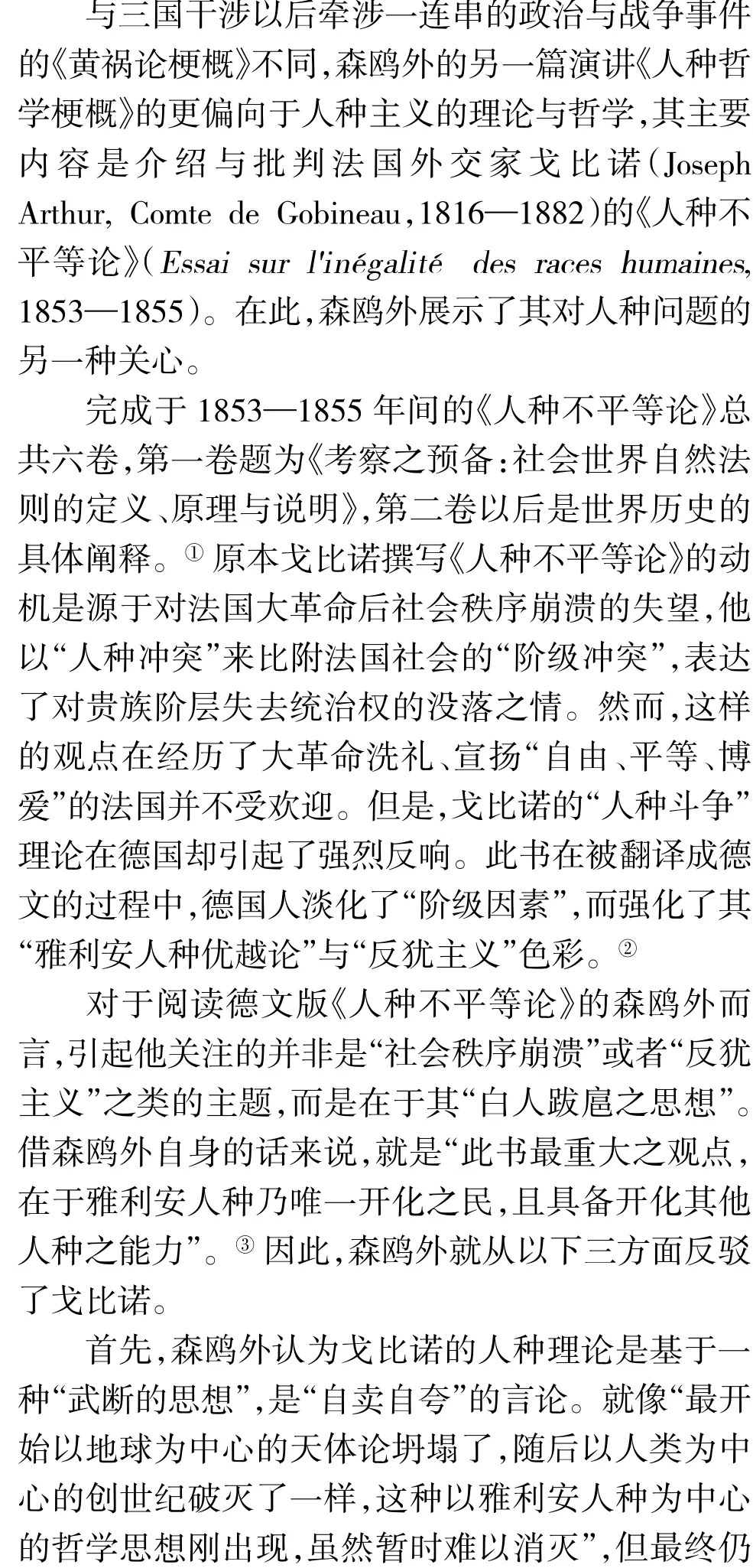


四、“人种卫生学”与“反人种主义”的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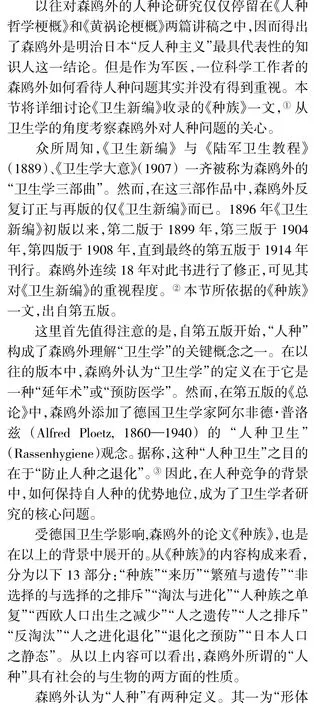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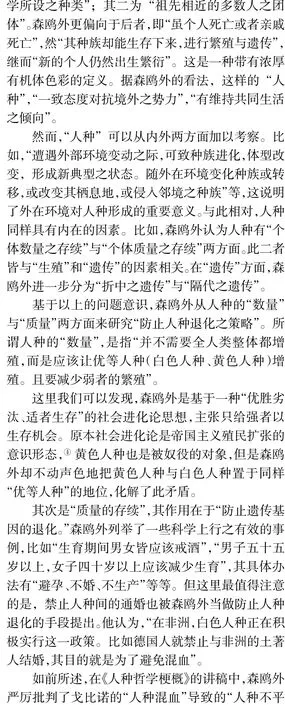

等论”。但是,在对卫生学的研究中,森鸥外对异人种间的混血导致人种退化却深信不疑。他与西洋学者的差异在于,“东非的德意志人与土人之婚嫁”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混血,故应该被禁止,但白人与黄种人皆为“优等人种”,故不属于禁婚之列。森鸥外继而写道,“白色人种与黑色人种的混血儿虽然优于灵智黑人,但其繁殖力却远不如白色人种。白色人种与铜色人种的混血儿亦如此”。这里森鸥外不仅明显地把黑色人种划分为劣等人种,他还给出了科学的证据:
白色人种与黄色人种渐渐得势。黑色人种却日益困苦。人种间的优劣之分在于其天才的多寡,距泥猴的远近以及血清组合的单复数。
正是“据泥猴的远近”以及“血清组合的单复数”这样的西方生理学的标准,构成了森鸥外人种优劣观的基础。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森鸥外批判人种主义的局限所在。一方面,他反对西洋人对黄色人种的歧视,但是对构成西方人种主义基础的生理学、卫生学并不持任何怀疑的态度。不仅如此他还借用同样的人种主义原则,对黑色人种表现出赤裸裸的歧视。
由此可知,森鸥外对人种问题的关注不仅没有停留在《人种哲学梗概》和《黄祸论梗概》两篇讲稿之中,反而随着卫生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在某种意义上而言,《种族》这篇小论文才反映出森鸥外对人种问题的客观的认识。这是因为《人种哲学梗概》和《黄祸论梗概》仅仅是日俄战争期间的特殊产物,讲稿之中也多有对白人帝国主义的义愤之辞,其中政治口号与民族主义情绪随处可见。但是阅读论文《种族》时,可以感觉全篇都是冷静客观的科学分析,用着极为标准的论文文体,注释也极为详尽。通过《种族》的分析,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森鸥外对导入欧洲卫生学最新研究成果的积极倡导;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极力主张“黄白人种平等”的背后,有着对西洋“人种主义”深刻的危机感。
结 论
《人种哲学梗概》出版以后,森鸥外被某些学者嘲笑为“梗概”博士。但是他却认为,“应该认可哲学史家与哲学家具有同样的功劳。然所谓哲学史,其实不出梗概之范畴。余在未来也会继续出版此类梗概著作,甘受世人嘲讽”。森鸥外在此表明,“哲学史”与“哲学”具有同样的价值,他还会继续介绍与批判西洋哲学作品。在这个意义上,《人种哲学梗概》和《黄祸论梗概》不仅对于森鸥外个人,其实对于整个明治思想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森鸥外通过对西洋哲学的研究,一方面看透了日本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深刻地指出“即使并不情愿,我们日本人也必须站在白人的对立面”的严峻形势;另一方面,他认为日本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明治维新,已经取得了不劣于西洋文明国的成就,这一点不能因为“人种”的差异被否定。日本人应该有信心继续明治维新的伟业。
从上诉两篇演讲观来,似乎可以看出坚定的“反人种主义”的“森鸥外像”。但是,作为卫生学者的森鸥外,引用西洋生理学、生物学的知识,积极主张“黄白人种平等”的同时,却赤裸裸地保留了对黑人的歧视性看法。这一矛盾的见解,一方面反映了日本人代表黄种人在国际社会要求“人种平等”的理论主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森鸥外自身对西洋科学,特别是卫生学的深信不疑,反而促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人种主义者”。
——写作品梗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