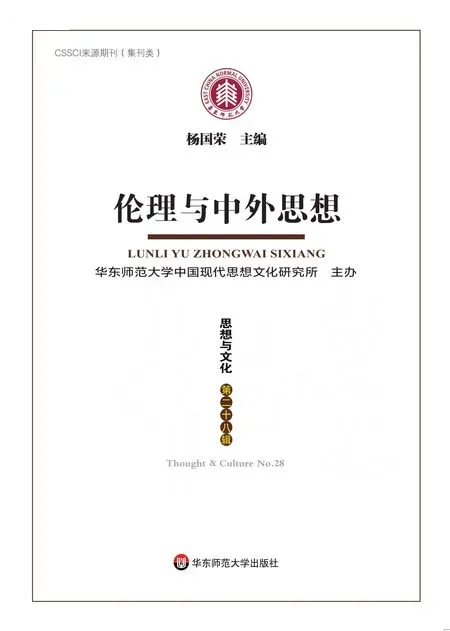冯契“智慧说”与德性伦理学*
●
冯契与当代“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1)关于virtue ethics的译法,之前大陆学界多译作“德性伦理学”,近几年多译作“美德伦理学”,台湾学界多译作“德行伦理学”。本文采用“德性伦理学”的译法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因为古希腊词arête(virtue是其对应的拉丁词)的含义不限于伦理美德,一是冯契也十分强调“德性”的本体论意义。并无交集,然而,他的“智慧说”却实质性地展示出了诸多德性伦理学的内容与特征。从广义认识论之“理想人格如何培养”到“智慧说”之“人的自由与真善美”的全面发展,从“化理论为德性”到“德性自证”,从对中国传统儒、道、释的理想人格的批判性考察,到“平民化自由人格”的提出,在此诸多理论创获或哲理格言中,我们看到,“德性”或“人格”概念与冯契“智慧说”如影随形,构成其“智慧说”的重要内容。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冯契的“智慧说”与德性伦理学做一交互诠释、互相发明的工作,亦可为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本文将首先勾勒冯契“智慧说”与德性伦理学的基本结构及其相关性,然后集中讨论冯契“智慧说”体系中的德性论。
一、 “广义认识论”与“整个的人”
当冯契晚年时(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已渐成气候,晚年的他对此应该没有太多的信息,但是,其“智慧说”与德性伦理学却有着实质性交集和共同的关怀。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对德性伦理学与冯契的“智慧说”及其相关性略作说明。
我们先看德性伦理学。学界公认,牛津大学哲学教授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1958年发表的《当代道德哲学》一文,对以康德式伦理学(义务论)和功利主义(后果论)为主流的西方当代伦理学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为当代德性伦理学在西方的复兴指明了方向,设定了议程,即把伦理学研究重心从“义务”概念转移到“与人类幸福相关的美德”上来。(2)参见徐向东编: 《美德伦理与道德要求》,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导论。经过半个世纪多的发展,时至今日,尤其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哲学圈,德性伦理学已与西方近现代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两种规则伦理学即康德式伦理学(义务论)和功利主义(后果论)渐成鼎足而三之势。(3)参见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 《美德伦理学》,李义天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6年,导论;黄勇: 《当代美德伦理学——古代儒家的贡献》,北京: 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导论,第3页。
不过,义务论、后果论、德性论三分法并没有得到学界普遍认可,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定性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李明辉便对此三分法提出质疑,他认为义务论和目的论是“既穷尽又排斥”的关系,其中没有德性伦理学的独立地位,德性伦理学要么从属于义务论,要么从属于目的论,他从康德伦理学的立场,很自然地把德性伦理学划归为目的论伦理学的一种形式。(4)李明辉: 《儒家、康德与德行伦理学》,《哲学研究》,2012年第10期。然而,牛津大学伦理学家罗杰·克里斯普(Roger Crisp)却表达了与李明辉不同的看法。克里斯普认为,如果把伦理学理解为意在说明何谓对错行为的理论,我们就无法认同所谓义务论、后果论、德性论的三分格局,事实上只有义务论和后果论的两分,德性论只是义务论的一种形式,即与“以原则为基础的义务论”相对的“不以原则为基础的义务论”;但是,如果我们把伦理学理解为说明德性的道德价值的理论,把焦点集中在德性的价值问题,而不是关注正确行为的概念,那么,德性伦理学作为一种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的某种人的理论便有了属于自己的理论空间。(5)R.克里斯普: 《伦理学有第三种方法吗?》,王腾译,《世界哲学》,2017年第2期。就关注行为对错而言,德性伦理学究竟属于目的论还是义务论,这或许还可讨论,这里我们把关注焦点放在克里斯普对伦理学的两种理解上。一般认为,关注行为的对错,这是近现代西方对伦理学的理解;关注德性的价值或成为某种人,这是古代人(中西方都有此传统)对伦理学的理解。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要回到传统伦理学的概念,把“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或“我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作为伦理学的中心议题,特别关注德性的价值。诚如克里斯普所言,在此理解下,德性伦理学自有其理论空间和意义。后文我们将看到,这也是冯契“智慧说”颇为关注的主题。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德性伦理学区别于两种规则伦理学(义务论和后果论)的基本结构与特征是什么。根据当代著名德性伦理学家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的概括,德性伦理学被描述为如下特征: (1)一种“以行为者中心”而不是“以行为为中心”的伦理学;(2)它更关心“是什么”,而不是“做什么”;(3)它着手处理的是“我应当成为怎样的人”,而不是“我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4)它以特定的德性论概念(善好、优秀、美德),而不是以义务论概念(正确、义务、责任)为基础;(5)它拒接承认伦理学可以凭借那些能够提供具体行为指南的规则或原则的形式而法典化。(6)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 《美德伦理学》,第27页。除了(5)之外,赫斯特豪斯基本认同此种通常概括,她本人力图证明德性伦理学也有自己关于正确行为的理论,也可提供行动指南。这说明,至少前四者是德性伦理学的典型特征。
我们再来看冯契的“智慧说”。冯契晚年回忆自己的哲学之路时谈到,学生时代阅读金岳霖著作时,便形成了自己的哲学问题:“和金先生讨论时,我感到碰到了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金先生在《论道·绪论》中区分了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他认为,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的人。研究知识论,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用客观的、冷静的态度去研究。但研究元学就不一样了,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对象上要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结果上,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这是金岳霖先生区别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的论点。”(7)冯契: 《〈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页。冯契当时就认为这种区分是有问题的,他说:“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认识论也不能离开‘整个的人’,我以为应该用Epistemology来代替Theory of knowledge。广义的认识论不应限于知识的理论,而且应该研究智慧的学说,要讨论‘元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8)冯契: 《〈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6页。冯契对这一哲学问题思考的初步成果便是于1944年发表的《智慧》一文。此后,智慧的问题便伴随他一生的哲学探索。在经历了四五十年的探索之后,冯契晚年形成了自己的“智慧说”哲学体系,其文字载体便是他自己命名的《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
在《〈智慧说三篇〉导论》中,冯契把他的“广义认识论”(亦可说“智慧说”)概括为以下四个问题: (1)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2)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3)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4)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9)冯契: 《〈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7页。冯契首先提出这四问题,是在他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绪论》中,他认为从辩正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来回顾哲学史,这四个问题是中西哲学史上反复讨论的问题;而且,在那里,他把这四个问题与康德哲学联系起来,认为前三个问题分别对应康德的感性、知性(关乎纯数学和纯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理性(关乎“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何以可能,用冯先生自己常说的话便是关于“性与天道”的智慧),最后一个问题关乎“自由”,因为冯契所谓“理想人格”主要是指“自由人格”。当然,这里的“自由”是比较宽泛的意义(详后文),不限于今人所热衷讨论的政治自由或“消极自由”。如果我们不从“广义认识论”而是从一般的哲学体系来看的话,前两个是狭义的认识论问题,第三个是元学形而上学或形上智慧何以可能的问题,最后一个是伦理学问题。一般知识论关注由无知到知识,而广义认识论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层,要求“转识成智”(冯契在此借用佛家语,但不必用其原意),由知识飞跃到智慧。知识(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元学智慧)要转化为真正的智慧,离不开具体的人格,因为知识必须实有诸己、落实在个体上才是“具体的智慧”。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的培养在“智慧说”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职是之故,冯契更为重视知识的获得而不是表达,也更为偏好具体的智慧而非抽象的知识。冯契在谈到自己与金岳霖的差别时说:“首先要问如何能‘得’?即如何能‘转识成智’,实现由意见、知识到智慧的转化、飞跃;其次要问如何能‘达’?即如何能把‘超名言之域’的智慧,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亦即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如何去说。金先生当时着重探讨了后一个问题。……而我当时有一个与他不同的想法。我认为虽然智慧的获得与表达不可分割,但首先应该问如何能‘得’,其次才是如何能‘达’。所以,我想着重考察前者。”(10)冯契: 《〈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7页。确实,就广义认识论的“转识成智”来说,智慧(包含德性或理想人格)的获得远比表达更为重要,因为只有表达容易流于谈玄而未必实有诸己,此即孔子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可见,冯契关注“得”而非“达”是与他设定的研究主题即理想人格的培养有关,按照中国传统的理解,“德”就是个体对普遍之“道”有所得而实有诸己。冯契又说:“金先生曾说:‘大致有两类哲学头脑,一类是abstract mind,一类是concrete mind。’他觉得他自己有点偏于abstract,而我这个学生可能比较喜好concrete。”(11)冯契: 《〈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0页。冯契显然默认了这一点,并且认为仅凭静态的抽象,无以把握具体的真理。不难发现,冯契与金岳霖的诸多对照性的区别,根源在于他把金岳霖的“知识论”扩展为“广义认识论”,亦即他晚年命名的“智慧说”,在内容上把元学的智慧和理想人格纳入其中加以关注和研究,这使得他不得不重视知识和智慧的获得而不仅仅是表达,也使得他不能停留于对知识做静态的抽象的分析,而必须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基于社会进化和个体发育的自然过程进行考察,以期达到某种人格化形态的具体真理或智慧。
综上所述,冯契“智慧说”特别关注“整个的人”与“理想人格”的培养,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其“智慧说”的目标;这与德性伦理学关注“我们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行为者”及其“德性”、“品质”等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而且,冯契“智慧说”也确实对德性的培养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论证,提出了不少理论创获。
二、 “自由—德性—智慧”三元结构
以上是就关注主题方面说明冯契的“智慧说”与德性伦理学的相关性,下面我们就理论结构来继续说明这一点。如所周知,古希腊人持有目的论的世界观,认为万事万物皆有其目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就说:“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12)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页。就人而言,幸福就是最高的善,尽管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不一。(13)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9页。所以,赫斯特豪斯在给斯坦福哲学百科撰写的《德性伦理学》(VirtueEthics)一文中区分了四种主要形式的德性伦理学,首要一种便是幸福论德性伦理学(Eudaimonist Virtue Ethics),它通过幸福来定义和说明德性:“德性是一种有助于幸福或构成幸福的品质。我们应当发展德性,是因为它们对我们的幸福有所助益。”根据赫斯特豪斯,实际上,无论何种形式的德性伦理学都包含三个基本概念要素: (1)德性(arête, excellence or virtue);(2)实践智慧(phronesis, practical or moral wisdom);(3)幸福(eudaimonia,通常译为happiness/幸福,flourishing/繁荣兴旺,well-being/活得好)。(14)Rosalind Hursthouse and Glen Pettigrove, “Virtue Ethic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8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8/entries/ethics-virtue/〉.
以德性伦理学的三元基本结构为参照系,我们很容易发现,在冯契“智慧说”体系中,德性和实践智慧(具体的智慧)亦是其核心概念——这从前述广义认识论的四问题便不难知晓。至于幸福,尽管冯契很少在字面上谈论“幸福”,但他实质上不断地谈论幸福,笔者以为他所谓的“自由”便是一种实质的幸福状态。这就牵涉到冯契对“自由”的理解。我们知道,“自由”是近代以来含义最为复杂且歧义颇多的一个概念,同一个术语表达了多种多样的思想观念,冯契所理解的“自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由观。他说:“什么是人的自由呢?简单说,自由就是人的理想得到实现。人们在现实中汲取理想,又把理想化为现实,这就是自由的活动。在这样的活动中,人感受到自由,或者说,获得了自由。”(15)冯契: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三卷,第1页。这是总说自由,“自由”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含义:“从认识论上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以及根据这种认识改造世界;从伦理学上说,自由就是自觉自愿地在行为上遵循‘当然之则’;从美学上说,自由就如马克思说的在‘人化的自然’中直观自身,即直观人的本质力量。”(16)冯契: 《智慧的探索》,《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八卷,第143页;又见《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三卷,第20页。此外,“自由”还有个体和社会之别,从个体的角度而言,“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由的个性,是知、意、情统一。真善美统一的全面发展的人格”(17)冯契: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三卷,第258页。。所以冯契经常把作为目标的“理想人格”等同于“自由人格”;从人类的角度而言,“要求自由是人的本质,是人活动的总目标”,“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走向自由的历程”(18)冯契: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三卷,第260页。,社会将成为自由人格的联合体。在此,冯契批评目的论的自然观,认为自然界的发展没有目的和意向,但是,人与自然不同,人的发展有其目的和意向,而且,“人的活动以目的因为动力”(19)冯契: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三卷,第260—261页。。不难发现,正如“幸福”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体系中处于目的的位置一样,“自由”在冯契的“智慧说”中也处于目的的位置;同理,正如德性和实践智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有助于或构成了幸福一样,德性和智慧在冯契那里也有助于或构成了自由,诚如他所言,“自由人格就是有自由德性的人格”(20)冯契: 《〈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0页。,“智慧是与自由内在地联系着的”(21)冯契: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29页。。
冯契又有所谓“哲学三项”之说,他认为中西哲学对哲学根本问题的讨论都集中到三项: (1)自然界(客观的物质世界);(2)人的精神;(3)自然界在人的精神、认识中反映的形式(即概念、范畴和规律等)。(22)冯契: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三卷,第1页。有时他把三项简称为: 物质、精神、观念。(23)冯契: 《〈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41页。哲学三项推演至历史领域和人生领域,涉及人的类的历史发展和个体发育,就成了“现实生活(或人生)”、“理想”、“人格”,在此“人格”对应着“精神”。何谓“人格”,冯契说:“从现实汲取理想、把理想化为现实的活动主体是‘我’或者‘自我’,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有一个‘我’——自我意识或群体意识(大我)……‘我’既是逻辑思维的主体,又是行动、感觉的主体,也是意志、情感的主体。它是一个统一的人格,表现为行动一贯性及在行动基础上意识的一贯性。”又说:“‘人格’这个词通常也只用来指有德性的主体……真正有价值的人格是自由人格。”(24)冯契: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三卷,第4、5页。由是可知,德性是最终获得自由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很容易在冯契“智慧说”中发现与德性伦理学三元结构相对应的结构,即“自由—德性—智慧”的三元结构。在此理论结构中,自由(或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是目的,德性和智慧是自由的必要条件乃至构成要素。在此框架下,接下来我们重点讨论冯契“智慧说”体系中的德性论。
三、 “化理论为德性”与德性的本体论意义
冯契批判性考察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想人格和人性学说,接续近代社会的变革,结合时代精神的发展,在德性论上提出了诸多颇具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和观点,其中最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要数“化理论为德性”和“德性自证”。此节先论前者,下节讨论后者。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冯契就提出了“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两化论”。冯契认为,哲学理论,一方面要化为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身体力行,化为自己的德性,具体化为有血有肉的人格。化理论为方法,主要体现在《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化理论为德性,关乎德性如何培养,理想人格如何养成。因此,我们在此只论述与主题相关的“化理论为德性”。
关于理想人格的培养,冯契首先梳理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尤其是儒、道、释三家的“成人之道”。《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为成人矣。”冯契据此认为,自孔子率先探讨“成人之道”,甫一开始就表达了知、意、情和真、善、美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观念。此后孟子所谓“充实之为美”(《孟子·尽心下》)、荀子所谓“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荀子·劝学》),都表达了类似的理想人格。虽然孟子重先天,荀子重后天,但二者都一致认为,德性的培养需要通过学习、教育和修养。与儒家不同的是,道家对理想人格的理解及其培养途径都迥然有别,道家的理想人格是“天地与我并生”(《庄子·齐物论》)、与自然为一的人格,其途径是超脱人伦关系和“为道日损”(如坐忘、心斋等)。随后冯契对魏晋、汉唐、宋明、明清之际以及近代关于理想人格的不同学说做了精彩的梳理和辨析,认为汉代独尊儒术以后,纲常名教借天命要求人们自觉遵守,而忽视了自愿原则;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把自愿原则与自然原则相结合,却忽视了自觉原则;禅宗“明心见性”、“随处作主”则统一了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降至宋明,理学家又忽视了自愿原则;理学家内部关于德性的培养,无论是朱熹的“道问学”还是陆九渊的“尊德性”,实质都强调“知”(明觉);反理学的王安石、陈亮、叶适等则突出了“行”;到了明代的王阳明则提出“知行合一”,认为本体随工夫而展开,进而发展为黄宗羲的“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明清之际黄宗羲提倡豪杰精神,强调意志的作用,王夫之则批判了“无欲”和“忘情”说,复归到先秦儒家的知、意、情全面发展的思想。(25)所述参见冯契: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三卷,第230—245页。
冯契认为,无论是孔孟所强调的君子、大丈夫人格还是老庄所推崇的至人、真人理想,无论是宋明儒者所在意的圣贤气象还是明清之际学者所倡导的豪杰精神,那都是少数人可以达到的目标,要求过高,不具有普遍性。基于历史的批判性考察,接续近代“新民德”思潮对培养新人的要求,结合时代精神的发展,冯契提出了由古代圣贤或豪杰人格走向“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理念:“自由人格则是一种平民化的、多数人可以达到的人格。这样的自由意识并不是高不可及的,而是一般人在其创造性活动中都能达到、获得的意识。任何一个‘我’作为创作者,不论是做工、种田,还是作画、雕塑、从事科学研究,都可以自觉地在自己的创作性劳动中改造自然、培养自己的能力,于是自作主宰,获得自由。就是说,劳动者不仅能自觉地主宰自然,而且能在改造自然的基础上培养自己的才能、德性,自作主宰。他既然主宰外在的自然,也能主宰自己内在的自然(天性)。”(26)冯契: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24页。任何行业的普通的劳动者都可以在社会实践中,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的才能与德性。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不分行业与贵贱,但无论何种行业,无论从事何种职业,“要求走向自由,要求自由劳动是人的本质。人总是要求走向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27)冯契: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三卷,第245—246页。。
如何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冯契提出三条途径: (1)实践和教育相结合;(2)世界观的培育和智育、德育、美育的统一;(3)集体帮助和个人主观努力相结合。下文分别论之。第一,冯契认为,实践和教育相结合是培养人格的根本途径。在实践中受教育要遵循人道原则与自然原则的统一,所谓人道原则是说,教育是“为了人”(提高人的价值,使人获得自由)和“由于人”(出于人的主动);所谓自然原则是说,价值创造要“出于自然”而“归于自然”,出于自然是说要根据现实的可能性和人的需要,归于自然是说最后要达到习惯成自然,使人的才能、智慧和德性仿佛就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可见,这一点实际上是讲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认识自己和成就自己,使认识和掌握的普遍之“道(理)”通过不断的实践活动而实有诸己,变成我们的每个人的“德(性)”。第二,冯契批评那种把世界观教育狭隘化为德育甚至政治思想教育的错误做法,认为完整的世界观的教育应当是智育、德育、美育的统一。智育也就是理性思维的培养,指向的是“真”;德育就是在遵循当然之则的反复操练中习以成性,形成个人的品德,“品德是道德理想在个人身上的实现,一个人的品德如果是真正一贯的、明确的、坚定的,那么它一定是某种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体现”,而“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智慧一定是个体化的”(28)冯契: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三卷,第249页。,具有美感和艺术的价值,恰如“庖丁解牛”那样“合于桑林之舞”。第三,关于集体帮助,冯契特别重视“爱和信任”的关系(这恰好也是义务论和后果论很少谈论而德性伦理学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29)Rosalind Hursthouse and Glen Pettigrove, “Virtue Ethic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8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8/entries/ethics-virtue/〉.),认为个性应当受到尊重和信任。就个人主观方面,则应当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培养自己。
冯契说,上述培养自由人格的三个基本途径,归结到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化理论为德性”。“这里的‘理论’指哲学的系统理论,即以求‘穷通’(穷究天人之际与会通百家之说)为特征的哲学的智慧,它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总见解,即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以及对这种认识的认识(此即智慧学说)。”(30)冯契: 《〈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8页。可见,“化理论为德性”中的“理论”主要系指哲学的理论与智慧。其所谓“化理论为德性”就是“把这种具有真理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化为德性……这种理论为主体所把握和表达。不仅是‘知道之言’而且是‘有德之言’。用哲学世界观来培养人格,就是要由‘知道’进而‘有德’”(31)冯契: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三卷,第352—253页。。
关于“化理论为德性”,冯契又从三个方面做了进一步阐释。第一,自由个性的本体论的意义。冯契认为,平民化自由人格首先要求自由的个性,“他有独特的一贯性、坚定性,这种独特的性质使他和同类的其他分子相区别,在纷繁的社会联系中保持着其独立性”,“自由的个性通过评价、创作表现其价值,在这里,精神(按,即自由个性、理想人格)为体,价值为用”。(32)冯契: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三卷,第255页。第二,把理想、信念转化为德性。冯契认为,理论要能指导人生,就必须首先取得理想的形态,不能停留在单纯的概念结构,而且,为了使理论取得理想形态,就要使理智、意志和情感三者统一起来。要进一步使得理想成为信念,就必须将其付诸实践;实践应“乐于从事,习之既久,习惯就可以成为自然,真正形成自己的德性”(33)冯契: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三卷,第257页。。这样,理论转化为理想,理想付诸实践,实践久而久之,便习以成性。理论关乎理智,实践关乎意志,久习则情感自得,所以,冯契再三申说,“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由的个性,是知、意、情统一,真、善、美统一的全面发展的人格”(34)冯契: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三卷,第258页。。第三,个性的全面发展。冯契认为,虽然各人因其性情之所近,个性的培养不能整齐划一,但是,不同行业在发展他们的才能时,都要求知、意、情全面发展,“个性如果不是全面发展,那就不是自由发展”,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在自在而自为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中展开的”。(35)冯契: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三卷,第258页。冯契认为,“道”或世界观、人生观是总说之道,各行各业有各自之道(理),每一领域的人们各有其才能、德性,从事某项事业,便需要精通这项业务,掌握其熟练技巧,因此,就专业之道来说,各有其才能与德性,没有全人;但是,就世界观和人生观来说,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总体之道有助于每个专业的人们成就各自的德性。
“化理论为德性”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化天性为德性”。冯契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批判性吸收了儒家传统的“复性说”和“成性说”,对天性和德性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说:“在实践基础上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反复,即天与人、性与天道的交互作用,一方面使性表现为情态,自然人化而成为对人有价值的文化;另一方面由造道而成德,使天性发展为德性,而把人自身培养成自由人格。”(36)冯契: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28页。又说:“人根据自然的可能性来培养自身,来真正形成人的德性。真正形成德性的时候,那一定是习惯成自然,德性一定与天融为一体了。……人类在实践与意识的交互作用中,其天性发展为德性。”(37)冯契: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13页。我们知道,关于德性与自然(或天性)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有一著名说法:“德性在我们身上的养成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反乎自然的。首先,自然赋予我们接受德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通过习惯而完善。其次,自然馈赠我们的所有能力都是先以潜能形式为我们所获得,然后才表现在我们的活动中。”(38)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36页。不难发现,冯契的“化天性为德性”的观念与亚氏的看法非常接近,也是比较符合常识的思想。
上述论述表明,冯契十分重视“德性”的本体论意义,这与英美当代德性伦理学仅仅强调道德德性有所不同,或可补后者之不足,因此,值得略作申说。冯契说:“我这里讲德性,取‘德者,道之舍’之义,是从本体论说的。人的德性的培养……都是以自然赋予的素材(天性)作根基,以趋向自由为其目标。”(39)冯契: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57—358页。我们知道,古希腊所谓“arête”(德性)亦具有本体论的意味,不限于人的伦理品质,如鸟之“飞”、马之“跑”、植物之“生长”等都可谓之arête。这一点与中国先秦时期的“德”概念颇为类似,老子所谓“道生之,德畜之”(《老子》第五十一章),其所谓“德”都是通人、物而言,万物皆有其“德”,人之“德”也不限于伦理品质。冯契所谓的“德性”更多地受到道家的影响,他经常引用《庄子》中那些普通匠人的纯熟技术来说明自由的德性,也表明他所谓德性不限于伦理品质。笔者以为,这可能是冯契德性说对当代德性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所在,因为后者就那些非伦理品质未能很好地给予考量,而这些非伦理德性对于德性伦理学所强调的美好生活无疑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诚如冯契所言:“人类通过化理想为现实的活动来发展科学、道德和艺术,创造有真、善、美价值的文化,改变了现实世界的面貌,同时也发展了自我,培养了以真、善、美统一为理想的自由人格,使理论(智慧)化为德性。”(40)冯契: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三卷,第230页。冯契之所以特别强调德性的本体论意义,这与他的“智慧说”把“整个的人”作为研究和关怀对象有关,显然,伦理只是“整个的人”的存在方式之一,人生在世以及人的幸福或自由,也离不开认知(科学)和审美(艺术)等活动,而且,即便单就伦理而言,也需要辅以认知和审美,才能形成真正的自由德性。
四、 德性自证与真诚
理论经过理想、信念与实践等环节化为德性,德性最终要落实在个体上,这就需要德性自证。德性自证首先需要肯认“我”(自我)作为德性主体的地位,为此,冯契批评中国传统哲学中老庄、佛学、理学的圣智“无我”说,颇为赞同王夫之“我者德之主”(41)王夫之: 《诗广传·大雅》,《船山全书》第三卷,长沙: 岳麓书社,2011年,第448页。的观点。在对王夫之相关说法的阐释中,冯契提出“凝道成德,显性弘道”的著名理论:
从“色声味之授我也以道,吾之受之也以性”(42)王夫之: 《尚书引义·顾命》,《船山全书》第二卷,第409页。来说,我在与自然物的接触中受自然之理,在社会交往中受当然之则,两者都是大公之理,是“不容以我私之”的。但不容私不等于无我。我接受了天道、人道,并使大公之理凝结成为我的德性(或者说我的德性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便是凝道而成德。而转过来,“吾授色声味也以性,色声味之受我也各以其道”(43)王夫之: 《尚书引义·顾命》,《船山全书》第二卷,第409页。,我在与外界的接触、交往中,使德性得以显现为情态,而具有感性性质的事物各以其“道”(不同的途径和规律),使人的个性和本质力量对象化了,成为人化的自然,创造了价值,这便是显性以弘道。凝道而成德与显性以弘道都有个“我”作主体,所以说,“我者德之主”。(44)冯契: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53页。
这是说,在人与自然打交道(天人授受)的过程中,人接受并认识了客观的道理,然后凝聚为自己的德性,体之于身,实有诸己;但主体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道,又具有积极的能动性,他可以遵循客观的道理,根据人的合理需求,来改造世界,使自己的德性显现为各种情态,使人之“性”对象化,成为人化的自然。凝道成德和显性弘道是一个循环往复、日新不已的过程,主体在这样的过程中最终达到自由。
以上所谓“凝道成德”,也即是把客观的普遍的道理在实践过程中凝聚成自家的德性,但究竟如何德性自证呢?这需要主体的自我意识或反省意识。冯契说:“我是意识主体。我不仅有意识和自我意识,而且还能用意识之光来返观自我,自证‘我’为德之主。这里用‘自证’一词,不同于唯识之说,而是讲主体对自己具有的德性能作反思和验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45)冯契: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53页。冯契借用传统儒学的一些思想资源来进一步阐明德性的自证。我们知道,北宋大儒张载有所谓“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区分。关于前者,张载说:“德性之知,循理而反其原,廓然于天地万物大始之理,乃吾所得于天而即所得以自喻者也。”(46)张载: 《张载集》,北京: 中华书局,1978年,第24页。冯契借助王夫之对张载的注解对此阐释道:“德性之知亦即‘诚明所知’,天道在我身上化为血肉,在我心灵中凝为德性,因此我能‘即所得以自喻’,‘如暗中自知指其鼻口,不待镜而悉’(47)王夫之: 《正蒙注·大心篇》,《船山全书》第十二卷,第145页。,这就是德性的自证。”(48)冯契: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27页。犹如黑暗中我们自知鼻口之所在一样,吾人亦自知德性之有无厚薄,不待旁人之褒贬评价,可见,德性自证有德性自知、独知的含义。冯契虽然借助张、王二氏的“自喻”说来描述德性自证,但是,他并不赞同张、王有关德性之知不萌于见闻之知的先验论。他说:“自指其鼻口也还是一种感性活动,德性的自证并不能脱离视听言动,而正是通过感性实践中的表现(情态)来自证的。”(49)冯契: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27页。在中国哲学史上,这样一种具有自我意识和反思意识的主体,儒家名之为“良知”或“良心”,这两个概念起源于孟子,发皇于王阳明,冯契称之为“觉悟的自我”(50)冯契: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27页。另,关于冯契德性自证的详细考察,参见付长珍: 《论德性自证: 问题与进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在冯契看来,德性自证意味着人的知、意、情等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和真、善、美的人格统一,同时也就是自由的实现。德性自证首先是精神(或人格)的自明、自主与自得:“自证,意味着理性的自明、意志的自主和情感的自得,所以是知、情、意统一的自由活动。”(51)冯契: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61—362页。进而,“理性自明、意志自主和情感自得,三者统一于自我,自我便具有自证其德性的意识,即自由意识。自由的德性是知、意、情的全面发展,已达到真、善、美统一为其目标”(52)冯契: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63页。。最后,“这样,便有了知、意、情等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这就是自由的德性”(53)冯契: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57页。。当然,自由德性的获得不是一蹴而就,无论是从人类还是个体来说,都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无限趋近的目标。
德性自证是主体的自觉活动,虽然人人有个“我”,或如孟子、王阳明所言,人人有良知、良心,但认识自己的真面目并不容易,“人常常自欺欺人,掩盖自己的真实面貌”(54)冯契: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54页。。因此,冯契认为,德性自证首要需要真诚的美德:“真正要认识自己,达到德性的自证,主观上首先要真诚。”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家讲“诚”,道家讲“真”,“两家说法虽不同,但都以为真正的德性出自真诚,而最后要复归于真诚。所以真诚是德性的锻炼、培养过程中贯彻始终的原则”(55)冯契: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54页。。冯契强调,所有真正的德性都须出自真诚,且真诚贯彻始终,这表明真诚是其他诸美德的基础或必要条件,或者说真诚是“德性统一性”(the unity of virtues)的基础。为何冯契会如此重视“真诚”这一美德?我们知道,在儒学传统中,“仁”一直是基础性的美德,是其他美德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孔子认为“仁为全德”(56)参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2页。和程朱理学所谓“仁包四德”无不表明这一点。然而,深受“五四”精神影响的冯契,一方面批评儒学的独尊和经学的独断,对传统名教的虚伪化保持高度的警惕,如他所言,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公开讲的是引经据典,满口仁义道德,实际想的、做的却是见不得人的勾当”(57)冯契: 《〈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233页。;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言行不一、缺乏操守的现象到处可见,鲁迅所痛斥的‘做戏的虚无党’仍然很活跃。‘做戏的虚无党’除了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外,什么也不信,却冠冕堂皇地说着另一套,摆出正人君子的面貌”(58)冯契: 《〈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24页。。有感于此,冯契特别从儒、道传统中拈出“真诚”这一美德作为其他美德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没有真诚,一切美德皆为虚妄,甚至转变为令人厌恶的恶德。
如何保持和发展真诚,冯契提出两条建议。第一,警惕异化现象。虽然我们对物的依赖不可避免,但可避免迷信权力和拜金主义,使人成为奴隶,失去了人的尊严,也丧失了真诚。冯契反复谈到鲁迅笔下的“做戏的虚无党”(善于用虚伪的口号、假面具来美化自己)以及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伪君子、假道学,便是异化的典型,对此要十分警惕。第二,解放思想,破除种种蒙蔽。冯契援引了荀子的“解蔽”和戴震的“去私”等传统思想,破除个人种种主观的私意和成见,或片面性和主观盲目性,消除导致异化的认识论根源。对于如何“去私”、“解蔽”,戴震说“去私,莫如强恕;解蔽,莫如学。”(《原善》下)一方面,要破除迷信,解除种种蒙蔽,积极提高自己的学识和修养;另一方面,要去掉偏私,在社会交往中正确处理群己关系,真诚地推己及人,与人为善。(59)冯契: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55—356页。
以上两条涉及真诚的主观面向,真诚也有其客观的面向。冯契说:“主体的德性由自在而自为,是离不开‘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客观实践活动过程。德性在实践活动中表现为情态,因而对象化、形象化,所以我们讲德性的自证,并非只是主观的活动、主观的体验,而有其客观的表现。心口是否如一、言行是否一致,一个真诚的心灵是能自知、自证的,并且别人也能从其客观表现来加以权衡、作出评价的。”(60)冯契: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56页。总之,旁观者或社会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种种外在言行和表现,来判断他是否真诚。冯契也注意到虽然他人的评价或一时所谓的“公论”难免有错,但吾人仍需不计得失,不较毁誉,坚持特立独行,坚持真诚。
在冯契看来,从事哲学事业的人尤其应该保持真诚。他说:“对从事哲学和追求哲理境界的人来说,从真诚出发,拒斥异化和虚伪,加以解蔽、去私的修养,在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活动中自证其德性的真诚与坚定,这也就是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的过程。”(61)冯契: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356页。又说:“理论化为自己内在的德性,成就了自己的人格。当达到这样一种境界的时候,反映在言论、著作中的理论,就文如其人,成了德性的表现,哲学也就是哲学家的人格。这样的哲学,就有了个性化的特色,具有德性自证的品格。”(62)冯契: 《〈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17—18页。这对于处在学术产业化时代的当代学者来说,同样具有警醒的意义,诚如冯契在经历磨难后说出的那句名言:“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我认为这也应该是‘爱智者’的本色。”(63)冯契: 《〈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15页。
冯契对真理与智慧的追求以及对真诚这一美德的重视,与英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德性伦理学家B.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看法遥相呼应。威廉斯一方面致力于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占支配地位的两种规则伦理学即义务论和功利主义(后果论)的道德思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盖正因为此,他被归入广义的当代德性伦理学阵营),另一方面,在其最后的著作《真理与真诚》(TruthandTruthfulness)一书中,他又继承了启蒙运动对客观真理之承诺的遗产,批评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真理否定论。为此,威廉斯从谱系论的视域阐释了作为真理(truth)的美德真诚(truthfulness)及其展开的两种具体美德——诚实(sincerity或honesty)与准确(accuracy)——对于人类社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真诚不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且具有“内在价值”,它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善”,“诚实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情”,“准确本身也是一件好事”。(64)伯纳德·威廉斯: 《真理与真诚: 谱系论》,徐向东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18、76页。威廉斯所谓“诚实”意指表达或说出真信念的倾向,这便是冯契强调的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真诚;威廉斯所谓“准确”意指获得真信念的倾向,而冯契强调的“解蔽”方法正是为了获得真信念。而且,无独有偶,冯契也谈到了德行的“手段价值”和“内在价值”,他说,道德行为不仅是一种“手段的好”,而且,“德行本身就是目的……德行本身有内在的价值”。(65)冯契: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三卷,第61页。进而,同冯契一样,威廉斯也把真诚与自由联系起来,在他看来,真诚的美德在于发现真理和讲真话,这就需要自由的人格。在名为“真诚与自由”的一节中,威廉斯说:“自由并不等于摆脱一切障碍。当你所能具有的那个渴望并不是你可以为了另一个渴望而随意改变的时候,自由才有价值。因此,自由的一种核心形式就是: 在向着你发现值得做的事情努力的过程中不受制于另一方的意志。”又说:“自由感就根植于其真诚中。”(66)伯纳德·威廉斯: 《真理与真诚: 谱系论》,第186、188页。这与冯契所谓“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保持独立的德操”(67)冯契: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三卷,第363页。的名言如合符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