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寻找被遗忘的中亚
陈娟
前些日子,作家刘子超和一个塔吉克斯坦籍留学生“好运”吃了顿饭,两人聊疫情,聊近况。
2018年,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一个酷热无风的下午,刘子超和好运在市中心鲁达基公园的旗杆下相遇。当时,他正在进行一场深入而漫长的中亚旅行,21岁的好运拦住他,说:“哥,我给你免费当导游?我正在学汉语。”之后,好运就一直跟着他,直到他离开杜尚别。
好运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哥哥一家在俄罗斯打工,寄钱回来供养全家。姐夫也去往俄罗斯讨生活,后来杳无音信。他和女朋友交往了两年,后来分了手。女朋友的人生目标是美国,而他则学习中文,决定日后要去中国留学、赚钱,出人头地。年轻的他总是很无助,口头禅是“我被困在这里了”。
2019年,刘子超发表文章《杜尚别悲歌》,里面讲述了好运的故事。文章在当地华人圈流传开来,很多人认识了这个失意男孩。后来,好运申请中国的大学时,面试官竟认出了他,他顺利通过考试,开始在北京读书。刘子超一直关注着他的生活,两人偶尔也会见个面。
中亚之旅结束后,刘子超开始写作,讲述自己一路遇到的人和故事,有滞留在中亚的俄罗斯人,有想得诺贝尔文学奖的“90后”作家,有依然过着游牧生活的牧民,有在中亚辛勤工作的中国人、朝鲜人……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揭开中亚神秘的面纱。这些故事,后来都被他收入新书《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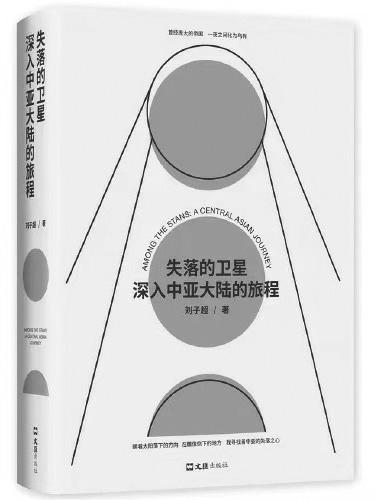
被困的中亚人
2010年夏,刘子超以记者的身份去了一次霍尔果斯。作为中国通往哈萨克斯坦的口岸城市,那里繁忙而混杂,等待通关的货运卡车排起长龙,远方是冰雪覆盖的天山。
“当时我想起了斯坦因等人写的纪行,回忆起历史课上学过的撒马尔罕、河中地区、七河地区这些词。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想跳上卡车,穿越边境,翻过雪山,看看对面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刘子超说。
雪山对面的世界一直诱惑着他。一年后,他背起行囊,前往乌兹别克斯坦,抵达首都塔什干。当时正值苏联解体20周年,他走在大街上,感觉苏联解体就发生在昨天。“街上跑的汽车还是苏联时代的拉达,人们的穿着打扮、城市建筑风格,都还停留在 20年前,像是被封存在了一个时间胶囊里,停滞不动。”刘子超回忆说。
另一个让他震撼的是,中亚人丰富的长相——蒙古人、突厥人、波斯人、俄罗斯人、高加索人、朝鲜人、鞑靼人,各种长相都有。再加上布哈拉古城、中世纪的清真寺等遗迹,他每到一地都受到了“文化冲击”,也被中亚所特有的“呼愁”(土耳其语,意为忧伤)所吸引。
回国后,刘子超拿出旅行途中的笔记,动笔写作。写了1000多字后,怎么也写不下去了。“苏联解体后,中亚像一颗失落的卫星,迷失了方向。它在全球化的边缘与大国的夹缝中,校正着自己的轨道。我迷恋这种挣扎、寻觅的失重状态,这种迷恋最终又化为理解历史潮流的渴望。”
刘子超意识到写中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必须慢下来、沉下去。接下来的几年,他开始了对中亚的探索,一边读相关的书,一边慢慢旅行,同时学习俄语、乌兹别克语,几乎去过了中亚所有可以去到的地方。他旅行的目的很明确——记录当下中亚人的生活和命运,勾勒出中亚的图景。带着这样的目的,他有意识地去结识不同的人,和他们聊天,打捞他们的故事。
在吉尔吉斯斯坦,经向导介绍,刘子超结识了一位年轻作家阿拜·扎尔扎科夫。阿拜生于1992年,会说俄语、英语和法语。他一直写小说,接下来打算写“全球化对吉尔吉斯人的冲击”,在他看来,苏联解体后,全球化将这个国家的信仰、生活方式冲击得七零八落,成为一片废墟,“而我们这代人,就在废墟当中,艰难地寻找可以依赖的东西”。
在乌兹别克斯坦,帖木儿广场附近的酒吧里,刘子超和生意人模样的阿扎玛聊起天。他最初从事出口贸易,将乌兹别克的干果出口到美国,之后开始购买房产,拥有七八套公寓,靠租金衣食无忧。两人边喝边聊,旁边一个男人突然开始向天空抛撒钞票,开始是幾张几张的,后来漫天挥撒。阿扎玛对刘子超说:“这就是现实!乌兹别克的现实!”
经由乌兹别克斯坦,刘子超北上咸海,在那里偶遇 “咸海王”。他是一个中国人,来自山东滨州,在荒凉的咸海边已生活了7年。他手下有4个工人,工作是在咸海收集泥中的虫卵,然后经过深加工,变成虾苗的饲料。每年有大半年的时间,“咸海王”都独自住在帐篷里,没有信号、没有网络,最近的WiFi在160公里外。日子很难熬,常常会濒临崩溃。每当此时,他会骑上四轮摩托,在荒无人迹的丘陵上狂飙,冲上高处,再冲下来。
“一路上,我努力去做一个倾听者。我感到,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困在原地,被生活、地域或者政治,又没有办法改变。”刘子超说。“这片大陆离哪里都很遥远,无论是地理上、心理上,还是文化上。全球化似乎有意无意地放弃了这里。”
带着目的去行走
这些年,刘子超一有空就往外跑,有时是工作需要,有时出于个人兴趣。他上一次出国旅行,是在2019年9月。因作品《乌兹别克斯坦:寻找中亚的失落之心》获得第一届全球真实故事奖的特别关注奖,他去瑞士领奖,之后又在欧洲待了两个月,11月回国,后来疫情到来,他再也没有出去过。
关于欧洲,刘子超不算陌生。2012年,他申请到一个中德媒体使者项目,在德国待了3个月。其间,他还去往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意大利等地。在布拉格的老酒馆,他遇到一直想移民到南半球澳大利亚的中年男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听到一个俄罗斯大叔用破碎的英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他的家人曾被关进那里;在布达佩斯,他走访当年中国倒爷白手起家的四虎市场,遇到卖景德镇瓷器的中国小伙儿……
回国后,刘子超开始回忆和记录那段旅程,花两个月写下6万字,后来这部分成了他的第一本旅行作品集《午夜降临前抵达》的前半部分:夏。第二年的冬天,他以自驾的方式再次漫游中欧。“中欧对我的吸引力,在于它始终生长在帝国和强权的夹缝中,执拗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刘子超说,它身上那种强烈的撕扯和游移感,让当时不到30岁的他感到了某种心灵上的契合。

那一时期的刘子超,从一个媒体跳槽到另一个媒体,采访、写作,衣食无忧,但内心迷茫。“常常会想,自己的作品在哪儿?特别是采访完作家或者导演以后,这个问题就会冒出来。”
2016年,他申请到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的一个研究项目,去做访问学者。有一次,他去剑桥过周末,在一家二手书店闲逛,偶然翻到一本旧书《惊异之城》,硬皮精装,只要5英镑。翻开一看,是伊恩·弗莱明环游世界14座著名城市的旅行随笔。
普通读者对弗莱明的印象都停留在小说“詹姆斯·邦德”系列。“我好奇于一个邦德式的作家在现实世界中是如何旅行的。”在《惊异之城》中,刘子超看到了作为旅行者的弗莱明:他不喜欢博物馆和美术馆,受不了在政府大楼吃午饭,对访问诊所和移民安置点毫无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离开宽敞明亮的街道,走进身后的小巷,寻找一座城市隐秘而真实的脉动。
“弗莱明是一位惊险小说家,在旅行中也习惯了以一个惊险小说家的目光观看世界。”刘子超说,弗莱明的旅行方式和写作,让他反思自己。牛津大学的项目结束后,他回到国内,翻译《惊异之城》。从此再也没有进入职场,而是专职写作,这时的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旅行文学。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中国商品不断走出去,但中国的旅行文学却没有跟上步伐。中国人如何观察世界,可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题材。”刘子超说。于是,便有了中亚之旅、从印度到东南亚之旅等。
与弗莱明一样,每到一个地方,刘子超都会去寻访别样的地方和有趣的人。在缅甸,他深入佐米亚,寻访还在刀耕火种的爱伲人;在菲律宾,他去看当地的国民运动斗鸡。最震撼的要数爪哇岛之旅,他去往伊真火山,探访火山湖和采集硫黄的工人。
登顶火山口,热气蒸腾,刘子超看到一些工人在湖边收集冷却成块的硫黄,然后用铁锹砸碎,装进篮子,再用扁担挑下山。“站在这场景中,我久久不能开口。在这样的世界,还有这样的人,在过这样的生活。”他说。在爪哇,一名普通教师的月收入不过100美元,而硫黄工人可以拿到150美元。后来,这些故事都被他写进2019年出版的《沿着季风的方向》一书中。
关于旅行文学的写作,美国小说家、旅行家保罗·鲍尔斯曾给出一对概念:写点东西的旅行者和会去旅行的作家。刘子超希望成为后者,带着目的去行走,然后以文学的笔触书写旅程、书写异域,“旅行慢慢变成了我的一种方法,它渐渐退后,让人浮现出来”。
当代游牧者,见证世界的流动
刘子超性格内向,不擅长社交。平日里“不在路上,就在去往路上的路上”,在家时就是读书、记笔记,桌子上放着很多文件夹,按国家、地区分类,不同资料放进不同夹子。偶尔也会做翻译,翻译的大都是旅行文学。
他最早的旅行是在阅读里。小学的某个暑假,他迷上了《哈尔罗杰历险记》,讲述主人公哈尔和罗杰在亚马孙、海底城、食人国不同地方历险的故事,拓展了他关于远方的想象。后来到初中,他读《鲁滨孙漂流记》,“鲁滨逊身上有一种开拓者的雄心,同时又兼具冷静、理性和智慧,完成了我对旅行者形象的终极认知”。
高中时,刘子超就读北师大二附中文科试验班,集体旅行是必修课。“就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体验不一样的生活。”高一那年暑假,他们去的是西北,在陕北吴旗农民家的窑洞住了好几天,每天捧着大碗,蹲在窑洞门口吃饭。后来去延安,坐的是大巴车,公路崎岖不平,“我几乎是飘着到的,屁股一直没沾到座椅”。高中后两年,又集体去江南、云南,都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之后,刘子超的旅行版图不断扩张,从国内到国外,从漫无目的地漫游到田野调查式的深入游。对他来说,通过旅行去实践、去发现、去写作——这就是诱惑所在。
在中亚,刘子超经历了一次深入天山之旅。途中,他偶遇到一个白色的帐篷,扎在空荡荡的山谷中。里面住着一家吉尔吉斯人,女人正在生火,两个小孩在地上拍洋画。女人端出发酵的马奶酒招待他。后来,在继续前行的途中,刘子超遭遇暴风雪,被牧民救回,带到家里——赶巧正是之前那家人,主人又拿出食物,热情款待他。

在內心深处,刘子超觉得自己也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不是草原游牧民族,而是当代游牧民族。就像牧民一样,有方向、有目的地移动,逐水草而栖,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与牧民不同的是,他游牧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还有写作。
关于写作,他的动力之一正是见证世界的流动。“制造流动并且居于核心的永远是人。人的生存经验就像历史河流中的卵石,从当下向着未来延展。当你通过旅行和文字打捞起这些卵石,它就慢慢地构筑起你的世界,这个世界可能比真实世界更牢固、更有依靠感。”
(摘自《环球人物》2020年第17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