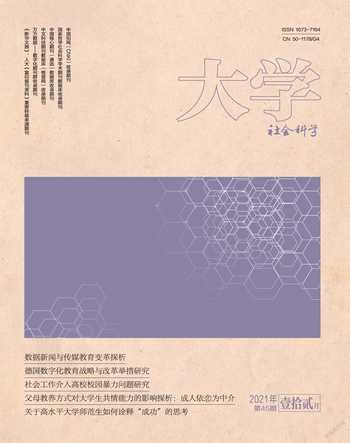辽代早期牧马地考
邓子聪
摘 要:马政是辽代群牧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牧地的选择与放牧区域的变化是马政研究的重点。一方面,契丹人的畜牧形式不同于汉人,带有强烈的本民族特色,畜马牧场常受政治影响而变迁,另一方面,辽王朝的南部疆域受其与中原王朝的战争而不断变化,辽人是否曾在战乱的河北地区牧马仍然存疑。《辽史食货志》中的一条史料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辽人在河北地区的牧马情况,对还原辽建国早期的牧地选择问题,乃至辽初契丹人南下中原的整体战略方面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辽代;马政;地理;五代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45-0044-03
契丹作为兴起于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凭借战马之利对外进行扩张,最终建立起幅员广袤的帝国。《辽史·食货志上》云,“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以是制胜,所向无前。”[1]观此,可知马在契丹社会中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性。目前,学界将马政视作辽朝畜牧业中的一部分,研究成果颇丰,主要研究成果有何天明的《辽代群牧制度源流考论》与《试论辽代牧场的分布与群牧管理》,张国庆的《辽代牧、农经济区域的分布与变迁》,杨军的《牧场与契丹人的政治》,周峰的《辽代北疆地区的开发》以及吴晓杰的《辽、北宋群(监)牧制度比较研究》等,但没有形成对辽代马政全面系统的研究。现有研究对辽代的马政多有讨论,但从目前可见的著述来看,以辽代马政为题者几无,唯民国时陈剑新先生的《辽金之马政》以此为题。自北魏至唐中期,契丹多次受到周边其他游牧部落、北方政权及隋、唐等中原王朝的军事打击,数百年间,契丹人的驻牧地基本在北起西拉木伦河下游,南至大凌河流域,西抵浑善达克沙地,东达辽河平原的区域内不断流窜[2]。自唐中期契丹开始崛起,至阿保机征服五部奚,契丹的牧地也随着其政权的武力扩张突破了原有的地域界限,逐渐南下河北地区形成了新的群牧地域范围。
一、研究背景
有关辽早期牧马基地的分布,张国庆先生曾撰文进行讨论,但在“‘南境燕北‘塞下等处的牧马基地”这一问题的论述中,他引用《辽史·食货志下》的内容,认为辽代的畜牧区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塞下”地区,“沿辽与五代各政权及北宋的边界向东和东南方向扩展开来……这一区域大致已及今京、津地区南部与河北省交界一带”[3],然而这一结论的准确性仍有待商榷。《辽史·食货志下》有记,“祖宗旧制,常选南征马数万疋,牧于雄、霸、清、沧间,以备燕、云缓急;复选数万,给四时游畋;余则分地以牧。”[1]这段描述看似对辽代早期牧马之地记述详备,但其中牧马地域的细节却颇有吊诡之处。何天明先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雄、霸、清、沧四州地处河北,位于黄河下游南北两岸,在历史上并非契丹之地,故而《辽史》所指的牧马地“其实际所指,当为四个地区以北,今天内蒙古赤峰、河北承德、张家口等地北部或周围宜于畜牧的广大地区”,即为南下战争做准备的“契丹军队主力的集结区”[4]。本研究经过深入考证此段史料后,得出与二者皆不同的观点。诚如何天明先生所言,此段史料最大的疑点为雄、霸、清、沧四州在五代至宋间的统治归属变化,按史书记载,这四州之地在五代晋、汉、周三朝长期由中原王朝统治,入宋后则一直为宋所有,并非契丹统治区。既然契丹并未在雄、霸、清、沧地区进行长期统治,那为何《辽史》中会有常在此区域牧马的祖宗旧制呢?这条旧制的记录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二、辽太宗与辽圣宗时的南下战略
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查证发现,“祖宗旧制,尝选南征马数万疋,牧于雄、霸、清、沧间,以备燕、云缓急”这段文字可推测或是源自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灭晋后曾做的战略部署。纵观辽代历史,契丹最大的两次南下中原掠地行动即辽太宗南下灭晋与辽圣宗、萧太后南下攻宋。而辽圣宗南下时一路直扑开封,并未侵袭位于黄河下游的清、沧二州界。战后宋辽两国于“澶渊之盟”中确定了双方的固定边境线基本以瓦桥关、白沟河为界,虽然此后辽人仍多有南下越界的行为[5],甚至在和议当年三月便出现了大量契丹马群南下宋境的边界纠纷。“(宋真宗景德二年三月)丁卯,雄州言,容城县状称戎人大驱马越拒马河放之,其长遣人持雉兔来问遗,求假草地。上曰:‘拒马河去雄州四十余里,颇有两地输租民户,然其河桥乃雄州所造,标立疆界素定,岂得辄渡河畜牧,此盖恃已通和,谓无间阻,可亟令边臣具牒,列誓书之言,使闻于首领,严加惩戒。况今欢好之始,尤宜执守,不可缓也。”[6]虽然这次辽人南下牧马引起了宋朝官方的不满,但仍只是试探性行为,其所至也不过是雄州以北的拒马河流域,此地距雄州尚有四十余里地的距离,更遑论雄州以南的清州、沧州等地。大规模的辽国马群越界南下,在宋辽澶渊之盟签订后已不常见,而偶然发生的越界放牧事件也不足以被称为祖宗旧制,因而《辽史·食货志下》的这条记录应当向辽圣宗前更早的时代溯源。在查阅辽早期史料后可发现,辽太宗灭晋前后曾短暂控制了雄、霸、清、滄四州所在的河北、山东之地,与辽圣宗南下时的情况相比,辽太宗南下时这种全面占领的局势显然更有利于为辽军的南征马群在此地放牧提供所需的必要条件。
大同元年(947)正月,辽太宗入汴梁城,并在同年二月即帝位,建国号大辽。但随后辽太宗所行政策失当,他纵容契丹军大掠民财,导致民心丧失,仅四个月后便因内外压力被迫北返,且最终病死于归途。从时间上看,辽太宗南下据有中原是极短暂的,然而,在《辽史》中有辽太宗回复皇太弟耶律李胡之语如下:“且改镇州为中京,以备巡幸。欲伐河东,姑俟别图。”[1]此时的辽太宗正因“官吏废堕”“民不堪命”以及河东未归,“西路酋帅亦相党附”的乱局而仓皇启程北返,所谓日后西征河东的刘知远不过是强撑场面之语,但在这一时期辽太宗升镇州为中京却也显示了其不愿轻易放弃中原的政治态度。而辽太宗病亡后,契丹面临的紧迫问题便是如何防备新建立的后汉政权收复后晋在中原,河北以及山东的领土,甚至威胁契丹所统治的幽州。因此,可推测在雄、霸、清、沧四州之地设立牧场的行动始于辽太宗南下灭晋时为契丹军队建立后勤基地的战略部署,后汉建立后,四州之地成为辽与后汉在河北的边境线,但契丹统治集团并没有彻底放弃这一地区,而是继续不时南下牧马以夸耀实力,使中原王朝不敢轻窥幽州之地。契丹虽在辽太宗后暂停了南下的计划,但其与中原王朝的边境并不稳定,尤其在河北地区,叛乱、摩擦时有发生。因此,契丹人每年派马群前往四州地区放牧恐怕不仅是“意欲夸示中国”向中原王朝展现实力[7];震慑新降伏的河北诸镇,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举棋不定的藩镇起到警示作用也是这一行动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雄、霸、清、沧四州的地理沿革
为佐证上述推测,本文又梳理了雄、霸、清、沧四州的历史沿革。雄州本名瓦桥关,霸州本名益津关,二者都是在后周世宗北伐时收复并建立州制的,此前曾在晋亡后为契丹占领。清州“本乾宁军。……晋陷契丹。周平三关,置永安县,属沧州……大观二年,升为州”[8],也是曾在晋时陷落于契丹,在周世宗时与雄、霸二州被一同收复,入宋后直到宋徽宗时才建立州制。沧州在史书中虽未明确记载其所属政权交替的过程,但根据《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第一》记辽太宗第一次伐晋失败后“分其兵为二:一出沧州,一出深州以归”及后汉时王景曾任沧州节度使一职可推测沧州应亦在晋亡时曾为契丹所占[9-10],后为后汉政权收复。由此可知这四州都曾在石晋政权灭亡时被契丹短暂占据,因此,辽太宗在灭晋时,将随军的“南征马”放牧于雄、霸、清、沧四州之地的战略是符合战略需求与现实条件的。然而,随着辽太宗本人病逝于归国途中,辽政权内战骤起,皇太弟耶律李胡与辽世宗耶律阮为争夺皇位兵戈相向。虽然辽世宗成功击败了祖母述律太后与叔叔耶律李胡,并登上皇位,但辽国内此起彼伏针对世宗的谋反使他无力顾及南方新占地的情况,而此时的后汉政权已取代后晋成为了新的中原之主,辽国虽仍控制着雄州、霸州与清州之地,却已无力大举南下伐汉。此后,辽国的马群虽仍在雄、霸、清三州的土地上纵横十余年,但其统治者早已没有了辽太宗时一统中原的雄心壮志,原来作为南征前线基地而开辟的牧地也逐渐变成了抵挡中原王朝北伐的防线,到周世宗收复三关后,辽太宗时期开辟的雄、霸、清、沧四州牧马基地便彻底脱离了契丹政权的掌握,成为了史官笔下一句模棱两可的“祖宗旧制”。
四、《辽史·食货志》契丹牧马地的史料来源
关于《辽史·食货志下》中这段记载的史源问题,苗润博先生在其著作《辽史探源》中进行过讨论,认为此文本出自史愿的《亡辽录》[11]。但其中仍有些许疑点,如“雄霸清沧”四州中的清州虽在《辽史·食货志下》有出现,但与这段文字同史源的《裔夷谋夏录》中却没有清州的记述,而另一同史源文献《文献通考·四夷考》更是只记载了雄、沧二州。出现这一情况的可能性有三:一是元代史官擅自增加清州以突出确切的地理范围;二是《裔夷谋夏录》与《文献通考》二书纂者擅自删減或漏记了原始史源中的部分内容;三是《裔夷谋夏录》等书在传刻过程中出现漏记,导致今本书内容不全。至于哪种推测更加合理,尚无确切答案。所谓“祖宗旧制”之语,在《裔夷谋夏录》《文献通考·四夷考》则都记为“上世”。而文本中“常选南征马数万疋”中之“常”字,虽《文献通考·四夷考》与之所记相同,但在《裔夷谋夏录》中却记为“尝”,文义略有不同,也可看作为一个疑点。
《亡辽录》的作者史愿在降宋前为仕辽的汉族官吏,对辽朝早期历史所知应是有限的。因此,《亡辽录》所记录之事虽可作为契丹史料的补证,但由于其著书年代据辽初已时间久远,而许多史事也是史愿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书写的,其中难免会有讹误或缺失,在使用该书时需要研究者自行判断其史料的真伪,《辽史·食货志》的这条辽早期牧马地史料便是《亡辽录》记录须考辨的明证。
五、结语
归总来说,《辽史·食货志下》所言“祖宗旧制,常选南征马数万疋,牧于雄、霸、清、沧间”极有可能是辽太宗南下灭晋后一次并不成功的战略布局,此后辽人在这一区域的岁牧活动也并非开辟牧场,而是对南方的中原王朝施加军事威胁,压制河北新收服藩镇的不臣之心,并没有将其视作正式的群牧区域。至于当代学者由这一史料得出辽早期马场向南已延伸至沧州黄河流域一带,及辽代放牧南征马的区域在今赤峰至张家口一带的结论,似乎是对史料分析不全面而得出的观点。
作为北方大国,辽王朝雄壮的马群资源既是其畜牧业繁荣的标志,更是其能够在二百多年间威压中原王朝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利器。通过对辽代早期雄、霸、清、沧四州牧马基地的探索,可从中窥见这个由契丹人建立的少数民族王朝是如何运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来服务于其早期的军事征服,并与中原王朝、地方节镇进行政治博弈。辽代马政因史料的散乱性而显得琐碎无序,但经过挖掘、串联之后,还是可以从这些细节中看到其发展的脉络变化及其背后辽王朝的兴衰交替。
参考文献:
[1] 脱脱. 辽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923.
[2] 毕德广. 契丹居地变迁考[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41(02):71-77.
[3] 张国庆. 辽代牧、农经济区域的分布与变迁[J]. 民族研究,2004(04):84-93.
[4] 何天明. 试论辽代牧场的分布与群牧管理[J]. 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4(05):72-74.
[5] 陶晋生. 宋辽金史论丛[M]. 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13:183-200.
[6]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杭州:浙江大学馆藏钦定四库全书本,卷59:24b.
[7] 刘忠恕. 裔夷谋夏录[A]//黄宝华. 全宋笔记[C].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85.
[8] 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0:1432.
[9] 欧阳修. 新五代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16:1011.
[10] 薛居正. 旧五代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16:1571.
[11] 苗润博. 辽史探源[M]. 北京:中华书局,2020:309-311.
(荐稿人:孙建权,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