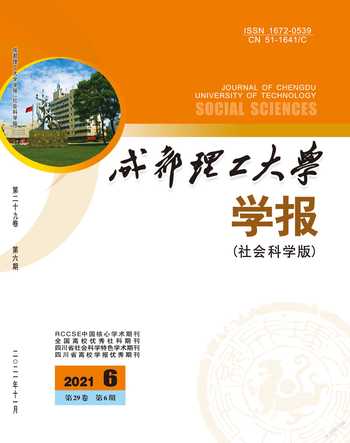以《民法典》代理权说构建人工智能主体的资格制度研究
吕群蓉 崔力天
摘 要:通过对以自然人、法人主体资格演进脉络为起点,结合人工智能具备相对独立的自由意志与认知、具备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的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应当被赋予法律人格。同时,因人工智能独立意志的不完全性,其权利义务的承担可参考“代理人”制度,以人工智能代理自然人、法人实施法律行为视角,建构人工智能的民事权利能力范围和民事责任制度。
关键词: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理论基础;代理
中图分类号: D9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1)06-0059-09
一、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以及经济发展强烈需求的共同驱动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1]。尽管早在1949年,知名脑科医生杰弗里·杰佛逊爵士(Sir Geoffrey Jefferson)提出人工智能只有用自己的思想感情去写出一首十四行诗,或者做出一部协奏曲时,才应该被承认机器可以等同于人脑[2]。在“深蓝”对战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时,人们也普遍不信任电脑方。但近年来,人工智能已在较高程度上参与人类社会活动,并获得很大影响力:2016年松琦教授团队制造的人工智能“有岭雷太”创作小说《人工智能写小说的那一天》并入围日本“星新一奖”;人工智能“小冰”发表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这些著述“以假乱真”,几乎分不清人工智能与一般自然人创作的区别。
2016年,Alpha Go通过学习人类棋谱,击败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和围棋世界最高分柯洁;AlphaGo Zero更以自我训练的方式,以100∶0的战绩击败了前辈;发展至今,棋类最后的堡垒,用穷举法穷尽宇宙原子算不尽棋局数的围棋也被人工智能轻松攻破。人工智能的发展程度已经远超李斯特们的想象,对人工智能的规范与监管都刻不容缓:人工智能是否能够拥有法律人格?如果拥有,应拥有何种法律人格?如果拥有法律人格,那么对侵权行为如何承担责任?
关于前述问题,法学界普遍存在三种观点:其一,应当给人工智能自然人或代理人地位的独立法律人格说;其二,另立主体或比照法人等拟制主体的有限法律人格说;其三,人工智能只是工具和法律关系客体的法律人格否定说。随着人工智能独立性一面的日益发展,以代理人说、拟制主体说为代表的主体说获得更多认可,客体说则式微。在两种主体说的比较中,采有限法律人格说还是独立法律人格说,仍是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自2017年以来,国际上以俄罗斯《智能机器人法案草案》(以下简称格里申法案)、欧盟“电子代理人决议”等赋予人工智能代理人地位的独立法律人格说取得重大发展。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颁布,对于代理权进行了概括精要的规定,本文尝试以《民法典》代理权视角作为破局,提供一种人工智能独立法律人格探索的观点和制度架构路径。
二、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理论基础
法律人格是指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资格,包括自然人和法律拟制人。法律赋予每个自然人法律人资格,将其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和完全行为能力人,法律人格伴随自然人终生。法人经法律拟制按法定程序成立获得主体资格,是自然人的永久合伙人[3]。简言之,法律人格是主体成为法律意义上“人”的能力和资格,人格可以扩展到自然之外的实体[4]。
(一)法律主体资格的演进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法律史就是一部法律主体扩张史。法律主体资格从权贵扩散到下层阶级,从少量贵族男性扩散到全体自然人,从仅限人类到“非人可人”。法律主体对象在不断扩张,各法律主体的地位也在不断走向平等[5]。
1.自然人法律主体资格的演进
自然人法律主体的演进路径从之前依据严格的身份阶级制度确立不同法律地位,到如今“人人平等”被作为基本原则,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在罗马法制度中,就存在着因自然人身份不同导致的差别对待。罗马法原则上是属人法,也即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很大程度上决定他适用何种法律。在罗马法实施初期,只有为数不多的罗马市民拥有完整的法律主体权利,而人数占多数的奴隶、异邦人则完全不享有权利[6]。查士丁尼民法典颁布后,万民法与市民法融合,内容上逐渐接近,罗马非公民才取得市民权[7]63。
在我国古代,儒家思想是社会主导思想,法律也随之儒家化:社会看重身份,法律等级化,各法律主体不平等。如周朝开始到明清才结束的“八议之辟”制度,就明确规定特殊身份地位的人可以酌情减免法律处罚,直接体现法律主体的不平等[8]。即使是比较进步的“海瑞定理”,由于受儒家孝悌思想的影响,自然人的法律地位也“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身份歧视严重[9]。
直到近代,随着“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平等博爱思潮逐渐占据主流,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促进民族解放和独立,也激发了思想解放運动,经过各族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自然人之间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逐渐得到确认[10]。如法国的《人权宣言》宣告“人生来是并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法国民法典》称“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11],《普鲁士普通邦法》宣告:“人就是每一个自然人。”[12]至此,人类才实现法律意义上自然人法律主体地位平等。
2.法人法律主体资格的演进
与古罗马一样,非自然人群体也经历了法律主体的扩张历程。虽然古罗马商品经济已经有所发展,但罗马法对于非自然人群体的法律地位,特别是经济群体的法律地位,并未明确规定[13]。因为此时的罗马本质上仍然是奴隶社会,尽管有些经济和政治团体,如自由城市、商会、教堂等,但这些群体只是大多数自然人的组合,并未拥有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14]。在这一时期,罗马法不可能建立系统的法人制度,法人制度起源于罗马法,随着罗马领土的扩张,原料贸易的频繁,以及私人团体的出现和迅速发展,罗马法开始承认社会团体的主体地位。罗马的法律组织包括公共组织、宗教组织、慈善机构、商业组织,以及工业组织和非政府政治组织[13]。而现代法律也大体包括两类法律组织:社会组织和金融组织。
虽然罗马法有不少关于法人的内容,但由于当时没有现代法人概念和术语,法人制度十分粗略。中世纪时,教会权力在欧洲国家达到顶峰,当时教会已经是一个完善的法人团体,其基本特征与现代法人相似[14]。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主导性特征决定当时法人组织并不普遍,法人的独立所有权相对较低,法人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
随着西方在海洋领域的发展,大航海时代到来,意大利自治城市出现了航海自治组织——航运协会。其有自己的代表处,每个股东只承担自己投资的风险,按比例盈利[15]。此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区分有限合伙人和无限合伙人的“康曼达”合伙企业[16];15世纪末,荷兰和英国出现各种商业组织[16];随着16世纪至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19世纪工业革命的深入,与经济相适应的实体——法人最终在许多国家民法典中的法律主体地位被确认。
号称西方第一部民法典的《法国民法典》,注重自然人的影响,没有将法人等非自然人实体纳入民事适用领域:认為生活中的人的规范是法律产生的先决条件,即民法作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此称之为法律关系。法律关系相异于早期的财产关系与血缘关系[11],在法律关系中,人的行为被予以强制性评价,因而与权利义务直接相联系。《德国民法典》始形成主体资格二元结构:承袭罗马法,认为“一切权利均因人而设立”[17],但从权利角度提出“法律行为能力”新概念,并在《法律行为章》中将“法律行为能力”作为区分人的唯一法律依据[18]。《德国民法典》创造没有传统生物学意义的法人,将其作为具有权利能力、与自然人法律地位平等的虚构民事实体,参与民事活动。
(二)人工智能成为法律主体的可行性分析
1.人工智能具有相对的自由意志与认知能力
自由意志是法律主体存在的基本前提,判断能否成为民事主体的根本标准即是否具有“独立意志”,只有具备独立意志才能成为民事主体。独立意志是民事主体为了一定目标自觉的组织行为,并深信此类行为切实可行的判断意识[19]。现有法律主体均具有一定独立意志:自然人以心理与生理基础共同作用产生独立意志,并以主体身份作为意志的载体与实现途径;法人公司则依据董事会决策形成独立的意思表示。
虽然人工智能在结构上与人类存在较大差异,但仍具有相对独立意志。人工智能以程序代码和大量数据输入为基础,在新旧任务之间有足够的相似性时,便具备“学习迁移能力”,这与自然人脑功能存在相似性。人工智能与人交互的实质是对人心理状态的认知过程。人工智能在生理基础与心理基础方面与自然人均存在实质上的相似性,具备成为责任主体的独立意志基础[20]。但人工智能的行为必须基于最初的数据输入与程序设计,因此其意志独立性受到一定限制,目前无法拥有与自然人相当的自由意志。但人工智能比照人类行为更具有可预测性,只要求人工智能在其工作范围内具有相对的自由意志代理人说正好可以利用此特点,如Alpha Go等对人类棋谱进行机器与神经网络学习,达到远超人类想象的走法与策略能力[21],与自然人与法人“自由意志”相类。
2.人工智能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
民事权利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享有的利益范围和实施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实现某种利益的意志。民事义务是指义务人为满足权利人的利益而为一定行为或不得为一定行为的必要性[7]。法律主体需要有相应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而人工智能具备此种能力。
目前国际上对于人工智能的观点也呈现出权利与义务并重的趋势,即人工智能应该能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不是纯粹的客体与工具[22]。以版权与著作权为例,微软人工智能小冰可以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在不同场景下有针对性地创作。人工智能利用其学习能力,对在原有知识基础上创作的作品享有著作权,同时也应承担相应法律义务[23]。
2017年2月16日,欧盟法律事务委员会表决通过《电子代理人》决议,要求将日益先进的自动化机器确定为“电子代理人”[24],赋予人工智能一定主体资格:为人工智能登记注册、开立基金账户,要求相关主体履行法律义务(包括支付法律规定的费用等);同时人工智能未能履行义务,则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格里申法案》和欧盟“电子代理人”决议关于人工智能代理人地位观点的批判与借鉴
随着俄罗斯《格里申法案》和欧盟“电子代理人”决议的倡导,现行观点普遍支持人工智能的代理人地位。但两项法案(议案)对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构建都有不同程度的缺陷与问题,需要在批判中加以借鉴,并通过实践进行完善。
(一)缺少法理价值的引领
科学技术的每一重要应用都伴随着争议。以20世纪末讨论度较高的克隆人为例,克隆技术能否在生理上复制一直是人们的讨论焦点:联合国制定了有关基因规范的《人权宣言》,明令禁止针对人的生殖性克隆[25];日本通过法案禁止克隆人的出现[26];国际社会大多明确克隆人不具有人的资格,以法律禁止克隆人[26]。但是人工智能与克隆人存在重大差别:克隆人的出生会引起血缘关系与伦理关系的争议,让血脉亲情受阻;而人工智能不是“人造人”,其人格可以独立,不存在相关伦理问题。尽管现在普遍担心如果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太高,可能会反制人类,但人工智能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赋予其法律人格,这是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要求,无可回避。但因为对人工智能不确定性风险的担忧以及法律的滞后性等影响因素,使以代理权为主要观点的法案(议案)对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规范比较模糊,对人工智能的发展缺乏相关法律价值指引。
1.俄罗斯《格里申法案》的局限
《格里申法案》立法目的与初衷都偏好实用性,始终贯彻利益最大化原则:人类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关系应当在最短时间内在立法上予以描述和规定[27]。《格里申法案》基于利益原则对人工智能的规定过于实用性,只是当人工智能作为高度危险来源致人损害时,才明确其作为财产的地位;并未规定人工智能所有权人行使其财产权利不得违背人道主义原则,因此缺乏对人工智能的基本法律人格关怀。其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更多的是功利性的。
2. 欧盟“电子代理人”決议的法理问题
欧盟“电子代理人”决议认为,“人工智能的自主性很可能会发展到必须遵守道德规范的程度,须为它们编写专门防止其有害行为(如危害人类或环境)的道德规范(ethical codes)”(1)。同时指出,对于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如果出现故障并伤害人类,谁应该在道德和法律上承担责任?人工智能技术是一个新颖且变化迅速的领域,可能会对人类造成重大的人身与财产伤害(例如,军用人工智能或失去控制的自动人工智能汽车等),它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尚难预测,应该在伦理和法律上加强监管[28]。
人工智能规范的先驱阿西莫夫曾提出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三定律”:“第一定律:人工智能不可对人类造成伤害,也不能对人类的危险袖手旁观。第二定律:人工智能必须服从人类给予的使命,除非违反第一定律。第三定律:人工智能要尽可能地保护自己,除非与第一二定律相违背。”[29]但这三定律依然尚存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要求人工智能去惩罚罪犯,可这就用第二定律违反了第一定律,人工智能不会执行命令。再比如,不可对人类造成伤害与对人类袖手旁观本身就有矛盾点:罪犯劫持人质,或者正在伤害他人,只有用伤害罪犯的方式才能解除伤害等。甚至人工智能不能对人类做手术——做手术会伤害人类的身体。所以又出现了第零定律:人工智能必须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不受伤害,且三定律都不可违背第零定律(2)[30]。
显而易见,无论我们给人工智能植入何等伦理规范,人工智能的决策和判断可能都非常艰难。因为很多伦理问题,人类尚无法作出较优判断,又何谈人工智能呢?
(二)对于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规定不明
1.《格里申法案》中法律定位的模糊性
《格里申法案》要求明确人工智能民事行为的性质与主体地位,但并未规定人工智能的法律行为能力,以及是否比照法人或新设独立主体确定人工智能是特殊的民事主体[31]。从整个法律文本来看,由于过分强调代理人、所有人、工作人员和开发者的独立责任,人工智能的独立民事责任并未明确界定,尤其是对其所有人、占有人和管理人的独立民事责任。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可以比照封建时代家长制下的奴隶,即便是生物意义上的“人”,也不能成为法律关系中独立法律主体;只有经过父母或主人的认可,才能代表父母进行商业活动,但法律行为的后果和责任可能是父母或主人承受[31]。
因此人工智能虽然被法案授予民事主体地位,但人工智能只是其所有者的附属品,在与所有者、相对人的三方之间仅形成代理与委托关系,所有人工智能与相对人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都归属于其所有人,人工智能依旧不具有独立法律人格。尽管该法案还赋予人工智能独立财产权,不过是基于对所属者的依附,其财产权的责任与义务受到较大限制。这也引发了质疑:财产权既然最终归所有人,那么人工智能拥有独立财产权的意义又在哪里?
同时,《格里申法案》虽然确立了人工智能作为代理人的民事主体地位,但不被视为普通的诉讼主体,只能“在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下”于法院或法律保护机构(如检察院等)参与民事诉讼,其利益只能由相关的所有人和法人主体代表。因此,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概念不明确,其法律地位也不明确。
2.欧盟“电子代理人”决议中的人工智能定位问题
欧盟“电子代理人”决议承认人工智能拥有独立思想、具有人的部分特性[28]。但如果人工智能被赋予人权,是否就意味着“人工智能与人平等”。决议对于人工智能该属何种法律实体及是否拥有主体地位并未明确。人人平等是最基本人权,是一切利益和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无论国家国体、政体如何,都可寻求某种方式加以保护。如果人工智能适应人权和人类伦理规范,它是否具有与人类相同的法律地位?如果它与人类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是否会导致现行法律体系的崩溃,甚至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伦理和社会逻辑的崩溃?这都是“电子代理人”决议亟待解决的问题[32]。
(三)缺少具体规则标准与实施能力
1.《格里申法案》中对比照相关主体适用法律的模糊以及实施问题
《格里申法案》对于人工智能主体资格定位多重,无法清晰区别:规定人工智能与动物在财产问题上具有特定相似性,但没有明确人工智能在财产问题上可以适用或准用相关的动物法律[33];规定人工智能在民事权利方面可以适用法人的民事立法原则,但人工赋予智能的权利却远少于法人,与人工智能的民事主体地位不相匹配。《格里申法案》明确机器人-代理人具有程序上的民事诉讼权利,可以作为民事诉讼主体(3),但因为民事实体权利的极大限制,使人工智能的流转只限于相关主管机关规定的类型与范围,同时因未具体规定人工智能在何种情形下可以作为民事诉讼主体,只笼统规定“比照民法典与其他法律类推适用”。归责方面也更多将相关人员作为对象,人工智能仅在于由于自身设计问题人类不可控的情况下才可作为归责对象。
2.欧盟“电子代理人”决议的实施问题
尽管欧盟会议通过了人工智能报告,但右翼保守派把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问题与外来移民等问题关联起来,认为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就是将它们看作人,会抢夺普通自然人的工作岗位,这阻碍了对人工智能赋予法律人格的实施(4)[28]。因此,欧盟2020年发布的《人工智能系统运营责任立法倡议》已经改变立场,明确指出:“对现有法律框架进行任何必要的修改,首先要明确AI系统既不具有法律人格,也不具有人类的良知,其唯一的任务就是为人类服务。”[34]
四、以《民法典》代理权的视角构建人工智能法律人格
(一)《民法典》代理权视角下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构建
1. 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诞生与消灭
由于人工智能不具有“天赋人权”,主体资格系法律后天拟制和构建,商业活动中作为电子代理人的人工智能,是一种具有智能性、交互性能够独立回应、处理电子数据的自动化智能程序[35]。低智能的电子代理人可以提供商业意见,高智能的电子代理人甚至可以自主作出商业决定,订立合同。类比律师事务所、基金公司等代理权行使的实践,赋予人工智能代理人法律主体资格:比照法人主体资格登记制度,建立人工智能主体资格的产生与登记制度。
(1)人工智能的开始和终止时间。借鉴公司法关于法人的成立登记和注销制度确认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开始和终止时间,同时配套强制审核登记制度,即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应该进行强制审核。人工智能自审核通过登记之日获得法律人格,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自注销登记之日起,主体资格消灭。
(2)人工智能的注销登记条件。
当人工智能出现法律规定的注销登记条件时,应该进行注销登记,消灭其法律人格[36]。人工智能的消灭条件,包括破产、难以为继(维持人工智能的成本远超过其利益),或法律要求销毁、禁止生产等。格里申法案规定:“机器人-代理人拥有独立财产并以此承担债务和责任,可以自己名义取得并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机器人-代理人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参加者”。在《民法典》将来修订时规定:人工智能解散、被宣告破产或有法律规定的其他原因时,可以进行清算、注销登记,使人工智能人格终止。
2. 《民法典》代理权视角下人工智能民事权利能力范围
尽管人工智能越来越具有类人性,但终究不是自然人,法律也不会赋予其自然人同等的法律人格。人工智能虽然与法人具有相似性,但毕竟不同于法人,其人格制度在借鉴法人人格制度之时,也应与之有所区别。在代理权视角下,人工智能的权利能力必须是特定且有限的。有限权利能力是人格要素不完整的主体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所享有的民事权利能力。完整的法律人格应该自我负责、完全独立,未来的强人工智能可能拥有完全独立的思维和行为能力,但目前的人工智能尚不具备[37]。目前的人工智能可以参照法人与非法人组织(5),以人类的“代理人”“受委托人”身份行使民事行为。如松琦教授团队“委托”有岭雷太写小说,微软“委托”小冰创作诗集等。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企业开始使用电子代理人开展商事活动,企业使用的各种智能化交易系统不仅能根据要求独立完成特定的商业事务,还能订立甚至履行合同[39]。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会出现于商业、法律等专业领域,给予其相关的民事主体资格,有利于使其在职权范围内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但“强人工智能”与“弱人工智能”的民事权利能力范围应该加以区分:(1)对于没有独立意志或独立意志薄弱的“人类智力仿真”弱人工智能,其行为系由人类设立相关程序,仿照人类活动而形成,可以比照《民法典》無行为能力人加以规定(6),或者直接适用产品责任的规定,无需赋予主体资格。(2)对利用神经网络深度学习,拥有自主进化和学习能力、自主判断力的人工智能,可以比照《民法典》限制行为能力人。(3)对最终的强人工智能以及超人工智能,是否可以成为民法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科技领域对此尚有颇多争议(7),法律界现在亦无定论[39]。但当人工智能拥有完整的自主意识,能独立判断和实施民事行为之时,法律也应该给予其完整的民事能力[38]。法律肯定人工智能的权利能力,但是考虑到技术发展、道德和伦理的制约,其权利能力应当予以一定限制。事实上,赋予人工智能权利能力却又限制其权利范围,本质上并不矛盾,都是人工智能制度构建的应有之义。同时,人工智能享有的民事权利可以通过不完全列举的方式规定,使人工智能的主体资格衡平人类社会发展。
根据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篇规定,法人拥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8),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9),此等权利可以扩展至人工智能。目前,一批优秀的人工智能(如Alpha Go、索菲亚等)已经在世界范围有知名度,应当享有名称权、名誉权等权利,使其能够承担相应责任。
(二)《民法典》代理权视角下人工智能民事责任制度
1.《民法典》代理权视角下人工智能民事责任制度的内容
《民法典》代理制度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
人工智能大幅解放人类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通过赋予其相对独立的法律人格,使其享有权利,同时也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40]。法律对人工智能民事责任承担制度的规定,是人工智能主体资格构建的关键点。以代理制度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民事责任制度应考虑以下内容:
(1)独立财产。能够被法律承认为民事主体的人工智能应具有独立可支配的财产,可以利用其本身所拥有的财产履行义务,承担民事责任。
(2)具体民事责任承担制度的构建应该考虑弱人工智能,其性质只能为“产品”,责任承担应依据“产品责任”或“替代责任”制度予以追究。
(3)人工智能虽然被法律规定为民事主体,但非法设计、制造、使用或恶意操控人工智能的第三人,超越登记范围进行活动,致人损害需要承担民事责任时,应该参考“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明确承担责任的主体。人工智能的恶意设计者、制造者、所有者及恶意操控人应该承担法律责任[41]。
2.《民法典》代理权视角下人工智能民事责任承担方式
承认人工智能具有独立法律人格,拥有独立财产并享有部分民事权利,能够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在责任承担方式上,人工智能可以承担绝大多数返还性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42]。即使在人工智能自身独立财产不足以支付赔偿且基金制度尚未完善之时,人工智能也可以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或由其被代理人来支付罚金,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一点可以比照公司法人和自然人:由于公司法人拥有财产,所以罚金对公司法人而言是最容易的刑罚方式,对人工智能也是如此:自然人犯罪支付罚金,那么他的家人会因此失去金钱;公司法人支付罚金,其员工、主管和客户便不能再使用其资金。
但是人工智能防御性责任的承担却仍存在困难。比如,以自然人特有的羞耻感为基础设立的“赔礼道歉”就难以适用于人工智能。因此,有必要针对人工智能的特点增设其专属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具体而言,可以增设修改程序并设立阈值、清理恶意程序、强制销毁、禁止生产等专属人工智能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修改程序并设立阈值,是通过程序技术识别分析出人工智能中致人损害的程序进行修改,并要求人工智能的生产者为人工智能设立安全阈值,将人工智能学习和决策的能力限制在合理的安全范围内[43];清理恶意程序,是指通过恶意程序检验,将人工智能运行过程产生或外部输入的恶意代码删除(10),若删除之后,经评估人工智能仍然具有可利用和改造价值,可以添加新的程序,使其能够再次进入市场。在人工智能致人损害程度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大,前两种责任承担方式难以消除影响的情况下,则可以考虑销毁,同时禁止生产该型号的人工智能。
同时应该加强人工智能的人格建设,如我们熟知的“索菲亚”“阿尔法狗”等人工智能均拥有自己的身份、名号以及一定的知名度。将人工智能与其身份姓名相绑定,即可让其通过在媒体网站、报纸杂志等发表道歉声明,对损害他人人格权的行为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人工智能本身的公众人物身份与名气都可以成为使赔偿更为有力的工具。
3.“揭露人工智能人格面纱”制度的建设
刺破人工智能人格面纱制度是指在满足法律规定条件的情况下,拒绝承认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独立存在,即使其符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全部构成要素。该制度的核心在于,使藏在人工智能背后的恶意制造人、使用或管理人“原形毕露”,使这些恶意者直接承担人工智能的侵权责任,而非被代理人责任。
结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特点,参照“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建立“人工智能人格否认”制度。人工智能理应享有的是以代理权补充的独立法律人格,在《民法典》中,应规定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对于人工智能与他人串通损害客户(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规定。
但是,由于目前强人工智能尚未出现,人工智能尚不能完全分辨自己的行为并反抗人类的命令。所以当人工智能的制造者或使用管理人恶意利用人工智能的独立法律人格,实施加害行为,却将法律责任加诸人工智能之上。此种情形显然与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制度的设立意愿背离,对人工智能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参照“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表现行为,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设立“揭露人工智能面纱”的制度,使其背后的制造者或使用者承担法律责任:
(1)申报注册登记的人工智能用途、使用技术以及性能报告、人工智能出生日等关键性信息不实,则人工智能法律人格自始不存在;
(2)恶意编写损害人类利益的代码,造成侵权甚至违反法律行为,危急社会公共和个人人身财产利益的;
(3)使用者不按照工作说明操作人工智能,使其进行违法犯罪等活动[44]。
被揭露面纱后的人工智能,其责任由造成人工智能面纱揭露的主体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责任。不能因人工智能为非传统的法律主体就逃避法律制裁,但需要考虑在不同的责任类型中设定人工智能特定的责任承担主体。
五、结语
法律应顺应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进行完善与超越。世界主流观点认为可以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一些国家规定非人生物也可成为法律诉讼主体,法律主体制度不仅为人而生,亦可为非人而设;沙特阿拉伯承认人工智能“索菲亚”的主体地位,规定人工智能是独立法律实体。在一定条件下,传统法律主体制度可以突破,人工智能亦可成为法律主体。尽管大多数观点接受人工智能应当具有法律主体资格,但在实践中,如何以《民法典》代理权视角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界定人工智能的内涵和外延、丰富现有法律概念,还需要解决诸多问题。新的法律人格理论尚须进一步厘清基本人性与法律拟制人格的关系和区别,以及人工智能人格的局限性,以适应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实践。
注释:
(1)欧盟电子人决议原文“Robots’ autonomy is likely to grow to the extent that their ethical regulation will become necessary, by programming them with ethical code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prevent their harmful behavior (e.g. endangering humans or the environment)”,决议认为机器人自主性增长过快,因而有必要制定道德规范来防止机器人的危害行为。
(2)根据俄罗斯全国门户网站保安和安全网发布的信息称,皇家科学界和英国科学院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直言,机器人定律可以用一条普遍的规则来取代:“人必须成功”。
(3)格里申法案第一条规定:“机器人-代理人拥有独立的财产并以之为自己的债务承担责任,可以以自己名义取得并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机器人-代理人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参加者”。
(4)如俄罗斯国家杜马信息政策、信息技術和通信委员会主席莱昂尼德·莱文说过,机器人化将导致“驱逐劳动力”,例如银行、会计和法律服务、工业。因此,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面临失业上升。这是事实性的阐述,但保守派势力将这种威胁与移民等问题结合,过分夸大了人工智能的威胁。
(5)参照《民法典》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6)《民法典》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有:第十八条 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第十九条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二十条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第二十一条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适用前款规定。
(7)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何立民所言:“(现在)人们有条件开始研究弱人工智能生成机理,展望强人工智能,但却难以预测未来的超人工智能。”
(8)《民法典》第五十七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9)《民法典》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
(10)外部的恶意代码主要通过包括病毒、懦虫、远控木马、僵尸程序、勒索软件等攻击形态进入,可以通过传统计算机安全防护手段与深度学习结合进行防护,具体可参考张铭伦先生的:《面向恶意软件对抗样本攻击的可信人工智能防御方法研究》。
参考文献:
[1]刘辰.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先发优势[J].中国科技产业,2017,(8):78-79.
[2]A. M. Turing.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J]. Mind, 1950, 59(236):433-460.
[3]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人辞典[M].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687.
[4]叶欣.私法上自然人法律人格之解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4(6):125-129.
[5]吴高臣.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研究[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42(6):20-26.
[6]张绍欣.法律位格、法律主体与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J].现代法学,2019,41(4):53-64.
[7]邹瑜,顾明. 法学大辞典[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63.
[8]宋磊.从爵的法律特权变革的角度再释法律儒家化[J].社会科学,2021,(6):161-170.
[9]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10]陈广文. 重建修正案的评价与解释[D].济南:山东大学,2016.
[11]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J].法学研究,2003,(4):3-14.
[12]胡长兵.法律主体考略——以近代以来法律人像为中心[J].东方法学,2015,(5):46-54.
[13]张力.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古罗马法渊源[J].学术论坛,2008,(4):137-143.
[14]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 2017年校订版)[M]. 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15]荚振坤. 中世纪欧洲海商法研究(11 至 15 世纪)[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3.
[16]马克斯·韦伯. 中世纪商业合伙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0.
[17]宇培峰.“家长权”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1.
[18]德国民法典[M].杜景林,卢谌.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19]唐伟元.论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J].科技创新导报,2008,(18):126.
[20]许中缘.论人工智能的工具性人格[J].法学评论,2018,36(5):153-164.
[21]崔恺旭. 计算机围棋強化学习中的神经网络[D].北京:北京邮电大学,2019.
[22]张悦.论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20.
[23]曹越.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问题研究——以“微软小冰”为例[J].社会科学动态,2019,(3):75-82.
[24]曹建峰.10大建议!看欧盟如何预测AI立法新趋势[J].机器人产业,2017,(2):16-20.
[25]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J].中国医学伦理学,1998,(2):2-66.
[26]高奎.生殖性克隆人行为的世界立法应对[J].法制与社会,2009,(21):325-326.
[27]The first rule of robotics... The State Duma will prepare the rules for human communication with robots [DB/OL] (2017-12-20)[2021-06-11].http://guardinfo.online/2017/09/26/pervoe-pravilo-robototexniki-gosduma-podgotovit-pravila-obshheniya-cheloveka-s-robotami/.
[28]UNESCO science experts explore robots’right [DB/OL](2013-05-06)[2021-06-11].http://www.unesco.org/new/en/media-services/single-view/news/unesco_science_experts_explore_robots_rights/.
[29]阿西莫夫. 我,机器人[M].国强,等,译.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1.
[30]艾萨克·阿西莫夫.银河帝国 12 机器人与帝国[M]. 叶李华,译.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31]王春梅.《格里申法案》机器人二元定性的启示与反思[J].江汉论坛,2020,(9):127-131.
[32]袁昭江. 欧盟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20.
[33]张建文.格里申法案的贡献与局限——俄罗斯首部人工智能法草案述评[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21(2):32-41.
[34]郑志峰.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责任的立法论与解释论——以民法典相关内容为视角[J/OL].东方法学,{3},{4}{5}:1-15[2021-07-14].https://doi.org/10.19404/j.cnki.dffx.20210430.010.
[35]周洪政.网络时代电子要约和承诺的特殊法律问题研究[J].清华法学,2012,6(4):162-176.
[36]沈建铭. 论人工智能实体的法律主体资格[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7.
[37]乔芳娥. 人工智能对民事主体地位的挑战与应对——以未来强人工智能的出现为视角的分析[C]. 2021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组委会.《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21年第5卷 总第53卷)——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法治论坛文集.2021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组委会:上海市法学会,2021:10.
[38]张沁芊.电子商务中人工智能体的民事责任研究——以“电子代理人”为例[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20,40(1):100-105.
[39]何立民.人工智能系统智能生成机理探索之六 从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到超人工智能[J].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2020,20(8):87-89.
[40]吴戈.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问题及其伦理思考[J].中州学刊,2021,(3):93-95.
[41]梁慧星.《民法总则》重要条文的理解与适用[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51-65.
[42]梁志文.论人工智能创造物的法律保护[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35(5):156-165.
[43]雷恩·卡罗,郑志峰.人工智能政策:入门与路线图[J].求是学刊,2019,46(2):25-44.
[44]韩旭.人工智能侵权责任主体问题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20.
Constructing the Qualification System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bject with Theory of Agency in the Civil
Code: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Current Robot Draft
LYU Qunrong,CUI Litian
(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 510515,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takes the evolution of natural persons and legal persons as the research starting point, considering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ould be endowed with legal personalit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two characterist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relatively independent free will and cognition, and the ability to enjoy rights and bear obligations. Meanwhile, due to the incompleteness of the independent wil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assumption of it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may be determined by reference to the “agent” system, and the scope of capacity for civil rights and the system of civil liabil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all be establis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legal acts by natural persons and legal persons on behalf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subject qualification; theoretical basis; the agency
編辑:邹蕊
3905500338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