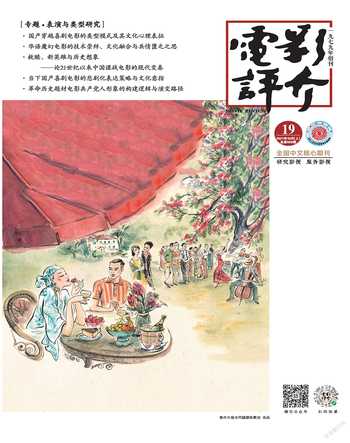救赎、新英雄与历史想象
陈昊

谍战片作为中国电影长期以来的特定创作题材之一,在经历“二战-冷战-后冷战”的政治环境与文化氛围后,显现出颇为特殊的发展脉络。这种脉络或可推演至身负重大任务的影片《天字第一号》(1946)、《黑夜到天明》(1947)、《忠义之家》(1946)等[1],再至十七年时期表现革命兼建设功能的集合体《山间铃响马帮来》(1954)、《神秘的旅伴》(1955)、《虎穴追踪》(1956)、《国庆十点钟》(1956)、《羊城暗哨》(1957)、《英雄虎胆》(1958)等影片,而后经过叙事技巧浸润与娱乐属性汇拢,谍战片在自身重构中拥有更富现代意义的类型特征,涌现出《保密局的枪声》(1979)、《特高课在行动》(1981)、《蓝盾保险箱》(1983)、《波斯猫在行动》(1986)等。至21世纪后,谍战片陷入国产商业大片与好莱坞高概念电影建构的瞬息洪流之中,显现出“自问此身”的彷徨与踟蹰,这种矛盾心态直接表现为创作热情的冷却与创作意图的回避。尽管如此,21世纪后依旧产出以《色·戒》(2007)、《风声》(2009)、《秋喜》(2009)、《东风雨》(2010)、《听风者》(2012)、《智取威虎山》(2014)、《一号目标》(2014)、《密战》(2017)、《悬崖之上》(2021)等作品为代表的谍战片,其中亦涌现不少佳作。
当然,作为新中国的间谍片、反特片抑或谍战片,必然与《天字第一号》等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基础与话语立场,也别于前苏联式的间谍题材文本,亦与“007”系列、“碟中谍”系列乃至“谍影重重”系列有着更为殊异的语境表达与价值选择。但从更为广泛的世界谍战片发展来看,中国式谍战片在某种程度上依旧无法摆脱战后以《天字第一号》为代表的“间谍片”类型特征,也深受风靡全球的谍战类“超级文本”扩散效应的影响。同时,中国谍战片本身也未被旧有规范所累所困,在21世纪的短暂沉积后显现出一系列新的风格特征,乃至被相关学者冠以“新谍战片”[2]之名。
一、再救赎:救赎母题的扩展与深化
作为人类永恒的母题之一,“救赎”母题在人类历史发展与文化演进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诺亚方舟到大禹治水,“救赎”被宗教、历史、文化不断进行多重演绎,不仅成为诸多童话/神话的文化根源与集体意识,也成为更具精神价值与指引能力的心灵感召。本雅明在《德意志人》(1937)中曾提及作为“拯救”象征的诺亚方舟,其题外之意在旁人看来不言而喻:“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洪流,通过文学获得拯救”[3],进而追求个体批判的救赎之路。但是,本雅明并未就此忽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意义,而是基于其救赎史观将神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将后者与法西斯主义的对抗性视为“当时唯一可以借助个体谋生和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介”[4],是用以实现神学意义上的末世审判与弥赛亚救赎的通途。由此,本雅明充分肯定了革命者之于世界的救赎意义,同时也将其视为“救赎”的功能承担者之一,而承担者的意义正在于本身的政治性和战斗性以及为了救赎任务而作的艰辛的奋战[5]。
实际上,作为“救赎”的功能承担者,革命者及其相关形象已然进入谍战片的人物序列,并作为整个故事重要的逻辑支点与意义生发点。在谍战片中,革命者(地下党)本身便是“救赎”行为的发动者,同时也肩负着卧底/潜伏任务背后更深层次的民族使命与政治责任。当然,在当下的中国语境,这种颇具宗教色彩的“救赎”母题被悄然置换为“解放”与“牺牲”,进而显现在谍战片中的是我方谍报人员为完成任务(通常为窃取、传递情报与营救、护送人员)作出的一系列地下工作。如在《风声》中,顾晓梦与吴志国二人需在5天内传递情报拯救组织;《秋喜》中晏海清需查明國民党撤离广州前的“阻挠计划”;《东风雨》更是直接以“珍珠港事件”中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代号“东风,雨”为题;而在《悬崖之上》中则是以共产党特工任务小队寻找并护送日军进行人体试验的见证者为目的的“乌特拉行动”为核心叙事动力。由此,这些行动因影片叙事逻辑具有了运作的正当性,一方面其本身作为彰显我方谍报人员英勇智慧的呈现情节,将拯救者进行具象化表现;另一方面则囿于历史事实与主题先验,这些任务即使复杂曲折但也是必然成功的,进而也就形成了救赎的必然性。从这一角度上来说,这些行动本质上即是“救赎”话语的附着物,即本雅明在《历史哲学史纲》中所言的“粗俗的、物的东西”“但没有这种粗俗的、物的东西,神圣的、精神的东西就无法存在”[6]。
同时,当下中国谍战片对于“救赎”母题的探讨更是显现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辐射范围,即从对同志、组织、被迫害人员的拯救推衍至更为深广的民族救赎与国家救赎。与教育意味颇为浓重的十七年反特片与新时期娱乐意识复归的间谍片,这一时期中国谍战片更多表现的是出自民族大义的使命感。当早期谍战片复制再生产“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有关警惕帝国主义颠覆势力和阶级斗争的话语时,当下谍战片已不断将“救赎”话语安排在人物自白与历史总结中,一如顾晓梦(《风声》)在遗书中提及:“我不怕死,怕的是爱我者不知我为何而死……只因为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在这里,我辈(革命者)作为挽救民族(民众)的拯救者不被直接言说,却是以挽救民族的崇高精神而存在。谍战片需要精神制高点,不能局限在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是要展示或弘扬一种难以达到的理想化的精神境界。[7]这种精神境界将个人化的信念追求与集体性的家国理想结合起来,成为支持个体英勇奋斗乃至奉献生命的不竭动力,也是号召及实现“救赎”的口号与旗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救赎性话语往往伴随的是性别及其权力关系。不同于此,前谍战片的性别表达与阶级对立,当下谍战片中女性逐渐摆脱作为凝视对象与价值批判的双重功能,从“事实上充当着视觉动力的给出者”[8]逐渐转型为足资想象的被救赎者具象,以此想象性地给出革命与女性间的对位关系。以《风声》《听风者》《东风雨》《悬崖之上》为代表的谍战片将女性附加于男性同样功能的革命者属性,进而将其改造为致力于救赎民族的革命者,化身我方间谍部门领导、特工乃至亦敌亦友的军统特工。这种处理方式固然为剑拔弩张、谍影丛生的谍战片带来一丝女性视角与异质情感,但更多的是以女性革命者、拯救者、殉道者的形象,借以抚慰某种历史焦虑与历史想象。在这个角度上,女性被托举至革命者的高度,成为“救赎者”的肉身镜像。巧合的是,谍战片的这种性别弥合或补充,竟暗合最初的谍战片——《天字第一号》,其女主角俨然同前文所指一样以“爱国女英雄”的身份肩负着救赎使命,并以自身与汉奸同归于尽成全战友,集拯救与殉道于一体。
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曾经的“美蒋特务”“苏修特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之初”为背景的隐蔽战线谍报故事却还在持续生产。这一创作现实尽管基于历史与民族背景,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与当下国家现状的断裂:至21世纪,当中国基本完成国家体系现代化建设,积极开展国家战略参与全球话语之际,谍战片这一集体记忆的影像造物所代表的却是国家建立的荣光及其伤痛病症。若前瞻至更远,谍战片对于“救赎”母题的再度阐述与生发无异于更具时代性与未来感,或许可以这样解释,中国谍战片的浸明浸昌与当代中国现状相勾连,当“救赎”的畛域与意义不断扩大,其对于现代中国所抱有的民族理想与世界情怀恰是一个完美的隐喻。
二、新英雄:英雄性美学传承与变化
卡尔·荣格基于心理学与神话学认为“我们在可视人类的形象中寻求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凡人,而是超人、英雄或者上帝,是‘准人类’,他是掌控和塑造灵魂的观念、形式和力量的象征”[9],而谍战片作为传统英雄叙事的经典影像类型,其突出功能便在于对英雄的塑造与阐释。从十七年时期的反特片、间谍片乃至公安题材电影始,银幕之上的特工们已然成为英雄的化身。这不仅仅是因其本身的“英雄品质”——智慧果敢、英勇机敏,乃至风度翩翩、能歌会舞,更在于其“行正义之事”而具有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可以说,以上两种属性共同建构了中国式谍战片的英雄形象,也大致确定了“英雄”文本的演进路径与基本元素。这种英雄形象的展现与传播在中国电影不断实践与发展的背景下获得了动态性的生成空间,随着中国社会步入现代与后现代混杂并置的大语境中,当下谍战片在建构传统英雄的同时也由此生发出新的英雄美学,即呈现出某种在“英雄”之上的美学特征。
所谓“英雄之上”,或可称其为“新英雄性”,意在指相对超脱传统英雄之外的“英雄性”。如前文所言,传统意义上的谍战英雄以勇力示人,往往具有某种刻板化或模型化倾向。这固然囿于特殊历史时空对英雄人物的特定要求,也受限于英雄本身所裹挟的神圣性——相异于普通人的成长、彷徨与精神危机。而当英雄遭遇某种身体暴力的直接施加时——如酷刑,便将传统的英雄性引入更隐蔽的斗争场域,即痛苦与意志的较量。需要说明的是,正是基于痛苦与意志这一相互矛盾且充满张力的元素,使“新英雄性”避免陷入某种暴力展示性的奇观美学,而指向英雄在遭受暴力过程中显现的精神性美学价值。
若有意忽略英雄叙事与集体主义间细小的悖论或断裂,那么对个体的身体暴力或许将会为“新英雄性”美学采获更广泛的意义与价值。当英雄落入敌手,采用暴力手段逼其就范实是常规手段。但谍战片对此进行超常规的直接描写,则在简单的二元对立中营造更大的戏剧冲突,进而把表现行刑类型及方式当作对于英雄美学的开拓。有学者将谍战片对酷刑的展示视作恐怖元素在当下中国语境的类型转移[10],亦有学者注意到当下意在“斗智”而实质上更多依赖酷刑(基本上到了不加节制的地步,这种无节制的暴力渲染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国产大片”中)[11]的谍战片发展现状,还有相关学者认为谍战片中酷刑的视觉效果更多的是视觉消费,而无助于叙事[12]。但以酷刑为代表的身体暴力并非仅仅局限于奇观展现或类型需要,而是将其作为“英雄”的升华路径,用以凸显“新英雄性”的美学特征。实际上,以酷刑折磨、逼供革命者的桥段早已有之,常见于革命历史题材。如在《烈火中永生》(1965)等影片中,便出现颇为极端的刑讯场面。但在之前的谍战片中,此類桥段并不多见,或有几部“打入”式影片出现主人公在重重考验中将被戳破或陡增怀疑的危急场面,但由于此类谍战的先验主题,往往难以形成真正的紧张氛围。同时,片中遭受暴力刑讯的往往也并非英雄本人,而另有殉道者或象征者。以《英雄虎胆》为例,侦查科长曾泰打入土匪内部时遭匪首李月桂怀疑,故派亲信佯装解放军被俘受刑,以此试探曾泰底细。特别的是,当听到远处阵阵惨叫时,李月桂向曾泰作出的解释却颇有用意:“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来什么。”这无疑是在公开地宣扬英雄的英勇与顽强,尽管与之后的“冒充桥段”形成明显的错位,但其根本用意却是显而易见的。而当曾泰即将暴露时,则另有同志冒充曾泰,以殉道者的形象承担肉体之痛并慷慨赴死。值得注意的是,影片虽展现了鞭打等刑讯样式,但并无意展现其酷刑本身及受难形象,而将其作为展现主角“英雄感”的侧面描写。
不同于此的是,当下谍战片以超写实的身体暴力展现英雄在生理上的苦痛与折磨,形成所谓的“濒死时刻”或“死亡逼近”,进而将英雄身上的英雄属性引入精神/信念领域。如果说此前谍战片对英雄塑造呈现出对英雄美好品德与优良品质的表述趋势,那么当下谍战片则更多地形成从静态到动态,从皮相到精神,从单线轴英雄到层次化塑造的基本走向。当明确、公开地对英雄采取暴力行为时,英雄需要经受肉体考验以证明理想与精神的崇高。因此,对于受刑英雄及凝视观众而言,承受并通过酷刑考验是比死亡更能证明信仰的绝佳路径,其最终结局虽依旧指向死亡,但与死亡相比,酷刑这一充满仪式意味与“表演”性质的处决程式,在本质上更能引发英雄本身的崇高感,进而激发观众情感认同与心理期待,显现出超出传统英雄外的精神美学。这种美学在以《风声》《悬崖之上》等影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同时也建构起较具代表性的影像元素:潮湿阴暗的空间、冷酷无情的行刑者、偏执暴虐的敌首、各式各样的刑具以及遍体鳞伤的英雄。实际上,《风声》中的英雄被绑在刑台上接受电击、针刑,便已然具有了身体消费意味;但当这种刑罚被持续性地直观展现后,所营造的暴力奇观便转化为以英雄为代表的观众自我与其假想敌的对立。尤其当我方英雄在经历莫大痛苦后依旧坚韧不屈,更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英雄性的生产与转化。而《悬崖之上》则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风声》的类型特征,并在其中融入家庭元素,使其“英雄意味”更富情感张力。此外,此类谍战片在个人/集体、民族/国家间试图开辟英雄表达的新路径,将英雄作为集体的某一投射。有别于“007”系列、《碟中谍》系列以及《谍影重重》系列等西式间谍片的“科技炫耀”与“绝对主角”属性,中式谍战片往往并不具备尖端的武器工具、无间的团队配合以及强大的后勤保障等“高概念”元素,其“英雄”本身亦往往最终消解在历史与人民的汪洋大海中,被指认为包纳多方话语的集体显现——“他/她只是普普通通谍战者中的一员,代表的是无数在隐蔽战场的无名英烈。”
由此,当下中国谍战片对英雄及英雄精神的塑造或在某种意义上再次实现了“英雄”对社会的意义询唤与价值建构,对英雄的缺失/空位作出了补偿,迎合大众对可视英雄的普遍需要,认可英雄背后所投射的文化意涵。在此基础上,谍战片以其“新英雄性”的美学姿态融入国家主流话语,尤其在建国60周年、建党100周年这样的历史节点上,重温革命历程与民族记忆,纾解现代与后现代下的集体焦虑与信仰困境,将同革命历史题材一样富于“献礼”意味的谍报故事献映于公众眼前,造就英雄绵绵不绝的心灵回响。
三、软历史:历史想象及想象消费
基于电影的“叙述—表意”能力,其往往被视作“历史”的一种叙述。这种电影叙述既需借鉴现有的历史文本,以此作为影像改编的先决基础,又需突破历史作为“前结构”带来的限制,将历史内在的“可能性”扩展为历史的“可想象性”,进而作为阐释与想象历史的依据与凭证。谍战片作为以特殊历史时空为背景的历史叙事创作,其对历史的再现或重述均建立于某种“可能性”之上,借以腾拓出更大的想象或创作空间。从这一角度来看,谍战片或许成为昭彰某段历史意义的存在,乃至成为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本身亦成为一种历史“事件”,与历史一样都具有“诗性”的深层结构,具备想象性与虚构性特质。若以新历史主义观之,谍战片在审视主体与历史,探求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中形成一种寻求历史性与文本性平衡折中的“历史诗学”,恰切合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立足点——“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也即形成谍战片对历史的想象性建构。但当这种想象性建构成为社会的符号消费对象时,重新解读历史的“想象”或“想象力”便被裹挟在“商品”类目中,消费主义的指向就开始从作为普通商品的消费品转向作为人类意义载体的历史,历史及历史的诸种转化都被当作消闲之资[13],当下中国谍战片便不可避免地承担着消费的功能。
不同于十七年时期的反特片以政治宣传、陈说为目的的历史,21世纪,中国谍战片在新历史主义语境下进行历史的重新演绎或转述,逐渐脱离刻板僵直的固定话术,转而在不断的方法更新与观念整合中求得一种通俗化、和缓化的历史“认同”“利用”和“化解”模式。这种模式既具有一定的总体历史观,对过往的硬性历史进行范围内的“微调”或“修正”,同时又贴合大众,以重意而非史的叙事满足当下对想象的消费需求。当然,谍战片本身并非一个超历史的审美客体,而是特定时代的历史、阶级、权力以及文化等语境的产物,对谍战片的读解也应当注意文本阐释的特定语境以及这种语境对谍战片存在方式与存在状态的“抑制”与化解等因素。因此,若要考查当下谍战片对历史的想象及其消费,即要进行“双向调查”:电影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其意义在阐述者/想象者所处的不同场域和语境中不断生成;而电影也只有纳入具体的时空语境之中才能显现其真正意义。作为依托真实历史环境或背景的谍战片,其本身意义的建立便在于其基于历史的想象及生发的现实关照,尽管这种历史同样经过权力的“挑选”和“抹除”,但作为正统历史的想象及其消费行为依旧能够反映出特殊的时代症候与社会需求。如果说,历史作为既有事实记录表述了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那么,作为依托历史的谍战片则在活动影像的技术上完成对历史的想象与重述,成为民族认同的群体表达。
实际上,21世纪后的中国进入一种民族复兴之路的历史阶段,其作用于谍战片内便显现出新的想象路径——从对民族/国家身份的追寻转进为一种对自身根源/传统承继的自信。这种路径在经历冷战—后冷战时代后又穿插了接轨国际与社会升级的变革历程,其变化是颇为显著的。与20世纪中国谍战片相比,在新世纪涌现出的谍战片已然出现相当程度的观念更新,国共两党的地下斗争已然不再是作为主要对立面被呈现,与国民党特工斗争也不再是确证自我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当英雄主动或被动采取行动,敌人被指认为集体性的敌人——日本特高科、伪满洲国保安局、汪伪政府特工总部(76号),所言说的故事也不再是反渗透、反破坏、稳固新政权的保卫故事,而是孤胆英雄潜入敌营获友方帮助共同完成抗敌任务的神勇故事。在这种故事中,新中国政权的历史选择性已不再是着重表现的重点,而是将民族问题、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推至前台,更多地将正邪对立放置于抗御外辱的战争之中,国共特工在意识形态的整合中寻求双方共识。由此,当下中国谍战片开始大胆引入国共特工间的合作活动,表现国民党特工在抗日战争中的正向作用,乃至在《东风雨》中展现日籍共产党员赴上海进行反侵略活动的情形。有趣的是,影片《风声》出于种种原因并未出现国民党特工的身影,但在其同名原著小说中却将顾晓梦身份设置为国民党军统安插在汪伪政权机要部门中的秘密特工,并最终与中共地下党员李宁玉配合送出情报,这一想象性的困境解决方案无疑是“枪口一致对外”这一统战宣传的明证。
从大历史角度而言,这种历史想象在尊重历史的基本脉络与基本结果的基础上,在历史局部开辟出合理发展的空间,同时又迎合当下社会的消费思潮,将历史想象的艺术功能与文化消费的经济功能相结合,伴随着受众对谍战片内在想象力与历史还原度的审美需求。因此,谍战片的历史想象及想象消费,或许是当下谍战片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一如前文提及的多种酷刑的还原写实,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谍战片除惊险悬疑、斗智斗勇外另一重要的票房增收支点。再如当下谍战片开始逐渐模糊历史与想象的界限,借用历史人物进行特殊的时空构建。《色·戒》中以丁默邨为原型塑造易先生,《听风者》中护送教授北上抵京似影射自钱学森归国一事,《悬崖之上》则以日军731部队在东北的反人类试验为背景,以上影片通过这种历史与想象相互交融的叙事方法,恰将历史想象以某种历史共时性或时空错觉式的方式建构并消费。可以说,谍战片的历史想象及其消费既体现出当下中国电影在新历史主义语境下的民族志书写,更是电影、经济与民族共同体的耦合与裂变,成为被遮蔽或被遗忘的历史的一种重写与猜测。
结语
综合来看,21世纪,中国谍战片在谍战片序列中拥有独特的地位与意义,其所显现的美学特征亦有颇多的价值与衍生,这些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的类型片,在延续传统的同时又凸显出救赎母题、英雄性美学以及历史想象的现代变奏。一方面,当下谍战片在变化中依托类型特征进行深化与重述,完成了更具当代精神的表述,以实现对以往谍战类型的更新或超越。另一方面,当下谍战片则以解构与重建的双重功能打通电影艺术与市场消费的界限,形成更为广阔的传播场域与接受面向,对既往历史进行想象性的“微调”,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功能重建为一种更具现代精神的信仰与价值。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谍战片这一跨越“冷战—后冷战”历史的特殊类型电影,其在当下显现出的新的特征既是类型传统的继承发挥,同时也是当代社会与受众的集体要求,尽管当下谍战片难续往昔盛况,但其在类型探索与美学追求上的尝试与努力,仍具有相当的意义与启示。
参考文献:
[1]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中国电影发展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170-176.
[2]胡克.新谍战片的美学倾向与文化分析[ J ].电影艺术,2010(1):64.
[3][以色列]格肖姆·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M].朱刘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05.
[4]高山奎.从“两面神”思维到救赎史观——试论本雅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神学根基[ J ].现代哲学,2018(1):26.
[5]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56.
[6][德]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M].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66.
[7]胡克.新谍战片的美学倾向与文化分析[ J ].电影艺术,2010(1):64.
[8]戴錦华.谍影重重——间谍片的文化初析[ J ].电影艺术,2010(1):61.
[9][瑞士]C.G.荣格.英雄与母亲[M].范红霞,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47.
[10]胡克.新谍战片的美学倾向与文化分析[ J ].电影艺术,2010(1):67-68.
[11]陈晓云.《秋喜》:谍战故事的另类叙述[ J ].电影艺术,2010(1):86.
[12]庄诒晶.新历史主义的华丽注脚——论21世纪华语谍战片的成与败[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2):19-23.
[13]秦勇.消费历史与价值重构——中国当下历史消费主义文艺思潮概观[ 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