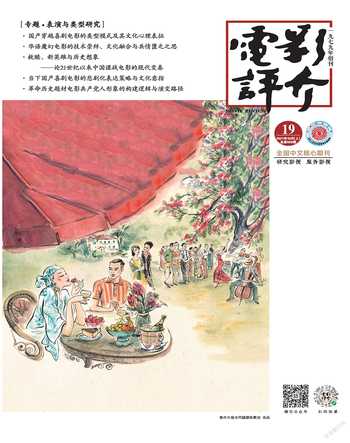当下国产喜剧电影的悲剧化表达策略与文化意指
孟琪
随着中国电影不断发展,不论是票房的屡创新高还是“爆款”作品的更迭出现,都不断向大众展示中国电影迈向产业化发展的累累硕果。这种产业化进程最鲜明的转变,首先是市场规模和空间的拓展,其次则是新兴创作群体和创作力量的加入,对电影美学方面的创新,其中,类型电影的本土化建构是重要一环。如果作品的商业价值和票房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大众审美取向的显影;那么,喜剧类型则因其创作模式的可拓展性与定义的宽泛性,以丰富多元的面貌,成为最易被大众接受,同时又可与多种类型相杂糅的“元类型”文本。这一特性虽促进了喜剧类型在中国电影市场化进程中的繁荣,但同时,因其异于其他通俗类型电影的编码程序,故而在对其定义的阐释以及类型美学的模式化界定中也造成一定困扰。《电影艺术词典》将喜剧定义为“以产生笑的效果为特征的故事片”[1],而在《类型电影教程》中,对喜剧的定义则是“喜剧片是一种用引人发笑的方法来表达人类的自信心和超越精神的电影戏剧类型”[2]。从纷杂的喜剧定义中不难发现,喜剧是一种关乎情绪的类型,而“笑”则是喜剧的核心和灵魂。同时,还应注意的是,“类型可以是非常具有伸缩性的、有弹性的,是随着不同时期的文化需求而不断演变的”[3]。因此,对近期的喜剧文本进行细读,及时总结其中的功过得失,分析其主要的喜剧策略和背后的文化意指,不仅能够为今后喜剧创作提供一个可行的模式范本,同时也可窥探其背后隐射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其实,对近期的喜剧作品进行梳理不难发现,从制作看,当下的喜剧电影经过2006年《疯狂的石头》,以200万元投资撬动2000万元票房资本之后,除了《唐人街探案》系列、周星驰的“西游”系列等少数影片外,这种小成本的制作模式一直延续,包括《港囧》(2015)、《夏洛特烦恼》(2015)、《羞羞的铁拳》(2017)、《超时空同居》(2018)、《西虹市首富》(2018)、《一出好戏》(2018)、《半个喜剧》(2019)、《你好,李焕英》(2021)等作品在内,都以其票房成绩证明了喜剧电影在观众心中的主流地位。在美学方面,虽然这些喜剧作品并未形成定型化的叙事模式,且很难对上述文本进行一种标准化一的总结和阐释,但从其悲喜剧的戏剧内核以及悲剧化的表达策略、背后的文化意指等方面,依旧可以较为清晰地寻得其中的统一性和共性所在。
一、喜剧中的悲剧性显影
对于悲剧,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完整的定义,认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们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4]之后,经由席勒、黑格尔等哲学家和理论家的延续,成为西方悲剧理论的主流之一;而另一角度,马克思、恩格斯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将悲剧理论延伸至更为广阔的历史和社会的视域之中,提出了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悲剧理论的不同观点,认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5]显然,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更为符合现代社会的背景和语境,但与此同时,因悲剧理论的研究对象还主要聚焦于文学、戏剧等领域,且随着社会语境的不断更迭,当下已然进入一个“悲剧远去”的时代,特别是在电影这一极具造梦功能的领域,现代的悲剧,更多的显现为一种“悲剧性”的塑造。这一悲剧性常被运用在喜剧的表达中,以一种悲喜剧的形式和精神,引发观众在嬉笑之后的片刻沉思与反省。但在电影中,这种“悲喜剧”与戏剧中的“悲喜剧”/“正剧”不同,其并未延伸至别林斯基所述的,“把严肃与滑稽,悲剧与喜剧,生活中的庸俗糟粕与伟大美丽交融在一起”[6]的美学范畴,而是更多地借用这一形式,以一种喜剧中的悲剧性意识,来丰富自身的美学表达。这一方面可以削弱悲剧中严肃与残酷对观众的冲击;另一方面,也让喜剧背后的精神能指不再空洞。或许,借由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理论,当下喜剧电影中的这种悲剧性营造,可以定义为客观现实的必然压力和这种压力所致的焦虑实际上并未得到解决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这种冲突或矛盾,也成为喜剧电影戏剧性的主要来源,贯穿于作品的始终。
喜剧与悲剧在之前的理论研究中,始终是一种对立且泾渭分明的状态,但“当现代剧作家尝试过用或多或少的喜剧因素来加深作品的悲剧意味后,他们更清楚地意识到眼泪并不代表悲的极致,笑容背后投射出来的悲哀才是大悲大悯喜剧”[7],“人生的喜剧观与悲剧观已不再相互排斥。现代批评最重要的发现或许就是认识到喜剧与悲剧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或者说喜剧能向我们揭示许多悲剧无法表现的关于我们所处环境的情景”[8]。这种悲喜剧所显现的张力,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已不罕见,从最早的《难夫难妻》(1913)、《孤儿救祖记》(1923),再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渔光曲》(1934)、《十字街头》(1937)、《马路天使》(1937)、《乌鸦与麻雀》(1949)等,都是以悲喜剧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进行展现,对底层人物或平民生活给予关怀。特别是蔡楚生导演的作品,不仅以“含泪的笑和形象反喻式的滑稽造型”,奠定了导演自身的作者风格,而且在蔡楚生的作品中,“不但有人物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乐观的精神时时出现在一些段落性叙事中,并带有一定的喜剧情节的贯穿,也从本质上表现出人物的渺小和无奈”[9],将底层人物的压迫与无力反抗的悲剧展现出来。之后进入“十七年电影”时期的《五朵金花》(1959)、《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通俗喜剧和90年代的冯小刚喜剧,喜剧电影的创作依旧能够看到悲喜剧形式的身影,并在题材方面逐渐生活化和去历史化,着力表现当时社会中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
喜剧电影因其不受固定类型模式的限制,因此在形式的表现与美学的表达等方面,都能够借助“笑”这一情绪,与其他类型复加,展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与特点。而悲剧性的加入,其一则是让喜剧作品在制造“喜”的同时,能够通过“悲”来反衬“喜”的价值。即是说,类型的拓展丰富了喜剧电影的外在形式与可观性,而悲剧性的加入,则从文化和精神层面,扩充了喜剧电影的深刻内涵。纵观中国电影的喜剧创作,这种悲剧性所引发的冲突性也随着不同的社会背景而嬗变。在早期电影中,悲剧性主要源于个体对封建社会中的制度、习俗的反抗,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之后,喜剧电影中的悲剧性冲突则更多来自于个体对阶级压迫和国族命运的担忧。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喜剧电影的创作开始聚焦于生活,通过对生活中种种问题的针砭,将现代性给人物个体带来的压力和焦虑进行显影,将“理想的丰满”与“现实的骨感”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展现出来。当下的喜剧电影延续了这一策略,正如C·弗雷里赫在《论悲喜剧》中阐述的一樣,“悲喜剧就像是一件用双面布料制成的斗篷,里子可以翻成面,面也可以翻成里子”[10],与之前早期电影中的“悲中带喜”不同,当下的喜剧作品大多都以“喜中带悲”为主,剧中的人物成为被层层压力所围困的斗兽,深陷其中却又难以逃脱。他们未曾经历大起大落的悲剧性冲击,但却在时代和生活的泥潭中苦苦挣扎。与此同时,喜剧则以一种嘲讽或戏谑的方式,将这些人物的性格缺陷或生存困境暴露出来,即使这些缺陷并非是“致命”的,且大多是可以被世俗原谅或理解的,但在这种喜与悲的对比之下,观众仍旧能够感受到剧中人物的悲情所在,也正是这种悲情引发的共鸣,让观众从喜剧中跳脱出来,从欢笑中察觉到创作者更深层的寓意。
喜剧电影中的悲剧性表达其二,则是能够引发观众对角色的体认,从而产生共鸣。当下的中国喜剧电影最明显的特点莫过于对小人物悲喜感的凸显,影片善于在开头给人物设置一个不可能摆脱的困境,在经过一连串荒唐、可笑的努力后,悲剧性与无力感开始显现,但最终人物却获得了圆满的喜剧性结局;即便这个结局看起来并不十分符合现实的逻辑或并未解决根本的困境,但却满足了观众在对人物进行自我认同后的期待心理。于是,在这悲喜的起伏中,观众从对人物处境的体认转变为对影片价值观念和精神的认同,不仅从影片中寻觅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焦虑,同时这种喜剧性的结尾,也消解了真实的逻辑,缝合了银幕与现实之间的界限,让观众暂时忘却现实的困境,从而在“圆满”中得到满足。
其三,悲喜剧的结合拓宽了喜剧表达的路径,促使喜剧向更为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悲剧与喜剧作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倾向,在融合后并非是进行简单的叠加,而是呈现出“1+1>2”的效果,“没有任何样式能够像悲喜剧这样鲜明地表现出一种样式的力量转入另一种样式的过程,没有任何样式能够像悲喜剧这样使低俗的样式和崇高的样式达到如此的平衡”[11],因此,通过对喜剧与悲剧的互融,不仅能够为创作者找到对社会纷杂现象和多元生活的表达路径,重新让影像回归生活应有的质感,同时也能让观众感受到更为多样的审美快感。
在当下的喜剧作品中,其悲剧性表达主要通过叙事进行建构,从而实现对社会和时代症候的凸显。但是,纵观近年来中国喜剧电影的创作,虽不乏口碑与流量齐具的作品,但在其对人物的挖掘、叙事的编排以及深层次喜剧精神的重塑等方面,都略显浅薄与“同质化”,这其中既是创作者对生活体察的缺失,对网络段子、庸俗笑料以及“拼贴式”笑點的推崇,同时也是对“喜”“悲”之间的“度”的失衡把控,在“笑”后,未能以喜剧的批判精神引发观者更深层次的思考。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对喜剧中悲剧性表达的分析也显得尤为重要。
二、当下喜剧创作的悲剧性表达策略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喜剧电影正是有了悲剧性的表达,才使喜剧不再是一个以搞笑为目的的空洞外壳,而是拥有了更多与社会和文化“共情”的能力。在当下中国喜剧电影的创作中,类型的杂糅成为其主要特点,特别是在近几年中国电影的产业化进程中,“复合类型”成为喜剧电影决胜市场、赢得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必杀技”,由此形成的以喜剧为主导,与其他类型或题材融合互渗的亚类型或复合类型的作品。
在都市爱情喜剧《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西虹市首富》《超时空同居》《半个喜剧》《大赢家》《寻汉计》等中,影片往往在都市这一空间展开,其中不仅有爱情类型,同时还穿插着某些传奇、励志色彩,以一种杂糅的形态成为当下国产喜剧中的主力军。细读这些影片便不难发现,爱情并非是影片的内核,其叙事动机基本都源于现代社会的生存标准对人物所施加的压力与人物内心欲望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展现也是影片悲剧化表达的来源。爱情成为影片美好主题的“调和剂”,将人物内心的欲望予以美化,同时也达成了影片主题和价值观念的正确表述。《夏洛特烦恼》通过穿越的形式,让夏洛重回少年时代,借由一系列的“时间误差”制造笑点,最终夏洛虽然实现了年少的幻想,但却幡然醒悟,重新发现当下生活的珍贵之处。影片虽然以对“初恋女友”的执念作为人物欲望的始端,但同时,影片开端,夏洛租借的礼服、汽车以及婚礼上同学对他的讥讽,包括最终重回的现实,也代表了社会标准对人物的价值评判,而夏洛回到过去,尽管满足了成功的欲望,但最终却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因此,在现实与过去的对比下,凸显出夏洛无法逃脱生活困境的悲剧性。在《超时空同居》中,当下成功的陆明是一种非法的成功,而因为爱情放弃成功的陆明则又回到生活的初始状态。同样的,《西虹市首富》中为了爱情放弃遗产的王多鱼,《半个喜剧》中为了爱情放弃北京户口的孙彤,都是如此。“圆满爱情”的结局成为弥合人物社会价值缺陷和成功欲望未得到满足的外衣,裹住了人物并未真正得到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显现出喜剧的悲剧化表达。
在荒诞喜剧《驴得水》《健忘村》《一出好戏》等影片中,荒诞风格一方面为影片提供了笑点的来源;另一方面,也为创作者对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找到了表达的切口。因此,在荒诞与喜剧的亲缘性下,创作者通常以一种“孤岛模式”展开叙事,在近乎“真空”的假定性空间和制度、文化语境下,展开对宏观背景的批判、解构与对个人境遇的自嘲和悲剧性表达。“它指向的是经历了由现代性失控所导致的巨大灾难之后,深陷于前所未有的集体创伤中,因而无可避免地对文明的意义感到彻底灰心绝望的人类”[12]。基于这种精神内核,荒诞喜剧的悲剧性表达已不再像爱情喜剧那样,仅仅是对平民阶层或“草根”人物的人文关怀和理性呼唤,而是成为一种在虚无主义的立场下,对人类文明或现代社会的一场略显锋利的审判,即便这种审判最终也是徒劳无望的。《驴得水》以一群在乡村支教的“知识分子”展开,在这个仿佛与世隔绝的空间中,上演了一场闹剧般的“错位”故事。影片以荒诞的风格展现了知识分子在面对权力时,内心的反叛精神和最终屈归于现实的无奈,同时也上演了一出极具自负的启蒙意识在固有的权力与体制下的无效悲剧。《一出好戏》依旧把叙事安置于一个与外界隔断的封闭空间——无人知晓的荒岛,讲述了在这个荒岛上,一群人重新建立起人类社会的“文明”秩序的故事。影片以喜剧的表达,隐射出人类在面对“从头来过”的假定性情境下,依旧无法避免的人性悲剧;同时,荒岛中的空间作为片头片尾现实空间中的“画中画”,也再一次以鲜明的对比暗示了人生就如黄渤手中的那一张彩票一样,即便中奖,也依旧无法兑现来改变现状的悲剧。如果说爱情喜剧中,爱情是遮盖悲剧的华丽之袍,那么,在荒诞喜剧中,荒诞则成为戳穿衣袍的刀刃,将悲剧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除此之外,以周星驰的作品为代表的魔幻喜剧类型,如《西游降魔篇》(2013)、《美人鱼》(2016)、《西游伏妖篇》(2017)等作品,也在喜剧背后通过悲剧化的表达让影片不再是单纯地疯癫搞笑和视觉冲击,而是多了几分喜剧精神的建构。在这些作品中,悲剧化的表达通常通过对英雄人物的解构和反向塑造进行展现。不管是《美人鱼》中的邓超,在最后一刻觉醒,起身护卫家园,与之前同阶层的群体相对抗;还是“西游”系列的唐僧,表面唯唯诺诺、胆小怕事,但最后牺牲自己,普度众生。这些片中的英雄都经过一个由“反”到“正”的成长过程,也正是之前“反向”塑造对人物内心的一次次痛苦逼问,使得最后一刻的觉醒变得更具悲剧的崇高性,这一“高光时刻”也让影片以喜衬悲的风格得以凸显。这类影片正是通过对既世俗又崇高的英雄人物的缔造,显现出背后的悲剧化表达。
还值得注意的是,以《无名之辈》(2018)、《我不是药神》(2018)为代表的一类影片,它们既不同于都市爱情喜剧中对底层群体的“普适化”困境展现,也不同于荒诞喜剧中对空间的抽离化建构和对人性、制度的虚无主义表达,更不像魔幻喜剧中刻意对英雄的悲剧性刻画,而是将目光聚焦于特殊的生存群体之中。影片中的英雄人物并非是自觉自愿地去扮演拯救者的身份,而是通过阴差阳错的机缘与目的让其与相关群体产生联系,做出因迫于现实的必然选择,以黑色幽默的风格,完成了影片的悲剧化表达。
在大多喜剧作品中,其悲剧化通常都是通过影片自身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来完成,这种价值体系往往带有某些屈从或妥协的成分,以一种犬儒主义的姿态,欲言又止地诉说着当下的社会问题。在这些作品中,人物往往深陷在生存的困境中,或存在未能被满足的需求,但这一困境/需求通常是很难实现或不具备实现条件的,这就促使人物想方设法地为此努力,以求获得满足,其中穿插着在实现欲望的过程中制造的笑料。这些笑料的源头都基于人物自身的性格缺陷和对缺陷的茫然不知,最终,真实的欲望并未得到满足,困境也并未有所改变,而是以代替性的“圆满结局”宣告落幕。《夏洛特烦恼》《西游伏妖篇》《半个喜剧》《大赢家》等作品皆是如此。这种价值观念的位移与代替,也成为喜剧作品的悲剧化表达策略,让观众沉浸在目标虽未达成,但结局至少圆满的同时,感受到剧中人物并未改变的生存境遇。
三、喜悲背后的文化之殇
类型电影之所以能够成为经久不衰的创作法宝,究其原因,即是其与社会和时代产生的一直未曾间断的互文关系,喜剧电影也是如此。但是縱观中国当下的喜剧作品,即便创作者依旧竭力挖掘喜剧电影的人文价值,重塑喜剧背后的精神意涵,但从作品的呈现来看,喜剧电影仍然依循着对现实的失真表达和对问题的回避性解决策略,满足观众的审美愉悦。“当我们意识到类型模式不仅包括叙事元素(角色、情节、场景),同样还包括主题时,类型的社会化影响就变得显而易见了。”[13]“每一种类型都作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的存在和观众的经验联系在一起。”[14]影片的主题体现的不仅是创作者对社会体察后的艺术性表达,同时也是观众体认角色的价值基础。
正如上文所述,喜剧电影中的悲剧化表达填充了喜剧背后的精神意指,让流于表面的情绪有了引人深思的内容。首先,当下的喜剧电影创作在主题方面,却显现出一种吊诡现象,即影片中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辨、人物处境的关怀以及悲剧性的表达全都处于隐退的状态,被为满足观众欲望的狂欢式情景所遮蔽。密集的网络段子、小品式的拼贴笑点将断裂的叙事逻辑和模糊的叙事动机串联起来,让观众无暇顾及喜剧本应表达的内容。《夏洛特烦恼》中,面对40平米的出租屋,同学的嘲讽和未被满足的虚荣心,回到现实的夏洛,生活处境并未改变,改变的是夏洛最终在自我梦境安慰下接受现实的心理状态;《半个喜剧》中,孙彤最终放弃户口选择爱情,但人物接下来的处境实则并未有所改观,从依靠朋友,变为依靠女朋友。甚至在极具批判性的荒诞喜剧中,校长、周铁男、裴魁山在经历了驴得水事件的风波中,依旧若无其事地准备同心协力把学校办好(《驴得水》);一群人重回社会后,人物的处境也如同马进的6000万元彩票,始终处于不能兑现的状态(《一出好戏》)……这些影片都以一种“精神胜利法则”将现实的困境包裹起来,回避尖锐的矛盾,折中般地促成最后的“圆满”。这一方面源于当下后现代思潮和青年亚文化的崛起对观众审美的改变,迫使创作者为迎合大众审美,赚取商业利益而进行创作的改观,即便“影片也流露出叛逆、怀疑的眼光,但是这种叛逆、怀疑由于大多采取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自我拆解的方法,往往使得目的性和批判性显得不明确”[15]。另一方面,创作本身的模糊动机和暧昧性主题,也成为当下喜剧电影精神缺失的始作俑者。影片开篇就将人物莫名其妙地置于一个非现实的语境中,如穿越题材的《夏洛特烦恼》《乘风破浪》;天降横财的《西虹市首富》《李茶的姑妈》;身体互换的《羞羞的铁拳》等,这样带有超现实的语境以奇异性不停地冲击着观众的笑穴,同时也让观众沉浸在这种泛娱乐化的氛围之中。除此之外,在这种非现实的叙事假定性之下,人物动机也变得随意。《乘风破浪》中的徐太浪在穿越到自己出生前的时代后,莫名与父亲成为好兄弟,且被父亲信任,而其身份与时代的不符以及家世背景的空缺却避而不谈;《西虹市首富》中,遗产从天而降,并开启了王多鱼的挥霍之旅,但人物自身的诉求却显得不清不楚,影片中夏竹的人设是讨厌追名逐利的单纯女生,但面对为继承遗产挥霍金钱的王多鱼,两人却擦出爱情火花;且在结尾处,王多鱼选择放弃遗产营救夏竹,而片尾,两人在捐献财产的时候却又表现出游离的态度,如上问题在其他影片中也随处可见。在这种模糊性的表达中,影片的主题实则也偏离了正确价值观的导向,进而将其诉诸于一个通过僵硬转化完成的“光明的尾巴”,而至于喜剧本该具有的反思批判精神和文化价值,也早已被这些搞笑的噱头抛之脑后。
其次,当下国产喜剧的创作,在进行严肃性的文化价值探讨和悲剧化表达时,往往呈现出一种同质化、单一且片面化的策略。影片中,不管是对哪类人物的刻画,其困境基本都围绕物质财富这一最为浅显,且无需任何前期铺垫的需求展开,进而催生出因物质缺陷导致的种种问题。这种设定或许可以将其视为一种集体性的“观影期待”,隐射出在当下飞速发展的社会和瞬息万变的文化中的某种大众性的“创伤需求”,但同时,这也造成喜剧电影的创作流于表面而无法深入探索的窠臼。如果说对物质的需求是影片叙事的外在客观动机,那么,对于爱情的追求则成为影片叙事的内在情感因素。围绕这种设定,影片中的女性角色则变成男性角色追求财富的永恒驱动力,但在叙事中却沦落为男性角色的陪衬品。具有牺牲精神的传统女性如《夏洛特烦恼》中的马冬梅、《西虹市首富》中的夏竹、《半个喜剧》中的莫默等永远等待着男性的“拯救”,而蛇蝎美人如《夏洛特烦恼》中的秋雅、《美人鱼》中的若兰等,则成为引导男性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走上歧途的罪魁祸首。“这些人物大多数时候属于‘符号人物’、被观众、观者被动感知的客体,而不是施动者或者‘完整符号’、自身能够帮助观众在角色中找到身份认同的主体”[16]。正是因为对人物和叙事的定型化创作,影片在对更深层的精神层面进行挖掘时,便很难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视角和价值维度。
最后,当下喜剧作品大多采用一种平民群众的视角展开叙事,试图借由此视角,通过对平民群众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喜剧化表达和悲剧化衬托,引起大多数观众的共鸣和体认,达成优于剧中人物的满足感。“喜剧精神就是轻蔑和优越感的结合。前者指主体对一切压抑个性生命力自由发挥的文化霸权、权力话语、等级制度、文明说教和道德禁忌等异己因素的轻蔑;后者指主體由对心性良知与生存价值的自我肯定而产生的内在优越感。”[17]但是在众多作品中,这种轻蔑和优越似乎以一种错位式的表达展开,在《夏洛特烦恼》《西虹市首富》《半个喜剧》以及“唐探”系列等作品中,小人物都以一种虚伪、懦弱、爱逞强,甚至有些“丑化”的形象进行展现,这些人物的缺陷,虽然能为影片增添更多喜剧色彩,但其对平民群众的定型化塑造,也显现出创作者对于这一群体的片面化认知,而人物产生的优越感也并非来自“对心性良知与生存价值的自我肯定”,而更多地来自影片中假定情境下的物质丰腴,且最终都是“黄粱一梦”,回归现实,这也形成了喜剧电影在现实与虚无之间的悖反,让其放弃探索平民群众背后更为深刻的社会境遇和喜剧电影的哲理性价值。
结语
当下的国产喜剧电影创作,虽在商业价值方面获利颇丰,通过与观众的不断磨合形成了以类型拓展为主要策略的相对稳定的创作策略,并试图通过不同的亚类型或复合类型的探索,对喜剧精神予以建构,以悲剧化的表达方式,凸显喜剧之外的思辨价值,发挥喜剧作为大众情绪“抚慰剂”的作用。但是,其中也不免隐射出创作者对于社会体察维度的窄化和创新性表达的缺失。正如别林斯基用“含泪的笑”来阐释喜剧背后的深层寓意一样,或许深掘喜剧背后的悲剧化表达策略,也是当下国产喜剧重拾喜剧精神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1]许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16.
[2]郝建.类型电影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59.
[3][美]罗伯特·克考尔.电影的形式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2.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3.
[5][苏联]米·亚·里夫希.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30.
[6]别林斯基论文学·别列金娜选辑(答《莫斯科人》)[M].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116.
[7]叶红.悲喜剧:由传统走向现代——从肖恩·奥凯西的“都柏林三部曲”谈起[ J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6):62.
[8][加]诺斯罗普·弗莱.喜剧:春天的神话[M].傅正明,程朝翔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183.
[9]高小健.生命的赞歌——蔡楚生电影的精神品质[ J ].福建艺术,2006(6):56.
[10][11][苏联]C·弗雷里赫.论悲喜剧[ J ].富澜,译.电影艺术译丛,1979(4):155,156.
[12]盖琪.在虚无中自嘲:荒诞喜剧电影的亚类型边界与本土话语机制[ J ].当代电影,2019(7):28.
[13][14][美]托马斯·沙茨.好莱坞类型电影[M].冯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5,72.
[15]金丹元,田承龙.找回似已失落了的喜剧电影之魂——试论当下中国喜剧片的精神缺失与文化担当之不自觉[ J ].艺术百家,2016(3):77.
[16][法]雷吉斯·迪布瓦.好莱坞电影与意识形态[M].李丹丹,李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7.
[17]陈刚.喜剧精神的当下意义[ J ].艺术广角,2008(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