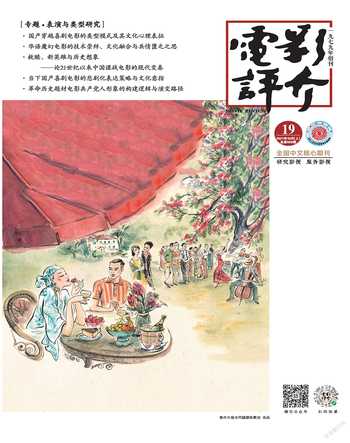唯美风、民族化与人道主义:中国电影话语范式的三个维度
刘福泉 卢肖寒
近年来,随着全球文化竞争的激烈,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盛况空前,中国电影的再发现与再解读再次成为国内电影学界的一个学术焦点。文章拟从写作形式与语言结构两方面出发,探讨中国电影的风格、思想与新话语问题。
一、中国电影唯美风格与写作形式的确立
要讨论何谓中国电影的写作形式,首先要厘清在何种意义范畴下讨论“中国电影”。由于电影在文化产业和文化宣传方面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电影的拍摄不可避免地贯彻着民族意志阐释与商业目的的焦虑。中国电影不仅应该来自中国的制片公司与创作者,而且应该体现中国的实际国情,代表中国的审美取向与思想文化特征;中国电影不应该是某个制片体系、某个创作群体、某种风格的创作者独占的名称,而是属于中华民族的电影体系。因此,中国电影必定要保持广博的胸怀,并且始终对不同的风格、思想与价值观念开放。本文讨论的中国电影,是将电影中直接的政治宣传影响与商业目标剔除后,剩余的单纯艺术行为。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共识性范畴,能够在艺术内在规律下兼收并蓄,容纳不同创作者的声音。要讨论中国电影的写作形式,除去中国电影的问题外,还需要厘清写作形式及其相关的电影写作概念。电影写作并非狭义上的为电影而进行的编剧等写作行为,而是与探究电影艺术特性与内在规律的电影作者论一脉相承的学术范畴。尽管这一描述看似只是拍电影的另一种描述方式,但电影写作本身具有的含义与面向要丰富和复杂得多。法国“自来水笔”学派曾经提出,应该让电影像作家手中的自来水笔一样被自由使用;法国导演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在其著作《电影书写札记》中提出了“电影书写”理论,认为电影的书写是“通过剪辑造就一种由动态画面和声音构成的艺术作品的过程”[1]。罗伯特·布列松强调电影的“电影性”,反对“影剧”传统,主张演员不是刻意模仿角色,而是以“电影模特”的身份将角色特有的气质自然地发散出来,并力主通过活动影像与声音的关系来重组现实,而不是去“再现”现实。中国电影如何在传承民族艺术美学传统过程中结合电影的表意形式,利用全新的技术媒介书写新的民族艺术审美境界,是中国早期电影主要面临和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在中国早期电影中,将中国传统的美学与影像叙事结合的实例已经不在少数。百年中国电影史在文化交流的层面上是东西方文化剧烈撞击和融合的历史,也是艺术家在电影这一舶来形式的实践中为中国故事、中国情感寻找释放空间的历史。回顾百年中国电影理论历程,面向以苏联电影与好莱坞为首的外国电影开放地借鉴的历程,以及现实情景下对中国自身的主体选择的强化,成为中国电影写作形式确立时的重要精神坐标。电影《故都春梦》(孙瑜,1930)中,私塾老师朱家杰为求名利迷失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在歌姬燕燕的勾引下疏远了故乡的妻女。有朝一日,朱家杰的靠山突然遇刺,燕燕丢下正患重病的女儿莹姑潜逃。朱家杰贪赃枉法的事情败露,幸得叔父破产相救才得以出狱。从朱家杰离家到出狱归家不过一年时间,春光依旧但物是人非,曾经的繁华生活宛如一场不堪回首的春梦。《故都春梦》流露出孙瑜的诗化导演风格,电影画面受中国传统文学的诗化观念启发颇深,常借鉴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比兴手法,以物寓情,注重联想、隐喻、简化对白、淡化叙事,以写意的抽象方式对人物心理与时间流动进行唯美主义的表达。蔡楚生拍摄的《渔光曲》(蔡楚生,1934)同样擅长利用生活细节来刻画人物。贫穷渔民徐福家的一对子女小猴和小猫,与渔霸何老爷之子何子英一起长大,何子英英俊成熟,小猴痴呆消瘦,小猫活泼可爱,尤其喜欢唱渔民中流行的《渔光曲》:“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晒渔网,迎面吹来大海风。”尚不知世事艰难的渔家少女在摇晃的驳船上歌唱,无忧无虑的少年们在波光粼粼的场景中嬉戏。在无声片时代,这样的场景宛如西方电影中让·维果(Jean Vigo)等人描述的诗意现实主义场景,让无声的事物表达出深厚意蕴的效果。孙瑜与蔡楚生为社会悲剧的主题赋予了生动优美的画面,同时又为近现代历史事件赋予悲剧的表现形式。影片中以景寓情、高度凝练的语言,以及唯美隽永的画面,都以高度电影化的方式将中国传统美学规范与社会命题生动地呈现了出来。尽管电影的主题与小猫的歌声不可避免地向“渔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爷爷留下破渔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转变,但这种含蓄唯美的书写方式却就此确立下来,在艺术内容、艺术形态和理论走向上呈现出诸多民族特色,并在之后的百余年中对中国电影美学的成熟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中外文化思想沖突中的话语表达
中国文化是一种与西方文化异质的文化体系。电影作为诞生于现代西方文明的艺术形式,需要经过中国文化的选择、民族审美理想的熏陶与民族思维方式的改造后发展为中国电影艺术和中国电影理论。其中,主张“需要追随时代发展不断向现代化演进,但这种演进不是消融而是保持和发展其民族个性”[2]的电影民族化观点,与认为中国电影的走向应更多强调对外来电影文化的引进,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对外开放论[3],形成了两种主流声音。前者就中国影视美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艺术美学传统与中国电影理论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中国电影美学并非西方电影美学的翻版,而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性,并试图以中国电影中的民族美学与民族文化作为重要依据;后者则冷静地着目于中国电影与世界其他电影强国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从电影艺术的本性出发,试图为中国电影找到一条可以绕过文化屏障与文化霸权影响的发展与传播道路。无论“电影民族化”的命题是否成立,这两种话语表达都具有相同的背景:在以欧美流行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大量涌入之时,电影作为当今世界媒介格局中对大众的思想意识与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传播媒介之一,势必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语言习惯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形成强力冲击。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初期,诸多好莱坞大片在市场化之初的中国电影院线所向披靡,盗版DVD光盘店与录像厅等场所,以及方兴未艾的娱乐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介,也同步传播着西方流行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民众对西方文化的想象、崇拜、追捧、向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电影的文化影响力却不容乐观。在历史和现实的必然要求下,中国电影开始在价值取向与艺术价值的参考上逐渐多元化。中国电影理论家开始积极寻找在外国电影之外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于是引起了电影与戏剧、与文学关系的探讨。
首先便是电影与戏剧关系的讨论。1979年初,时任北京电影学院教师的白景晟攒文《丢掉戏剧的拐杖》,文章具体分析电影与戏剧两种艺术门类在美学基础上的差异,提出中国电影应该丢掉使用了多年的“戏剧的拐杖”,这是新时期探讨电影艺术特性的先声[4];翌年,钟慵来在电影导演会议上呼吁“电影与戏剧离婚”,认为“如果我们从战术上提出这个问题,打破场面调度和表演上的舞台积习,取消镜头作为前排观众在一个固定席位上看戏的资格,并以两三年为期,使摄制全體心怀银幕,这样是否更有利于电影艺术的发展?”[5]其次是电影文学性的讨论。1980年,著名电影艺术家张骏祥在一次导演总结会上发言强调要重视电影的文学价值,并撰写长篇论文《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文章批评了20世纪80年代初电影创作出现的生搬外国电影手法和技巧、单纯追求形式的倾向,将许多影片艺术水平低下的根本问题归根于作品的文学价值不高,提醒电影创作者不要为了形式而忽视内容[6]。电影文学论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构建的要素之一,业内就电影的文学性和文学价值问题,以及电影文学与电影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与争鸣。许多评论家都赞同张骏祥文章的基本精神,认为这篇论文基于当时电影创作的现状和弊端有感而发,强调剧作家要写出高质量的电影文学剧本,具有有力针砭时弊的作用;也有人认为电影导演固然要重视电影剧作中的思想性与哲理性,但将电影比作文学,要在一门与文学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寻找文学性并将其作为最高价值旨归,是不确切和不科学的,“文学价值”的概念无法区别不同艺术的美学和诗学特征。自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以来,“中国电影新观念的形成”等成为学界积极探讨的热门话题,在戏剧说与文学说外,谢飞的《电影观念我见》等引起广泛讨论并具有代表性观点的文章。谢飞认为,电影观念从艺术角度出发应包括艺术思想、艺术内容、艺术技巧三个层次,中国电影应该在艺术技巧角度外对艺术内容、艺术思想予以更多关注。他认为,“电影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的观念应该包括商品、交流工具、艺术三个部分”,并联系中国电影的生产实际和生产体制认为“以片面的、狭窄的电影观念去指导电影创作,遂造成许多偏差与教调”[7]。这些讨论以广阔的视野承接了不同文化语境下人们对中国电影的看法,它们阐发的背景是中西方文化的冲突,然而对于电影本身的专注却将中国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深化于电影内部规律之中,不仅为出于过渡转型期的中国电影提供了理论与思想指导,而且在当下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三、当下中国电影及理论中的人道主义话语结构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全球化影响下中国社会文化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电影研究者与创作者对电影本质认识的不断加深,在银幕数量、电影票房、影片产量和市场规模等方面保持领先的同时,在更深层次的文化传播、价值引领和精神影响等方面向深挖掘中国特有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成为中国文化界、艺术界、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共识。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8]由此开始,中国电影在新时代语境下需要从写作形式开始重新谋篇布局,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创造文化的繁荣兴盛,继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先后与传统美学、文学、戏剧等文化资源或整合或“分手”之后,关注不同人群的生存状态,强调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及权利的人道主义最终成为召唤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与创作的热情呼声。不同意义在电影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电影形式与其他艺术形式中的滑动,最终归于人道主义话语的结构中,诞生出一种既有历史意识又具备现实关怀的全新中国电影形态。
2002年,翻拍自被香港电影金像奖评为百年百大华语电影第一名的《小城之春》(费穆,1948)的《小城之春》(田壮壮,2002)上映。这两部《小城之春》体现了中国电影写作形式与语言结构在数十年间的深刻变化,以及新世纪以来倡导的人道主义理念。1948年版的《小城之春》明显根植于中国传统,具有与中国古代诗人、文人的写作方式一脉相承的电影风格与审美取向。松江古老的城墙和旧式的房屋、战乱下的断壁残垣与生机勃勃的野草,都构建出诗歌般欲语还休、封闭而沉寂的情感空间;以小桥流水、断井残垣等自然景致的入画的构图方式也充满对中国戏曲写意风格的借鉴。女主人公玉纹生活其中,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在这破败空虚的城墙上”“像是喝醉,像是做梦,这时候,月亮升得高高的,微微有点风”等文学性极强的画外音描述其日常生活,这些台词传达出的信息与其功用并不在于叙事,而在于体现每天例行公事般买菜、绣花、照顾丈夫的年轻妇人内心的哀婉。破败小城中踟蹰迂回的玉纹,也被解读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在战乱中无所适从的心境代言。尽管费穆无心在学术或理论建构的层面倡导电影的民族化,但1948年版的《小城之春》却是将电影这一现代艺术门类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典型代表。玉纹送给心爱之人志忱的兰花,不仅象征着一个脆弱无助、充满生机却注定衰败的女性形象,流露出静静浅淡的忧愁哀思与旧时代中没落小家庭的自怨自艾,而且显示出电影所具有鲜明的托物言志、借物喻理等中国文化特征。作为“诗人导演”,费穆温和地将电影作为承载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田壮壮重写《小城之春》时面临的文化断层与文化民族化问题,与费穆选择传统风格时的情景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在第五代导演的一系列表现中国乡土景观与寻根思维的影片引起强烈反响之余,他在表达对中国电影先驱者的深深怀念和敬仰之余,在影片里置入自己对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理解。田壮壮版本的《小城之春》画面颜色变成彩色,叙事空间由破败的小城向更宽广的空间延展,玉纹不再念诵着诗歌般的独白踽踽独行,“传统”成为影片可选择性的资源之一,取而代之的是主人公旺盛勃发的生命力。四位主人公之间紧张的情绪反应消失不见,学校中出现了一群和戴秀一样充满了朝气的年轻人,他们在志忱的劝引下丢掉了害羞,灵巧活泼地学习跳舞;小城中也出现了延伸向远方的铁路与长势良好的稻田,玉纹站在城墙时看到的是一脉生机勃勃的景象。这样的处理方式明显融入了导演对新电影的理解和对新时代生活的态度。尽管在讨论中国电影美学时,费穆版《小城之春》通常在美学价值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现上拥有更高评价,但不可否认,两部《小城之春》都体现了不同时期中国电影创作者的文化主体意识。当下重新理解和书写中国电影,仍然需要既尊重电影艺术规律,坚守发扬本民族电影文化,真实表现“人”本身的优秀作品。
结语
从实践与话语角度出发对中国电影加以再认识的过程,也是对电影艺术规律再认识、对近代以来中国民族性与主体性的再审视过程。中国电影的写作形式与语言结构近代以来逐渐由概念与形式的探讨向人本主义方向偏移,“人”的书写以多样化的形式被纳入主流话语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建构之中。
参考文献:
[1][法]罗贝尔·布列松.电影书写札记[M].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35.
[2]罗艺军.中国电影理论研究——20世纪回眸[ J ].文艺研究,1999(3):204.
[3]邵牧君.纯与非纯——当代电影理论走向辨析[ J ].电影艺术,1988(3):15.
[4][5]丁亚平.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31,35.
[6]张骏祥.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根据国庆三十周年献礼片第二次导演总结学习会上的发言整理)[ J ].电影通讯,1980(11):2,7.
[7]谢飞.电影观念我见——在“电影导演艺术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J ].电影艺术,1984(12):11.
[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