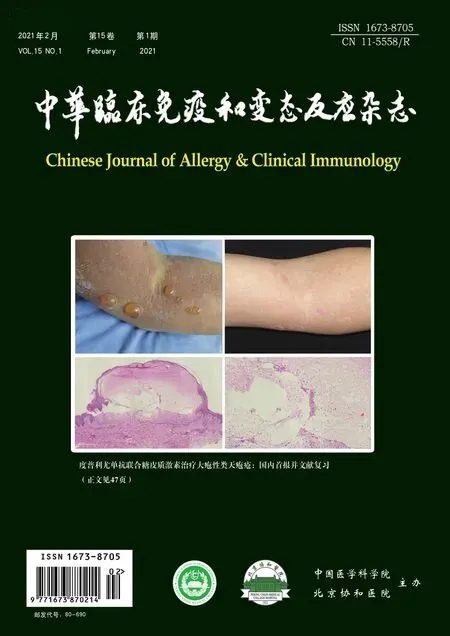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病因诊断结果
肖浩,张伟义,张虹婷,孟娟
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较罕见,据挪威[1]及澳大利亚[2]报道,其发生率分别为1∶6 000和1∶10 000~1∶20 000。近期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发生率为1.25/万[3],与国外报道相近。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发生率虽然低,但可危及生命。既往研究发现,致死性反应占3%~6%[4];近期研究显示,该比例下降至0~1.4%[5]。进行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病因诊断,对于避免患者再次暴露于致敏药物而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甚至危及生命,保证医疗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011年,欧洲药物过敏协作组(European Network for Drug Allergy, ENDA)总结了1980年以来所有法文和英文文献数据,得出引起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的常见药物及试剂依次为:神经肌肉松弛剂(neuromuscular blocking agent,NMBA)(63%)、乳胶(14%)、镇静催眠药(7%)、抗生素(6%)、血浆代用品(3%)、阿片类(2%),其余还包括氯已定(洗必泰)、肝素、亚甲蓝以及非甾体类抗炎药,局麻药过敏极其罕见,迄今尚无吸入麻醉剂过敏的报道[6]。目前我国仅有关于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病因诊断的个案报道[7-8],病因学数据尚缺乏。本研究对因可疑发生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并在本院进行病因诊断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检测结果进行总结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入排标准
纳入2016年8月至2020年4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过敏性疾病诊治中心,因可疑发生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进行病因诊断的患者。排除标准:(1)麻醉方式为局部麻醉;(2)既往曾有多种药物过敏主诉,但无全麻药物过敏史,麻醉医师出于对患者使用全麻药物安全性的担心,推荐至我中心进行全麻药物过敏评估;(3)既往在全麻过程中曾出现不良反应,但反应发生距今较久远,围手术期用药及反应的临床表现等具体信息不详,为近期手术拟使用的全麻药物安全性作评估。
1.2 临床病史采集
根据可得到的相关病历资料(包括麻醉记录单、出院记录、病程记录、手术记录等),结合患者病史问诊信息,必要时联系手术麻醉师或外科医生确认关键信息,系统全面地进行临床病史采集(包括围手术期所使用药品及试剂、反应发生的时间、临床表现、处理过程及转归)。通过对上述资料的分析,列出可疑致敏药物清单,结合每种药物的致敏机制,选用适合的检测方法,并结合病史对检查结果进行合理的解释。
1.3 麻醉药物过敏检测方法
皮肤试验,包括皮肤点刺试验(skin prick test,SPT)和皮内试验(intradermal test, IDT),是麻醉药物过敏诊断最主要的检测方法。皮试浓度见表1,阴性、阳性对照液分别为变应原稀释液和10 mg/mL组胺(ALK-Abello,丹麦)。SPT在前臂曲侧皮肤进行,15~20 min后判读结果。若风团直径较阴性对照 ≥3 mm为阳性;合并有红斑或痒感更支持阳性反应[9]。若SPT结果阴性或可疑阳性,再进行IDT检测。操作方法:将0.02~0.03 mL检测药品稀释液注入前臂曲侧皮下形成直径不大于4 mm的皮丘,15~20 min后判读结果。若皮丘直径较之前扩大3 mm及以上为阳性反应,伴有红斑和痒感更支持阳性反应[10]。若NMBAs呈阳性,则需再进行同类药物的交叉反应检测,选择可安全使用的替代。麻醉药物由于药理学特殊性,不能进行激发试验。
1.4 氯己定检测
在围手术期,患者接触氯己定的概率很高。因此,根据国际相关指南推荐[11-12],所有患者均需常规行氯己定过敏检测。包括SPT及IDT,浓度见表1。本研究将2%浓缩氯己定(福建维真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稀释成相应浓度后再进行操作。

表1 麻醉及其他相关药物皮肤试验浓度Table 1 Concentrations of anaesthetic drugs used for the skin test
1.5 抗生素检测
若可疑致敏抗生素为青霉素类药物,常规进行皮肤试验,皮试项目包括青霉噻唑酰多聚赖氨酸(penicilloyl-poly lysine,PPL;主要抗原决定簇,Diater Laboratory,西班牙)、次要抗原决定簇(minor determinant,MD;Diater Laboratory,西班牙)、青霉素G、阿莫西林及病史中可疑致敏青霉素。先行SPT,再行IDT。皮肤试验所需浓度见表2。若皮肤试验均为阴性,则进一步行激发试验以确定或排除过敏;若皮肤试验≥1个项目为阳性,则患者对青霉素过敏,进一步选用与致敏青霉素侧链不同的头孢菌素进行皮试及激发试验,以确定可作为替代的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头孢呋辛有口服及静脉使用剂型,为方便临床使用剂型的选择,因此本研究中除非临床有特殊需求,选用头孢呋辛进行检测(浓度见表2)。
如果病史中可疑致敏药物为头孢菌素,可疑致敏头孢菌素皮试(浓度见表2)与青霉素类药物皮试同时进行,如果均为阴性结果,则进一步对可疑致敏头孢菌素进行激发试验[12],如致敏头孢菌素皮试阳性且与病史有相关性,则选用与致敏头孢菌素侧链不一致的头孢菌素或青霉素类药物进行过敏评估(皮试及激发试验),以选择可作为替代的抗生素。

表2 青霉素及头孢菌素皮肤试验浓度(mg/mL)Table 2 Concentrations of penicillin and cephalosporin used for the skin test(mg/mL)
对于非β内酰胺类抗生素,目前缺乏有关皮肤试验灵敏度和特异度的研究,皮试结果可靠性欠佳,但可尝试使用原液进行SPT,若为阴性,进一步用1/100、1/10稀释液依次进行IDT。如条件允许,家属作为阴性对照同时进行相应皮试,以排除试验药物引发皮肤非特异性刺激反应的可能。若皮试为阴性,进一步行药物激发试验[12]。
1.6 乳胶检测
对于怀疑乳胶过敏患者,使用含乳胶的手套进行点刺-点刺试验和血清sIgE检测(Immunocap系统,赛默飞世尔公司,瑞典)。如果病史高度可疑,而皮肤试验和sIgE均为阴性结果,可进一步进行乳胶手套激发试验,操作步骤为首先让患者带乳胶手套,若无过敏症状出现,再用乳胶手套擦拭唇部黏膜[12]。
2 结果
共纳入患者23例,临床资料及检测结果见表3。其中男性13例,女性10例;年龄19~72岁,年龄中位数36岁(四分位数间距27岁,49岁)。

表3 临床资料及药物过敏检测结果Table 3 Clinical data and drug allergy testing results
所有患者均无变应性鼻炎、哮喘、荨麻疹病史,5例(21.7%)患者既往有药物过敏史。过敏反应可发生于围手术期各个阶段,麻醉诱导期最常见(17例,73.9%),其余依次为术前准备期(3例,13.0%)、麻醉维持期(2例,8.7%)及麻醉恢复期(2例,8.7%),其中1例患者经历2次严重过敏反应,术前准备期和麻醉维持期各1次。
患者发生过敏反应距检测的中位时间为43 d[四分位数间距(29.5,57)d,由于No.13以及No.16患者距离检测的时间超过1年,故未纳入此统计]。
18例(78.3%)患者经检测明确了致敏药物;3例(13.0%)患者虽进行了所有可疑药物的检测,但仍未能明确致敏药物;2例患者(8.7%)虽临床病史提示非过敏反应,但仍进行了全面检测以除外过敏反应的可能。
18例明确致敏药物的患者,致敏药物依次为:NMBAs 11例(61.1%),氯己定4例(22.2%),镇静催眠药3例(16.7%),抗生素1例(5.6%),琥珀酰明胶1例(5.6%)。其中,对一种药物过敏16例(88.9%),两种药物过敏2例(11.1%)。
11例NMBAs过敏患者中,顺阿曲库铵皮试阳性8例(72.7%),罗库溴铵、维库溴铵、阿曲库铵皮试阳性各1例(分别占9.1%)。
3例患者对镇静催眠药过敏,其中咪达唑仑阳性2例,丙泊酚阳性1例。
1例抗生素过敏的患者,为头孢唑林皮试阳性,且结合病史诊断头孢唑林过敏。行青霉素交叉反应试验,青霉素G皮肤试验呈阳性,不建议使用青霉素类药物。选用头孢呋辛进行交叉反应试验,皮试阴性,且进一步行激发试验阴性,可使用头孢呋辛替代。
3例患者未能明确致敏原(No.19,20,21),其中1例患者(No.19)根据病史考虑罗库溴铵过敏可能性最大,但所有检测均为阴性,再次手术时,根据本中心建议,仅更换罗库溴铵,麻醉过程顺利。
2例临床病史提示非过敏反应的患者(No.22,23),仍进行了全面检测以除外过敏反应的可能。其中1例表现为麻醉诱导期出现支气管痉挛、哮鸣音,但血压、心率正常,无皮疹及风团;另外1例表现为麻醉诱导期出现心率下降(25次/min),血压正常,无皮疹及风团。可能与麻醉药物(如NMBAs、丙泊酚)的药效学作用相关,如丙泊酚可作用于交感肾上腺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引起血管扩张,导致低血压,阿片类药物也可导致心动过缓和低血压。
对患者进行过敏检测后再次手术情况随访,14例(60.9%)患者再次手术,术中根据检测结果进行麻醉药物选择,麻醉过程顺利;7例患者迄今暂未进行全麻手术;2例患者失访(原发疾病为恶性肿瘤)。
3 讨论
本研究对23例因可疑发生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在本院接受病因诊断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分析,首次报道了我国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致敏药物的种类及特点。
本研究中,绝大多数患者(78.3%)明确了致敏药物,但有少部分患者(13.0%)虽进行了所有可疑药物检测,仍未能明确致敏药物。Krishna等[13]回顾性分析2005—2012年英国多个中心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患者共161例,其中30%的患者未能明确致敏药物; Meng等[14]的研究亦发现19.4%的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患者未能明确致敏药物。可见,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病因诊断非常复杂。一方面,患者在短时间内接受多种药物或试剂,而很多药物的致敏机制尚不清楚,缺乏有效过敏检测方法,尤其是全麻药物,如NMBAs、阿片类药物由于药理学的特殊性,不能进行激发试验,检测方法更加有限。即使进行体外试验,如嗜碱性粒细胞活化试验,可补充提供一些信息,但由于此检测方法尚未标准化,有效性尚待评估,目前主要应用于基础研究,尚未用于临床,因此无法根据嗜碱性粒细胞活化试验进行临床诊断。另一方面,不排除患者、麻醉医师及手术医护人员忽视、遗漏一些重要信息的记录和提供,导致检测实际上未能包含所有可疑致敏药物。
本研究明确病因诊断的18例患者中,最常见的致敏药物是NMBAs(61.1%),其余依次为氯己定(22.2%)、镇静催眠药(16.7%)、抗生素(5.6%)、琥珀酰明胶(5.6%)。 本研究结果与2011年ENDA总结的结果相似, NMBAs(63%)为最常见致敏药物,其余依次为乳胶(14%)、镇静催眠药(7%)、抗生素(6%)、血浆代用品(3%)及阿片类药物(2%)[6]。而来自英国的研究数据显示,最常见的致敏药物是抗生素[14-15]。可见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致敏药物的分布不同。
NMBAs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机制复杂,既可通过IgE介导,也可通过Mas相关G蛋白偶联受体成员X2(Mas-related G-protein-coupled receptor member X2 MRGPRX2)导致肥大细胞脱颗粒[16],但以IgE介导更为常见[17]。MRGPRX2受体所介导的严重过敏反应皮肤试验结果是否为阳性结果,目前研究仍有争议。Spoerl等[16]认为皮试结果为阳性,但亦有研究证实皮试是阴性结果[18-19]。Navinés-Ferrer等[18]提出皮试为阴性结果可能的原因为MRGPRX2通路的受体亲和力远低于IgE通路,或者可能由于皮试过程中,药物与皮肤蛋白结合后发生的修饰或生成代谢产物,改变了MRGPRX2的激活能力。本研究通过皮肤试验阳性结果诊断NMBAs过敏11例,可能为IgE介导,但亦不能排除MRGPRX2介导的可能;1例病因未明的患者,根据病史考虑罗库溴铵过敏可能性最大,但皮肤试验为阴性结果,再次手术时,仅更换罗库溴铵,麻醉过程顺利,该患者不排除为罗库溴胺通过MRGPRX2介导严重过敏反应。
在NMBAs中,顺阿曲库铵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非极性肌松剂。早期研究认为顺阿曲库铵的异构体基本无非特异性刺激肥大细胞脱颗粒的作用,发生IgE介导的过敏反应概率也低于其他肌松剂[20]。既往法国[21]、澳大利亚[22]及新西兰[23]的研究表明,罗库溴铵和乙酰琥珀胆碱是NMBAs诱发严重过敏反应最常见药物;新西兰[23]的研究显示,罗库溴铵、乙酰琥珀胆碱发生过敏反应的概率比阿曲库铵高约10倍。但随着顺阿曲库铵临床应用增多,其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报道逐渐增多[24-25]。本研究发现, NMBAs过敏的患者中顺阿曲库铵过敏最常见(72.7%),可能与目前临床上顺阿曲库铵应用相对较多有关,尚不能得出顺阿曲库铵过敏概率高的结论。
在NMBAs过敏的11例患者中,仅2例(18.2%)既往有全麻史,可能有NMBAs暴露史,此结果与Fisher等[26]研究结果相似(约15%既往有NMBAs暴露史)。上述结果表明,大部分NMBAs过敏患者首次暴露于NMBAs时出现过敏反应。为何肌松剂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特点与经典IgE 介导的Ⅰ型变态反应发生模式不同、缺乏致敏过程?1983年,Baldo等[27]研究证明,NMBAs的主要致敏结构是铵离子取代基。因此,致敏的途径可能为接触环境中含有铵盐基团的物质(如化妆品、消毒剂、工业材料等),或使用其他含有铵盐基团的药物(如抗精神病药、抗胆碱酯酶药、局麻药、部分抗生素等)[28]。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福尔可定的摄入量与NMBAs过敏的发生率之间存在相关性。Florvaag等[29]研究发现,挪威发生NMBAs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发生率是瑞典的6 倍,认为这是由于在挪威使用福尔可定导致季铵盐sIgE 浓度高,增加了NMBAs过敏概率,而瑞典临床上未应用福尔可定。自从福尔可定从挪威退市后,围手术期过敏反应的发生率也随之降低(从2005年的94例降至2009年的53例)[30]。另外近期发现NMBAs可通过MRGPRX2受体通路导致严重过敏反应,也可解释为何首次接触即可诱发过敏,因该通路不需要致敏过程。
本研究结果显示,氯己定为第2位常见致敏药物(22.2%)。氯己定广泛应用于医疗及相关产品,如中央静脉导管、尿道凝胶、皮肤消毒剂、漱口液及牙膏等。氯己定引起的过敏反应较罕见,但近年来相关报道渐增多,尤其是围手术期[31-32]。2009年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麻醉协会及2010年英国过敏及临床免疫学会制定的关于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诊断指南,均建议对发生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的患者常规进行氯己定过敏检测[11-12]。英国、丹麦、比利时对所有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患者均常规进行氯己定过敏检测,发现由氯己定过敏所致的比例分别为9%、9.6%及9%[33-35]。本研究发现,4例氯己定过敏患者中3例既往有药物过敏史,且根据病史推断既往药物过敏反应由氯己定诱发的可能性极高,例如多次静脉滴注不同药物(甚至生理盐水)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No.15),使用漱口水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No.16),或既往常规静脉采血后出现采血部位局部皮肤皮疹及瘙痒(No.18)。但既往均未能明确致敏药物,可见氯己定过敏漏诊率极高。其原因在于:(1)医务人员对氯己定致敏性的认知严重不足;(2)过敏症状起病时轻微而被忽略,有研究发现,氯己定诱发严重过敏反应患者,追问病史,大多数既往有暴露于氯己定后出现轻度荨麻疹的历史[36-37];(3)暴露隐匿,特别是在围手术期,医务人员往往没有意识到患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于氯己定。因此,医务工作者应充分认识到氯己定是一种潜在致敏药物。对于怀疑氯己定过敏患者,无论症状多轻微,都应进行过敏检测。一旦确诊过敏,必须严格避免再次暴露,以避免诱发更严重的过敏反应而危及生命。
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可累及皮肤黏膜(潮红、风团、血管神经性水肿等)、呼吸道(支气管痉挛)、心血管系统(心率下降、心率加快、血压下降)等[2]。在严重过敏反应中,皮肤症状往往是最早出现且最常见的。但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由于患者处于无意识或镇静状态中,全身为手术铺巾所覆盖,皮肤症状往往不易被发现,故支气管痉挛和循环衰竭常常成为首先被发现的症状。而围手术期常用药物,如NMBAs、丙泊酚,由于药物本身的药理学作用,可能会导致支气管痉挛、心动过缓、低血压等不良反应。因此,在围手术期,对于仅表现为呼吸道或心血管系统症状的患者,除了考虑过敏反应外,还应注意与药物的其他不良反应相鉴别。本研究中,2例患者临床病史提示为非过敏反应,1例表现为诱导期支气管痉挛、哮鸣音,另1例表现为诱导期心率下降,均进行了全面的检测除外过敏反应的可能性,考虑可能为麻醉药物(如NMBAs、丙泊酚)引起的呼吸、循环抑制。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尚无血清类胰蛋白酶的商业化检测试剂,无法通过该检测对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和药物不良反应的鉴别诊断提供更多信息。血清类胰蛋白酶升高是肥大细胞活化、脱颗粒的标志,是在严重过敏反应急性发作期内唯一有价值的血清学检测指标,因为无论严重过敏反应是由免疫机制介导还是非免疫机制介导,都可能导致其升高,故而类胰蛋白酶升高可证实严重过敏反应的诊断。中国亟待引进和开展血清类胰蛋白酶检测,对于提高严重过敏反应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水平至关重要。
总之,本研究对中国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病因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初步提示NMBAs和氯己定可能是中国引起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的最常见致敏药物。但由于本研究样本量偏小,仍需进行多中心、大样本量的临床研究,以期对疾病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尽管近年来围手术期严重过敏反应的研究日益深入,但其病因诊断仍是过敏专科医师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