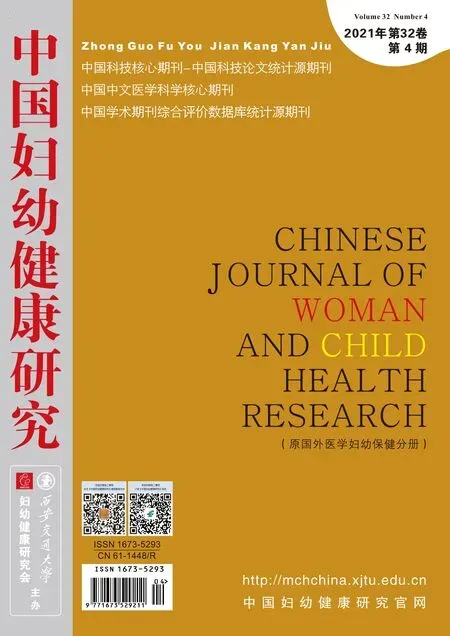上海地区生育决策决定因素的定性研究
喇雪娜,杜 莉,徐 飚,陈维怡,Julia Zhuya Kan,Lena Kan,朱丽萍,蒋 泓
(1.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与儿少卫生教研室,上海 200032;2.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32;3.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上海 200062;4.布里斯托大学医学院,布里斯托市BS8 1TH,英国;5.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博格公共卫生学院,巴尔的摩市MD 21205,美国)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生育率较低的国家之一,上海市生育率现已处于极低水平,即便自2016年起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也仅为0.9(2018年)[1],事实显示仅宏观政策层面的调整在短时间内扭转低生育水平的效果不佳。过低的生育水平会致使社会人口结构失衡,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下降。生育决策是指家庭或个人在生育子女问题上所作的决定或选择,是由生育意愿和所处的环境条件共同决定的[2]。现今社会个人和家庭的生育决策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时代特征[3-4]。目前,已有的研究多采用定量调查的方法针对育龄期女性或家庭进行生育意愿或生育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缺乏以生育的社会支持服务为出发点,以及从政策制定者、生育相关服务管理者、服务提供者等多身份和多角度探索导致当前生育决策深层原因的研究。本文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对生育相关政策制定者、生殖健康领域学者、生育相关服务管理者、妇幼保健服务提供者和育龄女性等利益相关者进行深度访谈,深入分析生育决策的决定因素,探讨家庭和个体生育决策及行为的潜在动机和原因,确定现有社会支持服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促进合理的生育决策,开展生育决策干预,改善低生育率现状提供科学依据。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定性访谈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上海地区生育相关政策制定者7人,生殖健康领域学者2人,生育相关服务管理者7人,妇幼保健服务提供者10人,育龄女性13人,共计39位利益相关者进行定性访谈,访谈对象来源见表1。

表1 定性访谈的对象类型
1.2研究方法
于2019年8月至2020年1月共开展了32期个人深度访谈和1期焦点小组讨论,主要内容包括从政府、服务供方和需方3个维度,了解生育决策的决定因素及其原因,对当前生育调节政策、生育相关的社会支持看法,接受度,存在问题,未被满足的需求,改善的建议等。访谈均获得受访者的书面知情同意。
在访谈过程中,进行对话录音,访谈结束后,将每份录音转录整理成Word文档资料,使用Nvivo 8.0定性软件进行逐级编码并进行主题分析。文中使用楷体字引用受访者原话。
2 结果
2.1上海地区生育决策影响因素
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深入访谈发现,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包括:住房、养育等直接经济成本,对女性家庭角色的社会传统观念和男性在育儿中的角色缺失,家庭照护压力,育儿理念,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女性职业追求的机会成本,个体生理因素。
2.1.1住房、养育等直接经济成本
所有的受访者都提到了经济成本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包括住房、生活和养育成本。上海作为一线城市,住房成本及生活成本难以忽视,高昂的养育成本也会对已生育家庭的再生育决策产生影响。此外,受访的一孩和二孩母亲均提到,各类辅导班及兴趣班的支出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压力。
“辅导作业班、舞蹈班、课余兴趣班很多,1个孩子最少1个月光上课要花1 000块钱。”(育龄女性——二孩母亲01)
2.1.2对女性家庭角色的社会传统观念和男性在育儿中的角色缺失
有受访者提到,社会常常认为女性的生育行为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女性在育儿和家庭中有义务承担更多的职责,这样的社会环境有可能让部分女性不愿生育。在本调查中发现,多数无二孩生育意愿的母亲表示自己的丈夫没有扮演好父亲的角色,也有儿童保健服务提供者提到,相对于怀孕即进入角色的母亲,父亲常常需要更长的时间适应新身份。
“宝宝出生,爸爸一直进入不了角色……在体检门诊,检查结束要帮宝宝换尿不湿,爸爸第一句话就是妈妈来,我不会。这已经是满月了还不会,这1个月里几乎就只是妈妈在忙。”(妇幼保健服务提供者06)
2.1.3家庭照护压力
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孩子的照护压力是进行生育决策时的重要考量。多数有过育儿经历的母亲提到,家里长辈在生育后能否帮忙照看孩子对自己的生育决策有直接影响。此外,孩子上学后的接送及课业辅导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有政策制定者指出,随着观念的转变,长辈帮忙照看孩子的意愿不再强烈,而长辈参与育儿也可能因为观念不同引起矛盾。
“原来想过[生二孩],我现在不打算生,因为没人看孩子,上班或多或少有点影响。”(育龄女性——一孩母亲02)
2.1.4育儿理念
有生殖健康领域学者提到,家长普遍存在“怕输在起跑线”的心理,进入过度保护、照护与提前学习的误区,缺乏对儿童自然生长规律的理解与尊重,儿童缺乏自由探索环境与自我解决问题的机会,而这样的育儿理念易导致家长疲惫,增加育儿压力;另一方面,家长过度重视儿童“物质”上的保障,追求事业发展以确保育儿的经济支出,缺乏在精神、情感方面的投入。在访谈中发现普遍存在“育儿焦虑”情绪,有家长提到自己本来想让孩子“自由成长”,但同班的孩子都在上补习班、兴趣班,自己的育儿理念很难不受影响。
2.1.5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追求生活质量和育儿质量同样会对生育决策产生影响。随着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首先希望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有政策制定者认为“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现代社会多元的娱乐和消费方式常常占据了年轻人的主要精力。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劳动力数量不再是家庭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微观家庭的生育决策开始偏好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
2.1.6女性职业追求的机会成本
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面临着从生理到心理的一系列变化,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劣势地位。有生育经历的3名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工作受到了生育的影响。有政策制定者表示,女性由于生育而产生的机会成本几乎无法避免,因为生育不是一个短期事件,从怀孕、分娩再到哺乳,都意味着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女性需要更多地平衡职场和家庭,已婚未育女性甚至会在职场遭遇“隐性歧视”,因此女性劳动参与率愈高,生育机会成本就愈大。
2.1.7个体生理因素
由于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晚婚晚育”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初婚和初育的年龄不断推迟。有卫生服务管理者指出,高龄产妇及前期的高剖宫产率带来的疤痕子宫等问题可能会影响很多一孩女性的再生育决策,此外,不孕不育人群的增多削弱了社会生育能力,也会导致生育意愿降低。
“做了人工[授精]必须要长期卧床,工作辞职了。我年龄有点大,属于高危产妇,怀孕之后各种不舒服……要是还生肯定要看身体情况的。”(育龄女性——头胎孕妇04)
2.2对社会支持性服务的需求与建议
2.2.1采取不同措施降低经济成本
多数受访者都提到经济补贴及福利政策对于生育决策可能起到积极影响。有人指出,孩子的养育是长期的,相较于单次的经济补贴,长期且覆盖面较广的经济补贴吸引力更大。多名政策制定者提到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税收优惠政策来减轻已生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如对多孩家庭实行个税抵扣,对婴幼儿产品降低消费税等。对于处于育龄期的年轻夫妇,专家们则建议可以通过提供低廉公租房的形式解决住房问题,保障有生育意愿的年轻人有一定的生活空间。
2.2.2促进教育资源进一步均衡化
对受访者普遍提到的教育理念问题,为了解决家庭的育儿焦虑,有政策制定者提出利用网络等信息技术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育的公平性和均衡性,以降低教育成本并促进教育公平。
2.2.3进一步完善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
上海市在婴幼儿托育体系建设中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但在调查中,政策制定者和托育服务提供者都提到托育服务供给存在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受访者对托育服务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多样性,而无论是制度建设、服务模式,还是课程体系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大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建立灵活多元、形式多样的服务供给体系;鼓励3岁以下婴幼儿教养以家庭为主,为家庭提供科学育儿指导;进一步推动3岁以下婴幼儿的科学教养研究,建立教养标准;加强托育服务管理机构队伍建设,拓宽托育机构从业人员的培训渠道,降低培训成本,保障从业人员的待遇及专业的发展。
“托育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要求越来越高,我们现在对这一块的探索也需要有很多的研究,比如说脑科学,卫生,营养,孩子怎么吃怎么睡怎么玩,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研究,目前跟国际上差距还是蛮大的。”(政策制定者07)
2.2.4为无生育意愿女性提供避孕节育服务以保存生育力
在全面放开二孩并鼓励生育的同时,生育力的保存问题同样值得重视。对于近期无生育意愿的女性,应当提供适当的避孕节育服务,减少意外妊娠,避免重复流产,保存生育力。有专家提到,要让女性“想生的时候能生,不想生的时候不生。”有避孕节育服务相关管理者指出,目前避孕节育服务的可及性与辐射面仍面临较大的挑战。育龄期女性的避孕节育知识掌握程度不容乐观,服务提供者本身的知识素养也有待加强。
“优生优育……想生的时候能生,不想生的时候不生。如婚前保健、孕前保健,就是要让她们想生的时候能生,而且生一个能够安全、健康。”(生育相关服务管理者06)
2.2.5建立灵活的生育假制度,鼓励男性更早参与育儿过程
有专家建议,可以建立灵活的育儿假制度,对于有育儿需求的家庭,可以提供一定的育儿假,由主要养育人自行决定时间分配。也有专家认为,要改变我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应对男性设立强制性育儿假,鼓励其参与育儿过程。也有育龄女性和妇幼保健服务提供者建议,增加男性陪产假时间,鼓励男性参加孕妇学校,让男性更早参与育儿。
“增加爸爸的产假,孕妇学校就应该参与进来了,妈妈是有这样一个产检假,但爸爸没有。”(妇幼保健服务提供者03)
3讨论
3.1培养夫妇树立适宜育儿观,探索构建家庭与社会共同育儿体系
上海作为超大型城市,相对较高的生活成本和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平衡,导致家长育儿焦虑不断凸显。有研究指出,育儿焦虑常体现在“竞争焦虑”“安全焦虑”“健康焦虑”,并受到家庭内部和社会文化的多重影响[5]。相较于传统社会中家庭承担了生育、经济、教育、赡养等多重功能,现代社会的家庭功能逐渐呈现出向社会外移的趋势,如生育、赡养、教育功能等,社会转型中的家庭所承担的养育功能具有一定局限性[6]。因此,引导家长树立适宜的育儿理念,涉及到个体、家庭及社会的共同参与;应当树立社会共同育儿理念,联动教育、福利、劳动、经济等各职能部门,构建同时满足家庭和社会的育儿支援网络。
3.2探索覆盖面广的生育福利政策,降低家庭生育经济成本
在访谈中发现,“养儿”的成本困扰着大多数家长。相较于其他低生育水平国家提供的多样性津贴福利,如生育奖金、育儿补助津贴等[7-8],我国尚缺乏长期且覆盖面广的鼓励生育福利政策。我国新个税改革提出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但是也有研究指出个税专项扣除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未考虑单亲家庭等不同的家庭结构,扣除额度计算方式不合理,扣除额度较低等[9]。因此,应当根据居民实际情况,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不同家庭结构,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探索涵盖孕前、孕期、养育、托幼、到学历教育结束的经济补贴和家庭福利津贴政策。
3.3进一步完善托育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根据上海市妇联的调查显示,上海市需要婴幼儿托管服务的家庭占到88.2%[10]。近年来,上海市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出台托育服务“1+2”政策,逐步建立托育机构管理机制。目前,上海市幼儿园托班一般仅招收2岁以上婴幼儿,而民办托育机构价格较高,难以满足不同层次家庭的需求。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加大街镇、社区托管点的建设,鼓励企事业提供公益性、福利性的托育服务。通过多元、多层次的托育服务体系,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0~3岁婴幼儿的托育涉及营养、保健和教养3个层面,同时还要兼顾“托幼一体化”背景下,保育与教养的衔接性与连贯性。因此,需要进一步鼓励脑科学、儿童医疗保健、早期教养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探索建立3岁以下婴幼儿早期教育课程体系和托育服务操作标准,完善托幼服务体系,减少生育决策的后顾之忧。
3.4加强女性生殖健康卫生服务,保障避孕节育服务供给
我国是重复流产大国,人工流产率居高不下。据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2005年至2017年人工流产平均每年高达784.59万例[11],非意愿妊娠导致的人工流产对女性的生殖健康造成了潜在的重大影响[12]。有研究指出,“全面二孩”政策后,计划生育服务应该增加对计划生育家庭的支持,应根据家庭或个体的生育意愿适宜地提供避孕节育服务[13],保存夫妇生育力。应当加强社会的计划生育意识,正向宣传避孕节育的重要性。为青少年提供早期性教育,并加强青少年友好服务供给。避孕节育服务应覆盖未婚人群,落实人工流产后服务规范,减少人工流产率及重复流产率。对产后女性应加强产褥早期和晚期的避孕宣教。
3.5探索建立灵活的产假及育儿假制度,鼓励男性更早参与育儿
2012年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但目前中国的产假制度存在弹性不足的问题,一味地延长产假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女性在就业市场所遭受的歧视。因此需要建立灵活的产假和生育假制度,探索以家庭为单位的育儿假模式,使家庭成员在平衡照料儿童和工作时具有更多的选择。为男性设立强制性的陪检假、陪产假、育儿假,鼓励男性从孕期开始参与育儿过程,强调男性同样有教养婴幼儿的职责。此外,要进一步完善女性的就业权益保障,减少男女就业差距。
——内蒙古托育产业发展情况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