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仙”二字为何值得玩味
周岩壁
水仙,这个名字值得玩味。古希腊神话中,此花是自恋成癖的美少年纳西索斯(Narcissus)化身,所以它就叫纳西索斯。可见,地中海北岸的希腊山地,大概是水仙的家乡。水仙并不是我们中国的土产。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八:
捺祗,出拂菻国。苗长三四尺,根大如鸭卵。叶似蒜叶,中心抽条甚长。茎端有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子。其草冬生夏死,与荞麦相类。取其花压以为油,涂身,除风气。拂林国王及国内贵人皆用之。
捺祗,就是Narcissus的译音;这是水仙最早见于我国文獻。拂菻,就是东罗马帝国,主要是土耳其小亚细亚半岛一带。再往东,就是阿拉伯人建立的大食国,和大唐的吐蕃(西藏)接壤。捺祗是由陆上沿丝绸之路进入大唐,还是先由印度洋到达东南沿海呢?综合可见到的文献,水仙以海路进入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可能性为大(参看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二章)。
唐代,关于水仙,也就段成式这么一条志异式的文字。我们知道水仙是不好养活的,它开花之后,根就逐渐烂掉了,要留种是很难的。所以,通过陆路在北温带的中国培植不易成就。我们认为,这就是它在唐代文献里鲜有人提及的原因——谁都没见过。
唐诗里也有“水仙”,但那个水仙不是有特定内涵的“水仙花”的水仙,不是指这种石蒜科植物。据后来的文献推测,水仙在中国站住脚,大概首先是在东南沿海一带,时间是宋代。泉州、漳州,福建沿海,传统地,是中西海上贸易的前站。宋初诗人赵湘在《南阳集》中说水仙“本生武夷山谷间,土人谓之天葱”。说明水仙在福建当地已经本土化了。晁说之(1059-1129)《四明岁晚水仙花盛开,今在鄜州辄思之。此花清香异常,妇人戴之,可留之日为多》:
前年海角今天涯,
有恨无愁闲叹嗟。
枉是凉州女端正,
一生不识水仙花!
四明山,在宁波、奉化西部。宁波当时叫明州,也是中西海上贸易的港口。所以,四明山里的水仙,也未必是由南方武夷山北迁而来。但有一点很明确,北宋时候,出于西南的四川盆地没有水仙。
和晁说之同时的黄庭坚,有很多咏水仙的诗。如《刘邦直送早梅、水仙花》之四:
钱塘昔闻水仙庙,
荆州今见水仙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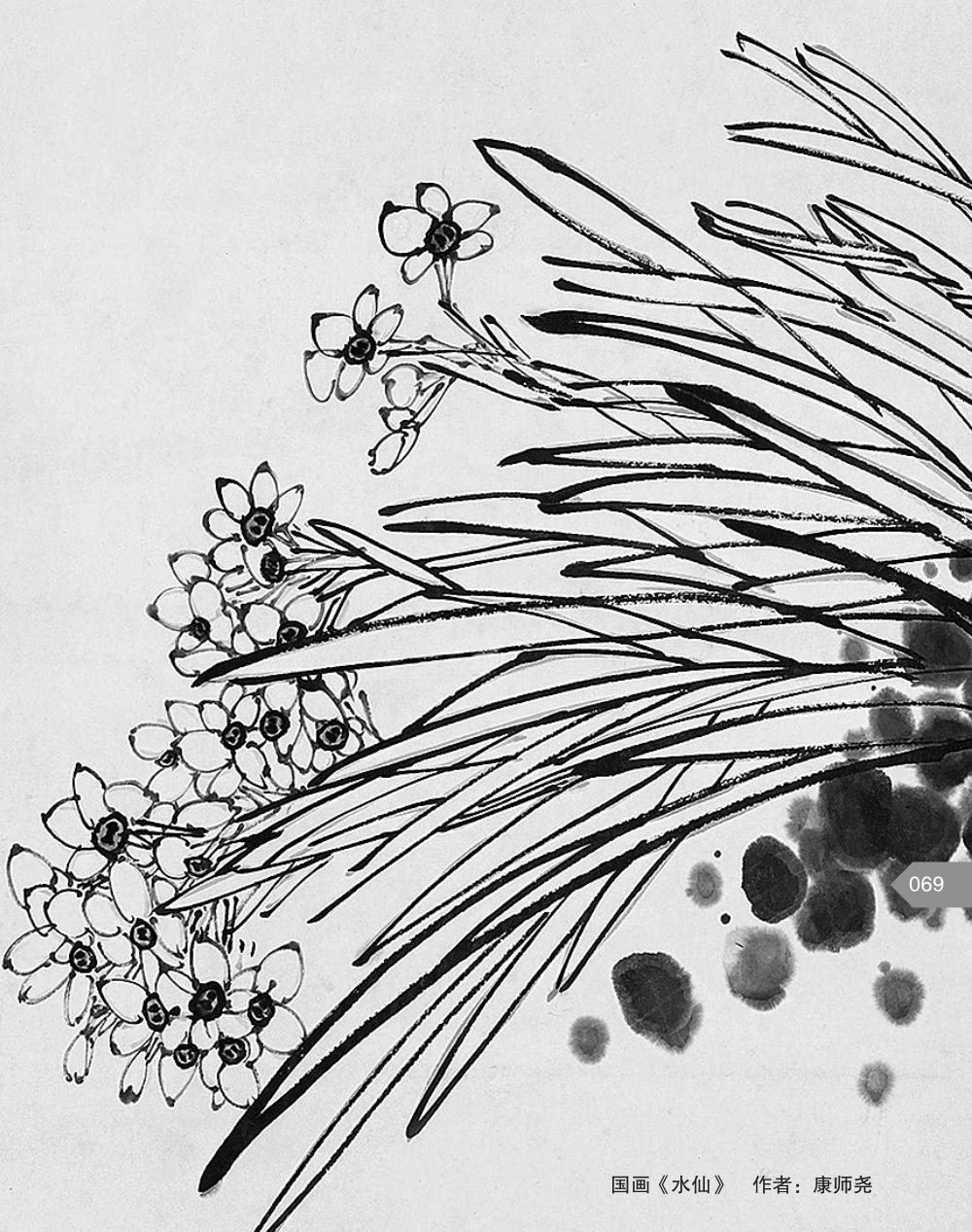
暗香静色撩诗句,
宜在林逋处士家。
《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
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
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
可见,北宋中期,水仙已经由东南沿海向西北远征到长江中游一带了。
同时代的张耒亦有《水仙花》:
宫样鹅黄绿带垂,中州未省见仙姿。
只疑湘水绡机女,来伴清秋宋玉悲。
此诗还有小序:
水仙花叶如金灯,而加柔泽,花浅黄,其干如萱草,秋深开至来春方已,虽霜雪不衰,中州未尝见,一名雅蒜。
这表明,彼时中原一带比如京都、开封,尚无水仙。黄庭坚把水仙比作“凌波仙子”,张耒把它比作“湘水绡机女”,从而把水仙和我们传统文化中洛水宓妃、湘江的娥皇女英联系起来。水仙在中国文化中的形象由此完全本土化,和它故乡的纳西索斯划清界限。
《广群芳谱》云:“水仙花,江南处处有之,惟吴中嘉定为最。”李渔《闲情偶寄》云:“水仙以秣陵为最”,“金陵水仙为天下第一”。秣陵、金陵,都是今天的南京。如此说来,明清时候,长江下游江南、太湖一带后来居上,成为培植水仙的中心之一。此时水仙品位步步高升。明人张德谦《瓶花谱》中,水仙高居“一品第六名”;袁宏道《瓶史》评水仙“神骨清绝”;李笠翁更是一本正经地说:“水仙一花,予之命也”,好像是离了此花,他老人家就没命了。
水仙花进入中国,经过长期培植,变种很多,和海外的面目全非,大异其趣,以致英国人称它是中国圣百合(Chinese Sacred Lily)——真是数典忘祖。虽然水仙虽变种很多,林林总总,大而化之,则可分两类。高濂在《艺花谱》中,就是这样分的:
千瓣者名玉玲珑;单瓣者名金盏银台。单者叶短,而香可爱,用以盆种上几。
高濂是明末杭州人,一生在江南活动;他说水仙“盆种上几”,摆在案头,大概是指江南。至于当时,北京是否以水仙为案头清玩,可就难说了。
康熙皇帝有《见案头水仙花偶作》诗:
翠帔缃冠玉为珈,
清姿终不污泥沙。
骚人空自吟芳芷,
未识凌波第一花!
可见水仙已成北京潭潭皇宫里南书房的清玩雅品。因为自己爱水仙把它地位拔高到凌波第一花,固然趣味是没法争论的,旁人也没有什么意见;然而因此怨屈原等骚人只知道“咏芳芷”,而没有着笔歌颂水仙花。皇帝先生可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因为不要说屈原,就是李白杜甫也没见识水仙的眼福;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哪里还能咏水仙呢?可能是皇帝先生一动气,忘了水仙原是洋货吧。
(作者系文学博士,郑州师范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