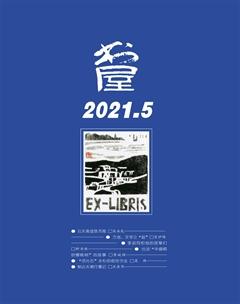邓石如讨“鹤”
李传玺
1937年4月29日,朱自清先生从清华大学进城看了场展览。有两件手札引起了他的兴趣。其一是《叶名琛小传》,其二是“邓石如给樊的信,叙述一只鹤的历史,并要求樊将鹤归还和尚”。
这里我们单说邓石如的信。邓石如,清代著名书法家,安徽怀宁人,乾隆八年(1743)五月出生,嘉庆十年(1805)十月去世,名琰,字石如,号完白山人、完白山民或皖白。邓稼先的六世祖。这只鹤是邓石如晚年的重要精神寄托,这封信就是后来在晚清书法界甚至整个文化界产生极大影响的《陈寄鹤书》。
一、寄鹤
乾隆六十年(1795)秋,五十三岁的邓石如去丹徒游访,在袁廷极家看到了袁家养的两只鹤。这两只鹤看到邓石如并不认生,相反表现出亲近感。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或者在传统士人眼中,“君子为鹤”,袁廷极看到这般情景,认为这是天人两界之君子的心心相惺情感契合,于是决定将这两只鹤赠送给邓石如,他郑重地对两只鹤说:“此乃尔主也。”
邓家的“铁砚山房”在大龙山下,山林茂密,两只鹤有一种回到大自然的快乐。它们给邓石如也带来了很多快乐。邓石如在写字看书之余,走到庭前,一声轻轻的咳嗽,两只鹤就会轻捷地跑来,在他面前展翅舞蹈,或者一抖翅膀直冲云霄,就在大伙儿快看不见它们时,它们又会一个转身一个俯冲落到庭前。
邓石如带回两只鹤,在当地也引起了轰动。左邻右舍听到这个消息,都想来看看这两只灵异之物。邓石如后来在给樊晋信中说:“元裳缟衣,铁足朱顶,鸣声闻于天,乡里以为异。谓‘徒闻千岁鸟,今见九皋禽,扶老携幼,日拥户外。”当然在这看的人中,也不乏不法之徒。不久,当两只鹤在附近林泉旁“饮啄”时,即被山林中打柴的“野人”乘两鹤不注意将雌的捉住,扭断长颈杀死。“雄鹤孤鸣不已”,邓石如在痛心之余,想到自己还要常常应朋友邀约出去游访,为了给雄鹤换个环境,也是为了给雄鹤有个更好的照顾,于是将之寄放到了离家三十里远的集贤律院中。
清康熙六年(1667)安徽设省,当时省会设在安庆。集贤关位安慶北,林木蓊郁,竹树交翠,关隘险固,山石嵯峨,被认为是省会的龙脉,又是往北去往京城的交通要道。律院就在集贤关旁。邓石如将鹤送去时,看到鹤依依不舍的样子,他这样嘱咐鹤:“尔乃胎禽,浮邱著经,云门鼓翅,华表飞声,带负霄汉凌云之志,恐终非贫家有也。尔有遐心,亦听尔之翱翔寥廓耳?不尔羁也。今嘱尔寄一僧,以修尔龄,僧托于尔以辅成其名,尔无负山翁寄托之意,以徜徉于此尔。此地有修竹古木可庇荫尔,有青灯古佛可忏悔尔,有云幡宝盖可威仪尔,有法座经坛可庄严尔,有蹲狮伏象可护持尔,有萝月松风可徘徊尔,有山花野卉可纾尔步,有溪泉潺湲可濯尔羽,有积石漫山可利尔喙,有苔华绣砌可逞尔狂,有高梧重重可张尔盖,有苍藤垂垂可排尔幢,有梵呗鱼板可醒尔梦,有蛇虺毒物可充尔粮,有钟鼓镗鞳声,可启尔海峤搏风、磅礴乎青云之志……有山禽鸣噪声,可动尔群下相融、物我熙熙、共乐林泉之度。”鹤仍是一副懊恼的样子,邓石如又接着安慰:“僧归尔伴,僧出尔守,月白风清,听经默首,毋徒饮啄,整饬尔羽,他日太清,衣冠楚楚,岂不尔驾,骑尔遨游!”“吾居不远,于焉三十里,尔若怀归,龙山凤水,尔其谛听吾祝辞”;“尔其安此,山翁时笠杖踌躇而来,谂尔于此。”表面是鹤依依不舍,实际是邓石如依依不舍。
邓石如将鹤寄托于此后,“担粮饲鹤,月有常例”,虽然自己“家徒四壁”,“家无石储”,仅靠自己卖字为生,但此时仍然拿出十金帮助住持性泰修建“寄鹤亭”,“施茶以济行人”,虽然“昨秋(1802)枯旱,犹以钱十千襄僧架此东轩”,让律院日渐兴盛。
二、陈寄鹤书
随着僧院的兴盛,此处也成了省城的“送迎佳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只鹤遭逢了一次厄运,也引出了邓石如的《陈寄鹤书》。
嘉庆八年(1803)年初前后,安庆知府樊晋从此路过,看到寺院已成规模一派兴盛,便走了进去。住持性泰连忙迎接。鹤就跟在性泰身边。性泰也是这样迎接邓石如的,在鹤以为,凡是他这样迎接的人都是他的贵客。于是像往常邓石如来一样,鹤也开始展示它热情的舞蹈。鹤是灵性之物、吉祥之物。樊晋没想到这里有鹤,更没想到鹤会向他献舞。他高兴,而随从们更是一片喝彩,能得到鹤的欢迎,表明知府大人前程一片远大,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做上一品大员。这些献媚之声更让樊大人飘飘然。这边樊大人一走,随之从省城过来了几个人,带着铁笼,将鹤强行捉进笼中,带给了樊大人。既然大人如此高兴喜欢,既然此物能给大人带来吉祥,何不让它时时伴在大人身边,何不也让它在大人的迎来送往中博得更多的欢心,为大人的升迁带来更多的助力呢。后来邓石如的信说是樊大人左右为了讨好樊大人自作主张干的。但又安知不是樊大人自己的意愿或授意呢?
住持无法也不敢阻拦,但这毕竟是老朋友邓石如信任自己交给自己帮助看护的。如此何以面对老朋友。他只好迅速致信邓石如说鹤被掳。
按当时“常情”,一地最大官想要自己的东西,草民还不抓紧奉上;如今强捉了去,何不来个顺水推舟,写个信表个白,送个顺水人情,最不济也就隐忍拉倒。
但邓石如偏不。他正在扬州大明寺游历,得知消息立即赶回。于花朝节前后回到家乡。当他听性泰具体说了此事经过后,立即洋洋洒洒写了封一千八百二十多个字的长信,《上樊大公祖(明清时士绅对府以上官员的尊称)陈寄鹤书》。在当时用毛笔书写的情况下,这个字数应该是相当长的了。这表明他听了此事经过后,情绪非常激烈,并决心一定要把鹤要回来。
信的开始交代了鹤的生命史,以及怎么来到他家,他又为何把它寄托到集贤律院;继之写他把鹤送到律院后两者之间的依依之情以及他对鹤的详细嘱咐;最后写他希望樊大人把鹤送还律院。而在这最后部分,邓石如又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首先说,这样把鹤带走,“物之报人以嘉祥”,却“有系囚之辱”,这样做实是对不起鹤;你来律院,住持等热情接待,最后却把其吉祥之物掠夺,“而使冷院枯僧,日郝颜于寄鹤之山翁”,这样做实是对不起律院之僧。既然这样两方面对不起,你只有把鹤送还回来才能化解。邓石如此段实在在写樊大人夺鹤的不正当性。接着邓石如给了樊大人一点面子。他这样设想,大人“之意万不如是,此不过近侍之吏图此以要赏赉”,你根本不知晓;或者就是当时喜欢之情还未尽,还想带回去“暂假娱情”,或许很快“乘兴招之,兴尽挥之”;或者你是想把鹤带回去放在眼前,“睹物怀人,远慕古贤琴鹤之风,以益励其廉清而光照皖国”。大人真要是这个想法并来进行治理那简直太好了,这岂不是包括“山翁”之内的治下之民的荣幸,但邓石如自此笔锋一转,因为如此目的来夺鹤包含着一个为政者的悖论,“益励其廉清”,那又“何贵于鹤”,还不应该将鹤快快送还吗?邓石如继续深化,如果你樊大人真有如此“廉清”目的,那何不“登高一呼,费可日集,院可日兴,兴此禅关,壮省会之观瞻,息征途之行旅,护国裕民,庄严三宝,为一郡之功德主,岂不超越寻常万万载!”这样做,对于一个知府来说,只不过“一珥笔之劳”,而换来如此大的功德,这才是真正的“祥瑞之兴”。既然如此,你更应该将鹤送回来。邓石如没有从樊晋“私欲”的角度去设想他,而是从他作为一个为政者正面角色的角度去设想他,既给樊晋保留了面子,又写出了送还鹤的必要性。邓石如可谓煞费苦心。信的最后,邓石如直接写出了诉求:还我鹤。“大人若徒手而有之”,我固然对不起袁廷极赠鹤之意,也对不起鹤本身对我的情意,但你必然要冒“夺山人之鹤”的外议。你若认为我这样做是“草野冒渎尊严”并处罚我,我也不怕,即使“山民化鹤,鹤化山民,所不辞也”。邓石如态度坚决,斩钉截铁,巍巍然,凛凛然。
樊晋拿到信后,一读之下,甚觉在理,爽快将鹤还给了邓石如。
三、《陈寄鹤书》的影响
要回鹤的邓石如非常高兴,写了首诗来纪念。《鹤归志喜》:“黄堂画阁丽三台,饰羽修翎亦快哉。底事樊笼关不住,空庭又见尔归来。阆苑蓬莱漫起予,且随鹿豕度居诸。丁宁莫更重干禄,免使山翁又上书。”这里的“樊笼”有没有双关的意思呢?
邓石如要回鹤,在士人和他的朋友中都引起了极大震动。云阳黄景峰、丹徒阎竹宾合作画了四幅通景的《完白山人放鹤图》。时任望江县令的师范(1751—1811),字荔菲,云南人,不仅在望江有政声,在老家云南也有一定影响。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授方癯先在给大家讲授《云南文化史略》概括嘉庆后云南文化时这样说:“诗以昆明钱沣、石屏朱雘为精,文以宁州赵大绅、赵州师范为高。”师范作诗称赞:“慷慨新陈寄鹤书,山民化鹤鹤难如。”后来更接二连三在有关诗画上题卷:“山人清比鹤,鹤忍负山人;寄去禅关迥,归来竹院新;大江秋捩拕,凉月夜回轮;添得诗兼画,纷纷为写真。”“不是浮邱伯,何人足赏音,曰归情乃适,作画感尤深,风雨三生梦,江山万里心,苔痕连月色,起舞又从今。”师范更开玩笑加羡慕似地表示:“我亦先生鹤,樊笼不许关。秋风吹古署,清泪隔蓬山。四野鸿方集,林中鸟未还。何当同息影,卧听水潺潺。”从这些诗画看,此事流传范围甚广,而且都很敬佩邓石如的所为。望江当时属安庆府,一个县令居然不去“同情”上司知府,而去赞赏山人邓石如,这里有着师范本身的另一种大胆。
而邓石如的信更成了有清一代书法的巅峰之作。编著《中国书法全集·邓石如卷》的穆孝天先生说,邓石如的信一出来,立即被人称之为“文美与书美的惊世之作”。邓石如五世孙,著名美学家、邓稼先父亲邓以蛰说到此时邓石如的书法,称赞是一派“倜傥诡异”。大家都想一读信的内容更想欣赏到信的书法,甚至以一见临本为荣。在这方面,上面所说的师范为邓石如信的流传做出了大贡献。穆孝天先生如此考证:“原稿最初藏于程横山家,曾由邬紫虚假归旅中反复诵读,后由云南师范(荔菲)任安徽大雷(望江县)县令时求而得之,带回滇中印行。”穆先生考证的版本乃邓氏亲笔涂改的底稿本。如今《陈寄鹤书》有三个版本:田家英小莽苍苍斋藏本(就是有涂改的底稿本),另有两个过录本,分别藏云南博物馆、四川博物馆。云南有一藏本,应该有着师范的“因缘”。
越到后来,人们对此信越发喜爱敬爱。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光绪甲午年(1894)无锡邓元鏸看到临本后,担心将来失传,想方设法找人将之临摹刻了出来。当重阳日那天完工时,他高兴地在“志”中说明心迹:“完白山民书名满天下,而著作少传。《寄鹤书》是其平生得意之笔,草书长卷。旧藏胡世荣澹泉(合肥人,清代画家)家,今其子孙犹秘守之。顾道穆丈偶得临本,余虑将来真迹之终失传,而临本亦未易遇也,爰录而刻之,以示耆古之士。”邓元鏸(1848—925),字纯丰,号弈潜斋主人,曾在四川成都等地任官职。他是清末民初围棋棋谱编撰家,也整理出版了许多书画著作,《陈寄鹤书》是其中之一。四川博物馆所藏,应该有着邓元鏸的“因缘”。
不知是不是师范印行后将原件送还了邓家,还是除了底稿外还有另外誊清本。当时邓家也还藏有《陈寄鹤书》稿本。薛玉堂(1757-1835)就曾这样记载:“嘉慶己卯(1819)六月九日访守之(邓石如之子邓传密,当时正跟随李申耆先生在阳湖暨阳书院学习)不值,于书棚中见此册(即《陈寄鹤书》),快读数过,恍若拜先生于禅关竹树之间,守之当宝而藏之。”为此,薛玉堂特意在《陈寄鹤书》后面写了跋以记载这个“发现”和感受。
——邓石如书法艺术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