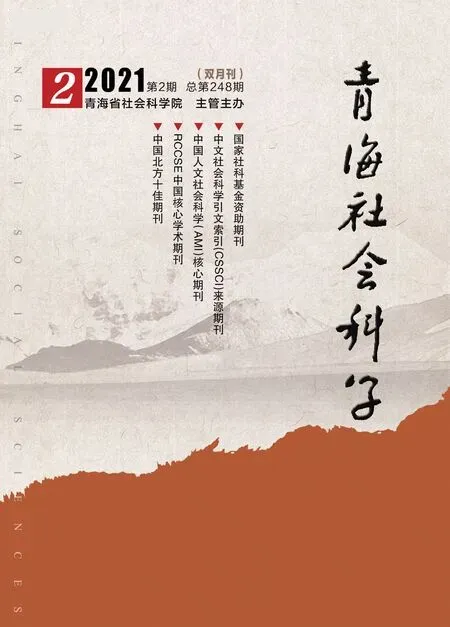生态安全观视域下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丁 姿 王 喆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要求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我国首批设立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①三江源、东北虎豹、大熊猫、祁连山、海南热带雨林、神农架、武夷山、南山、钱江源、普达措10个国家公园试点,涉及12个省份,整合了157处自然保护地。将区内所有自然保护地整合划入国家公园范围,实行统一管理、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跨行政区的整合是国家公园体制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处理“上下左右里外”的关系[1],不仅涉及到已有权力分配体系的变革,也切实影响到改革的成效和可持续性。
三江源国家公园在体制试点改革中的步伐相对较大,是最早也是受到关注最多的代表。在试点中,三江源国家公园以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为依托,打破原有“九龙治水”的行政区划范围,在管理层面形成“一园三区”的统一管理格局,在执行层面通过机构整合设立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以及资源环境执法局,在县级层面合并了相关的职能部门,重构了政府部门间关系,管理体制改革所涉及的范围和力度较大。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设担负着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使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主体功能全面得到加强的重任,其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走在各试点区前列。通过剖析其改革路径并探讨面临的新课题,将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提供有益借鉴。本文以生态安全观视域为切入点,以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建设为例,讨论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特别是探索打破“九龙治水”格局、研究改革中形成的新问题,以期为国家公园体制的深入改革提供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自1872年全球第一个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公园——建立以来,国家公园成为自然保护地最重要的类型之一。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是国家公园学术研究关注的重点和前沿问题,涉及到生态安全、自然资源的产权以及治理模式创新问题。
(一)生态安全战略与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历程
自然保护地建设对于国家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在定量分析自然保护地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对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作用后,科学评估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对国家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重要作用[2]。但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自然保护地间交叉重叠,管理目标冲突严重,无法形成真正的保护地体系[3],影响了自然保护地的保护成效[4]。因此以保护管理效能为划分标准,分类管理自然保护地成为改革的迫切问题。国家公园是我国“最美”的自然山水,是综合价值最高的自然保护地类型[5],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为首要目标,涵盖了最广泛的管理目标,成为了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通过国家公园建设试点引领自然保护地建设成为“十四五”时期重要的生态安全战略。
作为“中华水塔”的三江源是生命之源、文明之源,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区的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关系到全国的生态安全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为此,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后,2015年国家发改委等13部门联合发布《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并在同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6年青海省正式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工作,并将其列为“天字号”工程。在近5年的试点期内,青海省印发多部试点政策和地方性法规,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厅级单位),保护、管理和运营公园内的自然资源遗产,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改革之路。

表1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政策一览表(中央和省级)
(二)管理体制之争与“两统一”理念下的大部制改革
就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的管理体制,本世纪初曾爆发过“产权转移派”和“国家公园派”之争[6]。前者以旅游经济的营利性为目的,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由地方政府和旅游部门“合作”进行自下而上、由点及面的自发式改革。后者站在其对立面上,批判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开发导致的遗产破坏、公共利益牺牲乃至腐败问题,并推崇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当时尽管“国家公园派”的舆论呼声很强,但实际干预能力较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更高阶段后,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人们开始反思过分追求经济目标而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安全问题。①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年宝玉则保护分区核心区,水源、草场地、丰富的动物资源是重要的保护对象。此前,年宝玉则鄂木措景区年接待游客数量保持在10万人左右。大量的人类活动已经对当地的生态环保产生严重负面影响。2018年4月年宝玉则停止接待游客,以保护园区内外草原、湿地、野生动物等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目前,景区内已经拆除观景步道、观景台等设施,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管控。如何破解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背后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破解管理体制之争的首要前提是自然保护地的产权问题,及由此带来的保护、管理和运营考量。由于政府部门职责分散或者交叉,很难从山水林田湖草的整体生态系统角度、从国土空间整体角度进行管控和治理。加之事后的违法违规处罚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需要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来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效能。为此,2018年中央政府大部制改革组建了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简称“两统一”)。其下设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加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牌子:在空间上将自然保护地纳入统一管理,解决保护地空间规划重叠的问题;在管理体制上破除职能“九龙治水”、交叉重叠等问题。至此,在国家层面为10个国家公园管理体制试点区的深入改革提供了上位制度保障。
(三)本文分析框架的提出
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管理体制主要包括三种类型:自上而下型、自上而下与地方自治相结合型、地方自治型,其中以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制为主[7],突出全民所有和公益属性。在法理上“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是我国中央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是全体国民的福利[8]。试点中的中央政府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权分为中央政府直接行使、委托省政府代理行使、中央政府和跨省政府共同行使三个类型[9]。三江源国家公园所有权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试点期间由中央政府委托青海省政府代行所有权,探索分级统一的管理体制建设,实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同时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双重目标。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机构范式革新成为趋势,机构整合和职能优化是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从分散到统筹、从“九龙治水”到“攥指成拳”,尽管学界围绕政府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和动因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少有研究触及机构改革的过程及其整合经历[10]。在10个国家公园试点区中,一方面,三江源国家公园在部门整合中步伐最大,同时涉及到省一级和县一级机构改革和合并;另一方面,三江源国家公园涉及到的职能合并范围限定在一个省域内,也为深度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因此,本文以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为例,讨论管理体制改革的“上下左右里外”关系。
图1为导弹及其红外导引头的光学系统镜面的相对位置示意图. 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建立导弹弹头及气动流场模型, 划分计算流场网格, 红外导引头镜面网格, 辐射场计算网格. 从辐射照度和亮度的理论公式开始, 推导出适用于辐射网格的气体辐射积分式, 并将流场网格数值插值到辐射场网格, 求出各节点辐射值, 得到由导弹飞行状态确定的导弹头部流场气体辐射, 积分到红外导引头的光学系统镜面处, 求出导弹弹头流场对含于其内的导引头的光学系统镜面产生的辐射照度.
本文的分析框架图如图1所示。(1)从央地关系来看,剖析三江源国家公园在管理结构方面的改革。特别是从中央、省、自治州和县分层次的机构设置涉及到多元利益主体:国家公园管理局(中央)、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省)、各园区管委会(自治州)、县政府等。(2)从机构整合角度,分析“山水林田湖草”管理职能合并导向下的自然资源管理和综合执法职能整合的路径。(3)从部门协同的视角,阐述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综合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各机构间在职能转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综上所述,研究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执行路径,特别是打破“九龙治水”格局后在政策执行层面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趋势。

图1 国家公园管理体制试点改革分析框架图
三、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改革
(一)央地关系:中央政府委托省政府代行资产管理权
“央地关系”改革是我国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清晰的央地权责关系是国家公园管理体制试点改革成功的前提保障,特别是当面临钱、权的体制改革难点时,改变过去“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格局,清晰划定不同层级政府的权责关系,对于保护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都有重要意义。
事权划分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适当加强中央在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事权要求,改变中央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发展模式和中央收权下的“运动型”治理模式[11]。《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规定,“划入国家公园内的冰川、河流、湿地、草原、森林等自然资源为国家所有、全民共享,所有权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试点期间由中央政府委托青海省政府代行。”2016年,青海省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作为青海省人民政府派出机构,承担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以及青海省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各类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管理职责。可见,更加规范地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成为改革的重要取向,国家公园试点本身就是在探索一条“中央事权,上下联动”的体制优势之路。

图2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及执法部门改革①2020年11月6日,青海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国家公园警察总队)揭牌仪式在西宁举行。原青海省森林公安局及直属机构整体划转青海省公安厅领导管理,更名为青海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加挂青海省公安厅国家公园警察总队牌子。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警察总队。目前森林公安队伍转隶工作还在进行中,截至本文写作日期,尚未告一段落。
财政投入方面:中央对青海省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各类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以及社会资金投入为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提供了保障。《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第七条规定,要“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社会共同参与的资金筹措保障机制,三江源国家公园保护、建设和管理等所需资金由省人民政府申请中央财政解决”。我国自2000年起实施民族地区转移支付,2018—2020年的中央财政资金向青海省一般性转移支付分别为345388万元、392666万元和542515万元,②见2018年、2019年、2020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分配表,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官网。增幅明显。此外,中央对重点生态区实施转移支付制度,2019年对青海转移支付32.57亿元,其中对禁止开发区补助3.55亿元,对生态护林员补助1.69亿元。③财政部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对地方第二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财预〔2019〕95号),2019年5月9日。http://yss.mof.gov.cn/gongzuodongtai/201912/t20191216_3442182.htm。2020年对青海转移支付预拨36.28亿元,其中禁止开发区补助2.58亿元,限制开发区补助6.36亿元。④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财预〔2019〕180号),2019年10月21日。http://www.mof.gov.cn/gkml/caizhengwengao/wg201901/wg 201911/202005/t20200522_ 3518233.htm。可见,中央财政投入逐年上升,并根据青海省生态功能区的扩展而增加,由财政资金总量向分配结构转变,特别是对“人”的投入,应当是未来改革的重点。
(二)机构整合:大部制导向下的职能重组
青海省委省政府于2016年5月下发《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机构设置方案》,通过部门整合和职能优化,重构生态保护管理体制,行使自然资源管理和统一综合执法职能(见图2,作者自绘)。
1.“一园三区”管理格局。
形成统一的管理格局是改革的第一步。2016年6月,青海省整合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和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3个园区管委会,形成“一园三区”统一管理格局。关于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国家公园管理局加挂三江源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牌子,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园区管委会加挂三江源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分局牌子。长江源园区管委会派出治多管理处、曲麻莱管理处和可可西里管理处3个正县级机构。
2.县域综合治理改革。
由上述管理架构可见,为了配合三江源国家公园“一园三区”管理体制改革,遵循大部制改革思路,所涉玛多县、治多县、曲麻莱县、杂多县政府进行了县域综合治理改革。(1)整合设立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整合3个园区涉及4个县的国土资源、林业资源、水政水资源、环境保护等相关管理机构,设立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2)整合设立资源环境执法局。整合4个县森林公安局、国土执法、环境执法、草原监理、渔政执法等自然资源执法机构,设立资源环境执法局,内设森林公安局和资源环境执法大队。(3)整合设立生态保护站。所涉4县整合林业站、草原站、水土保持、湿地保护等事业单位,在园区管委会(管理处)设生态保护站,为正科级单位,乡镇加挂生态保护站牌子,增加国家公园相关管理职责,进一步理顺生态保护管理体制。
以长江源(可可西里)园区所在地治多县和曲麻莱县为例,根据中央和省委两个“9号文件”精神,治多县和曲麻莱县实行了大部制改革。县政府将所属国土、环保、林业、水利等部门人员和编制整体划转,分别组建了长江源(可可西里)园区治多管理处和曲麻莱管理处,管理处内设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资源环境执法局(资源环境执法大队、森林公安局),以及综合部、规划财务部和生态保护站这5个机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局和资源环境执法局既是国家公园的内设机构,也是县政府的组成部门,接受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县委县政府的双重领导。经过改革,县政府组成部门由原来的20个整合至15个。同时,治多、曲麻莱县党政“一把手”实行“一岗双责”制,分别担任园区管理处党委书记和主任,参与管理处重大工作的决策。
3.综合执法机构改革。
由上述县域综合治理改革可见,成立资源环境执法局意味着在执法层面改善了部门职能交叉的局面,也构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内“三级”综合执法体系的“中段”和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二级”执法体系。一方面,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下设执法监督处,加挂三江源国家公园森林公安局、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安局牌子。三江源国家公园执法监督处对曲麻莱管理处、治多管理处、澜沧江园区管委会、黄河源区管委会资源环境执法局进行业务指导。至此,建立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内“三级”综合执法体系,即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执法监督处——资源环境执法局——资源环境执法大队和森林公安局。另一方面,三江源国家公园执法监督处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8个保护分区内设立了16个森林公安派出所(直属),负责18个保护分区森林及野生动物、湿地资源的保护和执法工作[12]。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形成“二级”执法体系,即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执法监督处——三江源国家公园森林公安派出所。通过综合执法机构改革强化了纵向垂直合作综合执法。
总之,在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原则下,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大部制为导向进行了机构整合和职能重组,这在10个国家公园试点中走在了前列。由于辖区面积广大,通过“一园三区”管理格局的构建、县域综合治理改革、综合执法机构改革,从理顺管理体制和综合执法机构重组方面破除“九龙治水”难题,实行集中统一的保护管理和执法,在体制设计上解决了政出多门、职能交叉、职责分割的管理体制弊端,为实现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内自然资源资产、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两个统一行使”奠定了基础。
(三)部门协同:管理和执法机构间的竞合关系
随着机构改革尘埃落定,部门协同和职能融合成为重要问题,条块部门间的张力暗潮涌动。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采取中央政府直管、试点期青海省代管的垂直管理模式。垂直管理模式的设计是按照国家公园的总体布局,相关省市再依次设置相应级别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处),以减少地方政府对国家公园管理的干预,避免其承担过多的经济职能,实现以“保护为主”的功能定位[13]。随着央地关系和机构整合落地,自上而下的试点改革强行打破了原有的管理格局,新旧部门间的工作协同和职能融合成为试点中的关键问题。
1.上下对口难题:职责同构的困扰。
大部制改革只在县域层面发生,未能与州、省上级部门形成有效联动。为了履行“两统一”职责,在中央设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加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牌子),在青海省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加挂三江源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牌子)。在县域层面通过机构整合,成立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和资源环境执法局。至此,在中央、省、县域三个层次上实现了职责同构的“条”关系,构成了政策执行的“委托-代理”关系。但是,在政策操作层面,山水林田湖草的分类管理并未实现真正融合,由于具体执行机构同时接受管委会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而州一级和省一级并未进行相关的大部制改革,在案件的处置过程中,则出现了国家公园管理局没有权限、州和省一级政府不负责具体业务的情况,给管理和执法的操作层面带来了困境。比如当发生国土案件,园区管委会不负责执法,需园区资源环境执法局上报自治州国土局,再上报省国土厅,但是后者只对园区执法局有业务指导职能,没有垂直管理权限;如果园区资源环境执法局上报三江源国家公园执法监督处,但由于后者职能仅限于林业、野生动物执法等,那么也无法作出相应的决策。由此,上下对口出现了难题,职责同构困境带来了执法依据的真空,虽然整合了自然保护管理机构,但没有整合管理要素[14]。
2.左右横向冲突:从“九龙治水”到“二龙戏珠”。
在县域层面,面临着政府职能重组和权力分割的问题。在职权方面,还存在着园区管委会和地方政府职责不清、分工不明的情况。尽管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机构设置方案明确了园区管委会和地方政府的职责,但未厘清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和试点区地方政府的事权、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因此在工作中仍然存在纵向、横向衔接不畅的问题。特别是当原有的县域政府部门和园区管委会、园区管委会和国家公园管理局发生利益冲突时,部门间各自为政的情况拖累了改革的成效。在执法方面,同一个区域内存在两股执法力量,即资源环境执法局和国家公园森林公安派出所。在理论上,两者隶属于不同机构、职责分明,直属派出所对资源环境执法局进行业务指导。但实际中,资源环境执法局下设的森林公安局与三江源国家公园森林公安派出所之间存在着职能交叉,特别是涉及到生态保护监管方面的职权,面临着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问题。2020年11月6日,青海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成立,加挂青海省公安厅国家公园警察总队牌子,森林公安队伍整体转隶,隶属于不同部门的森林公安职能交叉问题得以缓解。但国家公园管理局执法监督处和森林警察总队间的职责划分,还需要在改革中不断厘清。打破“九龙治水”管理格局后形成的“二龙戏珠”新格局,仍需要加以追踪调研。
3.内外边界张力:县域和园区内外存在的张力。
在建设中,国家公园边界和功能区划依托于县域治理,但园区内外的政府职能很难被清晰切割。三江源国家公园辖区面积123100平方公里,涉及到12个乡镇53个行政村的16621户共计6.4万牧业人口,人口分布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实际生活中,园区内外的社区边界并不清晰,未划到国家公园辖区内的临近社区的生产生活乃至社会治理,仍然借助于国家公园内的行政和执法力量。如前所述,资源环境执法局同时受到地方政府和管委会的双重领导,以县域为界的国家公园管理范畴与自然保护区有重叠,因此即使一个地区未被列入国家公园辖区、但隶属于县域内,也需要园区内的执法力量保护。在实际调研中,如何划定执法边界,如何界定执法权限,也是基层执法部门面临的困境。为此,有学者提出地理依存的概念,国家公园范围内的社区和周边的社区的地理依存决定了经济依存,也决定了社区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国家公园内的自然资源[15]。因此,应从更宏观的视角去创新社区治理措施,加强区域合作协调机制,使国家公园外的社区成为共建国家公园的伙伴。
四、结论与讨论
在首批10个国家公园试点区中,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进行了先行先试的探索。在生态安全观的视域下,在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建设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遵循着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原则,从中央到地方厘清管理职责和权限,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加强融合协作。但整体来看,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的管理目标和管理机构职能还存在一定的偏差[14],特别是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执行层面各利益主体的分工协作、县乡层面综合执法机构力量的加强等事项。为进一步筑牢三江源生态安全屏障,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园建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一)厘清各级政府事权划分,加强“央地”协同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意图首先在于建立统一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中央政府强调战略指引、底线管控、局部聚焦,地方政府关注要素配置、增质提效、权益协调[16]。由于国家公园建设具有综合性、多部门的特点,因此还需要在央地事权划分和协同方面做文章。(1)在中央层面,建议成立国家公园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由中央有关领导担任,小组成员包括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中央编办、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门。高层议事协调机构有利于讨论研究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统一部署改革和发展工作。(2)在国家层面,国家公园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明确设在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管理局),既能够使国家层面管理机构实体化,更能提升国家林草局的统筹协调能力,加强各成员单位间的沟通联系,了解各方面工作进展和问题。同时,作为主管部门,国家林草局要继续深化理顺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职能,对内优化各司局职责,对外执行国家公园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决策部署。(3)在省级层面,因地制宜采取中央直管、地方自管、中央与地方共管等模式。自党的十九大以来,通过机构改革赋予省级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成为改革趋势。我国幅员辽阔,国家公园特点不同,需要中央向地方放权,采取更加灵活的管理体制。
(二)提升县域治理能力,夯实国家公园体制根基
在我国这个超大型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条”与“块”形成了“榫卯”结构[17]。在国家公园试点中可以发现,位于横纵治理网络的执行末端的是园区管委会及县域政府,整合后内设机构同时接受园区管委会和县委县政府的双重领导,除了国家公园事务外,他们还需要承担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等其他职能,而且由于国家公园地域广阔,其管理体制仍然依托于已有的县域治理力量。为此,一是树立本土化意识,夯实现有基层力量。三江源国家公园辖区平均海拔4000米,风景优美但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改革离不开现有的治理力量,特别是县域政府、乡村的治理力量和牧区人民的深度参与。要推动资源向县域下沉,积极调动属地政府和百姓的积极性。二是继续完善县域治理体系,进而提升治理能力。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立了5级管理体制,但到了县乡层面,管理要素的融合滞后于机构改革,加之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和原有的县域治理体系职责不清,因此在具体的操作层面还存在着机制运转不畅、工作目标不清、人员积极性不强等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提高。三是加强国家公园管理局、园区管委会和县域政府的横向协作。为了规避层层委托、一“垂”(垂直管理)了之,加强“一园三区”职能融合和共建共享、避免各自为政和职能冲突是未来工作的重点。
(三)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改革,扩展跨区合作
自2018年起,中办、国办先后印发《关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和《行业公安机关管理体制调整工作方案》,给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自然保护地的资源环境综合执法改革带来深远影响。(1)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改革,明确国家公园执法监督处和园区管委会下属资源环境执法局的职责权限。当跨县级以上行政区时,由属地相关执法部门多头执法,可能会因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影响执法效果,因此需要国家公园执法监督处履行相应职权。(2)加强园区内外跨区合作。国家公园内外和自然保护区内外并无明确的界限划分,要打破行政管理的边界,对国家公园体制引领下的自然保护地进行充分保护,打破因行政区划、资源分类造成的条块割裂局面。(3)逐步扩大国家公园管理范围。将周边同一生态系统具有同样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逐步纳入规划范围,如三江源源头格拉丹东、当曲、约古宗列3个保护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