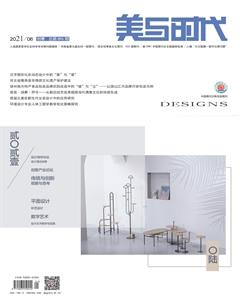感官·消费·符号

摘 要:当代偶像文化在历经多次嬗变后裹挟感官刺激、消费狂热以及符号生产等诸多文化症候以综艺选秀的形式再度“入侵”大众的眼与心。而将个体置于审美化生存语境之下考量,上述种种都暗自指向个体审美快感的生成。这种快感是当代偶像文化赋予个体的一种复杂的情感体验,已超越凝视偶像中的审美主体与客体,将快感拓展至更广域的社会文化层面。
关键词:偶像文化;综艺选秀;审美;快感
回溯大陆综艺选秀节目的发展轨迹,快感体验超越美感认知成为了偶像文化最为显著的审美转向。这种转变意味着对偶像深度的、持久的美感崇拜业已成为一种表层的、当下的快感体验;同时快感的无障碍化消弭了传统偶像文化中“神圣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界限,偶像的权威性因此被颠覆。于是,当代偶像文化对快感的建构超越了对偶像本体的推崇,偶像再一次成为了“傀儡”,其功能从意义生成嬗变为快感生成,这本身即一种“文化奇观”,而这对阐释当代偶像文化开辟了一条从“快感”进入的新路径。
一、“凝视”偶像中的感官快感
偶像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同“看”紧密缝合在了一起,早期人类在规定的场所“间离”地观看偶像,释放内心的崇拜与折服,克己以奉献自身,从而超越当下,借以此获得“净化”式的审美体验。这同传统美学始终受制于理性、伦理的约束密不可分,也即将美学包裹在一层伦理标准之中,同时被名为道德的锁链束缚;但如此也忽视了美学起源于感知,并深受感觉和知觉的双重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自20世纪以来,人们对于审美快感的讨论层出不穷,其本质在于将古希腊人认为的“感官快适”重新纳入美学的构建之中,重塑非理性要素诸如身体、欲望等对个体的价值。而其间生成的对快感革命性的认识,不仅令美学得以挣脱道德理性和宗教教义的抑制及束缚,也因此颠覆了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而这种颠覆毫无疑问首先体现在从“看”到“凝视”这一行为转变之中。
法国学者让-吕克·马里翁对观看和凝视进行了差异性分析,指出,“接受性为观看的主功能,也即主体处在纯粹被动地接受被观看者自身单方面释放给予物这一关系之中;而凝视则意味着主体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整体分析,因而主体对被给予物有着主动性的把控和构造”[1]。而玛格丽特·奥琳更是直截了当地将凝视定义为“视觉愉悦”,并且强调了“艺术理论的一个典型策略是将凝视澄清为像盯视一样的东西,一种被公众认可的偷窥行为”[2]。可见,“凝视”并非普通的“看”与“被看”,它不仅将焦点放置在被看他者的视觉性之上,且潜藏着对他者的控制、试探以及尋觅快感的行为,与权力和欲望紧密勾连。那么,这种观者身份的转变不仅意味着一种表层的审美化生存已然来临,更印证了“美学已转移到感知领域,并开始转向以感觉为核心的生产”[3],亦如伊格尔顿强调的那样,“快感已经彻底地重新返回”[4]。而当缺席已久的快感被允许重归的当下,一切坚固的壁垒都已然烟消云散,对偶像单纯的观看已经无法激起个体内心被压抑许久的快感,转而投身“交织欲望之凝视”亦是其终归之路。
也正因此,视觉形象的无限堆砌成为偶像文化在当下最重要的快感表征,而“身体”这个自古以来作为欲望客体的一贯选择首当其冲地“攻陷”了人们的视界。细数新近综艺选秀节目,对“身体美感”的打造可谓不遗余力。如在以打造女团偶像为目的的《青春有你2》《创造营2020》中,百余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女孩各具特色,镜头下的她们青春靓丽,精致到没有毛孔的皮肤、完美无瑕的妆容、无可挑剔的身材,再配合特殊“滤镜”的点缀,令其本身就成为了最具欲望表达的客体。虽然劳拉·穆尔维认为,“在一个由性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男性和被动/女性”[5]11,但需要厘清的是在“男色”“耽美”等文化概念流行的当下,这种主动与被动的身份已然被撬动并且可以相互转换。因此,在男团选秀《偶像练习生》《创造营2019》中,拥有俊朗外形、完美身材、唱跳功力俱佳的男性练习生同样“黏住”了大量粉丝的眼球。
于是,运用摄影技巧以及后期剪辑技术展现身体美感,令大众在视觉惊颤中获得感官快感的竞演舞台成了新近选秀节目比赛环节的不二之选。这是缘于竞演舞台不同于普通的表演舞台,残酷的淘汰制令所有怀抱梦想的练习生必须展现出超越常人的舞台魅力,而高难度的舞蹈动作通常被视作是最直接且常用的表现形式,令选秀节目得以通过对练习生手部、脚部、腰身特写以及全身中景,将身体所具有的柔、韧、力道等多重美感展现出来。同时,竞演舞台四周环绕的数十架摄像机全方位地跟踪拍摄,以及镜头移动侧拍、高空俯拍等多变的调度,为舞台上每一位练习生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solo”舞台。诚然,这种分镜头割裂了表演的整体性,却令视觉快感在被聚焦的练习生身上得以无限滋长。而选秀竞演舞台最后的成片往往并非按照表演中时间的线性顺序,这意味着选秀节目得以利用视觉节奏剪辑控制竞演舞台上的感官快感,于是画面的停顿、慢放、重放等剪辑设计,将镜头下练习生的身体以及动作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视觉维度呈现。如《青春有你2》中赵小棠在舞台《十面埋伏》中令人惊艳的前空翻入场,通过多次镜头的慢放、回放,不仅增加了其身体的滞空时间,且在缓慢落下的身体中,个体在此刻获得的快感被巧妙地增值了。
细数上述诸多技术手段其本质都是经由银幕将“身体美感”无限扩大,从而给在屏幕前凝视偶像的个体更为强烈且刺激的感官快感体验。而正如罗兰·巴特将身体置于阅读视角解读出“文本字里行间埋藏的不是意义,而是快感,阅读不再是人和人之间的精神交流,而是身体和身体之间的色情游戏”[6],那么,对偶像身体的凝视亦非是单纯视觉上的交流,更是从身体到身体的快感游戏,在这种被欲望包裹的嬉戏间,身体成了欲望凭依的客体,“美感”沦为了“快感”获取的工具,纯粹感官式的享乐取代了精神上的愉悦;且当这种直接的、无障碍的身体快感获得到达顶峰,欲望无止境的本能无疑会将潜藏在个体心底被“自我”压制的“窥视癖”激发。弗洛伊德以儿童的窥视活动为例,指出他们对隐私以及被禁止观看的事物有着极其特殊的看的欲望,且展现出强大的好奇心以及求知欲。虽然跟随年龄的增长,此类本能会因为“自我”的觉醒而被逐渐抑制甚至修正,但依旧会将禁忌之物作为看的对象从而获得快感。这意味着“窥视”处在隐藏/揭秘的二元对立之中,因而能够激起个体窥视快感的事物总处在不可得见的暗处,是有着强烈排他性的秘密。
但以诉求“快感”为核心的当代偶像文化自然不会轻易舍弃能生成个体快感的任何事物。在视觉文化大行其道的当下,影像缔造者们乐于将“非视觉化”的事物加以“视觉化”以满足人们那从未被满足的欲望;但在这里,“非视觉化”不仅仅包含了无法视觉化的事物,更是意味着被伦理道德约束而不能展现的事物——个體隐私。也正因此,选秀节目又为观众无处安放的“窥视欲”寻觅到了一个完美出口——偶像的私密生活及其隐私。回溯新近综艺选秀,除却在竞演舞台展示偶像身体美感之外,还将更多的摄像机对准了偶像“隐秘”的生活。正如劳拉·穆尔维所言:“主流电影以及它有意识地形成的规则,精致地刻画了一个密封的世界,它无视观众存在,魔术般地展现出来,为观者创造一种隔绝感,并激发他们的窥视幻想。”[5]9虽然其论述所指的是电影艺术,但当代综艺节目已经明显呈现出此种叙事规则。
最新的选秀节目,无一例外地特意将练习生置于远离城市的城堡,这种看似“与世隔绝”的环境,不仅生成了一种奇特的私密空间,更是将城堡本身打造成凝缩偶像隐私的场所。在这里,“窥视欲”的对象看似被密闭的城堡所遮挡,保持着严密的排他性以及神秘感,但这只是制作者的一种巧妙策略——看似不可窥探的隐私被其间构筑的无所不在的摄像机所记录,城堡并没有阻挡个体“窥视欲”的步伐,而是为其打造了一个全方位凝视的最佳场所。那么,跟随城堡中数百台不停歇记录的摄像机,练习生们的隐私生活变得清晰可见,包括日常起居、训练舞台、闲暇时光甚至是练习生之间的八卦趣闻,这些私人隐私恰恰是道德伦理之上个体不可触及之“私域”。但在这里,一切都按照欲望的要求被精心裁剪,摄像机取代了人类眼球,“窥视欲”的负罪感也被镜头所遮蔽,使得凝视主体得以挣脱“自我”的约束在其间肆无忌惮地获得那种无法轻易享有的窥视快感。
正如前文所述,美源于感知,而感知则有知觉和感觉的双重含义,“作为‘知觉,‘感知指的是对诸如颜色、声音、味道和气味等真正的感官属性,为‘认识服务;然而,用作‘感觉意义时,它指的是情感走向,以‘愉快和‘不快作为评价尺度”[7]67-68。而上述“身体快感”“窥视快感”都隶属于感官属性,过度依赖个体的感觉评价,且只用于满足其基本生理需求。这样,当代偶像文化很容易成为学者批判的对象,称其“仅仅强调了初级过程的沉浸式和非反思性的身体美学,仅仅满足了个体的视觉欲望以及身体的快感需求,但缺乏能够穿越视觉,直达人内心的精神力量,也就无法引起主体心灵的震荡并由此感到一种精神的满足和喜悦以至最终实现自我境界的升华”[8]。但当代偶像文化的缔造者们早已熟知自身的“弱点”并将偶像文化同消费文化紧密结合,激活了偶像文化本身早已蕴含的“宗教狂热”,巧妙地以“宗教超越”替代了“审美超越”,并借势生成了另一种快感——消费快感。
二、“宗教超越”下的消费快感
美学家韦尔施指出:“作为‘人类,升华的需要是我们本质性和决定性的需要,对人类而言,它是一种明显的对‘高尚的需要。”[7]71而将韦尔施所称之“升华”置于审美语境下考量,也即是审美活动的终极境界——审美超越。它是个体掌握生命自由和境界的一种方式,超越了当下所有的物质欲望与世俗生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意识活动,其最终指向的是个体内心世界以及精神境界的无限自由性。这就意味着个体的审美对象,并非是仅仅满足当下的、物质的、欲望的需求,而是通过自由地展示人的本质——超越性,获得直达精神的自由感与满足感,并通过审美对象印证个体心灵的自由。
诚然,审美的超越性对于个体生存实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超越性并非审美所独有的精神活动,“科学(认识)活动、哲学活动和宗教活动等也都具有超越性”[9],这些都是个体实践用以掌握世界的不同方式,他们同审美超越的区别主要在于超越的对象、方式、结果方面。而其中作为有着强烈情感性的“宗教超越”同“审美超越”有着本质的一致——即它们都是个体纯粹精神意识的活动,是个体心灵释放出来的富有想象力的直觉洞悉。那么,宗教超越在某种程度上和审美超越有着相同的功用与意义,即借由宗教超越净化个体心灵,直抵人类精神世界,从而实现自我境界之升华。
依据前文论证,可以窥见的是当代偶像文化对“感官快适”的疯狂推崇以及对物质欲望无止境的满足,终会令这种审美活动坠入一种低级的、肤浅的“身体”美学,而其间充盈的感官快感也注定令个体与其精神世界“绝缘”,必然导致当代偶像文化在感官刺激退潮的时刻被自身反噬,从而被另一种“快感文化”替代。但偶像文化能够在当下社会“肆意生长”的原因正是以一种“宗教超越”替代了“审美超越”,缝合了部分被自身割裂的感官世界与精神世界。而这种巧妙的替换也有其内在根源可以追溯,当提及偶像,人们最先联想到的可能是宗教与巫术,这同远古时期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恐惧而希望将某种神话想象“完形”有着密切的关联,可见偶像文化与宗教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蒂利希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在实质上是宗教,宗教在表现形式上则为文化。”[10]因而当代偶像文化也逐渐显现出一种“宗教狂热”似的文化症候,如宗教式虔诚崇拜、收藏与供奉偶像的衍生物、牺牲自我与奉献、仪式性表达等,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超越感官快感而在精神以及信仰层面上的满足与喜悦。但不能忽视的是,在后现代社会中,被科技文明“祛魅”的宗教文化早已丢失了其高高在上的精神“韵味”;而当代偶像文化却敏锐地捕捉到这种“上帝缺位”后个体精神世界空白的时代文化症候,以宗教超越之精神升华为“诱饵”,将个体精神世界碎片化以镶嵌到偶像文化的各个环节,同时借助宗教神话着眼人们的欲望,将这种宗教超越同生产与消费偶像的快感游戏接轨。
依洛文塔尔所言,当下的偶像文化已经由曾经的“生产偶像”转换为了“消费偶像”,那些曾经被崇拜的偶像在如今已经被深刻地“商品化”了,其合理性建立在“消费社会”这一突出的时代文化症候之中;而在选秀节目中,消费偶像不仅意味着生产偶像,更是获得快感的一种手段。这是由于新近选秀节目借助宗教超越“设置救度者”“奉献自身”“逆功利”的独特性质,为大众提供了一条充满世俗化、商品化、快感化的朝圣之路。细数新近选秀节目,当练习生还未能获得成团名额之时,它们被节目打造成需要“救度”的偶像,是“不可见”的偶像;此时的粉丝处在救度者的位置,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像宗教信徒一般尽可能地奉献自身,去救度自己的偶像,而“救度”的规则即——投票,尽管投票被当下众多选秀节目美化为“pick”“撑腰”“打call”“助力”等诸多“去消费化”的元气式口号,但其本质上仍旧是一种消费。以新近选秀节目《青春有你2》中的投票机制为例,最基本的方式为登录官方视频App软件投票,普通用户每天可以给心仪的练习生助力一次,而VIP用户则每天可以助力两次,同时亦可以通过其他合作平台如QQ音乐进行额外助力;但上述投票模式根本难以达到新近选秀节目动辄千万的投票结果。因而,宗教超越的“逆功利性”又成为一种精神指引,它被偶像文化借用以号召虔诚的粉丝舍弃个人的物质欲,去让渡自身价值尽可能多的投票令练习生成团——成为“可见的”偶像。因而,选秀节目的制作者“光明正大”地在品牌赞助商的产品之中附赠了不加限制的投票权,如被粉丝们戏称的“奶票”①,就是新近网络选秀节目常用的投票方式之一,而此种通过消费行为获得额外投票权力的方式才是缔造选秀节目令人咋舌数据背后的真正秘密。
于是,每当选秀节目的成团之夜,当粉丝心仪的偶像走向了属于自己的花路,终于成了“可见的偶像”,台下穿着应援色服装、举着应援标语的粉丝跟偶像一样热泪盈眶。此时的偶像以一种权威的、理想的、完美的模样出现,令粉丝个体意识开始呈现一种丧失的状态,使其主动与現实世界隔绝,退化到拉康所称之的“镜像阶段”——一种同幼儿在“镜像”中获取身份认同所类似的虚幻之境,令粉丝在舞台上的完美偶像那里,重塑了在成长之路上破碎的自我认同,且为其提供了一种“自我迷恋”的快感。在此种状态下,个体在精神层面直接感受到了非理性的宗教超越,暂时获得了现实世界未能满足的各种情感体验与精神满足,消解了其现实中的痛苦以升华为某种持续的快乐。
但在这里,“被救度者”成了一种可以参与生产和消费的物,“奉献自身”亦被“消费他者”悄无声息地替代了,奉献越多精神越富足的超越之路最终滑向了消费越多快乐越多的世俗之路。可见,身处偶像文化场域之中的个体,其“精神超越”的实现已经必须依赖投票这种购买与支付的消费行为,而粉丝投票这种消费行为并不意味着纯粹的物质交换,也并非为了获得消费后应得的使用价值,而是在本质上动摇了生产社会商品使用的单纯释义,构筑了全新的意义,激活了粉丝的欲望与联想,“使其面对无数梦幻般的、向人们诉说着欲望的,使现实审美幻觉化和非现实化的影像”[11]。在这里,“我消费故我存在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进阶转换成了“我消费故我偶像存在”快感主义意识形态。正如菲斯克强调的那样:“大众文化经济中,流通过程并非货币的周转,而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12]98也正因此,偶像文化中的“精神场”破裂进入了“消费场”,“‘真实消费很大程度上是这种‘精神享乐主义的产物”[13]。于是,消费主动将其低级物质交换的属性剔除,借助这条世俗化、商品化、快感化的朝圣之路,主动跃升至精神层面,将被社会批判的消费快感嬗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愉悦。
那么,当我们以审慎的态度去分析当代偶像文化所缔造的此种“宗教超越”时可以发现,此种精神世界的抵达并不是当代偶像文化所寻求的终极超越,而潜藏在这精神世界里的消费快感才是其最终目的。这种精神与信仰世界里的满足与喜悦,仅仅是给那些狂热的粉丝以片刻的宁静与喘息,从而令其一次又一次投入到此种“精神超越”的旅程以获得那种消费快感。可以窥见,偶像文化的快感之所以存在,是因体验到快乐与兴奋的大众自身生产出来的,而不是如其他快乐体验是从外部所赋予的。也正因此,不可否认的是大众都往往乐于参与到当代偶像文化的生产中来。但在媒介化生存的时代,大众的“能动性也不再仅限于以消费的方式进入偶像工业秩序,以此获得部分生产者的权力,创造性的文本生产成为一种新鲜的参与偶像工业的方式”[14]。正如菲斯克所言:“大众文化的创造力与其说在于商品的生产,不如说在于对工业商品的生产性使用。”[12]34于是,在当下这个“拟真”时代里,这种对于偶像的生产性使用,终将分裂直至抹去偶像的“能指”与“所指”,偶像被大众解构成了一个又一个带着快感的符号。
三、“偶像已死”后的符号快感
罗兰·巴特在《从作品到文本》中以受众主动性解读这一变化为肇始,将“作品”与“文本”进行区分,指出,作品止于所指,文本则为延迟,即“从视文学作品为具有确定意义的封闭实体……转向视它们为不可还原的复合物和一个永远不能被最终固定到单一的中心、本质或意义上去的永恒能指游戏”[15],而将对“作品”的研究转向了对“文本”的解读。在此意义之上,巴特所宣称的“作者已死”实则是表达作者同文本关系的断裂,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无法回到文本,而是在其文本中,作者亦同他者一样如宾客,不能对他们的文本拥有唯一的解释权,由此,文本便得以跨入无限衍义的场域,逃离作者主体单方面的控制。因而,巴特在上世纪所提出的这一隐喻,实则是向世人宣示传统意义上被建构出的自我主体性的消亡。那么,正如作者一样,往昔高高在上的偶像在当下的语境中是否依然保持着完好无损的主体性、是否依然可以单方面宣示对其自身拥有着独一无二的解释权,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诚然,当代偶像文化业已被系统化、体制化的商业模式宰制,一套完整的偶像文化产业体系垄断着偶像的生产,但后现代语境下文化艺术生产方式的嬗变赋予了大众对于偶像这一文化艺术商品进行生产性使用的机会。在工业革命以前,文化艺术生产依赖着手工的“仿造”,它用再现这一手法去还原“美”这一理念;而行至工业时代,本雅明清晰地指出机械复制生产取代了手工制作成了文化艺术生产的主要模式,力量与技术理性将文艺“祛魅”从而进入千家万户;而时至今日,“仿真”大行其道,它是后现代“受代码支配阶段”的主要模式;借助计算机解码编码,文化艺术生产通过数字技术就可轻易完成,“但它们本身难以辨识,因此无法识别”[16]57,因为“其一旦被编码,就再也无法追溯其本真——一种与仿造抑或复制品相反的现实模型”[17],无所不在的艺术生产仅仅只是拟像,是编码与解码的拟真游戏。因此,文化艺术生产完成了从物的再现到商品堆砌,再到景观膨胀,终至符号无尽生产的嬗变。
也正因此,大众得以运用数字技术对偶像重新编码将其符号化,并在体制的裂痕中创造出属于个体的符号元素去抗击霸权力量的宰制,颠覆权力所强加于偶像的单一意蕴;而大众的快感也恰恰就是“出现在被宰制的大众所形成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中,这快感是自下而上的,因而一定存在于与权力社会的、道德的、文本的、美学的权力相对抗之处,并抵制着企图规训并控制这些快感的那一权力”[12]20。如《创造101》中王菊和杨超越作为同当下所谓的“审美标准”与“艺术标准”格格不入的练习生却在此节目中收获了大量的粉丝与关注度;同样,《青春有你2》因性格原因实力“圈粉”的虞书欣甚至在收获大量关注之时并未参加任何既定程式化的竞演舞台。诚然,这种现象在新近综艺节目中的频频上演令固有的对于偶像的传统认知逐步瓦解,但却构筑了一个不确定并具有无限开放性可能的空间,“使人对于艺术‘好‘坏的评价与‘高‘低截然分开,而‘高‘低之中暗藏的恰恰是阶级偏见”[18]。因而,当代偶像文化所缔造出的偶像一旦进入社会传播领域,大众就能以“盗猎者”②的身份出现,自下而上地对偶像重新进行一系列的“戏仿”以及“某种类型的文化拼贴,并在已有的材料中抢救出能用来理解个人生活的只言片语”[19],从而在这种编码解码的游戏中建构出属于自己的快感。
舞台上“唱跳俱不佳”的杨超越因实力不足被人诟病,但仍旧未能影响她曾经的巨大话题量及热度,她的粉丝毫不介意她唱跳能力是否出众,而是利用一切手段将其营造成代表幸运的“锦鲤”,一时间转发由杨超越和锦鲤形象拼贴而成的祈愿图片成了网络空间最热门的“符号生产”,彼时的杨超越业已幻化成表征幸运的符号,充斥在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空间之中。同样,《青春有你2》中虞书欣不经意间“哇哦”一声赞叹,无意间同老牌电影公司米高梅开头动画形成了巧妙的互文,又经过粉丝对其视频截图精心的拼贴制作,让“小作精”虞书欣成了当下最流行的表情包在社交软件上大行其道,用可爱替代了严肃,将意义剥离了偶像。而这种被精心打造出来的文化符号“拼贴”,交织着持续与断裂、高级与低级的混杂,它们并非为了刻意的模仿,而是在这种看似陈词滥调的拼贴中,以快感为诉求用符号生产不断丰富着偶像的现在,亦如哈尔·福斯特所言:“它们将一切剥离,只留下象征,以半幻想的形式无限生产。”[20]正因此,诸多唱跳实力并不出众的练习生,却因为被粉丝通过文化挪用、意义拼贴所产生的快感以及价值认同而被接受。
如果说上述现象是基于偶像粉丝有意地拼贴制作,那《青春有你2》中李熙凝与秦牛正威在网络中所引发的狂欢,完全是作為“盗猎者”的大众彻底将她们从令人窒息与绝望的“萤幕”中解放了出来,因此后续一系列的模仿、拼贴与戏仿便流溢出熵的含义,化作一种符号、一种媒介,用一种全新的聚合规则打开了出其不意的意义与效果。节目中并不擅长rap(说唱)的练习生李熙凝和秦牛正威被迫进入了rap组,在导师多次指导后唱起rap依然像诗歌朗诵,被网友戏称为“reader”;而这两种艺术方式在同一人身上所产生的巨大落差,造成一种紧张期待的落空,瞬间点燃了大众的再创作热情。虽然她们最终被淘汰离开了舞台,但网络中如“‘reader的自我修养”“如何做一名合格的‘reader”“跟着李老师与秦老师学朗诵”等人造性且无深度的恶搞、鬼畜视频层出不穷。可大众喜爱的并不是作为偶像的她们,只是充分利用了其风格的独特之处,牢牢地抓住了她们的某些奇妙之点,将其视作一个获取快感的符号,制作出了诸多嘲笑本体的戏仿。因而除了真正了解其本人的粉丝,大多数深陷此种快感释放的人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日夜沉溺的“梗”中,主角究竟是何人,但这也令两位练习生幻化成符号与光标,向世人诉说着这一时期偶像文化的快感取向。
于是,作为“盗猎者”寄身于偶像文化场域里的大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宣泄着快感的形象,但这些形象仅仅是一个关于偶像的符号,“好似是虚假且拙劣的模仿,玩笑似地颂扬自身对于假名的借用,炫耀着自身的表面化和派生性”[21],那么这种偶像被符号化的当下,“当本真与拟像在同一运行整体中杂糅混淆之时,美学的魅力无处不在,一种无目的的戏仿盘旋于一切之上,它是技术性的模仿,有着无法定义的名声,且带着一种美学快感,即阅读快感和游戏规则的快感;流行符号、模式符号、媒体符号在幻象盲目的幻境中穿梭不息”[16]75。因此,偶像无处不在,因为符号亦是其现实的核心;而偶像又是“死亡”的,因为偶像本身已完全被一种与自身结构不可分离的美学浸染,它早已同其“拟像”混为一体,无法寻找其本真。
可以窥见,当代偶像文化中对偶像的诸多生产性实践最终指向的是否认偶像主体作为唯一意义来源具有的首要能力,偶像的单纯性与不可侵犯性终究让位于混杂的互文性,在大众乐此不疲的模仿、拼贴、戏仿中,被青睐的是符号的生产与快感的增值,而非对偶像单一意蕴的解构。在此逻辑之下,偶像可以经过一系列的编码解码,而快感化作符号轻而易举地就跨过私域投身公域,成为偶像文化同整个社会的连接器,至此,快感彻底被符号化了。也正因此,快感不在偶像那里而在符号那里,对符号的占有成了偶像文化里快感的源泉,而当下偶像文化恰恰就是在这种“超真实”的世界中完成了快感的构建与传播。
四、结语
毫无疑问,当下的人们置身于一个漂浮能指的时代,词语不再同事物恰当地附着,偶像也脱离“庙宇”任人把玩,没有任何的高级胶水将往昔的神圣传统同当下粘合。它们为个体打造出一个充满着欲望、消费与符号的快感世界,却只教会人们如何享受。而偶像主体死亡的最新哲学和符号的随意性,终究会令身处其中的个体被缄默的不在场所困扰、被意义和连贯性的丧失所困扰,被荒诞和虚妄的感觉所困扰。但这种“真实”的消亡,却令偶像幻化成为符号在文化空间中无限延展,不再具有唯一的意义。那么,倘若造就一个开放的循环,将符号化的偶像再次同凝视相连,接下来,我们所凝视的偶像究竟是何,而其间生成的诸多情感体验是将我们引向超越还是领进虚无,亦是一个更值得探究与思索的问题。
注释:
①蒙牛乳业冠名了《青春有你》《创造营》系列多档选秀节目。从2020年的《青春有你2》开始,蒙牛在自家酸奶商品中赠送可以给练习生额外投票的卡片,一张卡片可拥有数量不等的额外投票次数,正因其是购买酸奶赠送而被粉丝称为“奶票”。
②“盗猎者”是亨利·詹金斯从米歇尔·德塞都那里借用来的对于粉丝的称谓。他增补了德塞都“盗猎”理论,指出,粉丝并不是大众文化产品的原始宿主,而是充满易变性、不定性乃至矛盾性的大众文化洪流中的“盗猎者”。因此,文化挪用和意义解读成为“盗猎者”的最显著特征。但是在艺术符码化的当下,以快感为诉求的“盗猎”行为早已从粉丝拓展至更广泛的大众。
参考文献:
[1]Jean-Luc Marion.?tant donné[M].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13:351.
[2]奥琳.“凝视”通论[J].曾胜,译.新美术,2006(2):59-67.
[3]詹姆逊.文化转向[M].胡亚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1.
[4]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M].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53.
[5]Mulvey Laura.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J].Narnia,1975(3).
[6]汪民安,陈永国.身体转向[J].外国文学,2004(1):36-44.
[7]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8]梅琼林.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审美化生存[J].文艺研究,2008(8):13-20.
[9]朱立元,刘阳.论审美超越[J].文藝研究,2007(4):4-14,174.
[10]蒂利希.文化神学[M].陈新权,王平,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8.
[11]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98.
[12]菲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13]费瑟斯通.消解文化[M].杨渝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3.
[14]江怡.粉丝文化参与偶像工业的新可能——以《创造101》中的“文本盗猎”事件为例[J].艺术广角,2020(1):47-53.
[15]巴特.从作品到文本[J].杨扬,译.文艺理论研究,1988(5):86-89.
[16]Jean Baudrillard.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3.
[17]Tim Dant.Critical Social Theory:Culture,Society and Critique [M].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4:126.
[18]Leslie Fiedler.A New Fiedler Reader[M].New York:Prometheus Books,1999:287.
[19]詹金斯.文本盗猎者[M].郑熙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4.
[20]Hal Foster.Recodings:Art,Spectacle,Cultural Politics[M].Washington D.C.:Bay,1985:121.
[21]Richard Kearney.The Wake of Imagination[M].London:Routledge,1988:4.
作者简介:杨阳,硕士,河南省文学院研究实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