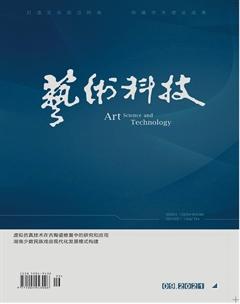唐代服饰审美及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和意义
袁雨航 胡琨鹏 马晓倩
摘要:唐代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其繁荣的经济条件、和谐的社会文化、自由的社会风气为唐代服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代服饰中展现出来的雍容大度、百美竞争的服装特点和独特的审美特征也成为文学作品中不可忽略的重点。本文通过对唐代服饰包容和谐、华贵精巧等审美内涵的梳理,进一步挖掘服饰写作在文学创作中的丰富人物形象、突出作品主旨、彰显自我形象的作用,希望能给予当代文学创作一定启发与思索。
关键词:唐代服饰;服饰审美;文学作用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9-00-02
《鉴略·三皇纪》记载:“有巢氏以出,袭叶为衣裳。”中国服饰的历史源远流长,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变。古代华夏民族有着无与伦比的服章之美,这是中华大地上人民灵魂的凝聚。一个人的肉体或许一生漂泊不定,但灵魂却扎根在一个固定的地方[1]。衣冠之于华夏,便是灵魂的具现化,象征着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而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其服饰文化灿若繁星,其中女性服饰的表现尤为突出,其样式繁多、风格开放、色彩艳丽大胆,将唐代的服饰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唐代服饰中体现出的对美的追求和独立的审美风格对唐代文学的发展也有着重大的启迪作用。
1 唐代服饰的样式
研究文本不能脱离时代[2],研究服饰特征也是如此。唐代的服饰总体表现为华丽富贵、媚态百生的风格。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文化的空前繁盛、对外兼收并蓄的态度,都为唐代服饰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武德令”是唐高祖颁布的关于服饰的律令,其中规定了唐代男子最常见的官服形式是圆领窄袖的上衣,腰系缀有玉方、金花的红鞓带,足蹬乌皮六合鞋。
唐代的时代特征使得男子无所畏惧,敢于尽情发挥审美想象[3],而在男权思维定势下,女性是按照男性的需要被造就出来的[4],为了迎合男性的审美需求,唐代女子服饰也因此更具艺术性。儒家文化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和经济,对各个方面都有着潜在的影响[5],唐代妇女衣着大胆,也得益于儒家文化对女性的束缚减弱。
唐代女装种类丰富,其中最经典的便是襦裙。襦裙本始于汉代,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裙腰愈高,上衣愈短,衣袖愈窄的特征。文学家总是在生活中寻找灵感[6],唐代很多文人都将襦裙写进了诗篇,如白居易诗中有云“平头鞋履窄衣裳”,描绘出女子着窄上衣的情形;《汉乐府·陌上桑》中“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则描绘了女子着鲜艳襦裙的形态。而到中唐后,社会审美更倾向于丰腴的女子,同时华夷意识日益加强,导致开始近乎病态地流行起了大袖纱罗衫。元稹在《寄乐天书》中谈到,“近世妇人,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巨怪艳”。而与大袖相配的是奢靡头饰,杜甫有诗《丽人行》云:“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盍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然而,符合当代人审美观念的未必就是正确的观念[7],这种奢华夸张的风气后来被明令限制。此外帔帛和衤盍裆也是女性的重要服饰,唐人诗词“粉胸半掩疑暗雪”“雪胸鸾镜里”便是对这种袒露服饰的切实描写。
女性穿着男装也是唐代的一种常见现象。《文献通考·四裔考》讲到“妇人亦脑后摄髻,无笈梳,其服与拜揖与男子同”,《中华古今注》中“至天宝三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这些作品都描述了盛唐时期女子纷纷穿上男子衣帽的情状,后来许多仆妾也纷纷效仿起来。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女性主义思潮,不可避免地顺应时代发展的脚步[8],在此时绽放出了一束光。
2 审美内涵
美是反思的,审美具有批判性[9]。艺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状况,服饰则是记录人们生活情状的特殊艺术。唐代的服饰文化体现出了和谐包容、华贵精巧的特征。
2.1 和谐包容
在封建时期,人们有着非常强烈的“华夷观”和“男女有别”的思想,但唐代开放的外交环境及繁荣的文化使得唐代服饰呈现包容多元的特征。唐代的常服属于胡服系统。所谓胡服,是指包含很多非本民族的他民族因素的装束。《车服志》云:“中宗后有衣男子而靴如奚,契丹之服。”这里的“奚”,就是匈奴的一个别支[10]。元稹《法曲》则写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这些作品都描述了唐代胡服、胡妆、胡乐盛行的情形,唐代对胡服及别国服饰文化的接受与吸收,体现了美美与共的包容心理。
在父权制社会,女性被禁锢在依附的地位[11],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然提高,但是男权礼教还是悄然影响着社会思想[12]。“男女不通衣服”是《礼记》中不可违反的铁则,但唐代出現“女扮男装”的情况体现了唐代独有的宽容开放的审美心态,成了服饰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闪光点。
除了胡服的广泛流传、男扮女装的盛行,上文提到的袒胸露臂的穿着方式也是体现唐代多元包容文化不可忽视的一大要点。著名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妇女的穿着便是典型,图中女子头饰艳丽花朵,身穿宽袖对襟纱罗衫,此衫通透丝薄,肌肤、胸脯若隐若现,有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无言美感。如此袒露,如此奔放自然,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少见的现象,正因为唐代如此包容的社会环境,唐代文化才能自由发展,多元的服饰才能如雨后春笋般浮现。
2.2 华贵精巧
唐代服饰的华贵精巧主要体现在唐代服饰的面料及花纹图案上。服饰的表现离不开面料这一载体,唐代非常重视衣冠服饰,并且有着发达的纺织手工业体系,制衣所用的面料有丝绸、纱、棉布、麻毛等。服饰代表着一个人的品位、身份、性格等[13],服饰的材质可以体现出阶级地位。一般来说,唐代社会中上层人民大多穿着经多种工艺处理过的丝绸。比如宫锦,《旧唐书》曾描写李白“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再如彩绫,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缭绫》有云“缭绫织成费功绩”,描绘的就是制作精巧的彩绫;还有刺绣,温庭筠词“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中提及的便是这种布料。
在服饰图案的设计上,唐代服饰改变了以往“君赋神权”的创作思想,更多地采用真实的花鸟鱼虫进行创作。唐代流行的纹样造型饱满、构图对称、色彩艳丽,有狩猎纹印、连珠鹿纹、花树对鹿纹等等。同时,由于唐代开放的对外交流,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唐卷草纹、宝相花纹、联珠纹也比较常见。
唐代人们服饰的面料、图案、色彩的丰富性,表现出了当时人们热情、敢于求美的时代风貌。他们将各种要素的审美效果与价值巧妙结合,形成了色彩对比鲜明、图案均衡稳当的华贵和谐之美。
3 服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
“能工巧匠塑造楼台亭阁,诗人却赋予他们传唱千古的诗情。”[14]服饰是一个人品位内涵、道德修养乃至个人境遇等的外在体现,而在作品中,作者的服饰描写对文章立意、形象塑造等方面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1 着装描写丰满人物形象
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中描写舞者:“案前舞者颜如玉,不著人间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纍纍佩珊珊。娉婷似不任罗绮,顾听乐悬行复止。”对于舞者的美,作者既没有浓墨重彩地描绘舞蹈的优雅,也没有直接描写女子的长相,而是通过对“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等服饰、配妆的描写衬托渲染,塑造了一位婀娜多姿、容颜不俗的美人形象。
而花间派词人温飞卿以服饰描写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也堪称一绝。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中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阅读该词作,我们不难从服饰和妆容中看出这位女子的娇俏艳丽,她有着雪白的脸颊,有着雪中青云般乌黑浓密的秀发,有着蛾须般弯曲细长的眉毛,有着如花似玉的可爱面容。在对该女子的身份与心境进行表现时,温公便展示出了他的高明之处。他通过写崭新绫罗短衣上贴绣的成双成对的金鹧鸪图案,巧妙地抒发了女子形单影只、相思成苦的闺怨愁思,细腻而蕴藉。又如,《新添声杨柳枝词》中的“一尺深红蒙曲尘,天生旧物不如新”中,“一尺深红”便是指女子出嫁时方幅红绸的盖头,温公巧借这一重要的装饰蒙尘暗淡塑造出一个幽怨的女子形象,表达出了女子被冷落的怨恨,对旧时幸福的怀念,对新人换旧人的不甘与嗟叹,睹物思人,不由感慨万端。
3.2 服饰凸显创作意图
刘禹锡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紫陌”明指京城长安的道路,实则暗指朝中新贵。唐太宗贞观四年定百官朝服颜色,三品以上服紫,以至于“每朝会,朱紫满庭”。在古时,紫色是权贵的象征[15],而诗中作者借“紫陌”表达了内心的不满。这首诗表面上写众人观桃花之景,实质上却具有暗讽趋炎附势的权贵高官之意,这些攀高结贵之人为权力奔走的样子正如在紫陌红尘中看桃花的人们一样。
白居易“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的“青衫”同样是“品色衣”的体现。唐太宗贞观年间,朝廷对官服颜色有硬性规定,三品及以上的官员着紫色衣服,五品及以下的官员着绯色衣服,六品、七品的官员服绿色,八品、九品的官员则着青衫。此时白居易连续被贬,官阶一降再降,是品级最低的文散将仕郎,故只能穿青衫。“青衫”也因此成了白居易作品中最意难平的存在。“惆怅青袍袖,芸香无半残”是白居易与李少府酬和之作,表现了他初入仕途的志向满满与被贬事实的巨大落差为之带来的苦闷之情;“蹇步垂朱绶,华缨映白须”则是他醉游候仙亭时所作,描写了自己年老体衰的情形,表现他仕途不顺只得浸心山水的无奈。
3.3 服饰与自我意识的投射
不同于想象奇妙、极具浪漫主义的李白,也不同于写尽人间疾苦、心系人民苍生、极具现实主义的杜甫,白居易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关注自我的中庸现实精神,这也使得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丰富可感的服饰描写,透射出了其真实的形象。在他的作品中,有身着官服的士人形象,如“薜衣换簪组,藜杖代车马”“解佩收朝带,抽簪换野巾”等;有身着野服的隐者形象,其中白居易尤爱白色衣物,与之有关的描写有“先生乌几舄,居士白衣裳”“乌帽青毡白氎裘”等;还有身着常服的本真自我形象,多为旷然自达的不羁形象,如“当时遗形骸,竟日忘冠带”“脱袜闲濯足,解巾快搔头”等。无论是官服、野服还是常服,这些都是白居易本人最真实、最可感的一个个侧面,这些不同的投影也体现了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后诗人在身份认知上的迷茫与苦恼。
4 结语
艺术恒久,服饰作为艺术的具象化形式之一,有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若晨星般璀璨的光芒。通过欣赏唐代服饰,欣赏服饰带给文学的不绝动力,不仅可以领悟到这些美好事物蕴藏着的内涵,也可以另辟蹊径,从服饰美、妆容美的角度欣赏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精髓。我们要继承和发展这些优秀的文化,在思索和启迪中让现代文学发光发亮。
参考文献:
[1] 焦健,宗昊,张天娇,等.论刘亮程散文中的故乡意象[J].安徽文学,2018(12):43-44.
[2] 刘微.唐传奇《李娃传》中李娃形象探析[J].大众文艺,2019(11):60-61.
[3] 侯婷.服饰变迁下现代女性审美观念探究[J].大众文艺,2019(08):218.
[4] 赵阳.美国电影《毒液》中女性边缘化塑造及文化反思[J].戏剧之家,2019(36):66-67.
[5] 浅析古装剧中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以《知否知否绿肥红瘦》为例[J].艺术科技,2019,32(08):81,101.
[6] 苏盛祺,论《聊斋志异》“狐嫁人士”故事的民间故事母题[J].汉字文化,2020(19):51-52,64.
[7] 谢语睿.从曹操和刘备形象的变化浅析中国审美价值的趋向[J].汉字文化,2020(15):41-42.
[8] 徐志豪,吉玉萍.所谓伊人:《聊斋志异·侠女》中高扬的女性主义意识兼蒲松龄的女性观[J].蒲松龄研究,2019(04):49-55.
[9] 匡华,易媛.网红现象的审美危机[J].今传媒,2018,26(10):58-60.
[10] 薛芳芳.浅论刚性美、柔性美和美育[J].大众文艺,2019(09):252-253.
[11] 赵阳.清代闺阁女性笔下的才女陈素素——以名媛题咏《二分明月集》为中心[J].三峡论坛,2020(04):59-61.
[12] 尹瑞雪.试论《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J].汉字文化,2020(19):58-58.
[13] 刘燕.浅析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中的职场理念[J].艺术科技,2020,33(07):58-61.
[14] 張小琦.李白的饮酒诗研究[J].戏剧之家,2019(33):211-213.
[15] 张瑾.谈文学作品中服饰的重要性[J].文史,2010(06):58.
作者简介:袁雨航(2001—),男,江苏南京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