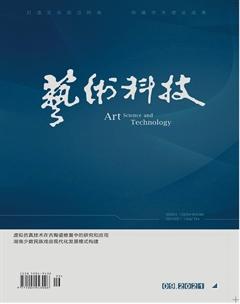“他塑”与“自塑”:好莱坞电影中华人男性形象构建的类型及启示
摘要:20世纪的好莱坞电影先后塑造了傅满洲、陈查理和李小龙三位经典的华人男性形象,并在“他者塑造”中凭借其全球流通性影响着西方乃至全球对华人形象的认识。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我国迫切需要提升影视作品的对外传播能力并自塑华人形象。在“自我塑造”的过程中,加深国际合作和主动出击都是必不可少的路径。
关键词:好莱坞电影;华人男性形象;国际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9-00-02
西方对中国人的凝视与想象由来已久,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可以称为西方利用电影媒介塑造华人形象的主要阵地。好莱坞电影的创作者从不同形式的作品中汲取灵感,利用新兴的电影语言实现对华人形象的建构[1],以此传达对中国社会的看法[2]。人物形象是电影中极其重要的元素[3],纵观20世纪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男性形象,具有代表性和深远影响力的当属傅满洲、陈查理和李小龙三位。
1 二元结构语境下华人男性形象的嬗变
1.1 对华人男性祛魅的二元结构
1.1.1 “黄祸论”的代表:傅满洲
20世纪初,傅满洲以类似撒旦的形象随着小说《神秘的傅满洲博士》的发表迈进了西方世界。作为一个被妖魔化的负面形象,银幕中的傅满洲极其脸谱化:高高瘦瘦、穿着清朝服饰并留着长辫子和长指甲。在容易捕捉和记忆的特征中,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刻板思维逐渐形成,同时他们认为中国和中国人就类似傅满洲,聪明又邪恶,即使年老体衰仍有着强大攻击力,而他们则成了惴惴不安的弱者和反抗侵略的正义者。傅满洲的出现符合19世纪末的“黄祸论”,作为“黄祸论”的代表,他也的确凭借14部电影的陆续问世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
1.1.2 “模范移民”:陈查理
在傅满洲风靡西方一段时间后,反对的声音显露头角,厄尔·比格斯曾说:“视中国人为罪恶之徒的观点早已过时了。”[4]随后,他便创造了一个与傅满洲大相径庭的华人男性——陈查理。陈查理个子不高、身材肥胖且性情温和,更关键的是他是为西方服务的侦探。陈查理的出现从表面上看是对穷凶极恶的华人形象的纠正,其实他是被美国文化同化并重新塑造的模范移民。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涌入大批移民,好莱坞试图以他为榜样来规范其他移民,原因是陈查理仆人式的角色完全符合美国对温良恭顺的移民的需要。
1.1.3 二元对立结构的同一指向
傅满洲和陈查理虽然在形象上大相径庭,但有着不可忽视的共同点:都是被好莱坞祛魅的华人男性形象,是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和种族歧视。好莱坞塑造的这两个被阉割的华人男性形象,一则褒一则贬,以二元对立的结构操纵着华人形象,利用影像传播的溢出效应[5],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话语策略,以此来维护西方人的优越地位。
1.2 对二元对立结构形象的有限消解
20世纪70年代,李小龙以犀利的拳脚功夫、充满力量的阳刚身材打破了之前好莱坞银幕上被阴柔化的华人男性形象。他不同于邪恶的傅满洲,扮演的是正面人物;也不同于温顺的陈查理,他肌肉强健、拳脚凌厉。好莱坞对华人男性的祛魅从身体特征上入手,那么李小龙便利用好莱坞表现西方男性的话语策略,即追捧阳刚的男性气质,通过表现自己的身体,开启了自塑华人形象的时代。
不可否认,李小龙的走红是对傅、陈话语的强力冲击,但这样的解构和重建也是有限的[6]。尤其是他在影片中仍延续了陈查理话语的无性化特征,即在情感方面对女性一直持有冷漠疏离的态度。虽然李小龙仍没有走出无性化的禁锢,但他阳刚正气的形象和其电影的成功都为华人在好莱坞获得主体性和话语权做了重大贡献。
2 影响电影中华人男性形象的因素
2.1 移民角度与“黄祸论”
19世纪末受国内战乱和国外金矿吸引,大量中国移民涌入美国,而傅满洲这一形象于20世纪初期形成,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20世纪初,唐人街已遍布美国各大城市。华人移民与美国人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并在唐人街形成了独特的社群。除了外貌和生活方式上与西方存有差异[7],华人在工作上的任劳任怨更是令美国人感到焦虑。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美华人就受到公开性的歧视和杀戮。在这样特殊的时代大背景下,美国的媒介开始大量涌现对于中国人的负面报道。
从移民角度出发,西方根深蒂固的“黄祸论”思维也无法忽视。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声称自己做了一个佛祖骑着恶龙入侵欧洲的噩梦,他恐惧不已,随即用“黄祸”来描述这种感觉。于是西方人把“黄祸”与当时的中国移民联系在一起,从而把對中国移民的歧视深化为受到威胁的恐惧与排斥。艺术渗透带有特定时代的功利性[8],此时,傅满洲作为“黄祸论”思维的集中体现被好莱坞搬上了银幕。
2.2 源于政治需要的话语转变
20世纪的30~40年代,随着二战的爆发,日本暂时代替中国成为新一轮“黄祸”恐惧的实体,中国的身份由威胁西方的恶人转变为联合对抗日本的亲密盟友。在新的历史阶段,美国更着重于表现一个对白人毫无威胁的仆人式角色。20世纪70年代,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转变带来了文化上的宽松环境,华人在好莱坞有了一定的主体性和发声空间,再加上李小龙电影中多次出现的反抗殖民者的主题与反帝主义浪潮相吻合,其走红也带着必然性。
傅满洲、陈查理和李小龙三者所代表的华人形象并不是互相代替,而是交织存在。20世纪前期,傅满洲以企图摧毁西方的邪恶面目出现;冷战时期傅满洲又以“反共”的面目出现。傅满洲的形象可以被看作中美关系的现实映射[9],在中美处于政治和谐期时他会退居幕后,其他时刻又会根据美国的需要粉墨登场。
3 当代语境下对塑造华人形象的反思
3.1 华人形象建构的困境
20世纪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大多来自他者塑造,这和当时中国国家力量薄弱、华人在外话语权的缺失不无关系。然而即使21世纪以来我国国力逐渐增强、国际地位也有了显著提升[10],但是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话语对抗式解码的现象仍然层出不穷。电影媒介作为一种文化输出的手段[11]和彰显国家精神[12]的有力工具,其中所表现的华人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因此认清当前华人形象建构的困境及如何利用电影媒介进行形象的自我塑造成了一个重要课题。
在如今的华人形象和国家形象建构中,国际国内纷繁复杂的环境都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方面,他者对中国形象存在偏见和误读,一些西方国家用“中国威胁论”打压我国;另一方面,我国国家形象要想实现真正立体化,还存在许多传统与现代文化符号的矛盾冲突以及自身能力建设的不足。
3.2 塑造华人形象的路径探析
解构西方对华人的刻板印象是我们的共同认知,但如何重新建构才是重点。利用电影媒介塑造华人形象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与好莱坞电影的合作;二是主动出击,增加本土文化自信[13],加快文化输出的脚步,祛除中国传统社会对于男女的刻板印象[14]。
在国际传播背景下[15],无论当今的美国电影或是中美合拍片,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方占主导地位。西方尽力开发中国资源,试图利用中国元素、中国故事抓住中国观众[16],在表达中国文化的内涵上却总是融入西方价值观。以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为例,中国观众认为《花木兰》是对中国元素的堆积和滥用,虽然任用了许多华人演员,但人物塑造无法让观众产生认同和情感投射[17]。从现实看,西方电影不会自觉改变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因此加深国际合作,学习好莱坞电影的同时输出中国元素和文化是减少文化误读和塑造正面华人形象的必经之路。
除了寻求中外合作,想要利用电影媒介塑造出真实、正面的华人和国家形象,还必须发挥中国电影的作用[18]。近年我国主动出击,自塑华人形象的影片并不在少数。《战狼》系列电影塑造了孤胆英雄[19],《红海行动》和《流浪地球》显现的是群像式英雄[20]。然而群像式英雄往往代表集体的力量,与西方个人英雄主义[21]不符,从而产生文化折扣;《战狼》又曾被国外观众质疑“太虚假”,不是中国的真实缩影[22]。艺术作品,主要是作者想让观众感知什么[23],或许爆红于国内外社交网络的李子柒能给予我们新的启示,由高高在上的庙堂式传播和脸谱化形象展示[24]转向小人物的刻画在华人形象的塑造和提高观众认可度上[25]更为深入人心。
4 结语
20世纪,西方的强势话语操纵着银幕上的华人形象的近百年时间里,好莱坞不间断地凝视与想象中国并建立起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全球观。认清历史是前提,重要的是中国的影视剧不能再在国际舞台上失语,将国际领域华人形象的塑造权拱手让给西方传媒。鉴于此,我国必须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以及主动出击的自塑华人及国家形象的方法,打破好莱坞电影的思维定势,建立起属于新时代的正面华人形象和国家形象,让世界听到、看到、感受到真实的中国。
参考文献:
[1] 黄霁风.议程设置理论下的电影话语分析[J].东南传播,2019(01):40-43.
[2] 杜彦洁.电影作品的叙事特色分析——以侯孝贤电影为例[J].汉字文化,2019(03):36-37,48.
[3] 位云玲.法国电影《触不可及》的人物角色分析[J].汉字文化,2020(12):124-125.
[4] 常江.从“傅满洲”到“陈查理”:20世纪西方流行媒介上的中国与中国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4(02):76-87,127-128.
[5] 李惠敏.助力乡村文化自信:涉农纪录片的当代价值研究——以记住乡愁为例[J].东南传播,2020(06):35-37.
[6] 吕志文.构建与解构:“男性向”网络小说改编剧分析[J].艺海,2020(07):82-83.
[7] 丁月明.危机与转机:网络综艺节目叙事策略的优化——以《心动的信号》为例[J].戏剧之家,2019(16):222-223.
[8] 王全权,周碧琬.论国产动画电影中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及其影响——以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为例[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04):17-21.
[9] 位云玲.观察类综艺节目走俏的原因探究——以《我家那闺女》为例[J].艺术科技,2019(03):115,128.
[10] 位云玲.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持续走红的原因探究——以《上新了!故宫》为例[J].艺术评鉴,2019(07):169-170,76.
[11] 黄晶晶.电影艺术中的传统文化承创——《Three Idiots》[J].戏剧之家,2019(22):102,104.
[12] 杜彦洁.浅析美国电影新英雄形象——以《蝙蝠侠:黑暗骑士》为例[J].大众文艺,2019(08):158.
[13] 李惠敏.经营体验类综艺节目的叙事特色分析——以《潮流合伙人》为例[J].汉字文化,2020(10):179-181.
[14] 丁月明.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电影女性形象塑造分析——以电影《霸王别姬》为例[J].戏剧之家,2019(15):83-84.
[15] 王莹.国际传播背景下美国华语电视节目研究[J].戏剧之家,2019(16):89-90.
[16] 石姝敏.电影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研究——以
电影宣传片《啥是佩奇》为例[J].戏剧之家,2019(16):104-105.
[17] 王灿,冯广圣.情感唤醒与乡村认同:从《向往的生活》看慢综艺热[J].新闻知识,2020(07):62-65.
[18] 尤旖芸.基于受众角度探究国产电影的发展方向——以《我不是药神》为例[J].戏剧之家,2018(31):57-58.
[19] 罗峻峰.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创作的问题与对策[J].艺术科技,2019(15):103-104.
[20] 陈芳芳.试论电影《流浪地球》中的生态美学思想[J].艺术评鉴,2019(11):158-159,185.
[21] 孙志宇.《血战钢锯岭》——真实的战争,耐人寻味的英雄主义[J].戏剧之家,2019(22):103-104.
[22] 張嫚.社会化媒体对家庭伦理剧的撕裂与弥合——以电视剧《都挺好》为例[J].艺海,2020(08):96-97.
[23] 杜彦洁.浅析张艺谋电影作品中的色彩运用[J].戏剧之家,2019(06):75-77.
[24] 朱克迎.姜文电影的人物形象美学赏析[J].戏剧之家,2019(06):85-86.
[25] 王灿.以《风味人间》为例探究饮食文化类纪录片传播新走向[J].戏剧之家,2019(15):79-80.
作者简介:李宇童(1998—),女,安徽滁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