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与抵达的双向流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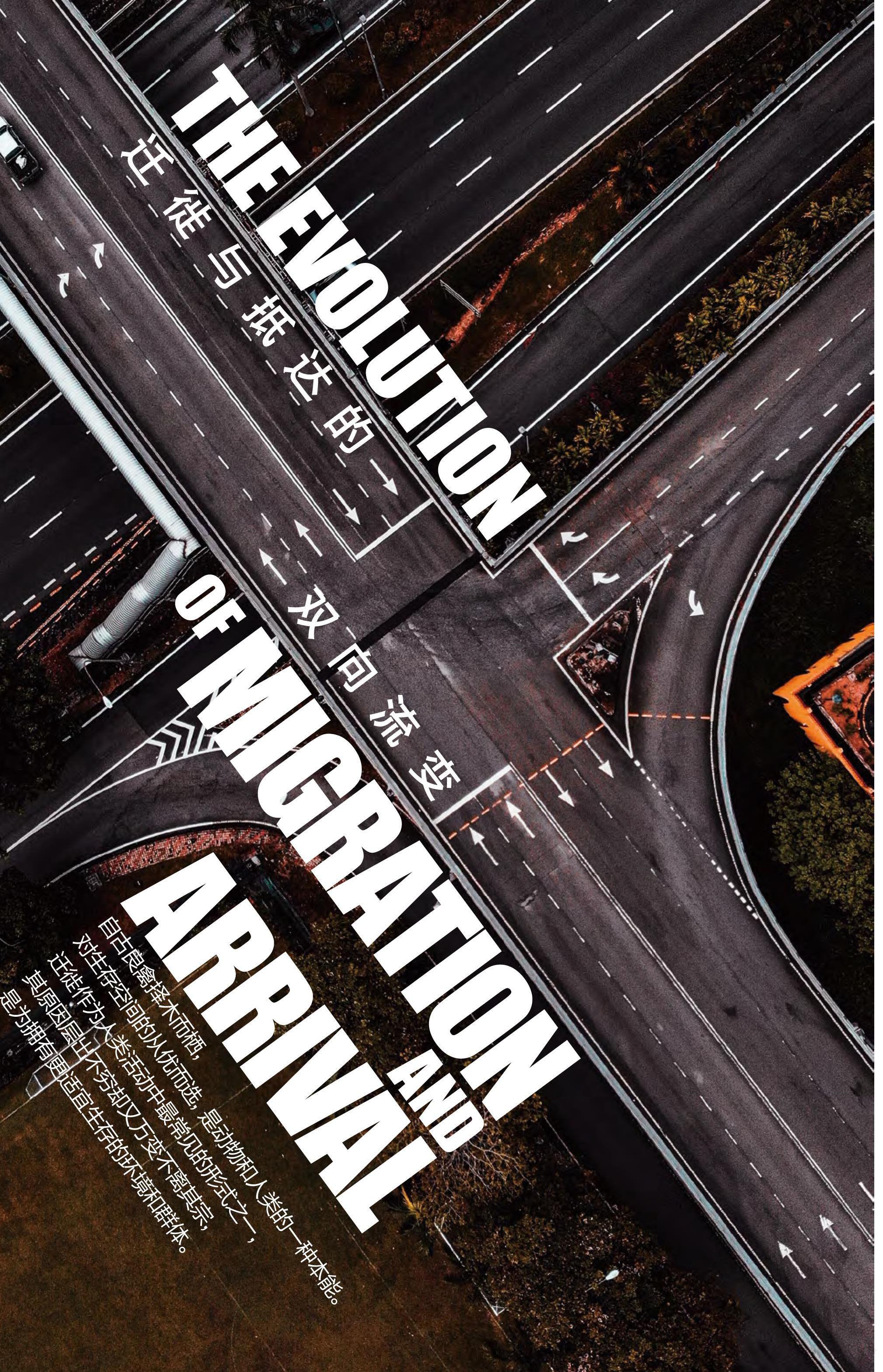


根据联合国发布《2019年全球移民数据报告》,全球移民数量达到了2.72亿,占全球总人口的3.5%,其中印度、墨西哥、中国、俄罗斯、叙利亚是全球最主要的五个移民输出国,数千万的人们因为個人学业工作发展、商贸往来、战争等原因背离故国。
在已经结束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近3.8亿人,比2010年增加了1.5亿人。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流动人口始终呈现增长态势,延续性的大规模乡城迁移流动促成了63.9%的人口城镇化。
从人口迁移的流向来看,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依然是人口集聚的目的地,随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崛起,一线城市已经不再是离开小镇和乡村,向城市进击的人们的唯一选择。杭州和成都既在“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又维持着近十年以来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量,其中除了来自小镇的人们,自然也有离开北上广的青年。
然而,在一个个冷静客观的数据背后,迁徙之路对于每一个在此浪潮中的个体,都是一个漫长而具体的过程:我是否需要离开?我将去向何处?在迁徙途中我将经历什么?抵达之后我又将成为谁?家乡是一个回不去的起点还是始终在等待着返航?
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语境中,地方被定义为—种“感知的价值中心”,以及社会与文化意义的载体,社会中的每一个体都将在出发去向一个新的地方的途中,产生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上的新陈代谢。“我是谁”的旧定义和新思考,两者关系或许是平行并存,或许是相互碰撞,也或许融合为一;但无论哪一种,都将为迁徙中的人们开启全新的视角来重新理解周遭的世界。
夏梦怡:迁徙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形式
“迁徙是一场生命的搏斗”这句话和我的状态很贴近,在一段段迁徙中去寻找自我,对现状很少感到安逸,但试着去享受每一段旅程,生命本身就是一场自我搏斗。我从6岁开始离开家乡,到现在对我来说创作和迁徙是一样的节奏,有时是理解和包容社会的一切善恶美丑,并与之为伍;有时是以所思所想把握好一个作品,对它们付以赤诚真心。作为作者我觉得应该是用自己爱做的事先构建好生活,先关照自己,才有能力去关照好身边的人,关照观众。迁徙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形式,只是现在物质条件各方面充实了我们想要的迁徙形态。
2018年我以北京为起点乘坐7000公里的火车为剧本创作进行了采风、2019年我在欧洲进行了三个月的旅行独自游历了十二个国家,这两段经历对我而言旅途中触动大于结束后的改变。2018年那次夏天的火车旅行其实是一开始为了逃避现实和北京,我有一位好朋友那段时间不幸发生意外去世了,在那一周后我还是很难过和寝食难安,就想要暂停在北京的生活出去半个月走走。火车旅行经常能给我带来很多灵感的,至今还有印象我第—次坐火车是1999年的春节,妈妈来广州接我带我在火车站穿过春运汹涌的人群,我们买了两个塑料凳子在车厢走道摇摇晃晃坐了一夜,到了半夜列车员带我们去空的车厢找地方给我们睡觉,一夜之后我们到了湖南的长沙。这是我记事以来人生的第一段旅行,往后的每—年都在春节前后坐两次火车在家乡和异乡之间来回。
2018年从北京出发沿途看到的景象让我开始频繁想起小时候坐火车的回忆,我很快静下了心和人交流。放暑假来北京探亲的西北家庭,姐姐弟弟轮流依偎在妈妈的膝盖上睡去,年轻小伙在座位上喂药照顾体弱的母亲,花式叫卖特产的列车员讲点单口相声,还有当众批评国家为难着列车长的“传教人士”,看热闹的人站着坐着在列车里围成了一片。这种氛围感觉对我来说真的太熟悉了,那段时间我在写一些随笔和故事梗概。其实《离家之日》里一个很重要的立意就是关于人的迁徙,它是90年代末的城乡发展背景下的一个在异乡漂泊的家庭故事,和我小时候从农村到城市生活的经历有关。在路上去思考和创作是幸福的,过程带着很多随机性,旅行的时候也脱离了一切睡眠问题,我在火车和汽车上睡着的速度也总是惊人。我想这种漂泊感应该在我生命初期就成型了,是刻在骨子里的,可能30岁之后都有一定的改变吧。
欧洲的旅行更多的是圆自己一个长途旅行的梦,起因还是因为电影,我那年夏天利用参加三个电影节的契机,在影展之间的空隙时间去不同的国家游历和拜访朋友。当时甚至觉得错过了就以后也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现在看确实是这样,投资一趟期待的旅程永远是非常值得的,尤其疫情后世界的格局产生的变化,我们没法再看到同样的状态事物。那趟旅行我交到了一辈子的朋友,关于电影、友谊、热爱都在一趟旅程中把回忆储存得满满的,去年疫情的时候就经常回忆2019年的旅行,这些点点滴滴都给了我很多力量。Q&A
CHIC:迁徙是—种流动性的发展,与影像记录的过程有类似之处,你当下比较关注的影像表达的主题有哪些?
夏梦怡:我从刚开始创作到现在都在关注跨文化,是在中国环境下的全球化文化现象,尤其是长沙纪录片三部曲的《隐居中国》和《我的第一位》,都是讲述外国人在中国探寻扎根的成长故事。这几年关注移民题材和社会问题比较多一些,在这些主题里面去构思特定个人或群体的故事,这些题材本身能给我一些开放的灵感思路,去做基于真实但美于真实的故事,我今年刚完成的一部剧情短片《午后》,主题是关于人、动物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CHIC:在你拍摄的《隐居中国》(2014)纪录短片中讲述了一位国外艺术家马蹄从长沙独自出发探寻中国民间艺术的历程,作为记录者你也随着主人公马蹄的脚步完成了一次“他者的迁徙”,但同时也是在完成“自我的迁徙”的影片制作,你是如何平衡、取舍拍摄过程“他者”和“自我”的关系,将三个月从采风到拍摄的素材凝聚成了越22分钟的短片?
夏梦怡:这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次创作经历,我当时21岁,那个阶段也奠定了对影像创作初期的方向和态度,做独立纪录片是我初期的一个理想,这种沉浸式的创作—方面必须是关怀他人的生活为先,作者把自己放在最渺小客观的位置,以小见大以微知著,只有拍摄和经历了这些故事,在另—方面才是照见自己。每部纪录片—方面都是通过拍摄对象的视角去看他眼中的世界和社会切片,只有真正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生活和记录,才算得上是真诚的拿起摄影机。马蹄本人的生活态度对我影响挺大的,通过记录他迁徙的过程我在地域变化中观察到不同的社会现象,比如说跨文化,传统民间艺术,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没有他的迁徙我也看不见也呈现不出这些内容,去理解和呈现他的理想也终究成了我在这部纪录片里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