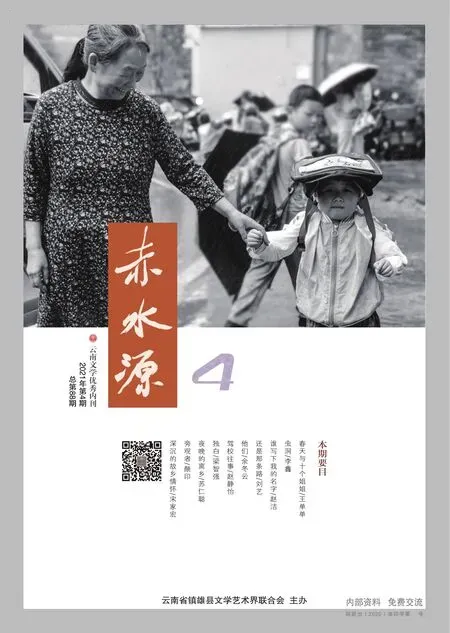“八卦‘甑’”前煮酒女
文/张光英
我的侄女儿,在她刚满二十岁时,嫁给同镇的一枚袁姓小帅哥为妻。小帅哥父母早亡,以二十来岁之龄独挑一家重担,侄女儿为人妇后便与他一道,承担起扶持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之家庭重任——所谓“长兄为父、长嫂为母”的传统之德,在两个小年青身上演绎得淋漓尽致:给二兄弟张罗婚事,送小兄弟入伍,再“盘”幺妹儿上大学……一大家子“娃娃兵”,在侄女儿小夫妻的带领下,总算慢慢熬过父母去世的打击,还有继母离去的困窘,生活,渐渐走上了正轨。而支撑一家生计的袁家“茅草房白酒”——这在他们家传了几代人的“衣钵”,可谓立下“汗马功劳”!侄女儿,作为长媳,也在为人妻为人嫂与为人母中,自然而然成为那煮酒炉旁氤氲着酒香味儿的煮酒女。
一日到侄女儿家闲逛,恰遇三个“毛孩儿”在热气腾腾的“巨无霸”甑子前忙碌:只见两个混泥土与铝板造就的甄子旁——其实说是“池子”更确切些,因为像这样每次煮酒烤酒都盛下八百斤或苞谷或荞麦的巨型甄子,在县内也找不出几个!只见侄女婿在白茫茫的热雾中指挥着,侄女儿挥舞着铲子把甑子里早已蒸得糯香的苞谷铲进大撮箕,小叔子一大撮箕一大撮箕地抬着晾到宽敞的坝子里,撮箕挨着撮箕的独特景致,加上如《西游记》剧中云飘雾罩似的场景,如果有高明的摄影师,用专业的拍摄手法,一定会留下无数幅充满生活气息的艺术照!
被浓烈的煮酒氛围吸引,我忍不住与几个小年青有一搭没一搭侃起来——
为什么是两个池子嘞?
我们叫“酒甑”,原来是只用一个甑子的,既煮酒又烤酒,不过到我们手里,改造创新,加一个大小差不多的甄子在旁边,一个甑子专门烤酒,一个甑子专门煮酒,它两个的合体就叫“八卦‘甑’”,也取“八卦阵”吉祥玄学之意!
呵呵,这土窖酒居然还带上了玄学之境!我更加好奇了,啰啰嗦嗦地继续和他们聊:从哪个甄子蒸苞谷,哪个甄子煮荞子,到“五粮液”的各种粮食哪种先蒸,哪种后煮;再从蒸透煮熟的苞谷摊晾降温到酒曲和匀置池发酵,到樱桃果酒的原味佳酿及紫色的葡萄怎么产出透明无色的“白酒”探讨;还有从发酵后的粮食返池熏烤怎么液化到冷却器,到如何成为汩汩“甘酿”顺着酒管到充满酒家特色的大坛子里……年轻人们并不懂什么深奥的玄学,但意图让传承久远的农家土法酿酒赋予固有的历史底蕴,且在新的发展中,让淳朴厚道本真的家风乡风持续传承,却也是这“八卦‘甑’”主人取名的初衷。
侄女儿一边大汗淋漓地挥舞着铲子不停地铲,一边儿不厌其烦地讲解着她家的“八卦‘甑’”,什么火候控制啦,什么时间估摸啦,什么三年库存窖酒,什么水源牵引来头啦……香汗湿透了她的衣襟,原本身形消瘦的她,为了一大家子的生计,似乎如“汉子”般力大无穷,这也更让我这个“小幺爹”心疼——“古有卓文君‘当庐卖酒’,今有我家小女临池煮酒”,在隐隐的心疼中,我以淡淡的幽默和俺家这个“煮酒女”开着小玩笑。不过,侄女儿对她承受着的辛苦,似乎不以为意:我这就是最好的减肥方式啦!怎么吃都不会胖!
就是在这六七年的时光荏苒中,侄女儿,从青涩到稳健,从娇娇女到一家之主,从“张氏女”成了袁家“茅草房白酒”地地道道的“煮酒女”。在她那个维持一家人生计的小酒馆里,几个沉淀着岁月酒香的大坛子,默默无声地承载着百年土窖酒的使命与家族传统。镇上的乡间旮旯,大门小户的餐前饭后,田家辛苦劳作后归来的阿婆,扛一袋洋芋刚歇下气的白发阿公,还有工地上苦力人的小憩闲尔,外来乡宾的推杯换盏迎来送往,一切尽在不言中。小酒馆临近窗边木板搭起的简陋“吧台”上,搁置着供“酒客”临时过“酒瘾”的几个杯子,坐于酒馆,经常是这样的画面和声音——
打一两酒嘛!
好嘞!
只见侄女儿麻利地一手持酒杯,一手掀开大坛子上的草盖儿,一只瓢舀下去再迅疾地抬起,酒杯里便溢出了满屋的酒香。不用秤称,不用刻度量,侄女儿似乎不计较多打了几钱,喝酒的人也似乎毫不在意分量足不足,只见喝酒人脖子一仰“咕嘟”一口,旁边的人还来不及怀疑酒在他口中的滋味儿是火辣还是清淡,没两秒的时间,或一两或二两的酒早已没了痕迹——“这次没揣钱,下次再付哈”,什么!只听喝酒人酒儿灌下去撂下这句话便跨步欲走,旁观者正认为这满足了“酒瘾”的“酒客”喝酒不地道,谁知侄女儿清脆如铜铃般的声音更是爽快:“好嘞!”就这样,一天小酒馆一两二两赊欠的人,总要见着好几拨!
可是也有例外!一次,一个脸色乌青的三十来岁汉子,缓缓来到酒馆——
打一两酒!
只有两块钱一两的了!
这么贵,不喝了!
欲过“酒瘾”的汉子悻悻离去,我百思不得其解。
不是一块钱一两么?怎么独独这个来,要涨酒钱呢?
他身体不好,经常喝酒,喝了酒后又乱整,所以为他好,就故意涨价希望他少喝酒的!
哦,原来如此!
在侄女儿并不算精明甚至老是赊账的经营中,小酒馆似乎也并不见亏欠,这人情世俗味儿浓厚的小镇上,一大家子人的生计似乎也还是照样依靠家里煮的酒维持了下来:可不,那没有什么所谓“商标注册”的字号里,除了行业部门赋予的资质标签,便无任何官方雅正的称谓,可是侄女儿家“茅草房白酒”却以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它不可的存在,让小镇的人们习惯于酒坊里酒糟散发出的清香;那“下次再付钱”的“酒客”中,有别人出重金也不愿卖出却肯慷慨分一只犬给侄女儿看家护院的,有昨天赊了酒但今天就带来大宗客户的,有在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时帮其带小娃煮饭喂猪奔前顾后左右张罗的……原来,酒的情谊,何止一两与二两!
侄女儿,这不精明的“煮酒女”,用她的辛劳、朴实与厚道,撑起了兄弟妯娌的和睦幸福,撑起一个家庭原本艰难的温暖与希望,她用大方的“舍”,换取了人间一抹难得的“得”,让茅草房的酒香,飘溢在镇上,飘溢在她身边每个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