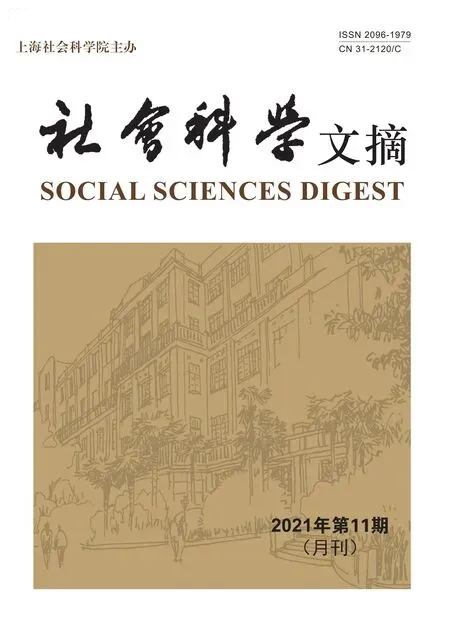从古典到新传统的多元性重建
——当代“中国哲学”世界的新开展
文/姚裕瑞 王中江
(作者单位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摘自《文史哲》2021年第5期)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开创了一些新局面,建立了“中国哲学”的新知识体系,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主要表现为几个彼此关联又层层递进的方面。对于这些方面的系统性总结,既是为了回顾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和进展,同时也是为了重新探讨和把握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提出新的看法,以此来澄明中国哲学当下的处境,并预设中国哲学突破的“未来”前景。
“学术回归”与中国哲学叙事的转变
第一个方面是恢复了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和重新积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如同其他领域一样,“中国哲学”经历了学术身份上的自我认识和确认,走向了学术化的研究和写作方式;自此之后,中国哲学的研究在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积累。
1979年10月,“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讨论会”在山西太原召开。这次会议被视为是“文革”后中国哲学重新“回归”和“转型”的起点。在参会的百余名哲学家看来,哲学研究虽说与社会、政治具有密切联系,但哲学史有其自身的认识发展规律;他们大都赞同列宁所说“哲学史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的看法,而反对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史”的定义;他们主张在研究某家或某派的哲学思想时,既要对哲学思想进行“阶级分析”,更要进行“理论分析”。经过这场“拨乱反正”的“学术回归”运动,哲学家们开始挣脱出“泛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的束缚,伴随着“政治中心取向”向“经济中心取向”的巨大转变,中国哲学研究也突破了单一的“泛政治化”写作方式,开始在“学术化”和自律的轨道中,逐步探索出“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轨迹与道路。
正是在这一“学术回归”和“中国哲学叙事”的整体转变和转向中(“政治化叙事”转向“学术化叙事”),40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才能够在诸多方面能够取得重要进展,并使得学术“积累”成为可能。因为对“政治”与“学术”关系的重新调整和理顺,4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在诸多方面均呈现出了自由创造的思想迸发的活力。从外在性的接受一种“模式”到自觉反思和转变自身的叙事方式,从一种“他律”的、单一的和“泛意识形态性”的写作到“自律的”、多元的和学术本身的探讨,中国哲学研究正是在反思和学术回归中走上了正途。
从“反传统”到文化认同与中国哲学的同情理解
第二个方面是中国文化认同促使人们对中国哲学的同情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中国文化不断增加的认同,人们对中国哲学的认识和解释也具有了同情的理解,克服了在“反传统”主义价值观之下的简单否定和由此产生的大量误解,澄清了中国哲学的许多内涵,发现了中国哲学的内在智慧和价值。
在80年代“文化热”中,“反传统”和“西化”的声音逐渐占据上风。大批青年学者纷纷将矛头对准传统文化,他们高呼“批判传统”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们试图通过文化上的反思与改造,而为现代化的加快提供某种文化上的合法性。“反传统”和“西化”的思潮也迅速席卷了中国哲学界,一些过去被视作是中国传统哲学“特色”或“优势”的思维方式,在此时却被评价为负面的或消极意义的东西。“批判式”的研究和“否定式”的写作如此之强势,以至于“反传统”和“西化”一度成为80年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但是到了90年代初,这种“反传统”的态度却突然发生了转变。伴随着“文化争鸣”的落幕,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传统”在20世纪的艰辛旅程进行反思。“传统”在当代的不幸遭遇引发了他们同情和忧虑。正是由于80年代的部分学者过分接受和信奉了来自西方的“启蒙叙事”和所谓“理性精神”,也由于他们极端地批判“文革”和反对“封建”甚至是把所有的“传统”都等同于“封建”,而使得这场“文化热”最终落入到了“反传统叙事”和“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困境之中。极端和不加反思地批判传统,不仅不能带来任何建设性的意见和价值,相反令中国哲学走入“自我否定”“自我解构”的危险。也正是在这种反思和反省中,中国哲学学者开始以较强的“传统认同”的方式来理解和研究中国哲学。
从“反传统”到“认同传统”的转向,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最不容忽视的一个新变化与新取向。应当肯定的是,发生在90年代的一系列有关“传统”的转变,它们既是中国哲学在“回归自身”过程中的一个极为关键的节点,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学者试图重新接续传统并重构中国哲学“主体性”的重要体现。
在“视域融合”的视角下,“传统”当然不应被视为是负面的或博物馆的东西,但我们也不能抱残守缺地希冀“回到过去”。因为“传统”是活的、连续性的,它就不仅不会构成中国人走向“现代”的阻碍,相反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与助力。“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就要拒斥“传统”;当然,复兴“传统”也绝不意味着就要批判或拒斥“现代性”。现在我们应当从整体上放弃一种所谓“批判传统”或“拥抱传统”的单向度的立场,而转变为“传统”与“现代”互动的双向度的立场。
出土文献与古典思想文本的互证
第三个方面是大量出土新文献丰富了早期中国哲学的世界。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发现了大量地下文献,这些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哲学和思想文本,特别是有关早期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文本。这些新文本的发现不仅求证了许多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而且大大扩大了早期中国哲学的世界,使早期中国哲学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90年代开始,随着“传统”认同的不断增强,出土文献研究也成为了一个新的学术热点和知识增长点。大批来自地下的文献,尤其是“六艺类”与“子学类”的哲学思想文本的重见天日(如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和“北大简”等等),为中国哲学研究带来了又一次难得的突破与契机。中国哲学研究者们从各个方面、多角度投入到了对于简帛思想文献的释读与研究工作中。这些研究在不同方面,深刻影响乃至改变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轨迹:其一,出土文本的研究印证了古代经典文本的可靠性,证明了早期历史记忆的真实性;其二,出土文本的研究还为古代哲学带来了一些“新知”。
当下,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出土文献热”,已然成为中国哲学研究领域最具潜质和活力的一门学科,其同时也在不断地塑造、发展着早期中国哲学的新故事。在犹如层峦叠嶂的各个侧面中,不同于以往哲学史记忆的面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呈现。
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自觉与“范式转换”和“深度视点”
第四个方面是追求“中国哲学”内在性的方法论的反思。人文学科的研究离不开回顾和反思。深化“中国哲学”研究的强烈愿望,促使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们开始对改革开放以来也包括1949年前的中国哲学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人们一方面肯定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存在着简单化类比西方哲学的缺陷,人们强调研究中国哲学要避免草率和表面性,就必须上升到方法论自觉的高度上,必须建立起中国哲学的内在理路和方法。
2000年初,中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大讨论。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即“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能否以西方哲学的方法和范式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问题。怎样看待这一“合法性”的讨论呢?首先应该说明的是,在21世纪初展开的这场以“合法性”为名的大讨论,其实质上,正是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中西”之争的延续。其探讨的,仍然是如何看待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以及是选择以西方哲学的方法和范式来理解中国哲学还是以中国哲学自身的方法和范式来建构自身的问题。只不过,在21世纪多元文化兴起的背景下,这场讨论显然要比一个世纪以前更为深入。因为争论的重点其实已不仅仅是中国有无“哲学”(西方意义上的哲学)的问题,更是应以何种“方式”、以什么样的“方法”来更好地理解和发展中国哲学学科的问题。
正是在这场“合法性”的讨论中,“方法”的自觉和“范式”的转换也开始走入学者的视野。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意识到:要想真正解决中国哲学意义危机,就必须深入到“方法论”的层面上并拥有系统的“方法”的自觉。于是围绕“中西之争”的方法论反思,也开始扩展为了对于整个中国哲学学科的“方法诉求”与“范式转换”。要求“改写”“重写”“重构”中国哲学的主张,要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声音不绝如缕,如何建立中国哲学的“内在理路”和“深度视点”以及具有本土性和创造性的“原创性叙事”,成为学者们新的关注。伴随着“方法论”讨论的深入,“范式转化”和“方法创新”成为20世纪以来最具建设性和启发性意义的观点之一。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既强调中国哲学研究的本土性和独特性,同时也强调它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及共通;我们既主张对中国哲学史的“梳理”和“重述”,同时也主张“方法”的自觉和“范式”的创立。健全的理智要求我们在“可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在“普遍性”和“差异性”之间采取一种双向性的立场。
中国哲学进一步的“范式转换”和“方法创新”,正有赖于我们在中西哲学的方法和语境中寻求适当的平衡。我们既要深沉地整理和重述自身的学术传统,更要通过“深度的视点”和“方法的自觉”,以促使中国哲学进一步的转型和创造。只要这样,差异才能是“普遍中的差异”,而普遍也自然是“差异中的普遍”。
“经学转向”与经典诠释学
第五个方面是“经”“子”的结合及“经学转向”。中国哲学主要是以子学文献为基础和线索建立起来的学术和学问体系,之前的哲学史写作也主要是围绕此而展开的。但由于儒家在中国哲学中的特殊地位,而儒家经学又同子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为了弥补过去以子学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心的单薄,自21世纪初以来,人们开始关注儒家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并展开了许多研究。
20世纪末期,中国古典学术领域中出现了又一个引人瞩目的新现象,这便是“经学”的复兴和经典研究的回归。作为曾经传统学问中影响最深的学科,经学在近代以来的解体和边缘化曾引起过诸多学者的惋惜。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离开对于经学的讨论,很多问题将不能得到准确的把握和理解。于是在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沉寂以后,“经学”在中国古典学术领域全面复归。经学的复兴也逐渐深入到了“中国哲学”的领域,许多以往被认为不够“哲学”或不够“义理性”的经典内容,也开始被重新纳入“中国哲学”的视域进而获得了新的解释的活力。
此外伴随着经学的复兴,“创建中国经典解释学”的声音也浮出了水面。“中国解释学”的提出与西方解释学理论的传入和影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发现在中国传统学术内部也存在着一个悠久且庞大的经典解释体系,这不仅包括儒家的经典诠释学,也包括道家的经典诠释学以及佛教、道教的经典注疏体系等等,而古人的思想见解也正是通过这些经典解释阐发和表达出来的。“创建中国经典解释学”的命题与古典研究相映成趣,成为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和思想界又一个显著趋势。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既肯定“经典”与“权威”在当代学术话语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同时也认为这些经典的研究必须进行现代性的转化和理解。正如同对于“传统”我们需要采取一种双向度的立场,对于“经典”我们也应当从整体上放弃一种单一向度的思维模式。我们要摆脱所谓“以哲学代经学”或者“以经学代哲学”的截然二分的主张,而是采取“认同”与“批判”、“权威”与“创造”以及古代经典研究与当代哲学发展相结合的双向性的立场。我们也不必再纠结于强调“经学”多一些还是偏向“哲学”多一些的问题,而是要将关注的重点转向,如何促进“经”“子”的互动,以及如何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来促成“经学”与“哲学”在更深层次上的融合。
从“中国的哲学”到“哲学”
第六个方面是立足于中国哲学历史性研究之上的新义理的阐发和发挥。中国哲学要不断焕发出新生命,人们既要塑造出动人的中国哲学史意义上的哲学故事,也需要塑造出中国哲学的新故事。
进入2010年前后,中国哲学界又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便是中国哲学进一步从“哲学史”研究走向了“哲学创造”。随着哲学建构自觉性意识的增强,部分中国哲学学者开始不满足于仅仅从事思想史料的“整理”与“重述”工作,他们尝试从“哲学史”走向“哲学”,并“接着”往下讲了。此外,要求“改写”和“重写”中国哲学的愿望也变得愈发强烈,要求恢复中国哲学“宏大性叙事”“整体性视角”和“主题性建构”的呼声陆续兴起。学者们不再停留于对中国哲学过于细碎化和片段化的研究现状,他们尝试摆脱一种过于专业化也过于精致和无聊的研究取向,开始努力地在“宏观”与“微观”、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双向互动中,开出一种新的“思想学说”和“理论体系”。
应该说,近年来出现的这些“新义理”“新学说”,它们既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哲学研究逐步积累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新时期最富有意义和令人期待的学术动向之一。如果我们从“哲学史”与“哲学”的关系来看:任何一种曾在哲学史上出现的学说和体系,它们虽说是历史性的存在,但在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却必然是出现在那个时代的“原创学说”。也就是说,它们首先是“哲学”,而后才是“哲学史”,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哲学当然亦不例外。纵观中国哲学史上那些重要哲学家的重要观点和学说,它们首先就是那个时代的哲学理论,而后才凝结、沉淀成了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哲学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哲学史”绝不只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对象”,更不是一成不变的或已经完成的内容。每一时代的思想成果总是会不断地融入哲学史之中而构成新的内容,并且这些新的内容也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中国哲学”的意义和内涵。
今天的中国哲学学者们选择从“中国哲学史”走向“哲学”,这正是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并以此来回应当下时代议题的内在需要。虽说这些各种各样的“新学说”是否都具有生命力,还需经过时间的检验,但从“照着讲”到“接着讲”、从“哲学史”到“哲学研究”、从外在接受一种方法到方法的“自创”与“自构”,这些转变和尝试本身,已体现出中国哲学学者在继承老一辈哲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试图重新建立和培育起中国哲学“新形态”与“新生命”的勇气和睿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