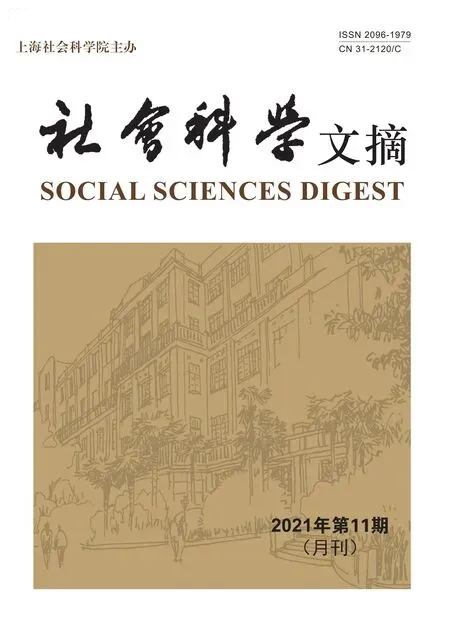论历史认识的检验标准
文/乔治忠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点,就是主张历史事物的客观性,强调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历史科学的目标乃是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为此,必须从理论上解决历史认识检验的标准问题。
历史认识检验标准的理论阐释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导地位的语境中,多数学者在整体取向上恪守唯物主义历史观念。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谈到历史认识的检验,很自然地会首先思考怎样运用“实践”标准的问题。这存有一个困惑,就是如何阐释“社会实践”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实质,如何讲清“社会实践”检验历史认识的内在机理。于是人们就一方面不承认“社会实践”能够直接检验所有的历史认识,因而提出不同的分层次检验方式,析解出多种检验标准、检验方法,但析解后又试图将各项层次性检验收敛、统一,“归根结底”地纳入“社会实践”的“唯一”标准。如此一分一合,相关的解说十分勉强甚至自相矛盾。
实践,在本义上就是指人们的实际行为,只要具备一种公共社会领域和行为指向的群体性活动,都成为整个社会运动结构的组成部分,都可称之为“社会实践”。毛泽东在经典的著作《实践论》中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此处举出“科学和艺术的活动”为例,显示出社会实践不限于物质的生产,而要点在于“社会的人所参加的”一切领域内的活动都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的产出有物质产品也有精神产品,但作为人们群体活动的实践,都是物质性的社会实践。
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社会”是一种高层次的物质,人们的社会活动是物质性的运动。因此,学术研究、政治宣传、文化传播等等,从进行这些运作的人们角度来定义,都是实实在在、不打折扣的社会实践。史学研究即史学实践,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态,不应当将之称为“间接社会实践”,不必划分“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史学研究作为整个社会许多学者工作的总和,不能再看成是精神性的活动,而是人的活动、是人们被社会机制组织起来的物质性运动,其产出的历史著述,才属于精神性的范畴。将学术实践排除于社会实践之外的观点,是保守、落伍、不正确的观念。
毛泽东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这不仅确定艺术活动、科学活动属于“实践”,更深切的意义是指明一个具体门类认识上的是非、正误问题,要由与之相对应的实践来验证,而不是所有人、所有行业的实践都来参与。在史学界许多涉及历史认识检验的论说中,诸如“作为检验历史认识真理性标准的实践,应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实践”“历史研究的结论……最终要由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进程的社会实践来检验”等类似的说法屡见不鲜,实乃大言无当。试想工厂中制造飞机、汽车、服装、食品、农药等等生产活动,加上所有政治活动的实践,怎么能够检验我们对王夫之的历史评价?怎么能够检验我们对《明史》的评价呢?这是根本做不到的。直接检验历史认识的实践,总会是历史学学术性质的实践。因此在历史认识检验标准的问题上,可以得出高度概括而又准确的命题:
史学界共同进行的历史学学术实践,是检验历史认识的唯一标准。
所谓“史学界共同进行的历史学学术实践”,这里的“史学界”,是说当代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认识检验的成员,主要应当由专业的史家承担,但“史学界”不是一种身份的固定畛域,任何人参与学术性的历史研究,皆等于加入了史学界,是其中平等的一员。而“共同进行”的实践,是每个学者研究活动的总括,其中必然充满不同见解的争论。如马克思指出的“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学术论辩正是在学术实践中检验以往认识是否准确的重要机制,是现代学术实践的固有内容,是推进认识向真理迈进的动力。
在近现代社会,学术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运作系统,并且逐步扩大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所占份额。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人类的所有重要行为之是非、得失,以及人们的价值观等等,最终或早或迟都将在学术研讨中予以审视和判断。学术要审视的对象在原则上没有限制,人为的学术禁区总会打破。学术性审断的自身是发展的、不容易最终定论,而对比于其他非学术性审断,则带有最终审断的性质。
在不少的论著中,提出历史认识的史实检验、史料检验、逻辑论证等等,其实这些也都是历史学者在学术实践中的检验方法,是历史学者将之运用,而不是史实和逻辑自动出来检验历史认识。历史学者是能动的主体,其在知识结构和方法之掌握上,需要包含以下各种要素:经过核实的史料证据,人类理性认识所积累和升华而来的逻辑思维,史学以及各个学术门类的知识积累与前沿探讨,处于先进地位的历史理论,各门类的先进学术理论和方法。总之,史料、逻辑思维、研究方法、历史理论及各种前沿理论都可以被史家带入学术实践之中,对历史认识的检验发挥作用。
历史认识的检验是不断推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检验进程也同时是历史的再认识进程。真理不可穷尽,历史认识总体上没有顶峰和终点,但不是所有问题都得不到最终的解决。在史学发展中,事实上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许多史实得以考证,许多历史评论得以确立。这切实显示了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靠近的步伐,那种对历史认识持悲观和消极的态度,是毫无根据的。史学实践产生历史认识,历史认识再回到学术实践中予以检验,这个进程不断反复,实践与认识的水平都在提高,历史学从而实现发展和深化。
以历史学的学术实践观破解历史相对主义的挑战
近代以来,从西方兴起历史相对主义的流派,从理论上表现为试图否认历史认识可以检验并且消解客观的历史事实。这对国内史学界有相当大的影响,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
相对主义的历史理论,其立说主要有两大支点:第一,声言历史事件一去不复返,无法复制历史研究的对象,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做反复实验来检验,因而不能成为科学;第二,认为历史往事以及相关的记载,如果不能被史家选择,就毫无意义,进入史家头脑并且通过思想中重新构建的历史才是真历史,但经过选择和重构的材料,已经被史家的主观思想所重建,成为主观上认可的事实,就无法验证也无须验证是否符合原有的历史事件。历史相对主义的这两个支点,我们应当以历史学的学术实践观予以破解。
现在先看第一个问题。中国历史学自产生以来对求真、实录理念的坚持与贯彻。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史学产生之后,也立即确立了以如实记载为最根本准则。中国史学产生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执政者记录史事的出发点就是保存史实以作备案,当时处于政权与社会大动荡之后,也无法不如实地记载时事。至春秋时期,已经树立了“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良史”的标准为“书法不隐”等理念。尽管这种记史求真观念有时与统治者的欲望冲突,但其道义地位从未动摇,官方和私家都标榜所修史书为实录,将“善恶具书,成败毕记”“君举必书,尽直笔而不污”列为规范。我们不要因为先前史籍未能达到完全真实,就轻视这种“求真”理念,有此理念为共识,即大大遏制了记史失实的现象。
西方古典史学从希罗多德《希波战争史》开始,希罗多德每每说明他所记述的某些情节,他自己也不能相信,显示出一种求真意识。到修昔底德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即声明“这些事实是经过我尽可能严格而仔细地考证核实了的”。美国史学家J.W.汤普森指出:修昔底德“相信历史家的首要责任就是消灭那些假的事实”,他的著述中没有任何神话的成分。修昔底德真正建立起西方史学的著述规范,就是严格的求真态度。发扬修昔底德撰史传统的史学家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4—122),更富于严格的批判性,他认识到,“在历史作品中,真实应当是凌驾一切的”。这种理念,在后来的博学时代的文献汇编与鉴定、理性主义的史学思潮与德国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畅行中得到发扬。
在记史求真理念的引导和制约下,中国、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长时代的历史学运行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产生了大量的基本如实记述的史籍,历史的宏纲大线基本确立,构成大体上符合客观史实的系统认识。历史的大事件、大线索基本得到如实的再现,这是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无稽之谈所不能抹杀的。这里不是说史学遗产中不存在失实之处,不是说历史叙述中没有人们主观因素的渗入,更不是说历史研究中不遗留未能认清和未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不断的历史学学术实践中逐步解决的。但即使有些终归不能考察清楚的问题,也不能动摇历史认识的总体架构,可以说是无伤大体。
当然,上述所有对历史学文本能够大体上符合客观史实的乐观性解析,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是指史学正式产生之后,进行规范性记载的那个时间段,至于史学产生之前的传说,则另当别论。
夸大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试结合事例予以分析。例如点燃一块木材,直到烧成灰烬,我们得出木材具有可燃性的认识。为了验证这个认识,我们再次寻得一块木材,仍然燃烧直至灰烬。在这个检验之中,是重复了认识的对象即木材吗?第一块木材其实已经烧尽而不可复制了,第二块木材与第一块不会完全一致,那么实验所重复的只是人所进行的研究实践。客观历史固然不可复现,但同一历史问题的认识却可以反复进行,我们所要检验的是历史认识而并非历史研究的对象,那么有什么必要总是强调历史不能重复出现?为什么竟然不注意历史认识的实践可以反复进行呢?
历史不可再现,人所共知,但如果我们假定历史事件可以重现,也不能作为检验历史认识的根本方式,因为历史认识不单单表述历史事件的实况,更重要的是予以分析、概括、总结、评价和置于整个历史进程中的综合论断。例如关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有许多不同的评价,都属于历史认识。假如重现这一历史事件,至多增加一些直观场景的感性认识而已,这对于检验该历史问题的某种理性认识是无效的。诸如“焚书坑儒”是否属于文化专制主义行为,是否是维护政权的必要举措等等,该场景重现的意义其实不大,最终还是依靠学术实践中研究和论辩来解决。
另一问题的要害,是相对主义的历史理论强调:历史认识是史家选择材料在思想中重新构建而成,不被选择和不能得知的历史事件毫无意义,从而消解了客观历史的意义,只有经过思想重构才是真的历史,真历史是当代人构筑的。这就是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现代史”命题的含义。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念流行之后,相对主义倾向更加彻底,通过将历史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干脆将客观史实剔除于史学的话语之外。如美国学者海登·怀特说的,“历史首先是一种言语的人工制品,是一种语言运用的产物”,“历史总是我们猜测过去也是某种样子而使用诗歌构筑的一部分”。因此他坚持认为历史学与文学、艺术完全一致,都是充满想象力而用语言构造的文本。这种说法尽管形成自我循环的封闭体系,倘若将之引出其自我话语的圈子,它能够禁得住历史学实践的检验吗?
第一,历史撰述中固然存在主观因素的加入,但自史学产生以来的历史学实践,反映在系统史学史研究的成果中,显示了人们的主观因素远未淹没对客观史实的考订和梳理。这种史学史反映的基本状况,上文已述。要之,“求真”“求是”理念成为历史学的共识,这是最大最根本的“主观”意识,遏制了其他干扰史学的想象。历史相对主义思想,不符合自古以来历史学的实践及其成果。
第二,马克思主义不否认历史认识中的主观性因素,恰恰相反,而是十分重视认识上的主观能动性。在尊重史实,维护“求真”这个历史学底线上发挥历史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就会在历史学学术实践中更多地揭示具体的历史真相,而且能够获得更深层次的抽象性宏观认识。
第三,靠想象构筑的历史叙事,在史学未曾萌生的远古、上古时间段也曾存在,后来也被纳入系统的历史叙事之中,例如中国的“三皇五帝”传说。但这恰恰是历史学质疑和否决的对象,从宋代的欧阳修到清代的崔述,有力的批判持续深化,近代“古史辨”派的研究,更是作出较全面的清算。古人出于某种学术外的目的把这种传说纳入历史叙事,乃是将之指认为真实可信,内在理路依然顺从于历史叙述需要真实的理念,与历史相对主义理论认可历史想象、想象之外无他物的说法并不一致。至于近现代,随着考古学与基因人类学迅速发展,人类社会的远古状况正逐步揭开,这一久远逝去的历史时代,也具备了丰富的客观资料,是可以被研究、可以被认识的,不是靠想象来构建。历史相对主义理论在这一领域,也没有立足之地。
第四,历史相对主义的理论家,大多没有做过历史研究,大多没有尝试美国史、欧洲史或任何一处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同时他们对于系统的史学史的知识体系不甚了了,特别是对于中国史学史的系统知识,甚至是一片蒙昧。史学理论本应当在总结自古以来历史学实践状况中、在学者自身的史学实践中得出,历史相对主义的理论家则在这方面一切缺如。那么,历史相对主义这种什么实践基础都缺乏的理论从何而来呢?也许是靠收集某些哲学思潮、文艺思潮的泡沫,再经过想象加工、推衍发挥而成。这种活动如果也算是一种实践,那也不是历史学的实践,其结论不应该当作史学理论。
综上所述,历史相对主义理论,与古往今来历史学的实践完全脱节,它自身也没有学术实践的基础。因此,这种理论犹如海潮上的浪花和泡沫,虽然容易被看到也比较引人注目,但只能即生即灭,并不能融入历史学大海的深层内容及结构。只要坚持历史学学术实践观,就不难解决历史认识论上的难题,不难破解形形色色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历史思想的冲击。
在根本的意义上,人的认识缘起于人类的实践,而认识又回到实践中被检验,此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历史认识论是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做这项研究的学者,不能只是在中外历史学理论“文本”的圈子里打转,应当把自己的认识联系历史学的实践:第一是深入了解以往的历史学实践及其成果,即掌握系统的中外史学史知识;第二是关注和梳理当下的历史研究状态;第三是拥有自己切实研究历史问题的体验。否则难以抵制各种错误史学观念的影响,难以做出史学理论建设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