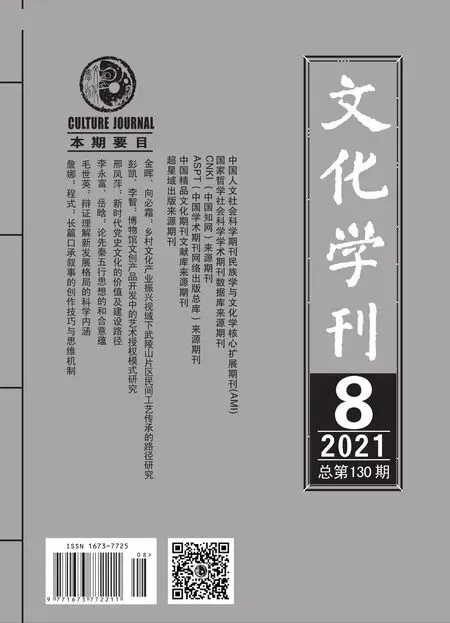四川古籍普查史研究
杜 鹃
引 言
关于古籍,文化部发布的《古籍定级标准》(WHJT 20-2006)定义为:“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从时间和装帧形式上对古籍进行了界定,而目前学术界也普遍采用这一定义。古籍普查就是对现存古籍的品种、数量、级别等所进行的全面调查、鉴定和记录, 结果比较全面、准确,但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较大,耗用时间也较长。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古籍普查工作,组织开展过两次重要的古籍普查工作:第一次是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制为目的的古籍善本普查;第二次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下的全国古籍普查。这两次古籍普查都是国家实施的重点项目。作为古籍资源大省,四川在这两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摸清古籍家底,推进古籍保护,培养古籍整理编目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两次普查的研究,前者着重于对普查成果也就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研究,知网上关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文章有51篇,着重于对书目内容的探讨,仅有3篇从整体的工作历程或是编纂史的角度来关注普查过程,缺乏区域性普查工作研究。2007年启动的古籍普查,知网上有相关文章131篇,主要从本地区普查实践出发,或围绕具体工作探讨著录细节,或分析工作现状,或展开工作思考等。没有从某一区域的角度对这两次重要的普查工作展开系统性整体性的考察,比较异同,总结相关工作经验。本文以四川为样本,从普查史的角度考察这两次古籍普查的历史背景、普查标准、工作机制与普查成果,分析其历史特点,并展开思考。
一、四川古籍善本普查
善本古籍普查是贯彻周总理作出的“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总目编出来”的重要指示,由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分为北片和南片编辑组,其中四川省图书馆参加的南片编辑组由上海图书馆牵头。四川省善本古籍普查开始于1978年,并参照全国善本古籍普查的工作机制,成立了四川省古籍善本编辑领导小组、版本鉴定小组,在省图书馆成立办公室,负责统筹全省的普查工作。普查标准为1911年以前,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或“在省内具有一定特色”「1」的古籍。这一范围是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注重四川的收藏特色,将普查范围延伸到清末的一些刻本和抄本。以经部尚书类为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收录四川10种,而四川省善本古籍普查收录32种,其中稿本《尚书大统集解》为清末民国经学大师廖平撰写,民国抄本《禹贡集注》为尊经书院学生杨琮典撰,都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稿抄本,丰富和完善了四川善本古籍品种。
善本普查从动员各单位开展普查,编目制卡、卡片审核、上报目录至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到编纂《四川省古籍善本书联合目录》经历了10年时间。其中卡片的汇总审核是一项纷繁复杂的工作,反映在卡片上的问题很多,如收录范围偏宽,卡片著录未能严格按规则进行,书名、著者项有大量错误,版本鉴定问题较多等,以至从1980年4月初编工作告一段落到1988年10月《联合目录》的正式出版,历时8年。换言之,善本古籍普查80%的时间主要用于数据的初审、复审以及成果的最终形成,这也正是古籍普查工作的特点和难点。经过普查,全省发现善本古籍5100余部,10.3万余册,主要收藏在以省图书馆、成都市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北碚区图书馆、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重庆大学图书馆为主的37家古籍收藏单位,其中有4757部收入《全国古籍善本书目》。通过分析普查成果《四川省古籍善本书联合目录》,在分类上基本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保持一致,如在四库分类法的基础上增设丛书为一部,较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于末卷列“丛书目”更进一步。但是款目不著录行款,可为是目录编纂的一种缺憾,如《荀子二十卷》下仅罗列明刻本三种,难以确定是否为同一版本,或是其间的区别,在作为目录的使用性上是有所欠缺的。
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下的四川古籍普查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正式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提出“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级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及民间所藏古籍情况”。并在国家图书馆成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负责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参照国家层面做法,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也于同年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川办发〔2007〕61号),并在省图书馆成立省古籍保护中心,负责全省的古籍普查工作。在此框架下,四川历史上第一次覆盖全省的古籍普查正式启动。
(一)普查标准与款目
按照《全国古籍普查登记手册》的普查标准,古籍的下限为1911年,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传统装帧书籍是排除在古籍认定范围之外的。如果简单以时间划定古籍的界限,是不符合书籍延续发展的历史的,正如黄永年所说:“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炉灶,如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或旧体诗文集之类,一般仍可划入古籍范围。”「2」这一界定是符合古籍的发展与特点的。而且在普查的实践工作中,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传统装帧书籍在省内各古籍收藏单位尤其是基层单位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此处仅以德阳市为例,来管窥线装书在各收藏单位的比重。

表1 绵阳市4家单位馆藏古籍统计表
4家古籍收藏单位中,有3家古籍藏量明显小于民国线装书的数量,这也从侧面反应了民国时期四川藏书和文化发展的状况,所以在普查工作中也将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具有传统装帧形式的书籍纳入普查范围。
这一次普查,在款目著录上经历了一次大的调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研发了“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内容包括分类、题名卷数、著者、版本、版式、装帧、装具、序跋、刻工、批校题跋 、钤印、附件、文献来源、修复历史、丛书子目、定级、定损、相关书影等信息,涉及字段100余项,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古籍编目工作。对于一部古籍而言,普查平台的著录内容对于清晰地揭示每种书的版印缘起、版刻源流、版本系统、版本优劣和递藏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能够对古籍研究者提供很大帮助。但这一著录标准对编目人员的业务素养要求高,许多基层古籍收藏单位基础数据不成熟,难以完成著录工作。据统计,全省参加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的单位一共有49家,但最后只有5家单位能在平台上完成著录,严重影响了古籍普查工作效率,也影响了普查工作的积极性。
为了协调目录的专业性与摸清家底之间的关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于2012年发布《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方案》,调整著录内容。将著录标准简化到6个必填项目,包括:索书号、题名卷数、著者(含著作方式)、版本、册数、存缺卷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逐步扩展项目,完成分类、批校题跋、版式、装帧形式、丛书子目、书影、破损状况等内容。著录形式也由“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的单一著录,转为平台与EXCLE表格皆可著录,即 “十三项”表格。作为古籍普查来说,“十三项”的著录标准基本能够揭示出一部书的外在形态,既解决了普查的效率问题,也满足了基本目录查询的需要。
(二)工作机制
在普查实施过程中,工作机制也发生了几次转变。启动之初,围绕古籍普查平台著录,普遍反映出古籍编目人才匮乏、著录质量不高等问题,这也导致了从2007年到2012年间,全省古籍普查工作进展缓慢,只有27家古籍收藏单位在开展普查工作。2013年,全省建立从“登记目录—古籍总目”两步走的工作机制,通过古籍普查登记形成《四川省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并在此基础上完善著录款目,形成《中华古籍总目·四川卷》与四川古籍书目数据库,逐步从普查账目的建立到专业化目录过渡。工作机制的转变,一方面实现了资产核查摸清家底的目的,另一方面也通过降低工作要求,解决了普查人才匮乏的问题。
(三)普查成果
目前共提交普查目录23万条,开始进入数据的汇总与审核工作。已出版的阶段性成果《四川省十一家单位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按流水号排序,因缺乏古籍目录最基本的分类项,其作用发挥有限,主要为资产登记、检索馆藏地。要形成专业性的版本目录,需要依分类体系,按经、史、子、集、丛分部类完成数据的初审、复审和定稿。从提交的数据来看,存在著录内容缺失、版本鉴定错误、丛书未合并等专业问题。相较于善本古籍普查,审校的难度更大,如何兼顾审校质量与工作效率,形成可利用的普查成果是下一步需要深入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四)经验分析
普查史的研究除了梳理普查的历史过程,还要关注两次普查的成功经验与总结分析。一是两次普查都建立了有效的工作机制,第一次是紧紧围绕善本书目的编纂,从汇编、审查到定稿,既完成了向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上报卡片的工作,也编纂形成四川省的古籍善本联合目录;第二次通过建立省古籍保护中心,统筹指导全省的古籍普查工作,分省、市、县三级,完成了全省21市(州)138家单位的古籍普查,而其间通过调整著录标准也成为普查工作顺利推行的重要原因。二是两次普查都培育了一批古籍版本整理人才,古籍整理是一项实践性很强、注重经验传承的工作,在普查过程中,通过过眼大量的古籍,结合版本、目录、文献学的相关知识,培养了一批热爱古籍整理事业的年轻人。三是对古籍的认识不断深化,第一次以编善本古籍书目为目的,重点是摸清家底;第二次从机构设置上,就明确了以普查为基础,加强保护修复、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这也反应了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对古籍工作的认识也更加全面与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