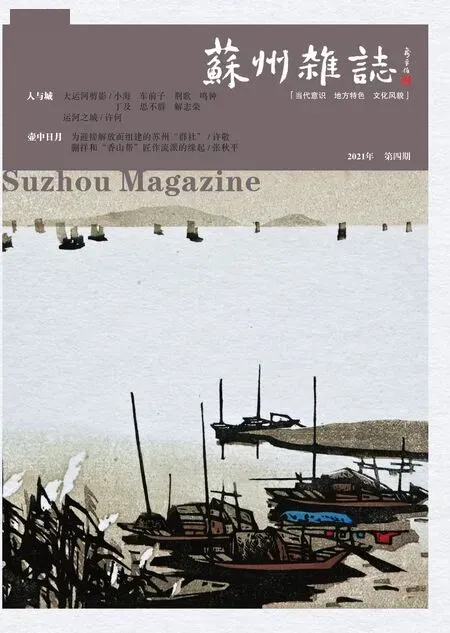一方风物
王茵芬
场院
往日村庄里家家户户有场院,用青砖铺就,像一方厚实粗糙的老土布,在日常里接纳各种生命,鸟飞上去,阳光在它的翅膀上追逐,土布不再是块土布,变成一张金属唱片。麦子熟了,稻子黄了,场院堆满粮食和柴草;秋收时节,黄豆、玉米、芝麻、高粱等农作物都会陆续来访;冬来,腌制咸菜和萝卜干的光景,场院最起码被它们占据几个日头,接着是芒草、枯枝落叶等柴禾的天地。
有关场院的记忆早已绕成一个线团,一旦拉出线头,就会越拽越长,颜色泛着麦秸的黄和青苔的苍绿。那些散落的时间,失散的亲人,遗忘的事件和物件,全都争先恐后地赶上来,与我重逢。
我的奶奶永远住在这个记忆的线团里。常出现的场景是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上,奶奶拄着楝木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在我的前面,坑坑洼洼的泥土路通往小镇。奶奶在一个针织厂里做摇线工,我在小学读书。
偶尔,奶奶带我去娘家看望她的母亲。奶奶屁股一侧的骨头生了东西,动过两次手术,一条腿走久后会隐隐酸痛。我们便在路过的人家场院边歇脚,找一块石板坐下。那是个夏日傍晚,场院上晒着一地欲黄未黄的草。我知道,这些草晒干后,就要用稻柴捆成一个个草干团,藏在茅舍里,是给羊储备过冬的粮草。一个大男孩在不紧不慢地收拢着场院上的干草。男孩朝我们看过来,他的眼睛很大,在夕阳里,目光尤其干净明亮。我和奶奶的身上披了一层余晖,相互依偎。一场草,被男孩堆在一起,它们被男孩的手轻轻地摩挲着,就像奶奶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发。就这样,我们坐在暖色里。
奶奶的母亲,我叫她老太太,八十多岁,满头银发向后梳成一个髻,一张满是皱褶的脸,有点扁,牙齿落光了,嘴瘪瘪的。每到腊月,老太太会来我家住个十来天。奶奶总慢笃笃地说,老太太不是来吃闲饭的,好多活等着她做呢。
老太太像我家的一张被屁股磨得光滑柔顺的草绳板凳,朴素憨厚,默不作声。和她说话,大多时候报以微笑。想不起来她和我说过几句话。记得那年夏天,人们都在为可能发生的地震做准备。老太太特地到我们家来,和奶奶一起做麦面饼。麦面饼是用面粉做的,有咸的,有甜的,薄薄的,圆圆的,一张张贴在铁锅上烙,烙到外皮有点焦黄,硬中带松脆。按往常,饼子烙得少,菜油自然多些,麦饼更香。这次的饼太多,只在锅壁上抹上一薄层油。待饼子烙熟后,用夹子夹起来,放进竹匾里摊开,等它们凉了,装进一只大坛子里,用麦秸编的盖子,盖严实,再包上塑料薄膜。说是一旦发生地震,没啥吃,就可以啃麦面饼。当然,还得储存井水,把井水灌在塑料桶或瓮内。我父亲把坛子和水瓮分别搬到场院上的草棚里,草棚是临时搭建的,原本是生产队的瓜棚。我当时总喜欢跟在大人身后,感觉很有趣,忘记了地震的可怖。老太太在砖场上,安详地坐在那张草绳板凳上折叠麦秸草把。她微笑着和我说,晚上住草棚里吧,床上张了蚊帐。我学她平和的模样,慢慢地摇头,其实是怕夜晚会不会有蛇游进去。
那次的地震警报持续了大约半个月。直到有天深夜打雷刮风下暴雨,感觉到房屋有点晃动,但没出现倒塌事故,大家的心才安定下来。那会儿,老太太和奶奶一直住草棚,母女难得有这么长时间生活在一起,每天都乐呵呵的,真有点因祸得福。
到了这年仲秋,母亲把我养的一只老湖羊牵到场院中间,让它卧在一块草席上,准备剪羊毛。那天的阳光特别干净耀眼,照得老湖羊懒洋洋地闭上了眼,母亲把一只布袋套在它的头上。她利索地使用着剪刀,有顺序地从羊肚开始剪,“咔擦咔擦”,动作慢腾腾的,生怕刀尖划破羊的皮肉,把白净的羊毛顺手堆放在草席上。当时,我只觉得那一地羊毛仿佛一堆麦秸在燃烧,整个场院被映得黄灿灿的,宛如一块巨大的面包。
场院,让我看见了生命的接纳和孕育。
菜地
场院前的一块菜地,被父母侍弄了大半生,是他们多年的“菜篮子”。父母各有分工,父亲干的是体力活,翻地、浇水、施肥、除虫、搭棚,母亲的活轻一点,播种、栽苗、除草、摘菜。
当山芋藤活泼泼满地跑时,杂草也不甘示弱,疯长着,母亲头戴遮阳帽,穿一身花花绿绿的衣服,蹲在一片浓绿里。她的背越来越驼了。那些野草有的注定开出花来,有的照例结籽。阳光一寸一寸踩过山芋藤蔓,土里的山芋在长个儿。母亲的影子在这片菜地上移动,像一个“瓜”字。
记得那次回家,母亲悄悄把我叫到房间,从旧木箱底下摸出一个布包,这块布是二十多年前我买给她的一方手帕。给过她皮夹的,她嫌用起来麻烦。打开手帕,几张不同面值的钞票,最多三四百元钱。她把一张五十元的钞票塞进我手里,让我买一只收音机,说是去菜地里带在身边,听听老戏。我看着母亲的憨样,忍不住笑了,把钱还给她。今天,母亲又拿出二十元钱,要买一条丝巾,秋天了,外面的风太凉。我每年买围巾给她的,它们都被她遗忘在哪个角落了。以前的事,她记得特别清楚,总记不得当下的事。
母亲十多年前得过抑郁症,现在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她几乎每天把自己的几双鞋子抱出来晒太阳。她忘记自己老了。这样也好。
母亲把杂草晒在家门前的场地上。我喜欢青草被阳光踩过后散发出的香味,俯身嗅着,想起母亲以前常说的一句话,人,有时候还不如一棵草。
场院西边搭着一架丝瓜棚。秋阳下,叶子显得苍老,一些花朵却开得有力,绿荫里的小丝瓜在长,长不大,就要老的,老在深秋里。
菜地里多了一棵木兰树。如果没有躲在桠杈间的鸟窝引起我的注意,或许不会在意一棵叶子泛黄的树。未曾见过这棵树开花的样子。它笔挺地站在那里,主干修长,枝条疏朗。母亲告诉我,三年前的早春,父亲去小镇路上,发现这棵树歪倒在废墟里。原本瘦弱的它遭遇硬物撞击,并挤压,根部几乎裸露,是主人遗弃了它,抑或无处安置它,不得而知。父亲弯下僵硬的腰,扶起它,抱在怀里。他像收养一个受伤的弃儿,将树种在菜地,用木棍和绳子固定主干,好让它挺直了往上生长。
泥土的气息唤醒了木兰树。它身上的伤痛被沃土治愈,在父亲期望的目光里一个劲地长高,长大。
鸟窝非常精致。这该是哪种鸟安的家?听父亲说,有灵性的鸟喜与人亲近、共处,把窝搭在家门前向阳的树上,这也说明家园的风水好。
菜地不大,一棵树的生命却是这般辽阔,可以让鸟儿栖息,搭窝,繁衍生息。
父亲拎着一把铁锹走上来,说,掘几个萝卜给我。他步子迟缓,腰明显弯了。内心不禁一阵酸楚,这些年,我忽略的仅仅是一棵树吗?一时无语,连“哦”这个字也哽在喉咙里了。自然的秩序,这样了然,顿生惆怅之意。
几十年来,父母种了一茬又一茬的蔬菜,菜地依然年轻,而他们老了,“老得像一个影子”。
河滩小径
菜地边的河滩小径,窄而短,两根扁担的长度,我走了半生。
一个盛夏的午间,来到小径,和两旁杂草欢喜相逢。首先和我打招呼的益母草,有点清瘦,穿着紫红碎花袍子;一个少年般的大叶紫苏微笑着,站在几个顽皮的车前草身旁;一群蓼草向我舞动起柔姿,串串粉红花穗像姑娘的辫子;刺苋和蒲公英在风中歌唱;马齿苋有点害羞,露着半边脸;艾草在稍远的河岸,像少年的伙伴们,天真无邪,走向青春。
河滩头的栀子花开得静美,花不再是那时的花。当年的我在河边蹲着,水里摇摇晃晃的影子有点瘦弱,像岸上那棵结着青毛桃的小桃树,在贫瘠的土地上成长。河滩石长得难看,也就四五级,蹲着的一块平实多了,下面还有一块长着青苔,静静地卧在河里。一群小鱼游了过来,我试图赤脚踏进下面的石板,“啪”一屁股跌坐在上面的石上,吓得缩成一团,不敢哭,只能坐着,坐在疼痛里,等自己长大。
两岸的各种树们长得茂密,如同一个绿棚,搭在原本很窄的河面上。河滩的风清凉里夹着些许水腥味。岸边老枫杨树上鸟鸣和夏蝉叫得欢。东南风吹着树下的草花,一年蓬野性十足,却又不失窈窕,而一种顶着紫色花冠的马刺蓟草显得拙朴,它们本来是被风播撒在这一带的,和从前乡间女孩一样,土气中透出清秀,自然生长着。每种植物都是有名字的,它们的形状、色彩、味道和品质都包含在名字里。
忽而,一只白鹭飞过,被风追赶着,停歇在合欢树的枝头,合欢花纷纷飘落,铺在浅绿色的水波上,像一块花布,散发出丝丝缕缕的香气,随之而来的,是静谧和安宁。生命延续繁殖,滋濡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往往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就这么一条小径,依然为我保留着尘世的纯真和素朴。或许,这是属于父母辈和我这样一代人的一种草木情怀了。
父亲拿着一把镰刀走上来,要割些朴树的枝叶,问及何用,父亲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话声很低,你大伯想趁活着闻闻家乡的味道。
几年前,八十多岁的大伯中风瘫痪了。他幼年父母因病双亡,由我奶奶抚养,少时离家去上海做学徒,成家后定居北方一个小城。
大伯半辈子驻扎西北修铁路,修到远方,远到戈壁滩。1970年代,作为一名工程师赴坦桑尼亚援建坦赞铁路,沿线环境恶劣,大伯险些献出宝贵的生命,回不了祖国。他可以用脚步丈量漫长的铁路线,而故乡于他,唯有用心抵达。
奶奶在世时,大伯每年寄家书和钱物。我给奶奶念过许多封信,开头的称呼始终是“母亲大人膝下、贤弟”。那时,觉得大伯真迂腐。奶奶也每年给大伯寄一些自家的风干食物,比如山芋干、毛豆荚干、柿饼……除了这些,还寄晒干的草木。
这些年,大伯每次打我父亲电话,一开口就诉苦:“我回不去了。”哽咽着,继而,像一个孩子,呜呜大哭。稍许平静后问:“我小时候种的朴树在不在啊?”
那棵朴树在河岸的最西边,高大挺拔,树冠婆娑,已有75年树龄,是大伯12岁离开家乡时栽种的,他希望让这棵朴树替他扎根在这块血脉之地,还因朴树生命力顽强,象征着一种朴实的品格,他要自己长成一棵朴树。
每年,父亲都会在树身上采摘一些叶子、剪若干细枝条,晒干后,用塑料袋包得整整齐齐,去邮局寄给大伯。
我年少时,大伯每次回转故里,总带着他的相机,给我们拍照,也常看见他站在朴树下,把照相机按在一个三脚架子上,然后听到“咔嚓”一声。后来我才知道大伯在给自己拍照。
现在,大伯和父亲都老了,又相隔千里,无法团聚,唯有小径和朴树能让他们的两颗心靠在一起,相互安慰。河滩小径,在我们的生命里不断延伸、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