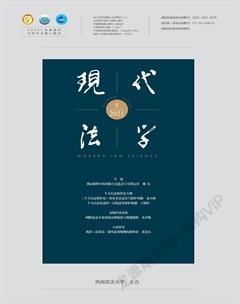论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公司抗辩权
摘 要:在我国目前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股东是诉讼的决定者,公司作为原本的请求权主体的诉讼决定权和抗辩权却被忽视了。在未来的《公司法》修订中,可以考虑增加股东派生诉讼的庭前司法审查程序,将原告股东资格、前置程序要件、公司利益受损的事实和违反公司利益的重大事由均列为审查事项。在该程序中,公司得以诉讼违反公司最佳利益为由行使抗辩权,以阻止诉讼的进行。法院对上述事项进行审查,特别是对公司抗辩事由进行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后决定是否进入股东派生诉讼的庭审程序,以此实现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平衡,并降低司法成本。
关键词:股东派生诉讼;公司抗辩权;庭前司法审查;《公司法》改革
中图分类号:DF591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 j. issn.1001-2397.2021.05.0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在股东派生诉讼中,由于原告股东主张的是本该属于公司的请求权,出现了行权主体与请求权内容及诉讼利益归属对象间的错位,这已然包含了股东与公司间的利益冲突。我国目前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尽管前置程序的安排要求原告股东必须首先要求公司自己起诉,但是并未给予公司针对诉讼向法院发表意见的机会,忽视了公司作为原本的请求权主体的诉讼决定权和抗辩权。本文将首先分析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公司抗辩权的缺失,之后探讨赋予公司抗辩权的原因,最后主张在现有的股东派生诉讼程序中引入庭前司法审查程序,赋予公司在此程序中进行抗辩的权利,并由法院经过审查后最终决定是否进入股东派生诉讼的庭审程序,从而在股东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权利与公司事务自治权间找到平衡。
一、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公司抗辩权的缺失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51条的规定,在可以提起股东派生诉讼的场合,满足条件的股东必须首先书面请求相应的公司机关代表公司起诉;只有在公司拒绝起诉或者自收到书面请求之日起的30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等三种情况下,股东才可以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此可见,除了紧急情况下的前置程序豁免情形,只要股东事先请求公司自己起诉但遭到拒绝或者公司未予及时回复,其即可以自己名义向法院提起股东派生诉讼,并直接进入庭审程序。股东由此掌握了启动诉讼的主动权,公司则只能作为第三人被动参加诉讼。在诉讼程序中,法院只会审查原告股东是否适格,是否履行了前置程序,以及诉请的事实和依据是否正当,至于公司因何拒绝起诉,或者公司拒绝起诉是否有正当理由,则并不在法院的审查范围内。也就是说,一旦股东启动了派生诉讼程序,公司便丧失了诉讼决定权,也不能以诉讼违反公司最佳利益为由阻止诉讼的进行。
在有些国家的股东派生诉讼程序设计中则赋予了公司抗辩权,比如德国和美国。德国在股东派生诉讼程序之前设置了一个独立的前置性司法审查程序,并在该程序中允许公司提出诉讼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抗辩。在德国,股东派生诉讼涉及两个程序:一个是诉讼许可程序(Klagezulassungsverfahren),一个是责任诉讼程序(Haftungsklage)。前者是后者的前置程序,即只有在前一个程序得到法院许可后,才能进入后一个程序,也就是股东派生诉讼程序。《德国股份法》第148条对诉讼许可程序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详细规定。在诉讼许可程序这一简易程序中,法院需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审查,分别涉及原告的持股时间、已经请求过公司自己起诉、合理怀疑公司因不忠实或者重大违法或违反章程而受到损害的事实以及是否存在与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相矛盾的公司利益方面的重大事由。①尽管在此程序中,申请人是股东,被申请人是董事、高管等派生诉讼的被告,公司只是作为第三人(Dritter/Beigeladener)参加,但公司需要承担公司利益冲突的举证责任。②如果公司能够举证证明訴讼的进行与公司利益相矛盾,而且经过考量,公司利益要比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更为重要,则法院会驳回原告股东的诉讼许可请求,股东派生诉讼程序不会被启动。《德国股份法》第148条第1款第2句第4项实际上赋予了公司抗辩的权利。美国的股东派生诉讼程序中虽然没有独立的前置性司法审查程序,但是也给予了公司发表抗辩意见的机会。在美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司法实践中,原告股东要求公司自己起诉但被拒绝后,其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股东派生诉讼。为应对此诉讼,公司董事会往往任命无利害关系董事组成特别诉讼委员会,授予其董事会的全部权力,对派生诉讼所控告的交易或者行为进行调查,决定是否应该继续进行诉讼。特别诉讼委员会经过调查,如果认为继续进行诉讼不符合公司最佳利益,则会要求公司向法院提出驳回起诉的动议。法院经过审查后,如果支持特别诉讼委员会的结论,则会终止诉讼,否则,继续进行派生诉讼程序。公司提出驳回起诉的动议和法院对该动议的审查,均发生在股东起诉之后、庭审开始之前,也就是股东派生诉讼程序的早期阶段。
德国的诉讼许可程序和美国的庭前司法审查程序,均发生于进入股东派生诉讼实体审理程序之前,决定着股东派生诉讼程序是否能够实质进行。无论是德国诉讼许可程序中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重大事由的举证,还是美国股东派生诉讼庭前司法审查程序中提出驳回诉讼的动议,均是公司行使抗辩权以阻止股东派生诉讼的表现。这样的程序安排无疑是为了平衡股东和公司的利益。股东尽管有派生诉讼提起权,但是毕竟公司才是原本的请求权人,其不起诉的决定作为公司的内部决策,理应首先得到尊重。
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其前置程序、股东起诉和庭审程序之间是“无缝衔接”的。公司在庭审前没有陈述其拒绝起诉的理由的机会,在庭审中作为第三人也不享有诉讼当事人的抗辩权利,所以,即使公司有充分的理由能够证明诉讼不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也无法阻止诉讼的进行,其要么接受股东的请求自己起诉,要么被动进入诉讼程序。显然,在我国《公司法》第151条所设计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立法者更多考虑了股东起诉的权利,突出了保护小股东利益的立法立场,而忽视了公司作为原本的请求权人对诉讼的决定权和不起诉的抗辩权,造成了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失衡。
据黄辉教授对国内2006年至2010年的股东派生诉讼案件的实证分析,在60个样本案例中,有19个案例中股东履行了前置程序,先请求公司自己起诉,其中5个案例中公司明确拒绝,14个案例中公司没有在收到请求后的30天内回复。但是,在所有的19个案例中,法院都没有讨论为什么公司拒绝或不予答复。“换言之,只要公司拒绝或不予答复,法院就允许股东提起派生诉讼,而不问原因”①,于是,即使是恶意的派生诉讼,公司也无法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有法院审理方面的原因,但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 实际上,在所有的股东派生诉讼案例中,法院均不需要考虑公司拒绝起诉或者不予回复的理由,因为立法上并未赋予公司抗辩权,公司也只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即使公司在诉讼中陈述不起诉的理由,也不会影响裁判的结果。
二、赋予公司抗辩权的原因
(一)股东是公司请求权的代行者
股东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派生诉讼的前提条件是公司拒绝起诉,怠于追究相关主体的损害赔偿责任或者违约责任。为此,各国公司法无一例外将股东请求公司自己起诉作为允许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前提条件。《美国民事诉讼法》第23.1条规定的“请求要件”(demand requirement),《德国股份法》第148条规定的股东必须证明其已经要求公司自己起诉但徒劳无果,这与我国股东派生诉讼中前置程序的要求本质上是一致的。按照德国法的规定,即使法院作出了许可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裁定,三个月内股东也必须还要再一次请求公司自己起诉,如果公司仍然不起诉,股东才可以启动股东派生诉讼程序,且公司随时可以自己起诉或者继续已经启动的派生诉讼。这说明,立法者通过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并非是为了赋予股东诉权而剥夺公司的诉权,而是促使公司自己主张请求权,只有在穷尽公司内部救济措施而公司仍然不起诉的情况下,才允许股东代表公司主张请求权。
股东的诉权派生于公司的诉权,此乃股东派生诉讼名称的由来。股东派生诉讼是公司直接诉讼的替代性措施。股东主张的是公司的权利,胜诉利益也归于公司,而非股东本身。因此,在美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股东被认为是名义上的原告(nominal plaintiff),而公司则是真正的利益方(the real party in interest)。①股东提起派生诉讼是基于公司利益受损,是为了实现公司的请求权,但是,公司是否主张及如何主张该项权利,则是公司的内部经营决策事项,公司本身应该有诉讼的决定权。基于此,在美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董事会收到原告股东要求公司起诉的请求后,有权经过调查之后以诉讼不符合公司最佳利益为由,拒绝起诉或者在诉讼开始后做出终止诉讼的决定,提出驳回诉讼的动议。在德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首先必须由法院审查股东的诉讼许可申请,其中审查事项之一即为是否存在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重大事由,也就是公司应举证证明派生诉讼与公司利益存在重大冲突。这样的安排,无疑是对公司诉权和公司自治的尊重。公司是推定的股东派生诉讼的受益人,法院作出终止或者继续进行诉讼的裁决,应该考虑诉讼对公司的整体影响,在进行评估时,法院应该考虑公司对诉讼影响的意见。②
作为原本的请求权人,公司有权利和能力从公司最佳利益出发决定是否必须通过诉讼途径主张权利。股东只是公司权利的代行者,其违反公司意志提起派生诉讼时,应给予公司向法院陈述其抗辩意见的机会,并在其抗辩具有正当性的情况下阻止股东派生诉讼的进行。当然,鉴于公司通常被大股东或者大股东委任的董事所控制,其不起诉,特别是针对大股东、董事和高管不起诉的抗辩是否正当合理,需要由法院依法进行审查,并最终裁定。
(二)公司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评判者
公司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处于复杂的经济活动中,一个决策的做出往往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成本收益的考量和各种风险的评估,进行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的衡量。特别是当考虑到公司利益的时候,公司的名誉、未来的发展、管理層的稳定等方面的非财产性利益,有时候要比财产损失对公司利益的负面影响更大。公司具有经济人的属性,当其利益受到董事等管理层侵害后,也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根据现行法律体系所提供的价格机制约束条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去选择是否起诉。③
股东虽然被赋予了派生诉讼提起权,却并不一定能从公司的最佳利益出发行使权利。为了鼓励股东提起派生诉讼,保护小股东利益,发挥股东监督公司管理的功能,各国法律往往并不会为原告股东资格设置过高的条件,从而使得持股比例很小的股东就可以提起股东派生诉讼。这意味着无论公司胜诉还是败诉,对原告股东构成的直接影响都很小,因此,他们很少有动力去考虑这一诉讼对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影响。“股东替公司做主,自行决定是否将公司拖入诉讼未必符合公司或其他股东的最大利益”④,而“董事会关心的是公司不会被(股东诉讼的)善意杀死”⑤。 此外,“股东通常不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如果股东拥有继续进行诉讼的绝对控制权,而该诉讼最终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害,该股东并不需要对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承担责任”①。 因此,“股东并不是决定派生诉讼是否符合公司利益的适当人选”②,不能指望诉讼对公司经济的有害影响能指引原告股东的诉讼决定。③
董事会作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机关,能够基于对公司经营情况的全面了解和专业知识经验而做出对公司最为有利的决定,当然前提是其具有与被诉对象无利害关系的独立性。诉与非诉,均应该是基于公司最佳利益考量做出的选择。公司拒绝起诉,并不意味着公司拒绝解决问题或者包庇有不当行为的董事、高管。有时候,诉讼并不一定是合乎公司利益的最佳方式。高昂的诉讼成本、时间成本和有关人员付出的精力,甚至诉讼公开带来的对公司形象的负面影响以及对员工士气的打击,都会让公司宁愿选择非诉讼的方式在公司内部解决争端。
是否起诉和如何主张权利属于公司内部事务,首先应该交由公司自己决定。法院即使基于股东诉权的行使能够干涉公司内部事务,也应该首先听取公司的意见,而不是仅仅基于公司拒绝起诉的结果就强制公司进入派生诉讼程序。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主体,其自身有决定内部事务的权利,也有能力基于通盘考虑做出选择。在符合公司最佳利益的前提下,这种选择应该得到尊重。
(三)防止诉权滥用
股东派生诉讼得以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针对公司董事和高管的违反义务的行为。由于董事和高管在公司中掌控着管理权,对其违反义务的行为,其他董事往往会出于同事情谊避免通过诉讼途径予以追究,甚至选任他们的大股东也大都会采取姑息政策,此时,股东代表公司起诉这些违反义务的董事、高管,就成为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必要手段,也使股东派生诉讼成为股东监督董事、高管的有效工具。但是,毕竟股东不是原本的请求权人,诉讼结果与其自身利益没有直接的关联,股东有可能不会顾及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而提起派生诉讼。此种滥权行为不仅不能起到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目的,反而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对公司造成有害的影响。为此,在股东派生诉讼的制度设计中,一方面要鼓励股东积极行使诉权,发挥股东的监督作用,对意图违反信义义务的董事、高管产生威慑力;另一方面则要防止股东滥权行为,阻止无价值的诉讼对公司的伤害。
防止股东滥权是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之一,体现在规则制定的多个方面,如对原告股东持股时间或者持股数额的限制、败诉时股东承担诉讼费用的分配原则、股东提供担保的规定等。而在股东派生诉讼程序前或者早期阶段设置司法许可或者审查程序,实际上也体现了对股东滥权的限制。德国的诉讼许可程序使股东派生诉讼的启动依赖于司法控制的框架条件,确定了具有过滤功能的阻止滥权的实施条件。④美国股东派生诉讼中对诉讼所涉交易或者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终止诉讼决定的特别诉讼委员会,则为公司在诉讼的早期阶段提供了使其摆脱无价值或者有害诉讼及“强袭诉讼”①(strike suit)的重要工具。②英国2006年《公司法》将股东派生诉讼分为两个阶段。股东欲提起派生诉讼,必须在第一阶段满足相关要求,经法官允许后才能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真正的股东派生诉讼阶段,而“法律委员会(Law Commission)在设置派生诉讼时,有意分开两阶段,即是为了防止股东滥用诉权,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③。
在我国现有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设计中,公司拒绝起诉后,股东即可直接提起派生诉讼并进入庭审程序,于是,是股东而非公司主导了诉讼活动。即使公司有充分理由认为诉讼的进行不符合公司最佳利益,其也无从申辩并阻止诉讼的进行。虽然这样的程序设计便利了股东提起派生诉讼,但完全不考虑公司的合理抗辩,实际上对公司并不公平,不仅忽视了公司作为原本的请求权人应有的权利,而且容易造成股东滥用诉权。如在“王存棉与上海绿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中,法院认为,“海博公司在与绿地建设公司结算买卖合同尾款时,自愿放弃891.39元的货款零头,并向绿地建设公司出具账款结清的收据,双方据此结清货款。海博公司与绿地建设公司的上述行为均系各自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行为,并无损害一方公司利益的事实,且海博公司系家族企业,海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海军系王存棉之子,王海军基于公司经营管理之需要而未在王存棉起诉前同意以公司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亦不构成对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损害。”④该案历经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法院最终还是以案涉交易乃公司正常经营管理行为为由未支持股东的派生诉讼请求,但是,这样漫长的诉讼过程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影响了公司的声誉和正常的经营活动,可以认为是股东滥权的结果。
如果在股东派生诉讼程序中赋予公司抗辩权,并在进入庭审前由法院先对股东资格、前置程序、公司遭受损害事实和公司抗辩理由进行审查,不仅使公司能够向法院申明不起诉的正当理由,法院也可以充分听取双方的意见,兼顾股东的监督权和董事会管理公司的权力及公司利益,同时滤掉那些无价值的、有害的诉讼,阻止滥权行为,节约司法资源。“整个股东派生诉讼程序都应当根植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公司需要能够摆脱那些可能危害大于益处的诉讼。”⑤“如果派生诉讼要继续发挥有益的作用,就必须在董事会的商业判断理应得到表达的机会的情况下,避免对簿公堂。”⑥
三、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公司抗辩权的立法方案
(一)增加股东派生诉讼的庭前司法审查程序
在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公司虽然是胜诉利益的归属者,却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24条的规定,在股东派生诉讼中应当列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虽然该司法解释没有具体说明公司是哪一类第三人,但对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即对原被告双方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是案件处理结果同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同时,由于股东代表诉讼的启动是因为公司自己拒绝起诉,而公司在该诉讼中也不可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应为“辅助型第三人”,且应为辅助本诉被告的第三人,“不是诉讼当事人,不具有与当事人相同的诉讼地位”① 。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2条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规定,公司虽然参加股东派生诉讼程序,但是无权提出管辖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且无权提起上诉。这样的诉讼地位安排之下,一旦股东派生诉讼程序被启动,公司只能被强制参加诉讼,且只能辅助被告当事人参与庭审活动,既无法从诉讼当事人的角度基于公司的利益进行抗辩,也无法阻止诉讼的进行。所以,在我国目前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一旦股东提起了派生诉讼,则公司无法以诉讼不符合公司最佳利益为由请求法院驳回起诉或者终止诉讼。
与我国一样,在美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股东在公司拒绝起诉后即可直接提起派生诉讼。但是,在美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在进入成本昂贵的集中庭审之前必须提出和固定所有的主张和证据,由此形成高度处分权主义的诉答程序(pleading)和多功能的审前程序(pretrial)”②。审前程序包括审前会议(pretrial conference)、庭前动议(pretrial motion)、证据开示(discovery)等。其中,庭前动议指的是当事人在正式庭审开始前书面请求法院就某一事项作出裁决。庭前动议能够解决围绕诉讼的很多问题,缩短庭审时间,为即将开始的庭审设定边界,也可以在庭审前终止案件。在美国的股东派生诉讼中,公司必须作为一方当事人参与到诉讼中,但是,尽管派生诉讼是为了公司利益提起的,公司却是作为被告一方出现在诉讼中,因为公司实际上并没有提起诉讼,而“法律也不主张强制某人作为非自愿原告提起诉讼”③。原告股东先要请求公司董事会代表公司起诉,遭到拒绝后,其可以提起派生诉讼,并向法院主张公司拒绝起诉是错误的。公司作为被告则可以行使其抗辩权。为此,公司组建特别诉讼委员会,其经过调查后向法院提出驳回起诉的动议,以继续诉讼不符合公司最佳利益为由要求终止诉讼。有时也会提出即决裁决的动议④,不经过庭审而以简易程序结案,实际上也是站在终止诉讼继续进行的立场。驳回起诉的庭前动议既表明了公司对股东派生诉讼的反对态度,也是公司行使抗辩权的方式。这样,股东派生诉讼的典型形式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由股东提起的诉讼:一个诉讼是针对公司,因其不起诉;一个诉讼是代表公司针对损害公司利益的人。⑤可以认为,前一个诉即相当于诉讼许可程序,如果特别诉讼委员会终止诉讼的动议得到法院批准,则诉讼终止,否則诉讼继续进行。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法律并没有设计功能如此多样的庭前程序。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审普通程序分为起诉和受理、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审理等诉讼阶段。其中,“起诉和受理”和“开庭前的准备”构成了开庭审理前的程序,即庭前程序,但庭前程序和审理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功能混同”①,这与美国民事诉讼程序中内容丰富的庭前程序存在本质差异。在庭前程序中,尽管也存在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法院驳回起诉的可能,但该程序主要还是用于法院依职权进行起诉审查和为正式开庭审理做准备,如送达诉讼文书、组成合议庭等。这样的民事诉讼程序设置之下,一旦股东提起派生诉讼,不管公司是否愿意参加庭审,也不管其是否有正当理由拒绝起诉,都会被要求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程序。所以,无论是基于股东派生诉讼的规定,还是《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司均没有主张抗辩的机会,其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诉讼中不仅无法行使抗辩权以终止诉讼,也不能在庭前程序中阻止派生诉讼的继续进行。
根据《公司法》第151条的规定,原告股东履行前置程序后即可以自己名义代表公司起诉,启动股东派生诉讼程序,如果仿效德国法增设独立的前置司法审查程序,则修法成本过高,与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程序也难以契合。为此,笔者建议借鉴美国的股东派生诉讼程序,增加股东派生诉讼的庭前司法审查程序。从《民事诉讼法》的角度,该程序应置于民事诉讼开庭前准备阶段,可以采用庭前听证的方式。法院具体的审查事项则在《公司法》中作出规定,包括原告股东资格、前置程序、公司受到损害的事实以及是否存在与公司利益冲突的重大事由。法院应通知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该程序,对存在公司利益冲突的重大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由此使公司可以向法院陈述其拒绝起诉的理由。如果通过了各项审查,则进入正式的股东派生诉讼庭审程序,否则,人民法院做出驳回起诉的裁定。这样的程序安排,在当事人的身份上不违反目前的股东派生诉讼的规定,在程序上可以融入民事诉讼程序的既有结构,以微小的改革成本实现修法目的,在无须增加新的诉讼程序的前提下,完成《公司法》与《民事诉讼法》的衔接。增加庭前司法审查听证程序,相当于在股东派生诉讼程序前设置了一个“过滤阀”,以排除那些无价值的、有害的、没有胜诉希望的诉讼。
通过对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司法审判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对股东派生诉讼适用一审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会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因为大量的股东派生诉讼请求因原告资格和前置程序要件不足被法院驳回起诉②,尚不需要对实体法律问题进行审理。因此,股东提起派生诉讼后,法院无须直接启动庭审程序,通过简单的听证程序即可完成对原告股东资格、前置程序要件和公司利益受损事实的审查。这些客观性的、程序性的要件通过审查之后,再决定是否进入股东派生诉讼的实体审理程序。庭前司法审查听证程序的设置,可以完成现有普通庭审程序中的司法审查,还能有效防止司法资源的浪费。赋予公司抗辩权,只需在此程序中增加对公司利益冲突重大事由的审查,既不会干扰现有的股东派生诉讼程序,也不会过多增加司法成本。
在股东派生诉讼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很多案件也采用了简易程序审理,这说明人民法院也意识到,从提高审判效率的角度出发,原告股东资格、前置程序要件存在瑕疵的股东派生诉讼案件完全可以简易化处理。如在“王存棉与上海绿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①中,一审法院适用了简易程序审理,原告就此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普通程序严谨的程序设计虽然能够体现法院审判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但其烦琐的程序流程却制约着审判效率的提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作为市场交易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迅猛增加,公司之间、公司内部的各种类型纠纷层出不穷,其中股东代表诉讼目前已经成为人民法院日常审理的普通案件类型之一,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范围”,原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合乎法律规定。再审法院认为该案件事实清楚,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没有问题。②
可见,以简易的庭前听证程序审查原告资格、前置程序要件、公司受损事实和公司抗辩理由,符合股东派生诉讼实践的趋势。在股东派生诉讼程序中增加庭前司法审查程序,既能赋予公司抗辩权,实现股东与公司利益的平衡,也符合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司法审判实践的现实,兼顾了制度设计的利益平衡和程序设计的司法效率。
(二)确定代表公司抗辩的主体
公司是没有生命的组织,其需要通过公司机关做出对外行为的意思表示。在德国,代表公司在诉讼许可程序中行使抗辩权,举证证明派生诉讼与公司存在重大利益冲突的机关是监事会。在德国股份有限公司中,监事会是独立的监督机关,在针对董事的诉讼中具有法定的公司代表权。在美国的股东派生诉讼中,公司通过特别诉讼委员会行使抗辩权。特别诉讼委员会通常在股东要求公司自己起诉后或者提起派生诉讼后组建,一般由两名以上成员组成。委员会的成员往往是被指控的交易或行为发生后或者派生诉讼提起后被委任的独立董事或者外部董事,以彰显委员会的独立性。“特别诉讼委员会成员通过核查关键文件、采访关键证人等途径对派生诉讼所指控的交易或者行为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们也可以咨询或者采访股东原告或他们的法律顾问以及被告。这种原被告联立进行的咨询磋商能够为调查提供有用的信息,也能够表明委员会的公正。”③特别诉讼委员会的调查以公司经营为导向,以公司利益衡量为中心,通常涉及如下内容:派生诉讼原告控告的法律理据、可能的诉讼费用、管理层浪费的时间和精力、导致诉讼的行为或者交易给公司造成的损害程度、对员工士气的影响、对公司进行中的业务的管理能力的损害、再次发生类似行为或交易的可能性、与公司责任保险范围有关的不利后果的可能性。④调查之后,特别诉讼委员会应该出具一份调查报告,阐明调查程序、委员会的发现及结论的详尽,此外,报告中还需要阐明委员会结论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总之,特别诉讼委员会的报告会使法庭能够从公司的立场考虑诉讼的成本和收益。
如果我国未来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增加公司抗辩权,应由哪个机关代表公司行使权利?我国《公司法》第151条根据起诉对象不同,交叉规定了代表公司接受股東起诉请求的机关。如果针对董事和高管起诉,应由监事会或者监事代表公司;如果针对监事起诉,应由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代表公司。这样规定的目的自然是为了防止利益冲突。上述机关代表公司收到股东要求公司自己起诉的请求后,必然也要代表公司做出答复,表达公司是否起诉的意愿。如果增加股东派生诉讼的庭前司法审查程序,也可以按此规定由上述机关代表公司行使抗辩权。但是,这样的安排也并非全无问题。如果公司没有设置监事或者监事会,该由谁代表公司?如在“周长春、庄士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①中,公司没有设置监事会或者监事,而且除原告外的其他董事均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此外,如果董事和监事同时被列为被告的,又该如何处理?如在“珠海政采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等与北京国信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与公司有关的纠纷”②中,原告股东起诉的侵权主体包括公司的董事和监事。上述案件中,按照《公司法》规定履行前置程序,或者客观上不能实现,或者已无意义,因此,法院都豁免了前置程序要件,允许股东可以不经过请求公司自己起诉的程序直接提起派生诉讼,进入庭审程序。法院的处理固然是正确的,但若赋予公司抗辩权,则上述情况下将缺少代表公司行权的机关。
笔者以为,应该秉持避免利益冲突的原则,要保证代表公司行使抗辩权的主体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在一般情况下,应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由无利害关系的董事或者监事对股东派生诉讼所针对的交易或者行为进行调查,并代表公司陈述公司拒绝起诉的理由。如果公司未设监事会或者监事,或者董事和监事均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则应该允许公司另行成立由无利害关系人员组成的特别诉讼委员会,代表公司进行调查并行使抗辩权。该特别诉讼委员会应由两人以上组成,其地位相当于董事会/执行董事或者监事会/监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以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机关权力划分相一致。
(三)赋予法院形式和实质审查权
公司虽然被赋予了抗辩权,但是该抗辩能否被接受并成功阻止派生诉讼的进行,最终还要取决于法院的审查。在德国,公司有权在诉讼许可程序中举证证明存在派生诉讼违反公司利益的重大事由,以此进行不起诉的抗辩。“法院依职权对违反公司利益重大事由的存在进行调查,并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由程序法院予以解释,因此不需要由公司机关进行衡量。”③也就是说,公司只需要负责举出事实,是否违反公司利益则由法院进行判断,法院享有实质的审查权。在美国,特别诉讼委员会经过调查之后往往得出继续诉讼不符合公司最佳利益的结论,向法院提出终止诉讼的动议,“只有屈指可数的案例中特别诉讼委员会提出终止诉讼之外的建议”④。因此,法院对特别诉讼委员会动议的审查标准至关重要,其直接决定着股东派生诉讼能否继续进行。在1979年的Burks v. Lasker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同意无利害关系董事组成的特别诉讼委员会可以终止未决的股东派生诉讼,这一案件带来了特别诉讼委员会的流行趋势。①在联邦和各州法院中,审查标准的区分主要在于形式审查标准和实质审查标准,前者适用商业判断规则(business judgment rule)排除法院的实质审查,法院秉持不介入公司内部事务的原则,仅对特别诉讼委员会成员的独立性、善意及调查的全面性进行审查,其典型案例是纽约州上诉法院的Auerbach v. Bennett②案;后者则还要对特别诉讼委员会结论的基础进行实质审查,典型案例是特拉华州高等法院的Zapata Corp. v. Maldonado③案,法院针对请求要件被豁免的(demand-excused)股东派生诉讼案件确立了两步审核法(two-step test):首先,法院会调查特别诉讼委员会的独立性、善意及支撑其驳回起诉决定的调查的合理性;其次,如果公司能够举证证明上述内容,则法院接下来会运用自己的商业判断决定是否应该驳回派生诉讼,其间不仅要考虑公司的最佳利益,还要考虑公共利益。④然而,“在绝大多数的案件中,法院都依据特别诉讼委员会的建议批准了其驳回起诉的动议”⑤。 但二十世纪初爆出“安然事件”等公司丑闻后,“这种司法尊重已经有些消失了”⑥。
我国目前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设计中,公司拒绝起诉后即进入股东派生诉讼的庭审程序,并不存在美国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庭前动议审查的环节。这样的程序设计,忽视了公司事务自治的权利,也未善用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力阻止无价值的诉讼的发生。“股东派生诉讼与一般民事诉讼不同,诉讼的真正原告——公司是缺位的,为保护公司和其他大多数股东的利益,法院理应作为一个诉讼主动管理者。”⑦ 美国特拉华州高等法院在Zapata Corp. v. Maldonado案中即认为,股东请求公司自己起訴的要求被拒绝后,股东个人并不会径自取得代表公司起诉的个人权利,董事会做出的驳回派生诉讼的决定应该得到尊重,除非这一决定是错误的。法院允许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决定,不是授予股东对诉讼的唯一控制权,法院也不应该通过自动赋予股东不受限制的对公司诉权的控制权而扩大这一特别救济(extraordinary remedy)的适用。特拉华州高等法院认为,善意的股东诉权不应该被董事会不公平地践踏,同时,公司也应该能够摆脱对其有害的诉讼。“在股东派生诉讼中,法院的基本任务是平衡公司董事会管理公司事务的权利和股东保护其利益不被董事会不公正地践踏的权利。”⑧为此,既要给予公司抗辩的权利,法院也需要行使其司法审查权。
有学者认为,我国应该借鉴日本的不起诉理由书制度,要求公司收到股东的诉讼请求后,如果决定不起诉,应该制作书面的不起诉理由书,阐明调查的情况和公司不起诉的理由,并通知股东。①该制度固然可以起到与股东沟通的作用,并督促公司经营者慎重对待股东的请求,但是其并不具有阻却不当股东派生诉讼的效力。因此,公司对于股东起诉请求的抗辩理由应该交由法院进行审查,利用法官的专业知识和法院的司法强制力过滤掉那些无价值的、有害的派生诉讼,防止股东滥权。
法院对公司抗辩的审查应包括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形式审查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法院要审查代表公司主张抗辩权的机关成员或者特别诉讼委员会成员的独立性。这一独立性的要求是为了保证不起诉的决策及调查的公正,要求该成员与派生诉讼所涉交易或者行为无关,且没有从中获得个人利益。董事会/执行董事和监事会/监事的交叉代表公司的设置,固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避免利益冲突,但是也要考虑是否存在受被告控制的情形,如当被告是公司的控股股东,而董事会的主要成员都是该控股股东选任的或者派出的。另一方面,法院要考察公司对被指控的交易或者行为的调查的充分性,如调查的方式、时间及报告的详尽程度及相关的证据等。这不仅有利于法院了解案情,也显示出公司不起诉的决定是慎重考虑后做出的。在实质方面,法院要审查公司不起诉决定的基础和依据。公司可以从法律理据、成本收益、公司声誉等多个方面进行论证,如损害赔偿数额过于微小、机关成员违反义务的行为极其轻微、被告没有赔偿能力、诉讼成本过高等。但这些理由能否被接受,还要取决于法院的审查和判断。通常认为,法院不应介入公司的内部事务,因为法院并不具备商业判断方面的专门知识。但是,决定是否起诉与一般的商业决策毕竟有所不同。相比较而言,法院更有能力对诉讼的结果做出判断。正如美国第二巡回法院上诉法院在Joy v. North②案中指出的:法官在此领域也并非全无经验,很多法院都裁决过利害关系董事交易的内在公正性,这当然在法官预测潜在责任的专门知识之中。
四、结论
我国现行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设计倾向于股东诉权的保护,而忽视了公司作为原本的请求权人控制诉讼的权利。现有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安排中,公司一旦拒绝股东的起诉请求,股东即可以直接提起派生诉讼并进入庭审程序,公司没有机会向法院阐明不起诉的理由,法院亦无权对诉讼价值进行庭前审查,公司被强制拖进诉讼,即使有正当理由也无法阻止诉讼的继续进行。进入庭审之后,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亦无法行使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从公司利益角度请求终止诉讼。这造成了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失衡。我国未来《公司法》修改时应增加庭前司法审查听证程序,在庭审前对原告股东资格、前置程序、公司利益受损事实和违反公司最佳利益的事由进行审查,公司可以在此程序中行使抗辩权。如果通过司法审查,则进入股东派生诉讼庭审程序;未通过审查,则法院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针对公司的抗辩,法院要进行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在股东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权利与公司事务自治权间找到平衡。这样的程序安排,不改变目前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公司的法律地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程序安排,兼顾了股东权利和公司利益,能够以微小的改革成本实现完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目的。
The Corporations Right of Defense in the Shareholder Derivative Action
HU Xiao-jing
(Law School,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In the shareholder derivative action system in China, the shareholder becomes the decision maker of the lawsuit, but the corporations right to decide and defend the lawsuit as the original claimant is ignored. In the Company Law reform in the future the pretrial judicial review procedure shall be introduced into the shareholder derivative action, in which the court shall review the eligibility of the plaintiff shareholder, the demand requirement prior to the derivative action, the harm to the corporation,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refusal of the corporation to pursue litigation. The corporation can state its reasons for defense in this procedure. The court will decide whether to enter the trial procedure of the shareholder derivative action after the review of the above items, especially the formal and substantive review of the corporations reasons to defend, in order to strike a balance of interests between shareholders and the company and reduce the judicial cost.
Key Words: shareholder derivative action; non-prosecution defense; pretrial judicial review; Company Law reform
本文責任编辑:周玉芹
收稿日期:2021-06-01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公司诉讼中的疑难问题研究”(2016QY027);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股份回购与公司资本制度改革”(21STA051)
作者简介:胡晓静(1972),女,辽宁义县人,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① 参见胡晓静:《德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评析》,载《当代法学》2007年第2期,第136-138页。
② Arnold,in:Münchener Kommentar AktG,4.Aufl.2018,§ 148 Rn. 52, 61.
① 黄辉:《中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实证研究及完善建议》,载《人大法律评论》2014年卷第1辑,第247页。
① Rodman M. Elfin, An Evaluation of a New Trend in Corporate Law: Dismissal of Derivative Suits by Minority Board Committees, 20 American Business Law Journal 179,181(1982).
② James D. Cox, Searching for the Corporations Voice in Derivative Suit Litigation: A Critique of Zapata and the ALI Project, 6 Duke Law Journal 959,968(1982).
③ 参见胡宜奎:《股东代表诉讼诉权的权利基础辨析——兼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完善》,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9期,第148页。
④ 耿利航:《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的成本承担和司法许可》,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175页。
⑤ Ian Ramsay,Corporate Governance,Shareholder Litigation and the Prospects for a Statutory Derivative Action,15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res Law Journal 149,168(1992).
① Laurel J. Lucey,Off the Bench and into the Boardroom:Judicial Business Judgment after Zapata,70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025,1037(1982).
② Ian Ramsay,Corporate Governance,Shareholder Litigation and the Prospects for a Statutory Derivative Action,15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res Law Journal 149,168(1992).
③ James D. Cox,Searching for the Corporation's Voice in Derivative Suit Litigation:A Critique of Zapata and the ALI Project,6 Duke Law Joural 959,960(1982).
④ Grigoleit/Rachlitz,in:Grigoleit(Hrsg.),Aktiengesetz,2. Aufl. 2020,§148 Rn.2.
① “强袭诉讼”通常是原告律师推动进行的,意在促成和解以获取律师费,而不是真正为了公司利益。
② Anna Panchenko,In re Oracle Corp. Derivative Litigation:Death of Special Litigation Committees? 3 Depaul Business & Commercial Law Journal 617,620(2005).
③ 林少伟:《英国派生诉讼的最新发展:普通法的回归》,载《时代法学》2011年第4期,第118页。
④ 王存棉诉上海绿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审二商申字第0224号民事裁定书。
⑤ James D. Cox,Searching for the Corporation's Voice in Derivative Suit Litigation:A Critique of Zapata and the ALI Project,6 Duke Law Joural 959,964(1982).
⑥ Thomas P. Kinney,Stockholder Derivative Suits:Demand and Futility Where the Board Fails to Stop Wrongdoers,78 Marquette Law Review 172,189(1994).
① 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63-166页。
② 傅郁林:《中国民事诉讼立案程序的功能与结构》,载《法学家》2011年第1期,第103页。
③ Richard D. Freer & Douglas K. Moll,Principle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s,West Academic Publishing,2018,p.514.
④ 如在特拉華州高等法院的Disney案中,被告驳回起诉的动议被法院否定,在证据开示程序后,被告又提出了即决裁决的动议,得到了法院的部分支持,之后又进入了庭审程序。
⑤ Ross v. Bernhard, 396 U.S. 531, 90 S. Ct. 733, 24 L.Ed.2d 729 (1970).
① 傅郁林:《中国民事诉讼立案程序的功能与结构》,载《法学家》2011年第1期,第100页。
② 参见胡晓静:《美国股东派生诉讼中对公司抗辩的司法审查标准》,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4期,第1099页。
① 参见王存棉诉上海绿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纠纷案,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徐商终字第00016号民事判决书。
② 参见王存棉诉上海绿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审二商申字第0224号民事裁定书。
③ Jerold S. Solovy,Barry Levenstam & Daniel S. Goldman,The Role of Special Litigation Committees in Shareholder Derivative Litigation, 25 Tort & Insurance Law Journal 864,877(1989-1990).
④ Jerold S. Solovy,Barry Levenstam & Daniel S. Goldman,The Role of Special Litigation Committees in Shareholder Derivative Litigation, 25 Tort & Insurance Law Journal 864,877-878(1989-1990).
① 参见周长春诉庄士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679号民事裁定书。
② 参见珠海政采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等诉北京国信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终14287号民事裁定书。
③ Stilz/Mock,in:Spindler(Hrsg.),Aktiengesetz,3. Aufl. 2015,§148 Rn.89.
④ Carol B. Swanson,Juggling Shareholder Rights and Strike Suits in Derivative Litigation:The ALI Drops the Bell,77 Minnesota Law Review 1339,1358(1993).
① Carol B. Swanson,Juggling Shareholder Rights and Strike Suits in Derivative Litigation:The ALI Drops the Bell,77 Minnesota Law Review 1339,1357(1993).
② Auerbach v. Bennett,47 N.Y.2d 619,419 N.Y.S.2d 920,393 N.E.2d 994 (1979).
③ Zapata Corp. v. Maldonado,430 A2d 783 (1981).
④ Zapata Corp. v. Maldonado,430 A.2d 783 (Del. 1981).
⑤ Ann M. Scarlett,Confusion and Unpredictability in Shareholder Derivative Litigation:The Delaware Courts Response to Recent Corporate Scandals,60 Florida Law Review 589,599(2008).
⑥ Ann M. Scarlett,Confusion and Unpredictability in Shareholder Derivative Litigation:The Delaware Courts Response to Recent Corporate Scandals,60 Florida Law Review 589,603(2008).
⑦ 耿利航:《論我国股东派生诉讼的成本承担和司法许可》,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178页。
⑧ Carole F. Wilder,The Demand Requirement and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Synergistic Procedural Obstacles to Shareholder Derivative Suits,5 Pace Law Review 633,655(1985).
① 参见朱大明、孙慧:《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完善——以不起诉理由书制度为中心》,载《证券法苑》2019年第26卷,第184-212页。
② Joy v. North,692 F 2d 880 (2d Cir.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