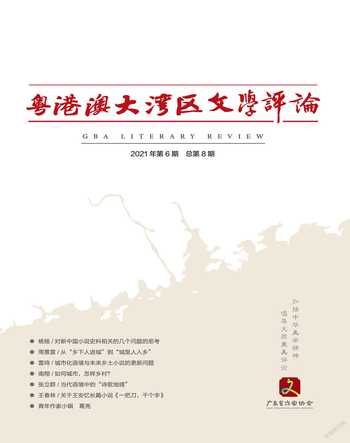烟火人生中的尖锐历史诘问
王春林
摘要:从艺术结构上看,《一把刀,千个字》被切割为上下两个部分。尽管在小说叙事过程中二者之间彼此交叉穿插,但相对来说,“一把刀”更多地对应着上半部,“千个字”更多地对应着下半部。作家在上半部里所集中讲述的,是男主人公陈诚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不断四处漂泊的人生故事。到下半部,整部作品的叙述方向却一下子就“峰回路转”,就由“一把刀”转向了“千个字”。时间的视点,也随之而由当下时代转向了二十世纪中叶。原来,这部小说真正的书写重心,其实并不在陈诚身上,而是最终被落脚定格在了他那一直处于闪闪躲躲状态的母亲身上。正是借助母亲这一形象,王安忆成功实现了所谓“尖锐的历史诘问”。
关键词:烟火人生;历史诘问;艺术结构;悲悯心理
正如同标题中的“一把刀”已经强烈暗示出的,在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对物质基础细针密线式的坚实建构,突出地体现在对男主人公那超乎群伦的顶级厨艺的精细描写上。比如,开篇处不久的这样一段:“胡乱想着,菜上来了。雪菜豆瓣是瓶装的;烤麸是冷藏;熏鱼倒出其不意的好。中国内湖污染重,淡水鱼难得像这样没有火油味,酱料足,炸得透,糖色重,所以还是老三件。红烧肉是上海菜的主打,其实最平常,弄堂里每扇后门里都炖着它,高低在于猪肉。”严格地说,作家在这里并不是在直接描写陈诚(因为名字不确定,我们姑且以“陈诚”来称谓男主人公)的厨艺,但间接反映出的仍然是他的厨艺。却原来,身为厨师的陈诚,之所以要邀请开农场的川沙朋友一起去曼哈顿的那家上海本帮菜馆吃饭,乃是意外地看到了那家的菜单上赫然列着一道“清炒鳝糊”菜品的缘故。依照陈诚来到美国后所获得的经验,这个地方是不可能有“软兜”也即鳝鱼存活的。对此,陈诚或者王安忆试图给出解释:“从小处说,北美没有水田,旱地为主,也许,可能,很可能,鳝,即软兜,是和水稻共生;大处来看,新大陆的地场实在太敞朗,鳝却是阴郁的物种,生存于沟渠、石缝、泥洞,它那小细骨子,实质硬得很,针似的,在幽微中穿行,人类肉眼看不见,食物链上最低级的族群,就可供它存活。”细细想来,这段话里所表达的认识和感觉,前边那小处的一部分是属于陈诚的。只有作为厨师的他,才能够认识到美国没有鳝鱼存活的地理差异方面的原因。后一个方面,也即所谓的大处,其实更多的是在一种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层面上,借助对鳝鱼生存条件的谈论,比较分析中美两种文化的异同。潛隐于其后的,乃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文化批判与沉思。根据我们对陈诚基本文化结构的了解来判断,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如此一番相当高明的思想见识生成。也因此,如此一种文化感悟,与其说是属于陈诚的,莫如干脆说就是属于作家王安忆的。来到曼哈顿的这家菜馆后,陈诚和他的朋友便要了一桌菜。请注意,在写到这些菜品时,叙述者所持有的更多是一个厨师挑剔的眼光。毫无疑问,如果不是陈诚,而是另外一个普普通通的食客,他哪里会对这些菜品做出如此一种鞭辟入里甚至有点挑剔的品评呢?也因此,这段话语看似描写的都是曼哈顿这家上海本帮菜馆的厨艺水平,但暗中所真切折射出的,却依然是陈诚自己的厨艺。还有那些关于陈诚初学厨艺略有小成的文字,展示了其厨艺,带有明显的日常意味,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掩映于厨艺背后的时代与人性状况。其一,从时代的角度来看,王安忆所巧妙写出的,是特定的物质匮乏年代人们窘迫的生存状况。正因为生活物资供应跟不上趟,所以,金针菜与黑木耳才会一年只有二两的数量。二两,即使到现在想一想,都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一个计量数字。正因为如此,人们也才必须在天不亮的时候就去排队购买。其二,更是同时揭示了上海人生活的精细和讲究情况。吃豆芽要掐去两头,吃蚕豆和花生米都必须去衣,类似这样的生活细节,非亲身经历者其实不能道出。这个,在外地人那里恐怕的确很难想象。还有就是,明明已经是物质特别匮乏的时候,但上海人却还是要尽可能地讲究生活品质,否则也不可能如同“螺蛳壳里弄道场”一般,非得把好不容易才买到手的半斤肉还一定要再搞出三四个花样来。当然,如果换一个角度的话,如此一种情形,也说明着上海人骨子里对生活的一种热爱,或者说就是生命力的坚韧。
王安忆的小说语言,句子很短,因而不但会给人以特别绵密的感觉,也有着一种内在的节奏感与音乐性。她的这种语言,看似琐碎,却一点也不显得空洞高蹈,反而特别及物,蕴含有极其丰富的信息量。即如作家非常细腻地介绍一种由小麦制成的特别面点,或许因为面点的制作食材更为关键的缘故,作家的重心其实落在了对食材特点与来历的详细展示上。首先,是制作过程中的分寸把握。什么“不能生,不能熟”,而且还“不能烂”,什么既要搓,还得捣,然后再揉,真正可谓细致入微。其次,更进一步地,在描述完制作的过程和食材的特点之后,也对食材的来历做了相应的补充性交代。这其中,尤其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如此一道现在看起来已经非常高雅的面点,原初的出身竟然只是盐城如东一带百姓春荒时救命的一种吃食。这样一来,自然也就构成了“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某种反命题。却原来,食物也会有如同人生一样起伏跌宕的命运沉浮。自然,除以上这些内容之外,还有一点,恐怕就是为王安忆所念念不忘,时不时就要穿插到叙事话语间隙之中的中美文化比较命题。“美国这地方,水土太丰腴。种什么,长什么,长什么都是肥硕壮大”,而陈诚所需要的却是中国的麦子:“颗粒小、瘦、高密度,从土里硬挤出来”。实际上,又何止是麦子,其他的那些植物,不也一样如此么?这样,也才有了接下来的相关话语:“中国的庄稼,哪一种不是?树的年轮压得死紧,铜线似地一周套一周,箍得个千年不朽”。读罢小说,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叙事话语所谈论或者指向的绝不仅仅只是所谓植物生长的问题。作家的用意可能更多地在透过笔下所写之物,而引发大家对物象背后两种文明的比较与思考。也因此,到底什么样的小说语言,方才算得上是细针密线的,不仅及物而且更有着丰富内涵的语言,王安忆的这一段叙事话语,其实就带有突出的示范性意义和价值。
实际上,也不仅仅是厨艺,其他如人心的细微,同样在王安忆的笔下得到了特别缜密的挖掘与表现。比如,阅读陈诚和师师在美国结婚前的一段饶有趣味的对话,让我既想起了著名的戏剧片段《三岔口》,也想起了现代京剧《沙家浜》中影响最大的《智斗》那个片段。陈诚和师师,原本是少年时上海弄堂里的玩伴,没想到很多年之后竟然在美国不期而遇。等到师师出现在陈诚面前的时候,陈诚已经凭借着他的厨艺以及机智,在美国立住了脚跟。但师师的居留,仍然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根本问题。师师要想在美国居留,有三条路径可供选择。一是政治庇护,二是转工作签证,三是找合适的人结婚。在师师这里,或许是因为自己不仅有过婚史,还生有一个儿子的缘故,首先,无论如何不想走第三条路,其次,即使万般无奈被迫走第三条路,也不会把目标聚焦到童年玩伴陈诚身上。但在陈诚这里,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单身一人早已孤独太久,另一方面则因为师师的出现仿佛一下子照亮了自己内心世界(请一定不能忽视这样的一个相关细节是“眼前的师师,有着饱满的脸颊,双眼皮很宽,仿佛墨笔描画的,唇线也如描画般鲜明。这一张脸凸起在后厨灰暗的光线里,周围的事物都失去三维的立体感,变得平面。”)的缘故,内心里早已对师师充满了不可遏制的欲望和期待。关键的问题还在于,陈诚的这种真实想法,并不能够对师师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很显然,这一番饶有趣味的对话的发生,正是建立在对话双方如此这般各自不同的心理基础之上的。话题之所以会由陈诚率先挑起,乃因为他对师师先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在对话的过程中,由于各自的想法不同,所以,一方一直在以一种暗示的委婉曲折方式在表白着潜藏于内心深处的情愫,另一方却一直在以一种貌似“没心没肺”其实非常坦诚直率的方式“拒绝”着。如此一种弯弯绕绕的情感表达的错位,在让我们为男主人公陈诚捏一把汗的同时,也更让我们恨不得自己跳出来替这位无法明言的男子把自己的真实想法直截了当地告诉师师。也因此,一直到后来,看到这两位在上海时的少年玩伴终于走到一起的时候,我想,大概很多人都会如同我自己一样,在彻底松一口气的同时,把那颗悬着的心放下。阅读的过程中,我的一种真切感受就是,王安忆的确是一位很有叙事耐心的作家。能够仅仅通过两个人的对话,便丝丝入扣条分缕析地把陈诚和师师他们两位的内心世界做如此深入的剖视,端的是艺术功力了得。
从艺术结构上看,整部《一把刀,千个字》被王安忆不无果断地切割为上下两个部分。尽管很难把标题中的前后三个字截然分开,小说叙事过程中二者之间彼此的交叉穿插,毫无疑问是一种客观的事实,但相对来说,“一把刀”更多地对应着上半部,“千个字”更多地对应着下半部。事实上,王安忆在上半部里所集中讲述的,乃是男主人公陈诚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不断地四处漂泊的人生故事。倘若仅仅聚焦于陈诚其人,断言这一部分带有一定的成长小说色彩,也是合乎文本事实的。具体来说,陈诚的漂泊人生是从他只有大约七岁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他大约七岁,住在上海虹口的弄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与那些长期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正常孩子明显不一样的一点是,小小年纪的陈诚,只是和一个被他称之为嬢嬢(上海话里关于姑姑的一种称谓)生活在一起。当然,他们两个能够在一起生活的一个必然前提是,这个时候的嬢嬢同样处于单身一人的生活状态。即使是作为当事人的陈诚,也只是到了后来,方才从嬢嬢那里进一步了解到,原来嬢嬢也不仅曾经有过自己的婚姻,还生过一个孩子。但因为男女双方皆属青春年少,对未来的爱情充满幻想,所以两个人还是不顾家庭的反对,坚持走到了一起。然而,少年人的热情来得快也去得急,没有过了太长时间,就在他们刚刚生下一子不久,他们的婚姻就出现了问题。分手前达成协议。也就是说,不从事任何职业的嬢嬢,之所以能够既养得起自己,也养得起陈诚,与她因为这桩异样婚姻所获致的经济补偿紧密相关。尽管说陈诚正是在这个时候,和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师师最初结识,但一个小小年纪的男孩子,成天价守着嬢嬢这样一个单身女子一起过日子,自然会有难以排遣的愁闷生成。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愁闷,使陈诚得以跟随黑皮的爷爷,也即自己的舅公,不仅来到了位于高邮西北乡的他们家长住,而且他也正是跟随着四处办厨的舅公才开始最早接触厨艺的。正是在跟随着舅公四处奔波的过程中,陈诚开始了他带有明显偶然色彩的厨艺生涯。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学习厨艺的同时,他也还接受着别一种教育:“传授厨事之余,舅公还和他讲书。嬢嬢用《红楼梦》作脚本,舅公是黄历。”虽然一直没有能够接受正规的科班教育,但陈诚却也并没有成为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从根本上说,恐怕也正是拜嬢嬢和舅公如此一种特别教育方式所赐的結果。就这样,一直追随舅公学习厨艺三年后,已经初通厨艺的陈诚,才离开高邮西北乡,再次回到上海,回到了依然孤身一人的嬢嬢身边:“再次来到上海,觉得一切都变小。街道窄了,楼矮了,一方方的窗格子,蜂房似的,人却多了,密密匝匝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一方面因为他刚刚从广阔的乡间大地回到其实逼仄的上海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三年的时间里,他的个子已经长高了不少。这个时候的陈诚,不仅个子长高了不少,还开始初通人事了。这一方面,一个标志性的细节就是,他竟然把自己学习厨艺过程中积攒下的一笔钱全都主动交给了嬢嬢:“嬢嬢用手帕在镜片后面擦拭一下,喃喃说:你还是个孩子呢!他低下头,窘得不行。这般大的少年人,最怕动感情,尤其他和嬢嬢,都不惯表达和交流。”一方面在嬢嬢的心目中,他已经长大成人,另一方面,也因为嬢嬢发现他已经在厨艺上有所成就,所以便决定利用自己即往的关系,给陈诚找一个比舅公的厨艺水平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的真正的淮扬菜大师傅,也就是嬢嬢一位久违的故人单先生。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这位单先生授徒方式不仅奇特,而且授徒效果也非常显著。但也正是如此一种只是口口相传式的点拨方式,到最后却奏了奇效。陈诚之所以在后来到美国开餐馆后不仅大获成功,而且还被别人以讹传讹、一厢情愿地指认为是淮扬菜系正宗传人莫有财的嫡传弟子,不管怎么说,都与单先生当年那番真正可谓煞费苦心的悉心调教和点拨,是分不开的。
我们注意到,在主要讲述陈诚如何走上厨师这一条人生道路的过程中,作家也会时不时地穿插讲述他后来怎么样想方设法地在美国落脚打拼的故事。具体来说,厨师陈诚之所以有机会来到美国,与他的嫡亲姐姐关系密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已经在三棵树插队的姐姐,首先是有机会被保送到工业大学,然后,等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又被推选公派留学,这样才有机会漂洋过海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留学。在经过一番周折,其实是亲身感受到母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之后,最终选择彻底居留美国。若干年后,陈诚携手父亲一起,以探亲的名义,步姐姐的后尘,也来到了这块新大陆。等到续签的三个月再次到期的时候,他终于下定决心“黑”了下来,非法居留美国不归。就这样,等到陈诚在法拉盛居住第三年的时候,大号名为“师蓓蒂”的师师没有一点征兆地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这样一来,自然也就有了我们在前面其实已经涉及的,师师的居留、他们之间的婚姻问题,以及相关问题的最后解决。
然而,就在我们根据上半部的小说文本,差不多已经要认定《一把刀,千个字》就是一部从陈诚的高超厨艺切入并最终描写表现他终其一生的漂泊(他后来的美国故事,自然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生漂泊故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长篇小说的时候,到了第七章开始的下半部,整部作品的叙述方向却一下子就“峰回路转”,就由“一把刀”转向了“千个字”。时间的视点,也随之而转向了某种意义上看似已经有点遥远了的二十世纪中叶。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也才会恍然大悟,却原来,王安忆这部长篇小说真正的书写重心,其实并不在前面已经占了很大篇幅的陈诚身上,而是最终被落脚定格在了他的其实一直处于闪闪躲躲状态的母亲身上。小说叙事上的如此一种“峰回路转”情形,倘若借用众所周知的名句来说,无论如何也都称得上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事实上,如果你的确称得上是一位敏感的读者,那么,早在上半部作家有意无意留下的一些蛛丝马迹中,就应该已经能够注意到陈诚母亲这一形象的若隐若现。比如,在父亲携带姐姐专程到上海来看陈诚的时候,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段叙事话语:“停一时,父亲开口了:以后,你管嬢嬢叫‘妈妈。嬢嬢接着说:这样,你就可以在上海读书。他有些懵,心里恍惚着,问出一句话:我妈妈呢?两个大人被问倒了,面面相觑,然后,他看见嬢嬢的眼镜镜片奇怪地闪烁一下,戴眼镜的人哭了。”由这一细节而引发的一连串无法回避的问题显然是,母亲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父亲要他喊嬢嬢为“妈妈”?为什么一提到母亲,嬢嬢就会哭呢?再比如第四章里写到陈诚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终于想方设法买到一只猪后蹄,并且做成挂丝的蹄髈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个他和嬢嬢以及朋友小毛一起看照片的重要场景:“再翻一页,就是一家四口,年轻的父母和幼雏儿女。小毛脱口道:你,兔子!他也认出父亲和姐姐,那抱他在怀里的,仿佛认识,却又不认识。”后来,等到故事情节行进到上半部最后的一个部分,也即第六章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与前面看照片的场景相呼应的另外一个场景,只不过,这一次看照片的,只剩下了陈诚一个人。其实,他是偷偷背着嬢嬢看照片的。但出乎意料之外的一点是,等到他取出相册打开来的时候,却发现此前那张一家四口合影的照片“不翼而飞”了。毫无疑问,由以上两个看照片的场景,我们所生出的问题,自然是那张无可置疑是包括妈妈在内的一家人的照片,到底有什么忌讳,会让嬢嬢“神不知鬼不觉”地抽走呢?难道说问题的确出在大家似乎避之唯恐不及的妈妈身上吗?对于这一切,王安忆在上半部里并没有提供答案,但那一首在陈诚偷看照片时窗外一直响着的“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对你说话”的歌谣,从此之后却时不时地就会回响在陈诚的耳际了。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一点,我想,无论如何都只能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予以解释。陈诚之所以总是要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少年时期在上海弄堂里听到过的童谣,不是因为童谣本身有什么微言大义,而是因为它很显然牵系着他内心深处某种难以言说或者说不足为外人道的精神情结。而这种牢固存在着的精神情结所指向的,就是他那位很是有一点“云深不知处”味道的母亲。
耐人寻味的一点是,陈诚的母亲,虽然在小说文本中拥有如此重要的一种地位,但却一直处于无名的状态。这也就是说,明明有着赋名权力的王安忆,却偏偏就是拒绝给她命名,总是径直以“她”称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执意”不肯命名的情况,大约是出于能够更圆满地表达作家思想意旨的缘故。依照叙述者的交代,出生于一九三四年哈市道里一户基督教家庭的“她”,在少年时期,曾经被酷爱音乐的母亲特别安排,跟着一个名叫亚历山德拉克娃的白俄女教师学习声乐。但尽管如此,等到中学毕业的时候,“她”还是违逆母亲意欲让“她”报考音乐学院的意愿,执意进入了一所工业大学:“学校起源于中东铁路培训人才的需要,一度名为‘中东铁路工业大学,是中苏交好的象征,也显示走苏联道路的基本国策。”既如此,置身于那个中苏友好的蜜月期里,包括“她”在内的这所大学的学生,在各方面倾慕向往苏联的时尚,也就是一種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早在大学的时候,“她”就已经表现出了对社会政治的浓厚兴趣。被誉为校花的“她”,曾经积极参与过大辩论。进一步说,“她”的最早引起陈诚父亲,也即老杨的注意,也就在这个时候。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她”和老杨其实也并不是一类人。很多时候,如果说“她”可以被看作是生活中的主角的话,那么,老杨只可能是生活中的旁观者。然而,生活的辩证法就在于,到最后,偏偏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居然走到了一起。关键的问题是,虽然“她”可以和老杨一起结婚并生育子女,但从根本上说,“她”从来都不属于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而只是天然地属于金戈铁马的社会政治生活。
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说,大学时代也即“反右”时期的“她”,如同很多人一样,其实也曾经是一个“左派”。从这个时候开始,到后来的1960年代中期,如果联系“她”在“文革”中的石破天惊之举来判断的话,不妨可以被理解为“她”思想转折的一种酝酿期。首先,是时代的转换迁移。但请注意,在“她”那张影响巨大的大字报出炉之前,曾经有过一次长途旅行的过程。而老杨,也正是在“她”出行未归的时候,出于平素对“她”的了解,就表达过一种强烈的忧虑:“认识她,他方才知道,世上有一种渴望牺牲的人,就像飞蛾扑火,由着光的吸引,直向祭坛。”这次外出旅行或者说“她”一个人的大串联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天津和大学宿友女同学短暂相聚时的一番促膝交谈:“她坐直起来,前倾着身子,说:我去过北京了。女同学不动弹,静静听着。天安门那么远,什么都看不见,她说,可是满地的人都在跳跃,叫喊,流泪——她止住话头,停顿片刻,接着说出一句:大家都疯了!女同学动了动,她继续:理性,理性到哪里去了?女同学在枕上问:你加入组织了?没有,她说,我读书。读什么书?《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读书好!女同学说。读书是不够的,她说,要到实践中去。”毋庸讳言,当“她”一力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的时候,这位对“她”一向了解甚深的女同学,已经预感到“她”想干什么了。这样,也才会有接下来的劝阻和拒绝:“女同学坐直了,俯身看向她:忘记它,想都不要想!可是我做不到!她说。”既然内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那个悲剧性的结局也就不可避免了。在春节之后写好大字报后,“她”把大字报毅然决然地张贴到了省委大院的外墙上:“总共十二页,标题为‘人民政权和群众运动,落款‘一名中共候补党员,底下是真名实姓。”关键的问题是,在那个大字报早已铺天盖地的年代,“她”的这张大字报到底特别在何处?凭什么一下子就能吸引来那么多人呢?请看叙述者的相关介绍:“文中的主张,似乎也没有偏倚,既不造反也不保皇,两边的队都不站,两边也都不支持。是要倒退到革命之前吗?却又像超越至最高目标,共产主义,消灭阶级,人类大同。”虽然现在看起来大字报中的观点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的政治漩涡中,却真正称得上是石破天惊的闯祸之论。事发之后,预感非常糟糕的老杨,曾经专门赶到单位去叫“她”回家,这个时候的老杨根本想不到,这一次,乃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到后来,老杨才意识到:“她不随他回家,是因为已经身不由己,不得离开。”就这样,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她”最终因为“冒犯天条”而被打入另册。但老杨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到最后,“她”竟然会因为这张大字报而性命不保。以至于,在若干年后,竟然不无反讽意味地被追封为“烈士”而加以顶礼膜拜。分析至此,一个不管怎么说都应该提出来加以讨论的问题就是,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中的“她”这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到底是谁?又或者,如果说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很多人物都会有生活原型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她”的生活原型又是谁呢?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联系那个特定时期东北所实际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来加以判断,那么,这个生活原型极有可能就是那位曾经被著名诗人雷抒雁在其名作《小草在歌唱》中大力讴歌过的张志新烈士。二者之间高度的相似性,明眼人一看即知。我们在这里不展开详细论述了。但必须强调指出的一点是,在《一把刀,千个字》这部长篇小说中,王安忆能够从陈诚这样一个淮扬菜系的优秀厨师而进一步延伸并触及如同张志新烈士这样一种深度历史话题,无论是写作勇气,还是艺术智慧,都应该得到高度的肯定。而我们这篇文章标题中所谓“尖锐的历史诘问”,实际上也只能落脚到这一点上。
或许是因为存在着某种书写禁忌,又或许,在王安忆最初的创作构想中,原本就是要把书写重心最终落脚到以陈诚为代表的子一代此后的人生漂泊上,然后,再以如此一种书写方式巧妙地折射回望母亲当年所遭逢的历史悲剧。对此,曾经有论者进行过深入的剖析:“其中有个锋刃般尖利的内核:丈夫在事发后提出离婚,女儿同母亲划清界限——这是那个时代屡屡上演的一幕。但王安忆没有直接撕裂这真相给人看,这一尖锐让她层层包裹,覆以一家人漂泊的命运和颠沛的生活。儿子就是那位大厨,因年幼对这些全然不知,只是成长颇为艰辛,从他视角看过去,一切是混沌不明的。父亲和女儿是当事人,则每每爆发冲突,不肯原谅对方,实则是不肯原谅自己。”[1]换而言之,如同母亲“她”这样一位因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反抗而在事后被封为“烈士”的人物,到底会在怎么样的一种程度上困扰影响到亲人们未来的命运走向,这个恐怕才是王安忆创作《一把刀,千个字》的初衷所在。事实上,陈诚年仅七岁就已经被迫开始了的人生漂泊,从根本上说,正是拜母亲的不幸遭遇所赐的结果。我们注意到,在第八章刚刚讲述完母亲的悲惨故事后,作家的笔锋陡然一转,一下子就转向了对陈诚即将开始的未来漂泊命运的书写。母亲“她”那个天津的女同学到来后,不由分说就把尚处于懵懂状态的陈诚带走了。到哪里去了呢?接下来第九章的开头所给出的,其实就是相应的答案:“他的记忆从嬢嬢的亭子间开始,窗户底下,女孩子跳着皮筋,唱到: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对你说话。”这样一来,因为陈诚的人生记忆实际上从上海弄堂,从嬢嬢,从那首“马兰花”开始,所以,母亲就被推置到了人生的后台,虽然“她”所投射出的巨大阴影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不论是陈诚后来参加夏令营时的中途逃脱,抑或还是他后来的坚决拒绝进入高中读书,都可以从这个意义层面上得到很好的解释,都是其难以抚平的精神创伤记忆发生作用的结果。母亲,是碑,是纪念碑。而老杨和那一双儿女,不过是被迫驮碑的龟。到这个时候,母亲当年行为的是与非,其实已经不在王安忆的关注视野之中。与母亲当年的壮举相比较,更令王安忆聚焦思考的,乃是母亲的如此一种壮举给亲人,给儿女们所造成的精神后遗症。从这个意义上说,老杨所谓“驮碑的龟”的说法,不仅别出心裁,而且也真正可谓既形象又准确。很大程度上,小说所集中描摹讲述的陈诚不仅地跨中国南北,而且也横越大洋两岸的人生漂泊遭遇,就可以被看作是“驮碑的龟”的一种形象展示。
究其根本,也只有充分地联系那样一个在陈诚他们后来的生活中避之唯恐不及的母亲形象的隐然存在,我们才能够很好地理解陈诚在美国和师师结婚后的一些不正常举动。这一方面,最典型不过的一个举动,就是他毫无征兆地悄然失踪。尽管我们都知道,悄然失踪后的陈诚,不过是过一把能够自控的赌瘾,然后一个人在朋友倩西的住处休整几日,但在他的妻子师师那里,却毫无疑问会生出其他的理解。大约也正因为他们是一种夫妻关系,所以,实在想不出答案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把事情想歪,就会联想到男女之间的关系上。唯其因为师师做了这样的一种理解,所以也才有了她自己和那位无名老头之间对陈诚的报复性行为。但其实,师师对陈诚存在着某种极大的误解。正如同姐姐在安慰师师时所一再强调的自家弟弟不会有其他问题,只不过是拥有某种恋母情结一样,实际的情形尽管未必是恋母,但和一直隐然存在的母亲有着莫大的关联。说到底,无论是恋母也罢,抑或还是仇母也罢,反正在陈诚的潜意识深处,始终有一个隐然的母亲形象在不时地晃动着。对于如此一种情形,我们恐怕也只能够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去做出合乎情理的理解和阐释。
在一部篇幅不是很大的长篇小说中,王安忆能够纵横捭阖地以一种伏脉千里的方式,时而国内,时而国外,时而过去,时而现在,既“思接千载”,又“视通万里”,通过对一种高超厨艺的精细描写,不仅最终把自己的笔触探向历史的深处,而且也还对这段一直到现在都暧昧不清的历史提出强有力的思考与诘问,无论如何都应该获得高度的肯定与认可。
[注释]
[1]吴言:《烟火处的悲悯——王安忆长篇〈一把刀,千个字〉读札》,见《收获》微信公众号,2020年10月31日。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