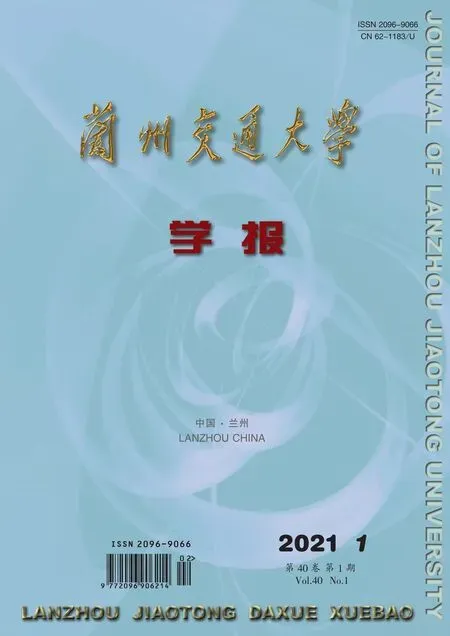《史记·太史公自序》与司马迁的子学
李 昕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史记》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长河中一块瑰丽夺目的珍宝,它包罗万象,贯通古今,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著作。但它也绝非是单纯记载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史书,作者司马迁在这部巨著中不仅熔铸了自己毕生的心血,还融汇进了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使其兼具了史书和子书的双重特点,《汉书·艺文志》就将《史记》列为春秋一家,而司马迁本人最初也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这些都表明了它本身充满了子书的色彩。
既然《史记》是这样一部兼具史书和子书双重特点的巨著,那么我们在研究其所记载的具体历史事件与人物时就需要同时关注其作为子书的另一面,若忽略了这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对《史记》的研究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一些缺漏和不足。而带着子学的思维来认识这部著作,反之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和正确地把握其所叙述的历史事件的内容。但是由于《史记》是一部鸿篇巨著,我们要细致入微地从字里行间去认识司马迁融汇其中的子学思想,着实为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司马迁在全书最后一卷专门作一篇《太史公自序》来统领和总结全书,并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家族历史、家学背景、个人生平以及撰写《史记》背后的思想取向,全文相对篇幅较小,却“追溯了民族的历史、家族的源流、政治的变迁、文化的传承,融自己的遭遇和志向于一炉,是一篇大文章。”[1]历来学者都将这篇文章看作是叩开浩如烟海的《史记》研究大门的一把关键钥匙。因此,本文也将着眼于《太史公自序》,将其作为纲领来探讨司马迁贯穿于整部《史记》的子学体系和价值观念。
一、子学传统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
何谓“子学”?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篇》中开宗明义地解释道:“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2]也就是说子学是指那些通过阐述自己对宇宙和人生的“道”的深刻认识来表明自己思想观点的著作。之后他又提到子学的另一个特点:“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2]指出诸子的著作往往都广博地阐明了各类事物。中国历史上子学发展得最为繁荣与集中的时期便是春秋战国,这与春秋战国以来士大夫阶层在人生价值方面的终极追求有关,《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曾记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3]自此便引出了著名的“三不朽”理论。从“三不朽”的表达中,我们不难看出三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次第顺序,而孔颖达的注疏中对三者的界定更能明确地表达出它们的深刻区别:“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3]“立德”、“立功”和“立言”三者因其各自不同的目标和结果而有着不同的实现难度和影响深远度,这也就决定了三者之间自由高级与低级之分,并最终导致“立德”成为“上圣之人”的目标,“立功”成为“大贤之人”的追求,“又次大贤者”[3]则努力实现“立言”以不朽。如若让此“三不朽”所对应的实现对象更加世俗化、明确化,即可参照《左传·襄公十九年》中所载:“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3]过常宝和高建文先生在其文章中便根据天子、诸侯和大夫的此种分化,认为“三不朽实际可表述为:天子立德,诸侯立功,大夫立言。”[4]而这“三不朽”中虽然“立言”对社会和时代的影响远不及“立德”与“立功”,也最容易实现,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对于在人数上相对处于较广泛阶层的普通士大夫而言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给予了他们值得追寻同时也是能够追寻的人生目标,使他们对自己的人生、对身处的社会现实甚至是遥远未知的后世都充满了强烈又积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春秋中叶以后,诸子百家学说逐步兴起,当时的卿大夫乃至普通士阶层纷纷著书立说,阐明各自的治国理念和人生价值观等追求。这些纷繁复杂的学说大多并未得到当时各国的统治者的亲睐,众多士大夫也并未得到诸侯的重用从而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但他们的言辞或是著作却有许多都流芳百世、影响深远。孔颖达在其注疏中也标举了“老、庄、荀、孟、管、晏、杨、墨、孙、吴之徒”[3],反映了这一时期诸子之学的繁荣发展。
及至秦汉,稳定的中央集权和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自然使得士大夫们更少地拥有通过改良朝政或者抵御外敌来建功立业的机会。在此时,要实现“立德”和“立功”的目标对他们来说更加艰巨,因此秦汉时期的士大夫阶层也更容易将目光投向“立言”这一目标,这就是秦汉时期士大夫阶层“立言”意识依旧十分强烈的原因。但依刘勰所言:“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牗。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此远近之渐变也。”[2]在战国以前,距离周公、孔子等圣人还在世的时代不太远,所以那时的士大夫可以以一种超越当下时代的高远眼光侃侃而谈、自成一家。但到了两汉以后,子学的体势逐渐衰弱下来,大多都只是沿袭和模仿旧说。尽管士大夫们依旧热衷于“立言”,但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标新立异、各执己见的诸子百家学说层出不穷的局面已很难再现。也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论辩著书着实蔚为大观,使后代士大夫阶层难以独辟蹊径、另立门户,再著就如《荀子》、《韩非子》一般博大雄浑地记载言论思想的子书。
既然百家争鸣时代的著述风尚后世实在难以望其项背,那么后代士大夫便转而寻求更加多元的“立言”方式来传递自己的思想理念。正如孔颖达所云:“屈原、宋玉、贾逵、杨雄、马迁、班固以后,撰集史传及制作文章,使后世学习,皆是立言者也。”[3]这也就说明随着时代和文学的发展,“立言”已经不再仅限于百家争鸣时期那样对士大夫言论和思想的单纯记录,还开始包括记叙历史事件的史书的著述和具有文学性质的诗词歌赋文章的创作等形式。作者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和政治理念等融合进丰富多彩的文学体裁中来传递给世人,而这些用以“立言”的子书虽然表面形式上已经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书相去甚远,但其本质与核心仍然是“入道见志”,在纷繁的文学形式背后阐述自己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和对于人生最深刻的理解和洞见。
司马迁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创作《史记》的,他也与当时绝大多数的文人士大夫一样,将“立言”以不朽作为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梁启超曾在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一书中写道:“迁著书的最大目的,乃在发表‘一家之言’……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5]而司马迁本人也在《太史公自序》中借用孔子所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6]来表明自己并不想以春秋战国时期直接记录诸子言论的形式来著书立说,而是欲借助可记叙“行事”的史书来传递自己的思想观念。由此观之,《史记》实在是一本记载和传递着司马迁自己思想观念的子书,其最初的书名《太史公》或《太史公书》也恰好应证了这一点。而《太史公自序》一篇则因其对于《史记》这部皇皇巨著的总结和补充成为画龙点睛之笔,司马迁通过这篇自序十分详细又层次鲜明地向世人传递了自己利用撰写史书的方式来“立言”的动机以及他通过种种史实想要表达的核心理念。
二、《论六家要旨》与论“治”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详尽地追溯了自己的家族历史和文化传统,并通过记述父亲司马谈的临终嘱托——“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6]来表明自己写就《史记》的创作动机,也就是通过“立言”而达到“立身”,此处不再赘述。如上文中所提到的,《自序》在历数家族背景与创作动机的同时,还承载着阐发司马迁重要自学思想的作用。司马迁在《自序》中通过载录和论评父亲的著述《论六家要旨》、记述自己与上大夫壶遂的对话以及概述《史记》创作特点这三个部分阐发了自己欲立之言。接下来就将通过对这三部分的逐一分析来深入理解司马迁在《自序》中所体现的子学思想。
司马迁在《自序》中详细地载录了其父司马谈的文章《论六家要旨》。全文分为两大部分,依照张大可先生的研究,文章的前半部分应当是司马迁对父亲论述六家文章的精要摘抄,只简要精练地陈述各家思想的特点,而文章后半部分应为司马迁结合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对父亲所作文章进行的发挥性阐释,前后两部分内容有经、传之差。[7]
这篇文章主要列举出战国时影响最为重大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比对式的讲述。其中最鲜明的特点是,司马谈在文章最开始分别点明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的优点,与此同时也会指出其缺点,例如他认为阴阳家过分强调征兆,儒家的典籍过于繁多,学习起来很辛苦,且很难获得很显著的成效,以及墨家所追求的简朴近乎苛刻,一般人难以忍受这样的生活等等。但他在最后评论道家之时,却全方位地肯定了道家思想的种种优点:道家会使人精神凝聚,一心不二用,它是“顺着阴阳的大势而为”[1],吸取儒、墨、法思想中的精华部分,随着时代的变迁其思想内核也会适时地发生变化以适应新的时代,此外也能按照某个具体时间和地点的特点以及风俗来采取措施,“根据老百姓的想法而推行政策……因势利导,走阻力较小的路线。”[1]因此,他认为真正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是善于根据简易的治国理论进行变通的,而不是死记硬背一些教条法规,这样才会在治理国家方面事半功倍。总括而言,便如张大可先生在其分析《太史公自序》的文章中所说:“道家言‘无为’,又言‘无不为’,吸收各家的长处、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7]
司马谈如此隆重地将道家放在压轴位置来介绍,并且未见半句批评之语,足以说明道家在司马谈思想体系中所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道家所呈现出的思想状态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理想表现。而生活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的司马迁,为何要将父亲这篇看似十分尊“道”的文章摘进这篇对《史记》具有总结性意义的《自序》当中呢?仅仅只是记录父亲所作的学问传以后人吗?显然不是。前段已经提到,文章的第二部分既为司马迁对父亲思想的发挥性阐释,那么其中一定掺杂着司马迁自己的思考和洞见,他将自己与父亲的思想理念相融合,以一种“共同宣言”的模式表达出来。
而这份集合了司马氏父子思想的共同宣言背后到底想向世人传递怎样的理念呢?从文章开篇来看,司马谈引用《易大传》中的句子:“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6]天下虽然有百家思想争鸣不休,但这些不同的学说和理念最终都会复归于同一个目标,那便是“务为治者也”[6],探讨治国理政之道。自此司马谈几乎是开宗明义地表明探讨如何治理国家才会使国强民富、社会和谐稳定才是诸子百家不断争论的核心和现实意义。那么他在文章中表面上是全方位称赞道家的思想体系,实际上则是在肯定道家思想体系下所形成的这一套治国方略。甚至包括他点评其他家在思想方面的得失,在另一方面来看也是对其各自政治理念方面的批判性陈述。“可见,司马谈是以赞‘道’为名、论‘治’为实”[7],同时也融会贯通其他各家学说来完善和充实自己的治国理念。将父亲文章录入《自序》并进行重新补充阐述的司马迁自然也是十分支持与赞同父亲这些思想的,他将这一家学传统继承下来并在整部《史记》中发扬光大。他在书中提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6]等观点,最终将《史记》著就成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都表明父亲思想对其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司马迁“务为治”的思想也体现在他在文章后半部分进行自己补充阐述的时候,将道家和儒家进行更加详细的对比点评,实质上还是将汉初时所推崇的黄老道家与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强硬政策做对比,对道家赞许有加也是想表达自己对这两种政策的立场:汉初无为而治、因循自然的治国方略较之于汉武帝好大喜功的政治策略以及对思想和社会的管控力度过强而言更甚一筹,这一立场可以说奠定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历史人物方面的思想基础。
三、答壶遂问与创作《史记》的宗旨
司马迁在此篇《自序》中也详细记录了自己所敬重的上大夫壶遂与他之间的问答,并在一问一答之间将自己的核心思想更加深刻、明晰地发表出来。我们可以从二人的对话中明显地看出,往往是壶遂抛出一个问题只有几句话而司马迁的回答却占据了壶遂几倍的篇幅,这也就表明司马迁在此处录载这段对话目的更多是倾向于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
二人围绕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和宗旨这一核心问题进行问答,而壶遂没有直截了当地询问司马迁著史的目的,转而是以孔子作《春秋》为此番对话的引子,问他孔子作《春秋》的动机。周朝末年,周天子大权旁落,各诸侯之间征伐不断,王道衰微。此时的孔子原本想通过直接做官来参与政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却遭遇诸侯冷落,士大夫的排挤陷害。孔子最终认清了这残酷的社会现实,他明白了在这样混乱的时代利用直接参政的方式来使大道恢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于是他便潜心编纂出一部《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以来的兴亡历史,并判断其中是非好恶。对当时上至诸侯,下至卿大夫在内的朝政之事评点批判,以此达到自己对王道的追求。司马迁在此处则引用董仲舒所云来回答这一问题,当然能借用董仲舒的观点便说明他也对此十分认同。孔子是想利用《春秋》一书对历史的记载来阐明自己的王道之志,正如司马迁紧接着引用孔子所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6]此句在前文也曾提到,司马迁借此处引用清晰明了地表达了孔子著就《春秋》的本质目的。“空言”是指言辞道理,“见之行事”是指从具体的事例中参看其中道理,也就是从历史事件中总结切实的经验教训。[8]而后司马迁更是高度评价《春秋》的内容和现实意义,认为它向上追明了夏商周三代之道,向下又成为后世人分析人伦道德关系的纲领。替世人明是非,使他们可以分清何为忠贤,何为奸佞,何为正确的君臣父子之道。除此之外,还记录下来已亡之国的风貌流传于后世,具有无可比拟的文化历史价值。对《春秋》一书的具体内容点评结束以后,司马迁便一语道破《春秋》的最显著特点:“《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6]直至此时,司马迁终于通过前文对孔子作《春秋》的原因以及它的具体内容的铺垫,将自己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落回到一个“治”字之上。之后他更是表明“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6]再也没有像《春秋》这样的经典可以如此切近地将这动荡不安、人伦法纪不明的社会进行拨乱反正,作为人们往后行动的纲领。司马迁更是将其作为君主和臣子的必读书目,如若一国之君没读过这部经书,那么他就不会区分贤士能臣和奸佞小人,如若身为臣子而没有读过《春秋》,那么他便不会知道如何坚守自己的原则阵地,遇到变故也清楚如何权衡利弊。《春秋》在司马迁的口中已然成为每个参与政治的人面前的一面镜子,让参政者们可以时刻对照它来自省。参政者能时时反省自己所实施的政策或者自己所上奏的建议是否合宜,那么整个国家和社会也就很难走向混乱,社会稳定和谐,王道便充行于世。于是我们可以看出,依司马迁所见,《春秋》这部经典的重点是对王道衰微的社会和国家拨乱反正,为参政者提供深刻的借鉴,而这实质上也都是就治理国家而言的,依旧“务为治也”。
在前文中我们曾经探讨过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一大动机便是他感知到了时代的召唤,认为汉武帝时代距离孔子去世已经过去了将近五百年,这个时代注定要出现一位像孔子那样承上启下的大人物。孔子在他那个时代所进行的“修旧起废”[6]便是“论《诗》、《书》,作《春秋》”[6],而司马迁要向孔子学习,便是要效法孔子之作《春秋》,以记载前世今日,继往开来。既然司马迁想要效法孔子之作《春秋》,那么所以他对壶遂所提问题的回答虽然表面是在深入探讨《春秋》的创作宗旨和历史价值,但是其背后蕴含的更是司马迁自己创作《史记》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和效果。既然依司马迁之言“治”为《春秋》一书最显著的特征和目标,那么它也同样可以用于《史记》之上,“治”便也成为了司马迁熔铸于《史记》中的核心思想,至此便与其摘录并阐释父亲文章的最终落脚点一致。洞察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将其作为前车之鉴,以此来整顿人心,避免往后重蹈覆辙,《春秋》和《史记》的历史意义便都在此。司马迁在后文中提到的“述往事,思来者”[6]也正是再次印证和确认其想借《史记》以实现的社会理想。
四、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在《自序》的最后精炼地概述了整部《史记》的创作特点:“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6]这一处与其在另一篇经典文章《报任安书》中所言近乎一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9]而司马迁的这两段话,也成为了后世人们探索其蕴藏于《史记》中深刻思想的重要突破口。“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6]便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相对应,两者最终的目的都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以“成一家之言”。如此看来,司马迁通往“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路径便分为两条。
首先为“究天人之际”,“天人之际”一词最早来源于董仲舒。《汉书·董仲舒传》中有记载董仲舒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祸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10]这也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自汉代以来广为流传的天人感应学说。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司马迁所言的“天人之际”与董仲舒之间还缺少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词“相与”,“相与”即想表明“天人会合,互相感应”[8],天和人之间互相作用与影响的关系在此处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紧密。董仲舒最初的目的本是想借助天人感应学说来对至高无上的君权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预防君主为所欲为,昏庸暴虐,使国家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采用这一“遣告”的方式让君主“畏天”,从而可以不断自省,避免实行不符合天道的政策,招致灾祸。但是这一学说却由于过于放大天对人的影响而最终陷入了迷信天的泥沼。
司马迁并没有全盘采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他从中剔除了“相与”二字,便直接从字面上极大地削弱了天将会施与人的过多影响,使其直观地转换成为天与人之间的交际处,除此外,还要将这交际处“究”一番,便更突出了他实际上是倾向于“天人相分”的[8]。而司马迁想要深入探究“天人之际”,也说明了他想要借《史记》的创作来明确天与人之间真正的关系,从而“肃清‘天人感应’思想的迷信与局限”[11],这是司马迁超越于他所处时代的思想传统而迈出的巨大一步。汪荣祖先生就曾对司马迁的这一思想突破进行了高度评价:“当司马迁之世,天人感应,五德终始,方士求仙,皆风尚不衰。作史者不可不记,而迁独疑之,别究天人之际,其识可谓高矣。”[11]既然他相对弱化了天对人行为的重大影响,那么从另一角度说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动性,人不必再一举一动都去考虑自己是否违抗了天命,反而是自己去主动探寻历史发展的道路,做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人。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再迷信天,人们便会从由人的切实行动所融汇而成的历史长河中总结和学习古往今来兴亡成败的规律,借古鉴今,见贤思齐。
通过“究天人之际”司马迁破除了人们对天人感应的迷信传统,下一步便是“通古今之变”使得重新激发主动性的人们在新的历史时代中所行所想皆有切实的历史依据,不再只是依照一个虚妄的天。因此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是就《史记》的取材而言。在此之上他运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承敝通变”等治史方法将纷繁复杂的史料进行串联编排,最终使得《史记》成为一部对人类文化历史无所不包的皇皇巨著。“‘究天人之际’,讲自然和空间,划分天人关系。‘通古今之变’,讲时间流变,人类社会是随时间的流逝而演变。司马迁所要捕捉的就是这一个‘变’字。”[8]使得人们在这每分每秒都在流变的历史舞台上能够“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也就是“通过考察历史来把握历史演进的内容,认识治乱兴衰的规律”[8],从而让这部书成为当世参政者们的一面镜子,为他们提供充分的历史借鉴。而将这治乱兴衰的道理糅合进不断流变、难以捉摸的历史事实,便是司马迁践行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具体表现。
由上文可见,司马迁借由“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两种相互承接又相互影响的路径与方法,达到如《春秋》般让参政者“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的效果。换言之就是司马迁意欲通过破除对天人感应的迷信而后总结古往今来历史发展的兴衰规律,使得当下时代的统治者掌握更加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治国方略,其最终落脚点依旧在一“治”字之上,此一“治”字就成为司马迁在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后终于成就为“一家之言”的核心灵魂。
五、结论
出生于史官世家的司马迁承袭父亲太史令的官职,并深受家族修史传统的影响,发愤著就出此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史记》绝不仅仅是一部单纯实录历史事件的史书,不论是春秋至汉代以来子学传统对司马迁这类士大夫思想的浸染,还是父亲临终前声泪俱下的谆谆教诲,都让司马迁拥有着更深层次的人生追求和志向,这一志向便是“成一家之言”,通过“立言”以“立身”、以“不朽”,完成父亲对自己的殷切希望同时也是实现自己作为一名志存高远的士人最崇高的价值追求。也正是因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这一强烈的现实愿望,使其得以完成愿望的载体《史记》同时成为了一部不折不扣的子书,书中司马迁将自己的思想通过载录包罗万象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方法展现出来,这一独特的表现方法又使其与春秋战国以来其他子书却别开来,自成一家。当然,《史记》全书共“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我们要通过通读全书毫末来细致地把握司马迁的子学思想实为不易,但《太史公自序》作为全书的纲领性篇章,篇幅相对较小,我们便可以从中窥探出司马迁想透过《史记》一书所表达的核心思想。而从他摘录并解释父亲所作文章《论六家要旨》以及他与上大夫壶遂的问答中我们看出,“治乱”这一核心思想贯穿始终。直到文章最后叙述《史记》全书特点与体例,所言背后无不渗透一“治”字。
综上所述,司马迁以“成一家之言”为全书的创作宗旨和追求,把《春秋》当作效法对象创作《史记》,将“治乱”思想融会贯通于全书之中,“澄清治乱成败之源,探明为治之道”[12],“实‘务治之书’”[12],为当世参政者提供充分的治国理政方面的参考与借鉴资料,并通过这些资料了解怎样的政治才算是好的政治,由此来指导每位参政者的行动,已达到维护国家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使王道行于天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