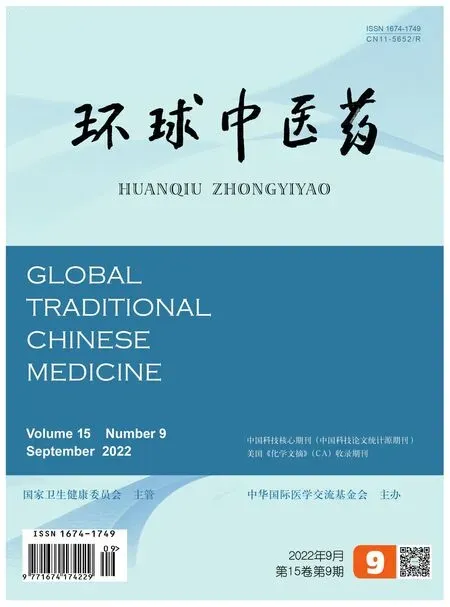柴胡桂枝干姜汤病机浅析
王天君 刘晓鹰
柴胡桂枝干姜汤出自张仲景《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147条及《金匮要略·疟病脉证并治第四》附《外台秘要》方。第147条:“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金匮要略·疟病》附方(三):“柴胡桂姜汤方治疟寒多微有热,或但寒不热,服一剂如神。”原方:“柴胡半斤、桂枝三两(去皮)、干姜二两、瓜蒌根四两、黄芩三两、牡蛎二两、甘草二两(炙)。”
历代医家对柴胡桂枝干姜汤的病机见解颇多,如少阳病兼水饮内结、少阳病兼表邪未解、少阳病兼津液损伤、太阳少阳病兼阴阳两伤、少阳病气化失常、胆火内郁兼太阴虚寒、上热下寒寒热错杂等[1];诸多病机中又以太阳少阳合病、上热下寒、寒热错杂、少阳病兼水饮内结、少阳太阴合病论述及运用最多,其病机主要争议有三:太阳之邪是否解也;是津液损伤还是水饮内结;是否存在太阴虚寒的病机。后文将主要从这三点进行病机探讨。
1 太阳之邪已解,少阳之邪未解
“太阳之邪未解”的观点认为,汗下后,太阳之邪未解,而邪入少阳,致太阳、少阳合病,而配伍桂枝,其意在解太阳之表邪。如尤在泾《伤寒贯珠集》[2]曰:“伤寒汗出,周身漐漐,人静不烦,为已解;但头汗出而身无汗,往来寒热,心烦者,为未欲解;夫邪聚于上,热胜于内,而表复不解,是必合表里以为治。”柯琴《伤寒来苏集》[3]:“此方为柴胡证俱,而太阳之表尤为未解,里已微结,须此桂枝解表,干姜解结,以佐柴胡之不及耳。”方有执《伤寒论条辨》[4]言:“桂枝甘草,和解未罢之表邪。”而“太阳之邪已解”的观点则认为配伍桂枝是通达阳气,助气化,如刘渡舟《伤寒论讲稿》[5]中专门提到:“为什么加桂枝、干姜?是因为桂枝、干姜通达阳气,温化脾气……桂枝则通阳气,行三焦,行津液,利小便。”由此可看出,对“桂枝”配伍意义的不同看法是产生两种观点的原因之一。
笔者认为是少阳之邪未解,太阳之邪已解。首先,由于历史沿革,张仲景《伤寒论》中“桂枝”的名称及药用部位与后世有所差别。日本学者真柳诚从多方对仲景方中桂类药物进行考证,结论为北宋林亿等[6]对《伤寒论》《金匮要略》进行校对时将书中所有桂类药物(包括桂、桂心、桂皮等)均改为了桂枝,他认为汉代所用“桂枝”很可能是现今所用的“肉桂”。清·张璐《本经逢原》[7]言:“《本经》之言牡桂,兼肉桂、桂心而言, 言箘桂,兼桂枝而言也。”由此可认为《伤寒论》中“桂枝”应为《神农本草经》所言之“牡桂”,即现今所用之“肉桂”。
《神农本草经》言:“牡桂,气温,味辛,无毒。主上气咳逆,结气,喉痹,吐吸,利关节,补中益气。”(一般同时代的医方与药物著作可相互参考,且《神农本草经》成书早于《伤寒论》,所以其所记载药物功用应是仲景乃至汉代医家对药物认识及应用最为可信的证据来源)。清代张锡纯以《神农本草经》为旨对“桂枝”作了详尽的辨论:“其味辛微甘,性温。力善宣通,升大气,降逆气,散邪气。桂枝加桂汤用之治奔豚,是取其能降也……小青龙汤原桂枝、麻黄并用,至喘者去麻黄加杏仁而不去桂枝,诚以《神农本草经》原谓桂枝主吐吸,去桂枝则不能定喘矣……桂枝善抑肝木之盛使不横恣,又善理肝木之郁使之逆者下降。其宣通之力,又能导引三焦下通膀胱以利小便”[8]可见,“桂枝”的降逆气,抑肝木以调节少阳枢机是其主要作用之一;正如《长沙药解》[9]所说:“桂枝,入肝家而行血分……最调木气。升清阳之脱陷,降浊阴之冲逆……入肝胆而散遏抑。”
其次,仲景方中配伍桂枝而治太阳表邪未解的方如桂枝汤、麻黄汤、小青龙汤、桂枝加葛根汤、葛根汤等,是取其辛散大热而宣通阳气的作用;而非桂枝发汗或止汗以祛邪,即张璐《本经逢原》言:“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营弱卫强,阴虚阳必凑之,皆用桂枝发汗。此调其营,则卫气自和,风邪无所容,遂从汗解,非桂枝能发汗也”。且仲景明言“桂枝本为解肌”,而不是桂枝本为解表或解卫,肌为营,在里不在表,因此“桂枝”的作用不是能解表,而是宣通阳气。
再次,《伤寒论》146条:“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方为小柴胡汤和桂枝汤各取原方量之半合剂;若是太阳之邪未解,而邪已入少阳之证,完全可用柴胡桂枝汤方。
由此可见,柴胡桂枝干姜汤证中“此为未解也”为少阳之邪未解,太阳之邪已尽。其配伍桂枝的意义也非解表,而是抑肝木以降逆气,调节少阳枢机,宣通阳气而疏导三焦。
2 津液损伤,而非水饮内结
津液损伤、水饮内结之病机争议,主要是对条文中“小便不利、渴而不呕”的理解不同而来。以“水饮内结”作注解,其依据主要是少阳有邪致枢机不利,而手、足少阳经常相互影响,导致手少阳三焦因之雍滞不通,津液输布运行不利,则水饮内结。如唐容川《伤寒论浅注补正》[10]:“阳气下陷,水饮内动,逆于胸胁,故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水结则津不升,故渴……故用柴胡透达膜腠,用姜、桂以散撤寒水,又用栝蒌、黄芩以清内郁之火。”另吉益东洞《类聚方》[11]、汤本求真《皇汉医学》[12],及国医大师梅国强教授主编的中医教材《伤寒论讲义》[13]等书中对“小便不利、渴而不呕”均以“水饮内结”作注解。
然而,成无己《注解伤寒论》[14]、汪苓友《伤寒论辨证广注》[15]、刘渡舟《伤寒论讲稿》[5]等则以“津液损伤”作解,其依据主要是汗下后损伤人体津液,导致津液不足,再加少阳枢机不利引起气化失常,津液不布。如汪苓友称:“小便不利者,此因汗下后三焦津液少也;惟津液少而非停饮,是故渴而不呕。”刘渡舟言:“渴,为津液虚,而不是胃有停饮,所以不呕,小便不利与渴而不呕应连起来看,如果是停水的口渴,小便不利往往就有欲呕,而津液虚则渴而不呕,并提出这里的渴而不呕有鉴别诊断的意思。”两位医家不仅认为“小便不利、口渴”是津液亏虚所致,并且还将“渴而不呕”作为鉴别“津液亏虚”和“水饮内结”的关键症候,即刘老所说的“渴而不呕”有鉴别诊断的意思。
笔者认为是津液损伤,而非水饮内结。从“小便不利、渴而不呕”的症状来分析。纵观《伤寒论》全篇,水饮内停的方证如:小青龙汤证、茯苓甘草汤证、五苓散证、猪苓汤证、真武汤证等,小青龙汤证治“小便不利,呕、渴”;茯苓甘草汤证治“小便不利,不渴、呕”;五苓散证治“小便不利,渴、呕”,猪苓汤证治“小便不利,渴、呕”,真武汤证治“小便不利,不渴、呕”,小青龙汤、茯苓甘草汤为水停心下,五苓散为水蓄下焦,猪苓汤为水热互结,真武汤为阳虚水泛;均有水饮内停,不论渴或不渴,都有呕的情况出现;因此柴胡桂枝干姜汤证强调“渴而不呕”确实有与水饮内停之证鉴别的含义;且《伤寒论》第59条:“大下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明确提出汗、下之后出现的“小便不利”是因津液损伤所致。
从柴胡桂枝干姜汤中的方药配伍来分析。方中配伍瓜蒌根、牡蛎,合为栝楼牡蛎散,《金匮要略》:“百合病,渴不差者,用后方主之。栝楼牡蛎散方。”《神农本草经》言:“栝楼,主消渴,身热,烦满,大热,补虚安中,续绝伤”“牡蛎主治伤寒、寒热,温疟洒洒,惊恚怒气”《医宗金鉴》对栝楼牡蛎散的注解称:“与百合洗身而渴不瘥者,内热甚而津液竭也。栝楼根苦寒,生津止渴,牡蛎咸寒,引热下行也”,说明天花粉、牡蛎两味药主治口渴乃津液损伤。“但头汗出”是因津液随气逆上冲,见头汗出,而身无汗,也说明机体津液不足。
3 太阴虚寒
“太阴虚寒”的病机,是刘渡舟先生根据陈慎吾老先生之言“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少阳病兼阴证机转者,用之最恰”的理论,并经过多年临床实践而悟出的。刘渡舟在《伤寒论讲稿》[5]中提到:“此条论述因伤寒误治而导致邪传少阳,气化失常,津液不布的柴胡桂枝干姜汤证,并认为此方是与大柴胡汤进行对比的方子,大柴胡汤治少阳之邪归并入阳明,阳明燥热,既解少阳,又下阳明,是治实证,而柴胡桂枝干姜汤是少阳之邪不解而有脾寒和气阴、气津受伤,气化不利是夹有一定的虚寒的,有太阴病的阴证机转的。” 并总结为“胆热脾寒”,即少阳病兼太阴虚寒;并强调了“阴证机转”,意思是病虽涉及太阴但未必有太阴病之“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等典型的太阴里虚寒证;汗、下之后,邪未解,势必会损伤人体正气,并且使脾胃受损,而“不呕”说明胃腑未受影响,而脾是否受损却未明言;所以说“阴证机转”。
笔者认为“阴证机转”与仲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思想一脉相承,本身柴胡桂枝干姜汤证就是少阳有邪,少阳之邪传于太阴,或影响太阴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虽未见太阴之病的明显症状及脉证,但在治疗上当先“实脾”,方中配伍“干姜”即是温脾散寒,《神农本草经》言:“干姜,味辛、温。主治胸满,咳逆上气,温中止血, 出汗,逐风湿痹,肠澼下利,生者尤良。”干姜与宣通阳气的桂枝、补中益气的甘草相配伍,其温脾、实脾的作用更强。刘渡舟老先生更是认为:“干姜是理中汤的最主要的药,干姜配伍甘草是半个理中汤。”
林玮怡等[16]从六经归属及五行理论分析“柴胡桂枝干姜汤”之病机亦认同该方确有“胆热脾寒”之病机。并且现代医家依据“胆热脾寒”的理论,于临床中应用柴胡桂枝干姜汤亦效果显著。如石维娟等[17]通过数据挖掘总结柴胡桂枝干姜汤临床应用规律,结论是柴胡桂枝干姜汤证临床核心症状出现的频数按降序排列有口渴、口苦、纳差、心烦、便溏、胸胁满闷、小便不利、腹胀、失眠、胸胁胀痛、神疲乏力;“纳差、便溏”之太阴证的症状频率甚至高于“胸胁满闷、胸胁胀痛”等少阳之证的症状频率。李碧娥等[18]用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胆热脾寒型复发性口腔溃疡的临床观察,其结果显示“便溏”恢复正常的比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林震群[19]运用柴胡桂枝干姜汤加减治疗胆热脾寒型慢性胆囊炎43例,其总有效率为90.70%,并可显著改善胆热脾寒型慢性胆囊炎的“口干不欲饮、大便溏泻”等临床症状,减少慢性胆囊炎复发,远期疗效效果更佳。因此,柴胡桂枝干姜汤证太阴虚寒的病机是非常合理的。
综上,柴胡桂枝干姜汤证之病机为少阳有邪,津液损伤,太阴虚寒。伤寒五六日,为邪传少阳之时,邪陷少阳,枢机不利,故胸胁满,微结,往来寒热、心烦;发汗泻下后,胃中无停饮,而机体津液损伤,故小便不利,渴而不呕;少阳有邪,枢机不利,气化失常,津液输布不利兼津液损伤,故“但头汗出”;少阳之邪,很可能影响太阴,据仲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理论,及方中配伍干姜、甘草以温中,可见该方证有太阴虚寒之病机。
4 柴胡桂枝干姜汤临床验案分析
4.1 瘾疹
患者,女,7岁,2019年8月8日初诊。因“反复全身皮疹1年余”就诊。1年前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周身皮疹,在外院口服中药、抗过敏及激素外擦等治疗,皮疹反复时轻时重但从未消褪,现全身皮疹,如鸡皮状,瘙痒,受阳光照射后加重,纳可,大便偏稀,日一次,口干,夜汗多,平素易感冒、怕冷。面黄,形瘦少华,全身满布米粒大小可触性淡红色皮疹,仅面部、手背无皮疹,压之不褪色,疹间皮肤颜色正常。舌淡,苔薄白,脉细。诊断:瘾疹;辨为少阳有邪、太阴虚寒兼津伤证。处方:柴胡10 g、桂枝10 g、干姜9 g、黄芩6 g、天花粉12 g、海蛤10 g、当归5 g、生地黄10 g、川芎10 g、赤芍6 g、苦杏仁10 g、厚朴10 g、辛夷20 g、苍耳子10 g、细辛3 g、炙甘草10 g、黄芪15 g,14剂免煎颗粒剂(华润三九),日1剂,早晚分2次服。
2019年8月23日复诊,全身体瘙痒较前明显缓解,无皮疹,晨起偶鼻塞,纳食可,大便调,尿频,量一般。舌尖红,体淡红,苔薄白,脉细。守上方:去厚朴,苍耳子减至6 g,黄芪加至20 g,14剂免煎颗粒剂(华润三九),服法同前。服药后皮疹基本消退,效不更方,继服药14剂,随访半年未复发。
按 该患儿皮疹1年余,时轻时重反复发作,是邪扰少阳,正邪抗争在机体半表半里的临床表现,正气抗邪外出,则皮疹轻微或处于缓解期,正气虚弱,邪气偏盛,则皮疹加重。面黄,形瘦少华,是脾气虚,平素易感冒,怕冷,舌淡红,进一步提示太阴脾虚寒。口干,为津液损伤;其主要病机少阳有邪、津液损伤兼太阴虚寒;遂用柴胡桂枝干姜汤加减,柴胡桂枝干姜汤和解少阳调枢机兼能养阴,当归、生地、川芎、赤芍合为四物汤,因皮疹瘙痒还多与风、虚有关,如《外科大成·诸痒》[20]强调“风盛则痒”,再则患儿病程日久耗气伤津,用四物汤养血活血,取“祛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意,加细辛、苍耳子配桂枝、赤芍等进一步调和营卫,干姜、黄芪补太阴之虚,全方合用少阳、太阴同治,且兼顾气血同治,使邪去身安。
4.2 鼻渊
患者,男,7岁,2019年5月16日初诊。因“反复鼻塞半年,咳嗽3周”就诊。患者半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鼻塞,流鼻涕,在外院诊断为鼻窦炎,口服药物无明显缓解,3周前发热,热退后咳嗽至今,夜间咳嗽为主,咳吐脓痰,无发热恶寒,无咽痛,口干,纳差,大便可。舌尖稍红体淡,脉细。诊断:(1)鼻渊;(2)咳嗽;辨为少阳有邪、太阴虚寒兼津伤证。处方:陈皮15 g、姜半夏15 g、茯苓15 g、炙甘草9 g、柴胡9 g、桂枝9 g、干姜3 g、黄芩6 g、天花粉10 g、牡蛎20 g、辛夷20 g、苍耳子10 g、炙麻黄6 g、淫羊藿10 g、细辛4 g,7剂免煎颗粒剂(华润三九),日1剂,早晚分2次服。
2019年5月30日二诊,服上方后,无呕吐,无咳嗽,无鼻塞,无流涕,无咽痛,易汗,无乏力,纳少,食欲差,有口气,大便可。面色少华,咽红,舌稍红,苔薄白,脉细滑。守上方,姜半夏减至10 g,苍耳子减至6 g,加黄芪15 g,7剂,免煎颗粒剂(华润三九),服法同前。后续服10剂,随访半年未复发。
按 患者有纳差、舌淡提示脾阳虚,太阴不足,鼻塞及咳嗽缠绵难愈,反复发作,可看作是少阳证往来寒热在鼻部的表现,少阳有邪,正气抗邪外出,则鼻塞缓解,正气稍弱,邪胜入里,则鼻塞发作或加重;口干,进一步提示少阳枢机不利,气化失常,津液不足,兼输布不利,导致津液凝聚成痰,可进一步加重其鼻塞、流涕的症状,并导致咳嗽难愈。患儿少阳有邪、津液损伤兼太阴虚寒,遂选柴胡桂枝干姜汤加减,方中柴胡解少阳之邪,配黄芩清肝胆郁火,以利枢机,桂枝配姜半夏、陈皮可降痰饮之逆而止涕,配干姜可温脾家之寒,加茯苓增强健脾利水之功,天花粉、牡蛎清热生津、散凝结之痰,加苍耳子、辛夷通鼻窍,增强通鼻窍之效。
4.3 谨守病机,异病同治
上述两个病案,病案一中患者的临床表现是皮疹反复发作、时轻时重;而病案二则是鼻塞反复发作,时轻时重;两者虽疾病不同,但症候特点相同,均与“往来寒热”的发作特点相似,是少阳有邪的表现;两者均无小便不利,但都有口干不呕,是津伤不甚且胃中无停饮的表现;病案一患者面黄形瘦、怕冷、舌淡,纳虽可,但便稀;病案二患者纳差,便可,舌淡,虽临床症状不同,但均为太阴脾虚寒的表现。两者主要病机为少阳有邪、津液损伤、太阴虚寒三者兼有,用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效果尤显。可见,在临床应用中,虽患者的临床症状与原文描述的“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等相差甚远,但只要病机相同,均可用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如张葆青[21]认为在临床上只要辨证为少阳肝胆郁热兼太阴脾虚有寒,皆可应用柴胡桂枝干姜汤。李珊等[22]运用柴胡桂枝干姜汤合升降散治疗慢性夜咳的临床经验,认为柴胡桂枝干姜汤方兼顾少阳与太阴,既可治热证、实证,又可治寒证、虚证,同时兼顾津伤。
5 讨论
柴胡桂枝干姜汤之病机为少阳有邪,津液损伤,太阴虚寒。该方在临床运用中所治疾病极多,临床症候多样,证型不一,但病机均兼顾少阳及太阴,津伤程度不一。少阳证症状多见“口苦”“咽干”“胸闷胁痛”“胸胀”等,太阴证症状多见“便溏或大便偏稀”“纳差”“食欲欠佳”等,津伤的症状多见“口渴”“口干欲饮”等。临床运用时,应抓其病机的主要矛盾,即少阳与太阴虚寒证,而津伤为其次要矛盾。笔者认为临床若辨证为少阳兼太阴虚寒证,即可选用柴胡桂枝干姜汤加减化裁进行治疗。
小儿疾病应用柴胡桂枝干姜汤方时,又需结合小儿生理特点来看。小儿体禀少阳,其脏腑焦嫩,形气未充,抗病能力较弱,易于发病,且病邪传变迅速。外邪侵袭,太阳受邪,因腠理不固,易内传少阳,而当邪犯少阳,枢机不利,则见疾病反复发作;且小儿体质“脾常不足,肝常有余”,若少阳有邪,则往往兼有太阴脾虚。少阳证临床常见的“口苦”“咽干”“目眩”“胸闷胁痛”等症状,在小儿疾病中往往难以被患儿或其家属准确描述,为医者判断小儿是否少阳受累带来很多困难;笔者认为凡患儿病程日久不愈,且反复发作,病情时轻时重等均需考虑少阳枢机不利的问题;若临床症状有少阳证特点,并伴脾虚寒(如纳差、便溏等),津伤口渴、不呕的症状,兼或不兼有热象(如烦躁、口臭、舌尖红),兼或不兼表证(鼻塞、流涕、咳嗽、皮疹、发热、畏寒)皆可使用柴胡桂枝干姜汤加减化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