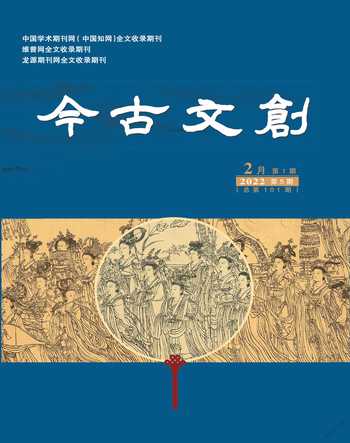汪曾祺后期作品风格及其成因
彭雅兰
【摘要】 汪曾祺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大众的视野,他的代表文章《受戒》等都呈现出一种清淡悠远的风格。但是较少有研究者注意到汪曾祺晚期作品风格及题材的变化,本文在阅读了相关文献之后,对汪曾祺晚期作品的风格及题材做简单说明,探究其晚期作品风格转变的原因。
【关键词】 汪曾祺;晚期作品风格;影响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5-0031-03
一、引言
汪曾祺的作品在大多数研究者眼中都被定义成一种温馨、恬淡的风格。在他的文字里,通常看到的是温馨的家长里短。他师从沈从文,二者的文风也一脉相承,不仅朴素、淡雅,还用温馨的文字各自在作品中为读者打造了有着家乡印记的世外桃源。不同之处在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充满了激情的,而汪曾祺笔下的水乡则更多地展现出一种温馨、和谐的情调。
这是一位怎样的老人呢?在他的文字里,通常看到的是温馨、是家长里短,是普通人的平淡生活,而这些叙述中,没有大悲、没有大喜,仿佛浩瀚海洋中漂泊的一只小船,晃晃悠悠,有时面对疾风,有时享受宁静。
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的风格是在转变的,尤其是在他的晚期作品中,都能读到一些不同于之前的东西。这里所说的晚期作品主要指的是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及90年代写的作品。在这一时期,汪曾祺丢弃了充满温情的眼光,开始认真审视世界,也就是说,汪曾祺晚期的作品区别于之前的“清淡和谐”,转而追求一种反叛、悲凉的风格。[1]
二、晚期作品主题
(一)生活之苦
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汪曾祺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评价生活,描写生活中痛苦和悲伤的一面。《百蝶图》中能干漂亮的王小玉,始终不被爱人的母亲认可,在爱人母亲的阻挠下,他俩被迫分离。相比于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对巧云未来的美好祝愿,汪老在这篇文章中向读者揭露了真实的生活。并不是所有的两情相悦都能修得花好月圆,这世間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阻碍。
汪曾祺对于保安队是不大喜欢的。在他看来,保卫团就是一群吃饭不干活,还仗着自己的身份地位欺压平民百姓的人。在这些保卫团的人物刻画中,《鲍团长》中的鲍崇岳是他笔下唯一一个有着正面形象的民国军官,他为人正派,朋友也多,将不怎么正派的保卫团管理得井井有条,对维护地方的安定起着不小的作用。他作为一个团长,按理说应该受到别人的尊敬,却在生活中处处碰壁。自己的儿子情窦初开,喜欢上了当地大户杨家的女儿,而平日里待鲍团长很客气的杨宜之,却在鲍团长面前暗讽鲍家门第太低。鲍团长觉得尴尬,便不怎么与杨家往来。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受人之托,前去规劝平日里无法无天的“八舅太爷”,却吃了个闭门羹,只得尴尬离去。而他好不容易等到一位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回乡小住,在他满怀希望等着这位名书法家指点一二的时候,却不料别人压根没看上他的字。
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他终于知晓,自己在这个职位,受到的尊重都是表面的,平日别人里所谓尊敬和恭维,在关键时刻却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他并没有真正受到大家的敬重。“团长”这个职位,并不能为当地百姓、家人、甚至自己谋得一点儿好处,却反而让自己自尊受挫。在最后,他选择了辞掉这个职务。吃饱喝足之后,他写下一封辞职信,并题诗一首,“田彼南山,荒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①这封信看似洒脱,实则是心酸与不忿凝结而成的。
当鲍团长发现自己一生蹉跎,老无所成的时候,备受打击的他以倔强的方式保留了自己最后的一点体面。他的内心是痛苦的,在这个位子尚且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何况是离职之后呢?恐怕连表面的尊重和客套都没有了吧。鲍团长对于周围的人来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罢了。一个团长受到的待遇也仅仅只是这样而已,更遑论普通人了。从这些小人物的不幸中,汪曾祺带领读者探索了生活中不如意的一面。
(二)性爱与身体
汪曾祺在后期的作品中,通过对性的描写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剖析,宣扬一种自由、随性的生活态度,提醒人们遵循本能欲望的呼唤。作为一个抒情作家,汪老之前的作品中是极少提到性爱的,即使有主人公两情相悦的结合,也往往用清淡的文字一笔带过。但是在后期作品中,他开始反转自己之前的写作态度,大胆地、露骨地描写性爱,用一种赤裸、真实的描写颠覆了原先的抒情世界。
在《薛大娘》中,作者用直白的语言描写她的乳房,“引人注意的是她一对奶子,尖尖耸耸的,在蓝布衫后面顶着”。作者赋予她一种无拘无束的生命观和率性而活的生活态度,震撼着之前那个和谐的圣境。[2]
汪曾祺作品中的这些在底层生活的人,用自己的行为去反抗生活,却总是以失败告终。[3]汪老往往给作品中的这些小人物的结局留下一片空白,给读者想象和回味的空间。也正因为如此,生活的痛苦与人物的不幸在这种留白中被放大、延长。
(三)死亡与离别
死亡与离别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悲伤话题,但它们又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情。他们总是来得那么突然,不给人一点准备的机会。在汪曾祺早期的作品之中,这些话题总是被刻意回避。即使是《大淖记事》中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十一子,也能因为一碗尿碱起死回生。但是在后期的作品中,汪老选择正视这些话题,不再笑而却之,而是用自己的语言描绘这些痛苦但是真实的话题。[4]
《小孃孃》中,乱伦的谢淑媛和谢普天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作者通过描写两人乱伦的变态行为,展露了世界的冷酷和人精神上所受的压力。不伦的性与爱受到的不仅是世俗舆论的冲击,还有主人公内心的自我谴责。二人只拥有了短暂的快乐,就在纠结和遗憾中结束恋情,最终以死亡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告别。
(四)现代与古典的融合
汪曾祺晚年一大成就是改写了蒲松龄的《聊斋》,著成《聊斋新义》。《聊斋新义》并不是简单将古文转化成大白话,而是在转述故事的基础上对人物和情节做了改动和整理,虽然整体脉络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但故事的展开更合理,结构也更清晰。最为重要的是,作者向故事中注入了现代意识,使之有了不同于原著的现代观念。
《陆判》一文中,作者放弃了原本关于朱尔旦及儿子官至达官显贵的主线情节的描写,着重写朱尔旦妻子换头后种种怪异的行为。在故事结局,朱尔旦的老婆说:“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是我,还是不是我。”朱尔旦妻子的追问中暗含着很明显的现代性,汪曾祺将“我是谁”这个充满了现代意识的思考,融入古典的神鬼作品中,引起读者对生命和自我的思考,颇有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双灯》中,汪曾祺则以一种梦幻的方法来描写离别。勤劳的二小,因为家境贫寒还没有说亲,此时突然出现的女郎和她面前举着双灯的丫环让他大吃一惊。二人甜蜜相伴两年之后,女郎却在某天突然离去。二小不解,女郎回答道,“我们,和你们人不一样,不能凑合。”在原版《聊斋》中,蒲松龄给出的女郎回答是:“姻缘自有定数,何待说也。”因爱而结合,缘尽就分手,改写后的《双灯》表达的是一种超前的婚恋观念,不凑合,不将就,这是现代人追求却并没能达到的境界。在这篇作品中,汪曾祺以人鬼之间的恋爱与分手诠释了这种超前现代的恋爱观。
汪曾祺晚期风格的转变是很明显的了,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他的转变呢?一位年事已高、功成名就的作家,为什么要冒着这样的风险去推翻自己从前建立起来的美好温馨的世界呢?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和资料,结合汪老的人生经历,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看法:
三、晚期风格转变的原因
(一)“衰年变法”的决心
作者的所思所想往往体现在作品之中。每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会因为作者的心境和所处的状态而有所不同。汪曾祺也是一样,到了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年龄的增加和身体的衰老,汪曾祺也开始认真审视自己之前的生活。人总是要老的,但他想让自己老得慢一点儿。如何使自己老得慢一点呢?那就是要多多和年轻人交流接触,了解新事物,保持新的思想。汪老在为几个年轻作家写序的时候接触到了他们的作品,通过阅读新一辈文学家的作品,汪曾祺常常对写作生发出新的思考,用他的话来说,这是给他自己这盆奇形怪状的老盆景下了一场雨。
70岁在汪曾祺的一生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水岭。他在这时候明确提出“衰年变法”的意图,并在之后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所谓的变法就是指在作品里融入更多的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可以融合的,传统文化和外来影响也是能够相互促进的,作为一个作家,要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一点新的刺激。[5]
汪老在1997年去世,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年,他一直笔耕不辍,甚至比之前更加高产。对他而言,这是一次新的航程,他也深知这次变法的艰难,但是古稀之年的他还是选择了继续前行。
衰年变法,展露的是汪曾祺对这个世界新的理解和感受,这种新的眼光和心态通过作者的笔端投射到作品之中,就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风格和作品主题。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温馨与宁静是靠牺牲人的欲望换来的,隐藏在和谐生活背后的是被压抑的人性,于是在晚期的作品中,他将目光大胆地投向了这方面的题材,用一种直接的方式去书写人的本来欲望。[6]
(二)使我们的人民变得文明起来
汪曾祺为人友善,用善意的态度去对待身边的一切人和事,即使在青壮年时期度过了一段艰辛的日子,他也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爱意。
在前期的作品之中,汪曾祺往往是在写自己的儿时回忆,家人的宠爱、殷实的家境、父辈的言传身教,为他打造了一个快乐的童年。童年时期的种种快乐,带给汪曾祺的是温暖和勇气,让他在逆境中也能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当回忆起家乡的时候,他就忘却了一切不幸,仿佛一个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所感受到的只有温暖和善意,这也使得他的作品展现出一种恬淡、和谐的情调。
但是人不能靠着回忆过日子,拼命想要遮盖的伤疤还是会在那里,当你不小心拉扯到它的时候,它曾经给你带来的一切痛苦都会被无比清晰地放大在你的眼前。汪老后期的作品大胆直率地向人们揭示了生活中的其他痛苦与不幸,这一切都是生活的再现。[7]生活是复杂的,人们常常会在柴米油盐中感受到生命的乐趣,另一方面,鸡毛蒜皮的小事和突如其来的灾祸又会将人们打个措手不及。
作者写這些普通人的生活,写他们经历的曲折和伤痛,目的是为了提醒读者。[8]人们通常很容易就会忘记犯过的错误,汪曾祺通过作品记录下来的这些瞬间,是希望让大家牢记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要努力使我们的人民文明起来。
(三)现实主义的复现
汪曾祺在四十年代初期发表的作品中,有一部分已经很明显地体现出西方文学留下的印记,这期间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复仇》。这部作品不同于80年代作品的风格,而是体现出一种意识流小说的韵味。作者处于一种情绪放空的状态,意识的流动决定了作者的思路。汪曾祺在大学的时候阅读了很多外国的作品,他也承认自己受到了现代主义、意识流方法的影响。
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一船鸟,一船百合花。深巷卖杏花。骆驼。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惨绿的雨前的磷火。一城灯!
—— 《复仇》 [9]
主人公的意识是流动的,作者的意识也在一起流动,通过这样的方式,二者的距离被缩短,使得作家能够更好地贴近人物的来写。作者在这里不是以第三者的视角叙述人物的故事,而是以一种平等的视角展现主人公的想法和意识。这对于传统的叙述性的写作方法是很有冲击的。
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也体现出比较鲜明的现代主义的色彩,代表性的作品有《绿猫》 《待车》等。在《待车》这篇文章中,作者在回忆与现实之间来回跳动切换,在时空中都进行了大跨度的跳跃,而对于人物背景和情节脉络,作者并没有交代清晰,使得整篇文章笼罩在一种朦胧模糊的情感之中。[10]
在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中,虽然现代主义的印记已经不太明朗,但在作者结构文章的方式中还是能发现现代主义的痕迹。他往往以一种自由的方式结构全文,没有情节的高低起伏和大起大落,而是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在大量的风物人情的描写中自然而然地展开对人物和故事情节的描写,这种抒情性的诗意风格,或多或少都保留了一些现代主义的影子。
到了20世纪90年代,汪曾祺进一步强调写文章要回到现实主义。写作时要将民族传统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不仅要用温情的目光看待人世,也要有对生活痛苦的思索。
汪曾祺的文艺思想是在进步发展的。因此在晚期的作品中,他更加大胆地尝试一些新的题材,对于生活和人性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汪曾祺在大学时阅读过的西方的文学作品,接受过的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到了20世纪90年代,就更为鲜明地凸显出来,印刻在作品之中。[11]
四、小结
温馨平淡的生活不是永恒的,现实中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遗憾。汪老先生的作品,如话家常一般,以单纯质朴的方式向我们诉说生活的美丽,给读者打造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但是现实与小说总会有一定的距离,真正的幽默或许总是以悲凉为底色的。汪曾祺用回忆过滤了生活的苦难,温暖读者的心灵,让读者发出由衷的欢笑。其实,不论是平淡温馨的作品,还是面对死亡与离别、直抒人性的作品,都是他自己在某一阶段对生活的真实体悟和感想,这些风格不一的作品融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汪曾祺。
注释:
①汪曾祺:《鲍团长》,《小说家》1993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摩罗.悲剧意识的压抑与觉醒[J].当代作家评论,1997,(05):3-13.
[2]翟业军.论汪曾祺小说的晚期风格[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08):24-32.
[3]吴丹.和谐遮蔽之下[D].广西民族大学,2013.
[4]郭洪雷.汪曾祺小说“衰年变法”考论[J].文学评论,2013,(06):78-87.
[5]汪曾祺.人生有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12):37.
[6]吳晨.汪曾祺的晚年写作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
2012.
[7]李丹凤.汪曾祺晚期小说研究[D].伊犁师范大学,
2019.
[8]沈佳.“十七年文学”经验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D].华东师范大学,2019.
[9]汪曾祺.复仇[J].文艺复兴,1946,(1).
[10]宋尚诗.极端伦理·性书写·越界——论汪曾祺小说的晚期风格[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03):274-285.
[11]马杰.汪曾祺小说研究综述[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4(01):5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