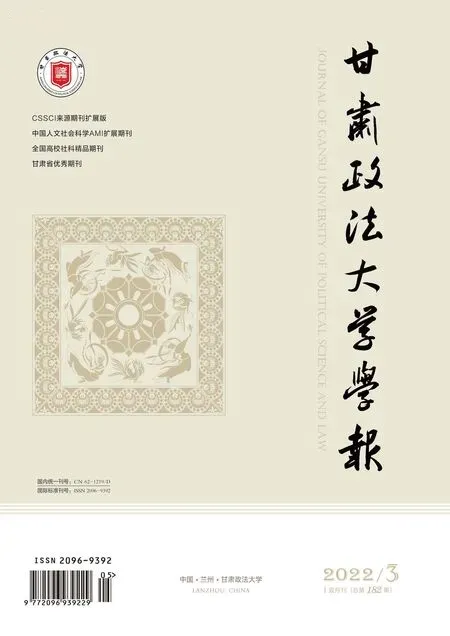股东会决议:内涵界定与理论依托
王湘淳
随着公司成为我国主流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东会决议常见于经济生活。〔1〕为方便表述,本文所称“股东会”包括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以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但因缺乏对“公共”的理解,人们往往将公司视为工具,进而对股东会决议产生了认知偏差。实践中,人们通常将股东会当作分配利益与权力的场所,将股东会决议当作争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经理身份的工具。公司不通知或瑕疵通知原告,即召开股东会罢免其法定代表人等身份是最为常见的决议瑕疵。〔2〕参见蒋胜勇诉天津力美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案,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14)北民初字第770号民事判决书;苏安秀、朱兴培诉徐州意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案,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4)鼓商初字第0302号民事判决书;阿颖诉云南万华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民五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相应地,股东会决议法律制度也难以被准确理解。如在某案件中〔3〕参见杨毅诉青岛厚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青民二商终字第95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认为案涉股东会的决议内容严重侵犯了其股东权益,主张撤销股东会决议。法院在审判时通常也会回应此类诉求。这导致股东权益而非公司权益成了决议撤销诉讼审查的重心。(1)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与无讼案例网中选取了94个包含“股东会决议撤销”或“撤销股东会决议”的案例,其中,34份案例的判决书明确提及股东权益受损,仅有4份判决书明确提及公司权益受损。但依据现行法,决议撤销诉讼的功能是通过维护股东会意思形成的公正性与合法性,进而维持公司组织健全性。(2)参见王湘淳:《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功能重校与规则再造》,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1期。股东权益受损也并非法定的决议效力瑕疵事由。
股东会决议的“熟悉且陌生”也体现在理论层面。主流观点视股东会决议为法律行为,以法律行为说指导股东会决议。(3)涉及具体分类,存在不同观点。第一种,认为决议行为乃是多方法律行为下,与共同行为并列的一项独立的法律行为。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104页;第二种,认为决议行为属于共同行为。共同行为可分为合同行为与合成行为。社团决议属于合成行为,而非合同行为。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页;第三种,决议并非属于现有的法律行为,而是单独的决议行为。参见柯芳枝:《公司法论》,三民书局2002年版,第239页。相对地,一些学者认为法律行为说难以恰当地理解、全面地概括及有效地回应决议,主张股东会决议是公司意思的形成过程,应运用意思形成说指导股东会决议。(4)意思形成说代表观点,参见陈醇:《意思形成与意思表示的区别:决议的独立性初探》,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6期;徐银波:《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李志刚:《公司股东会撤销决议之诉的当事人:规范、法理与实践》,载《法学家》2018年第4期;陈雪萍:《程序正义视阈下公司决议规则优化之路径》,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1期。这一争论的核心是股东会决议是否有别于法律行为,这种区别能否支持股东会决议从法律行为中独立出来。为了能充分地理解股东会决议的性质并选择相应的理论,本文首先描述股东会决议运行的基本样态,还原法律规范背后的股东会决议商业实践的原貌,然后再对此商业实践的法律特征进行分析,希望借此能够减少理论争议,促进研究的深化。
一、股东会决议的法律界定
法律行为说认为,决议行为隶属于法律行为。股东会决议作为决议行为的一种,自然是法律行为。意思形成说认为,股东会决议过程是公司意思的形成过程,决议结果是公司意思的体现。按照意思形成说,意思形成与意思表示是两个不同阶段,法律行为是纯粹的意思表示制度,不适用于意思形成。(5)参见陈醇:《意思形成与意思表示的区别:决议的独立性初探》,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6期。这种争议在相当程度上源于股东会决议存在多种内涵。通过重访股东会决议的商业实践,我们认为股东会决议包含股东投票与决议形成两个基本阶段。
(一)股东会决议的不同内涵
股东会决议主要存在四种内涵:第一,指股东的投票行为。典型表述如股东会决议行为是股东行使社员共益权的方式。第二,指股东会的决策过程,又被称为股东会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38条规定,首次股东会会议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此股东会决议不仅包括股东的表决行为,而且包括议事方式与表决程序在内的会议程序。第三,指从召集到决议的整个会议过程。这种股东会决议在前述股东会会议之外,还包括召集、通知、召开、送达程序。如召集程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股东会决议被通说称为可撤销的股东会决议。召集程序已不能被第二种股东会决议所涵盖。这种意义上的股东会决议是股东会这一公司机构所实施的法律程序。(6)参见廖大颖:《公司法原论》,三民书局2009年版,第179页。第四,指股东会的决议结果,即以股东会形式做出的公司决定,通常以决议文件为载体。如《公司法》第22条所称的决议内容,是在结果意义上使用股东会决议的概念。四者间关系为:股东投票包含于第二种股东会决议当中,第二种股东会决议是第三种股东会决议的核心阶段,第四种是前三种股东会决议的结果。
(二)股东会决议的商业实践
股东会决议在商业实践中呈现这样一种运行样态:董事会形成需要股东会进行审议的议案后,股东会的召集人向各股东发送包含议案在内的会议通知。股东收到通知后,依据通知的时间与地点参加会议,就特定的议案进行议论,并投票表决。公司对股东投票结果进行统计。股东投的“赞成票”达到法/章定多数,议案就转化为肯定性的股东会决议;未达到法/章定多数则形成否定性的股东会决议。决议形成后,股东会主持人通过会议记录、决议文件等记载决议的结果,并将决议文件等送至董事会、公司股东及潜在投资者。
通过对股东会决议商业实践的再现,可知股东会决议至少应包括股东投票与公司决议形成两个不同阶段,股东投票是股东通过投票表达其意思,决议形成是指公司在受领数个股东投票的意思后形成自己意思。股东的投票与公司决议形成的结果是相互独立、相互衔接的意思表示。(7)参见石纪虎:《关于股东大会决议效力的探讨》,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5期。每个股东的投票都是独立的意思表示,公司是其意思表示的受领人。(8)参见叶林:《股东会会议决议形成制度》,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10期。在股东投票阶段,各个股东意思并不会结合。在公司意思形成阶段,股东的意思依据资本多数决的规则相互结合,并转化形成公司的意思。持法律行为说的学者多以股东投票行为为对象来理解决议,如决议是指“数个当事人之间以多数决形式达成合意的法律行为”。(9)王利明:《合同法分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1-432页。其重心在于多个当事人达成合意。达成合意的方式可以是全体一致同意,也可以是多数决。也即,依据法律行为说,公司决议形成并不独立于股东投票。
(三)股东投票与决议形成是股东会决议的基本阶段
股东会决议指股东投票形成肯定性或否定性决议,包括股东投票与公司决议形成两个阶段。这在法律构造上反映为,股东会决议是“多种行为的结合体,既有股东意思和表示,也有公司意思的形成,是个体股东在决议事项上形成的偶然结合”。(10)叶林:《股东会会议决议形成制度》,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10期。
第一,股东投票。股东投票是股东行使投票权,表达其意思,参与并影响决议形成的方式。公司是拟制的法律主体,无法在缺乏股东意思的情形下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形成自身意思。依据法人拟制说,股东投票为股东会决议不可缺少的要件。“在法人内部,法人成员组成了法人(财团法人除外),成员是法人团体性的要素之一,若没有这一要素,拟制的根基都荡然无存”。(11)谢鸿飞:《论民法典法人性质的定位——法律历史社会学与法教义学分析》,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6期。法人实在说认为,法人机关类似自然人的大脑,它为法人形成意思。实在说的要旨在于强调法人与其成员的意思彼此独立,而不是认为成员大会这一法人机关无须成员参与,无须成员投票即可形成法人意思。
第二,决议形成。股东通过投票表达的个体意思只是构成公司意思的要素之一(12)参见许中缘:《论意思表示瑕疵的共同法律行为——以社团决议撤销为研究视角》,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6期;周淳:《组织法视阈中的公司决议及其法律适用》,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6期。,无法自动形成公司意思。股东意思在转换为公司意思以前,并不产生决议的法律效果。股东投票后,还需决议形成阶段才可形成公司意思。因决议存在这种特性,各国对股东会决议的规制,也从放弃了以合意为基础的私法自治原则,转而明确规定决议的形成要件。“只要发生了法律规范假定部分中要求的事实要件,客观发生即直接转化为当事人间的特定法律关系”。(13)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资本多数决而非合意成为了股东会决议主要的形成方式。持法律行为说的学者,也不否认在股东意思表示之外存在独立的形成要件。(14)参见谢鸿飞:《论民法典法人性质的定位——法律历史社会学与法教义学分析》,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6期;王雷:《论民法中的决议行为:从农民集体决议、业主管理规约到公司决议》,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可以说,学界对此已经凝聚了相当程度的共识。
二、股东投票形成决议的理论争议
(一)法律行为说可适用于股东投票
意思表示,是指“表意人向他人发出的表示,表意人据此向他人表明,根据其意思,某项特定的法律后果(或一系列法律后果)应该发生并产生效力。”(15)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50-451页。股东投票是股东针对议案,以格式化的形式做出的单个意思表示,此意思表示针对公司,而非其他股东。(16)参见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67页。相对于其他意思表示,股东投票这种意思表示存在两点特殊性:内容受限,只能针对议案;格式化,只能在同意、反对和弃权三种格式化的意思表示中择一选取。
股东投票是股东的意思表示,但是否属于法律行为存有争议。因为股东投票与决议效力并无必然关联,也并不必然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因为“仅凭个别股东之意思表示,根本无法形成会议决议,个体股东的独立‘意思表示’,并不当然产生通过或否决议案的效果”。(17)叶林:《股东会会议决议形成制度》,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10期。若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必然导致民事权利义务的设立、变更或终止,则股东投票不是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33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根据人大法工委的官方释义,“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是意欲达到一定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18)李适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14页。,并不要求必须达到一定法律效果。以此为标准,股东的投票行为属于法律行为。这种判断标准也与法律行为的传统理论相契合。(19)梅迪库斯认为法律行为旨在引起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这种效果之所以得以产生,皆因行为人希冀其发生。法律行为的本质在于引起法律效果之意思的实现。参见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拉伦茨则认为,法律行为是一项行为,或若干项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为,其中至少有一项行为是旨在引起某种特定的法律后果的意思表示或意思实现。参见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31页。法律行为根据意思表示或参与法律行为的主体之数量分为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与多方法律行为。股东投票只需要一项意思表示就可以成立,到达公司时即生效。公司只是股东意思表示的受领人,负有受领股东投票的义务,但无同意或者拒绝的权利。因此股东投票属于单方法律行为。(20)梅迪库斯认为,单方法律行为是指只需要一项意思表示可成立的法律行为。参见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页;拉伦茨认为,单方法律行为是指原则上由一个人即可单独有效地(即能够发生法律效果)从事的行为。参见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32页。必须强调的是,股东投票生效仅指股东投票这一决议的构成要素已经产生了法律上的效力,而在与其他股东的意思表示结合之前,决议并未生效。
在法律行为说可以解释股东投票行为时,对股东投票适用法律行为说,不仅是尊重既有理论的体现,而且避免了不必要的争议与困扰。故而,就股东投票而言,除非出现明显不合理或不正当的结论,否则应采用法律行为说。必须指出,股东投票行为属于法律行为并不代表其可以径直适用意思表示瑕疵的相关规范。(21)参见陈彦晶:《重大误解规则商事适用的限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意思表示瑕疵与行为效力的关联是价值判断的结果。法律行为的规范是以合同为原型而抽象出的产物,其所体现的价值判断结论主要也针对合同。但股东会决议是存在并不对立的多方主体的组织契约(22)参见伊夫·居荣:《法国商法》第1卷,罗结珍、赵海峰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股东会决议的利益结构与合同并不相同。
(二)法律行为说难以适用于决议形成
就决议形成阶段而言,股东会决议相较于合同等法律行为,其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采用资本多数决规则。资本多数决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多数决与资本决,两者给法律行为说造成了挑战。
1.多数决造成的挑战
“意志与法律效果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质,构成了法律行为概念的根本特征”。(23)朱庆育:《法律行为概念疏证》,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3期。这种关联性,是贯彻自由价值的关键,也是意思自治的精髓。但股东会决议采用多数决之决议规则,这导致决议中任意主体的意志与最后的法律效果并无必然联系。且未有观点倡导决议应当建立这种联系。多数决导致的意思他治现象给强调意思自治的法律行为造成了挑战。法律行为说可以诠释意思自治的正当性,但难以回答为何意思他治也具有正当性。
为了回应上述挑战,持法律行为说的学者尝试引入社会契约理论。(24)参见王雷:《论民法中的决议行为:从农民集体决议、业主管理规约到公司决议》,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如卢梭言,“多数决的规则,其本身就是一种约定的确立,并且假定至少是有过一次全体一致的同意。”(25)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页。但概括的一致同意是否能赋予制度充分的正当性?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普通决议的表决权比例可由章程规定。若章程规定允许少数股东同意即可形成普通决议,是否就意味着少数决定具有充分的正当性?若认为多数决定的正当性仅源于一致同意,多数决相对于少数决,为何更具有正当性?即便是社会契约,其正当性也不仅仅来源于初始的一致同意(26)社会契约论不过是一种虚构的事物,并不包含真实的意思表示。参见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页。事实上,由于高昂的交易成本存在,社会契约不可能达成。公权力源于私人权力而非是平等的契约,国家公权力无非是最为强大的一种公权力。参见桑本谦:《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山东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页。,而且在于任何时刻都可重新签订,但这并不适用于公司。
同意能够赋予多数决议正当性,此结论存在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同意是主体在充分知情的情形下做出的。如合同通常是由平等主体自由协商、谈判所订立的。但在公司这种长期的、高度不完备的契约中,股东受限于信息成本与有限理性,难以充分知情。随着公司公共性的增加,同意与知情间鸿沟会变得愈加巨大。(27)参见张维迎:《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若将主体加入公司的行为视为达成契约,类推适用合同法,其仅具有形式正义而不具有实质正义。即便将股东加入公司的行为隐喻成与公司达成契约(28)参见蒋大兴:《论公司治理的公共性——从私人契约向公共干预的进化》,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6期。这里所说的契约,既非单纯的协议(Agreement),亦非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承诺(Legally Enforceable Promise),而是指称互惠安排(Reciprocal Arrangement)。参见周游:《从被动填空到主动选择:公司法功能的嬗变》,载《法学》2018年第2期。,这种契约也属于关系契约,而非古典契约。(29)参见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3页。关系契约采用整体主义思想(30)参见易军:《个人主义方法论与私法》,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已不能为法律行为说所涵盖。
2.资本决造成的挑战
平等是法律行为说重要的价值取向,此处所称的平等是强式意义上的平等。(31)参见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股东会决议采用资本决,以股份为计量单位,在事实上导致了参与决策主体的不平等,不符合强式意义上的平等。
资本决体现的平等是客体(股份)平等而非主体平等,这使得资本多数决的内涵不同于传统民主决策:第一,民主多数决“要求的是可以改变的多数”(32)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下册),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多数派并不是持续、稳定的集合体,而是存在不断集合与解体的过程。资本多数决下,控股股东是持续、稳定的多数派,这提升了多数专制的风险。第二,民主决策强调主体平等,采用一人一票规则。其目的在于让弱者通过人数优势平衡强者的实力优势。早期公司受此影响(33)See David L.Ratner,Government of Business Corporation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Rule of One Share One Vote, 56 Cornell Law Review 1 (1970) ; Grant Hayden and Matthew T. Bodie,Shareholder Democracy and the Curious Turn toward Board Primacy,51 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2071 (2009-2010).,采用一人一票规则。但资本决打破了平衡(34)从历史角度来看,资本决对于一人一票背离,不过是晚近兴盛的现象。See Stephen M. Bainbridge, The Short Life and Resurrection of SEC Rule 19C-4,69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Quarterly 565 (1991).,产生了强者强权、弱者弱权的股东不平等现象。(35)国外学者将经济权力与所有权成正比的资本决称之为“富豪”原则。而在历史上,英国、意大利乃至我国的公司法律都曾尝试过打破这种原则。参见F.卡尔卡诺:《商法史》,贾婉婷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33页;1904年《公司律》第100条;1914年《公司条例》第145条。故而,采用资本决的股东会决议制度并不属于民主决策制度,而是借鉴了民主决策的若干特征。当然,公司决策中的资本多数决与政治决策中的多数决存在不同的正当性基础与逻辑脉络,资本多数决与人数多数决的差异并不能够成为否定资本多数决的理由。但政治理论对于多数决的观察与思考确有启发意义,如广受诟病的“资本多数决的异化”现象,其根源正是在于资本多数决非民主决策。
综上,股东会决议至少包括股东投票与公司决议形成两个阶段,法律行为说仅能适用于股东投票阶段。法律行为采用一致同意规则,因而即便在客观现实中存在个体意思表示与共同体意思形成两个阶段,从法律上来说意思形成阶段也无独立的必要,更无须理论学说单独回应。
(三)意思形成说对资本多数决的回应
1.法人独立责任是资本多数决的前提
伊斯特布鲁克教授曾指出,如果说有限责任是公司法最为显著的特征,那么在彰显公司法的特征方面,投票机制无疑稳居第二。(36)See Frank H. Easterbrook and Daniel R. Fischer, Limited Liability and the Corporation,52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89 (1985).资本多数决这第二显著的特征又以有限责任为前提。
组织法规则可分为资产规则与治理规则,前者为后者奠定了经济基础,并塑造了后者的具体形态。(37)参见李清池:《商事组织的法律构造——经济功能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有限责任属于资产规则,一股一票规则(资本决规则)属于治理规则中的股东表决权配置规则。有限责任为一股一票奠定了经济基础。股东有限责任规则意味着股东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其拥有的股份(责任份额)进行投票,这意味着“股东大会上投票最终是一种经济利益的表达”(38)斯蒂芬·波特姆利:《公司宪治论——重新审视公司治理》,李建伟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40页。,实现了身份到财产的转变。股份取代个人成为投票的计量单位。正因如此,在股份公司中拥有多个股份的股东可以就不同的股份分别行使表决权,就同一事项同时投出“赞成”与“反对”票。与之相对,采用补充连带责任规则的合伙企业则应采用一人一票规则。
有限责任也是资本决转化成资本多数决、多数决定取代一致同意的重要原因。(39)参见王湘淳:《股权对外转让限制规则:阐释与再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之研究》,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一方面,出资者对企业债务承担不同的责任,是不同类型的所有者保护规则(owner shielding)(40)See Henry Hansmann, Reinier Kraakman and R. Squire, Law and the Rise of the Firm,119 Harvard Law Review 1335 (2006).,对于所有者资产提供不同程度的保护。公司采用有限责任这种强式所有者保护规则,意味着公司决策对于股东的影响限于其出资额,降低了股东参与公司决策的动力。也即,有限责任破坏了股东一票否决(一人一票)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有限责任规则下,公司以自身资产作为决策的责任财产。因此,决策规则设计应当考虑公司的利益。而“公司股东人数众多,如果将个体股东的独立意思表示以合意方式转换为公司意思,容易导致公司决策的久议不决,影响公司决策和运行效率。”(41)叶林:《股东会会议决议形成制度》,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10期。并且,采用一致同意的规则意味着赋予所有股东一票否决权,让少数股东成为事实上的决策者。这不利于多数股东股权利益的实现,而且可能激励股东运用机会主义行为损害公司。
“股东有限责任与公司独立责任在语言表达上有别,但性质基本相当”,是公司与股东的法律地位相互独立在责任领域发展出来的两个相关范畴。(42)参见叶林:《公司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公司人格的独立(责任的独立)决定了其意思形成应当采用资本多数决规则。这也初步诠释了资本多数决的正当性,回应了对资本多数决正当性的质疑。
2.资本多数决以效率为价值目标
学界对于多数决规则体现了效率价值并无争议。持法律行为说的学者也认为,“决议行为中人数众多,取得所有人的一致同意往往很困难,决议成本过高,因此,决议行为往往采取多数决的合意方式。”(43)王利明:《合同法分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5页。同样,资本决规则也体现了效率价值。法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对于采用有限责任规则的公司,表决权与剩余索取权、收益权相匹配是最有效率的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故而,若以效率为价值目标,股东的表决权应以股份为计量单位。
公司是市场的替代物,交易成本低于市场是公司存在的根本原因。资本多数决相对于一人一票、一致同意等具有效率优势,以资本多数决取代一人一票、一致同意等规则可以降低集体决策成本,是一种帕累托改进。(44)See Douglas C. Ashton,Revisiting Dual-Class Stock,68 St. John's Law Review 683 (1994).这说明了股东会采用资本多数决的合理性。(45)根据Hayden 教授的研究,在政治领域采用一人一权的投票规则符合经济理性。See Grant M.Hayden,The False Promise of One Person, One Vote,102 Michigan Law Review 213 (2003).若将效率视为是一种价值取向,则资本多数决还具有正当性。资本多数决规则有助于高效地形成公司意思,其虽然限制了个体的自由,但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46)根据汉斯曼教授被广为接受的企业所有权理论。低决策成本低代理成本的组织是竞争力最强的组织。若不能将两种成本都控制在低水平,那么应当采用低决策成本高代理成本的组织形式,而高决策成本低代理成本的组织在竞争上处于劣势。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下迫使公司以效率为导向。See Henry Hansmann, 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53-149.,与整体主义的意思形成说相契合。多数决与资本决被统一于效率这一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下,共同解决一个问题,即如何将股东意思高效地转化成公司意思,进而降低决策成本。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不惜在此过程中偏离自由的价值取向,对个体的意思自治进行限制。采用资本多数决规则的股东会决议制度,并不具有契约主义正义观下充分的正当性。相反,其不过是高效且公正地形成公司意思这一目的下的最不坏的方式。资本多数决具有正当性是经比较而得出的产物,而不是先验的结论。对于股东会决议而言,资本多数决规则相较于其他规则更具有正当性。
3.通过民主程序提升多数决的正当性
法律行为说强调决议的正当性源于主体的意思自治。但如前所述,股东会决议包括股东投票与公司决议形成两个阶段,股东投票对股东具有约束力,其正当性确实源于股东的意思自治。但决议形成采用资本多数决,其正当性并不仅仅源于股东初始的同意。正如学者指出,“当把公司自治等同于单纯的多数统治时,股东的一部分就会变成非股东。只有多数控制受到受少数股东基本权利的限制,股东才总是包括全体股东。”(47)蔡立东:《公司治理中的“多数派暴政”问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5期。因此,需要在资本多数决外,强调股东的充分参与、自由表达、磋商争论,并通过民主的决策程序对此加以保障。由此,少数股东得以被尊重,多数股东得以被制约,从而将多数决定转化为民主的决定,提升股东多数决的正当性。
民主决策能够提升多数决定的正当性,这在公法学、法理学乃至政治学等领域已经得到充分论证,限于篇幅,笔者不再详细展开。值得指出的是,民主是股东会会议程序及程序规则的外在价值。民主价值的实现,有赖于程序规则为各项程序性股东权利的行使提供保护与便利。哈贝马斯论述民主程序时曾指出,“只要在程序上能保障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平等参与,且他们有平等机会互相影响,在结果上也为所有参与者创造了平等机会,那么所达成的协议就可以被视为是公平的。”(48)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这在股东会决议场合依然成立。股东会程序规则平等保障每个股东的知情权、参与权、发言权与表决权,从而让多数决成为民主的决定,具有约束力。换言之,“只有在可以进行实质性质疑答辩及讨论等合法议事运营程序下所产生的多数决结果,才具有作为会议体统一意思的价值。”(49)张凝:《日本股东大会制度的立法、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页。彰显民主价值的会议程序能够缓解资本多数决的弊病,平衡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的利益,为股东会决议提供正当性。
三、股东会决议程序规则的理论依据
股东会决议包含股东投票与决议形成两个阶段,是一个动态过程,而此过程主要通过程序规则进行规范。相较于私法领域内的其他决议,股东会决议的程序更为全面与细致,程序规则的重要性尤其突出,股东会决议的理论应对此有所回应。
(一)股东会决议的程式特征
程式(formalities)是公司的重要特征(50)参见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页;朱锦清:《公司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2页。,包括组织形式与交易手续两个方面。股东会决议程序是公司程式的组成部分,也是程式在股东会场合的体现。股东会程序的典型代表是股东会会议程序,股东会通过会议做出决议需经过明确议题、会议召集与通知、会议召开与出席、意见表态与协商、进行表决到作出决议及对记录签名确认之流程(51)参见周游:《公司法语境下决议与协议之界分》,载《政法论坛》2019年第5期。,此流程对应的程序即为会议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召集程序、议事程序、表决程序等。
召集程序为股东会决议的起点,是指“为召开会议所为之必要程序”,始于董事会作出召开股东会的决定,终于主持人宣布股东会会议开始。召集包括召集决议的作出和发出召集通知两个阶段。董事会是股东会会议的法定召集主体,唯有在董事会不能履行或不履行召集职责时,监事会、适格股东始得召集。决议违反这一规定属于决议存在召集程序瑕疵,这导致决议可被撤销。(52)参见黄光烈、吴述政诉牡丹江天利食品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牡商终字第64号民事判决书。就通知程序而言,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应当于会议召开前的规定时间内发出,通知内容包括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和议题。《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得超出通知事项,但对于通知主体、通知内容、通知对象等并未作出细致规定,这导致实践中通知程序流于形式。(53)参见夏孟依诉江苏名豪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2013)泗商初字第0370号民事判决书。笔者认为,通知对象应为全体股东,这有利于保障股东知情权,提升股东参会的意愿与质量。Quorum规则(54)即为使会议能有决定权的(最低)参会人数或表决权数。参见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7页。规定了股东会的最低出席人数(投票权数),可防止通知流于形式。
议事程序和表决程序是会议程序的主要内容,也是公司意思形成的关键环节。议事程序围绕“议”,涉及议事的主体、方式、内容、主持人;发言的方式、顺序、时长等内容,现行法规定得较为粗疏,难以回应实践需求。如现行法对发言的范围和主持人的权利、责任并未做明确规定。实践中经常就“无表决权的股东能否在会议上发言”产生争议。如果仅注重股东投票,限制不具有投票表决权的主体发言似乎是理想选择,但这一观点忽视了意思互动的可能性。“根据到场集会原则,这在理论上始终是可能的,即该股东有可能通过其理由陈述而促使其他股东作不同的表决。”(55)格茨·怀克、克里斯蒂娜·温德比西勒:《德国公司法》,殷盛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54页。实践中股东通过发言,改变其他股东投票倾向的案例并不鲜见。就表决程序而言,除决议的投票比例外,需要强调的是累积投票规则,该规则可以应对多数专政,保障少数股东权益。《公司法》第105条确认了公司有权实行累积投票制。根据戈登教授的考察,这受到了政治理论的影响。(56)See Jeffrey N. Gordon,Institutions As Relational Investors: A New Look at Cumulative Voting,94 Columbia Law Review 124 (1994).利益冲突股东的回避程序是另一项重要但充满争议的程序。对其讨论体现了股东会程序及其规则受公法、政治理念影响,但与公法、政治规则相异的特点。(57)参见张穹:《新公司法修订研究报告》(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106、147、210页。
此外,实践当中一些问题需要更为细致的程序规则予以回应。如《公司法》第102条规定,股东会不得对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此处事项是指议题还是指议案?(58)议题是指作为大会目的之事项,而议案是指某个议题的具体内容。如提议解任董事为议题提案,而提议解任董事甲为议案提案。参见近藤光男:《最新日本公司法》,梁爽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页。为保障股东的知情权,议题提案必须在通知中载明,而议案提案则可以通过临时动议的方式当场提出。又如股东会的地点、与会股东的座次可否任意设置?可否分成不同的房间开会?英国等国家的成文法或判例对这些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相较而言,我国《公司法》对此仍是空白。虽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规范性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空白,但如标题所示,其规范对象限于上市公司。然而,这些规定所针对的问题也存在于非上市公司中。
会议程序不仅独立于股东的意思而存在,而且自有其内在逻辑与理论需求。股东会会议各个环节的程序都与公司的意思形成息息相关,任一程序的调整都属于公司意思形成的变动。如开会的方式看起来不会影响股东的意思表示,但有可能影响决议结果。当然,程序的这种影响多是不确定的,难以从决议的最终结果反推。(59)参见周淳:《组织法视阈中的公司决议及其法律适用》,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6期。在具体案件中,也难以运用逻辑推演的方式,作出“如果某一程序得到了遵守,决议结果会如何改变”的判断。但不确定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更不构成被忽视的理由。
(二)程序是意思形成说的重要内容
股东会决议场合,程序的重要性首先体现于缺失程序则无法形成公司意思。公司意思是股东意思互动的产物,而程序使互动过程规范化,是公司意思得以形成的关键。公司实质上是一种促进合作的想象。(60)参见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3页。想象是否被采用,不在于观察者是否有足够的想象力,而在于观察者是否信赖这种想象。程序要求个体以特定时间、地点、步骤、次序与方式行为。一方面,这有助于在客观现实中区分公司的意思形成过程与一般的个体互动过程,进而区分公司行为与个体行为、公司责任与个体责任;另一方面,程序通过仪式化的方式,强化个体对意思形成这一想象过程的信赖,从而在现实与想象两个层面构建起公司意思。股东会决议对于程序极为重视,这也是各国法律普遍对未遵循适当程序的决议之效力进行否定性评价的原因。持意思形成说的学者认为,决议以正当程序为原则。意思形成说着力于对个体意思互动形成团体意思的过程进行研究,对于过程进行规范的程序是意思形成说的重要研究内容。(61)参见陈醇:《意思形成与意思表示的区别:决议的独立性初探》,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6期。该理论认为,团体意思是个体意思互动的产物,程序是行为的调节剂与稳定剂,可以规范行为,防止行为恣意。程序规范互动过程,是团体意思得以形成的关键。正当程序使得股东会决议制度在追求效率价值的同时可兼顾自由价值,这让股东会决议比其他决议制度更具正当性。
必须指出,如前文所述,股东会程序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公法、政治观念的影响,许多规则或借鉴或直接来源于公法、政治领域。一些在传统私法中不成问题的事项在股东会决议中也需要被认真对待,而这不过是公司运作模式源于政治组织(62)See Franklin A. Gevurtz,The European Origins and the Spread of the Corporate Board of Directors,33 Stetson Law Review 925 (2004).,且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受到政治理论影响这一命题在股东会决议场合的体现。(63)对于政治理论对公司法的影响,可从下列文献中窥见一斑。See Peter N. Flocos, Toward a Liability Rule Approach to the One Share, One Vote Controversy: An Epitaph for the SEC's Rule 19c-4,138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761 (1990); Stephen Bottomley, From Contractualism to Constitutionalism: A Framework for Corporate Goverance,19 Sydney Law Review 277 (1997); John Pound, The Rise of Political Mode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Control,68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1003 (1993).股东会决议的这种特性对其理论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该理论必须存在接口,可与公法、政治相连接,吸收其理论思想,不仅可回应已有的程序规则,而且存有余量,以回应将来可能出现的“政治性程序规则”与“公法性程序规则”,避免股东会决议理论永远落后于实践;第二,该理论需有效地将其内化,从私法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从而让公私得以协调,避免股东会决议规则公私二分。故而,意思形成理论与公法的关联性非但不是其应当受到批评的理由,反而是其优势所在。
(三)法律行为说无涉程序
若要对公司法上的股东会决议法律问题进行全面的回应,不仅需要研究股东投票行为,而且需要对包含各项会议程序内在的会议制度展开研究,而这是轻意思形成的法律行为说所难以胜任的。
法律行为说重意思表示而轻意思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民法以自然人为规范对象。自然人的意思形成过程是民法没有涉及也不能涉及的领域。正如梅迪库斯所言,“私法主体的动机是一种禁忌”。(64)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自然人的意思形成深藏于脑海中。将意思形成纳入法律的规范范围,会加重相对人、裁判者的负担。从经济的角度进行考虑,规范意思形成成本过高且无必要,而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对人的尊重。意思形成难言合法或者非法,对其进行评价是道德而非法律的任务。民法未将意思形成纳入规范范围,正是为自然人提供了一个由其自身独立支配的空间,在此空间内人享有意志的自由。公司是组织体,其意思形成事实上是数个个体在特定条件下交往、互动的过程。多个意思表示互动的效力问题,自然可以适用法律行为说。但遗憾的是,个体主义的法律行为说轻过程研究,并没有足够重视意思互动,未对意思表示的互动过程进行系统性的回应。
法律行为并非不涉及程序,要约与承诺的过程是一种较为简单的程序。一方面,意思自治已经给予主体充分的保护,无须通过程序进行保护;另一方面,程序要求以特定的时间、地点、方式、步骤与次序进行行为,本质上是对行为的规范化、类型化与标准化,反对行为恣意与随性,是对主体意思自治、行为自由的限制。因此,法律行为说并无孕育程序理论的空间。在法律行为说的视角下,法律规范被分成意思自治规范与对意思自治进行限制的规范。程序规则属于对自治进行限制的规范。德国私法学者认为,程序与自由存在冲突,过多的程序会限制人们的自由,故有学者感慨,“德国人在创造法律行为概念的同时,就决定了程序在私法之中被忽视的命运。”(65)陈醇:《私法:程序与权利并重》,载《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第11期。
综上,股东会的会议过程,在实然上存在复杂的程序及程序规则,在应然上应视为公司意思的形成过程。中国传统商文化注重洽谈、协商,讲究和睦,中国商人无论是对外谈判还是对内合作,皆不重视正式的程序。选择不重视程序的理论,可能会加剧这一状况;选择重视程序的意思形成理论,在其指导下完善股东会决议程序规则,有助于抑制不规范经营的现象。(66)参见成亮辉:《论股东大会决议之瑕疵》,载《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5期。
余论:需要何种股东会决议理论
法律行为说偏重于个体视角,更加注重个人权利。法律行为说在探讨股东会决议时聚焦于股东的投票行为。此视角下,股东会决议的程序规则是“程序化的私权行动规则”。(67)吴飞飞:《论中国民法典的公共精神向度究》,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4期。意思形成说从整体视角分析股东会决议。此视角下,股东会决议程序是公司程式特征在股东会场合的体现。程式有助于维持公司独立人格,保障公司意思独立于股东意思。(68)参见王湘淳:《论公司意思独立的程序之维》,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4期。股东通过投票表达的个体意思需要经过程序的转化才可成为公司意思。
意思形成说与法律行为说是不同研究视角的产物,这也意味着两者并非截然对立——基于同一研究视角下的不同分类才是此种关系,如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因此,股东会决议的理论学说并不存在对错之分,只有优劣之别。当学界在讨论股东会决议是意思形成还是法律行为时,是在为股东会决议“定性”,也是在寻求一套妥当安放、解决股东会决议法律问题的理论框架。因此消除争议并无可能,但至少可以尝试分析何种理论更为适宜。对于这一实用性的目标,本文也以实用性的标准进行评判:何种理论对股东会决议的商业实践更具有解释力,何种理论便是应当采用的理论。因为法学理论与法律规范必须重视其所要调整的事实和生活领域内的效力关系,而不是改变它们。(69)参见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77页。
股东会决议包含股东投票阶段与公司决议形成阶段。对于前者,采用法律行为说并无太大问题,且能减少不必要的接受成本。对于决议形成,法律行为说不能很好地回应资本多数决之决议形成规则。相对地,效率导向的意思形成说可以解释资本多数决的合理性,并辅以民主决策强化决议的正当性,而民主的程序有助于民主决策的实现。程序是决议形成的重要构件,股东会决议具有程式特征。法律行为说无涉程序,而决议程序与程序规则是意思形成说的重要内容。股东会决议的法律规则主要是程序规则,程序是决议的成立要件、程序瑕疵是决议的效力瑕疵事由等也表明我国股东会决议法律制度在总体上已经以意思形成说为依托,尽管立法者未必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70)参见王湘淳:《股东会决议效力规范:诠释与完善》,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5页。未来对股东会决议法律规则的立法完善应尊重现有的法律规范,以意思形成说为理论依据,如依据意思形成的瑕疵程度不同来区分股东会决议效力(71)详细论述参见王湘淳:《股东会决议效力规范:诠释与完善》,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5页。、完善股东会议事程序规则(72)详细论述参见陈雪萍:《程序正义视阈下公司决议规则优化之路径》,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1期。、强化股东会决议效力诉讼的客观诉讼属性。(73)详细论述参见李志刚:《公司股东会撤销决议之诉的当事人:规范、法理与实践》,载《法学家》2018年第4期。如此,可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更好地产生体系效应,形成制度张力。正如学者指出,“对决议行为性质的界定,非无谓争辩,而是旨在指导制度建构。”(74)徐银波:《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意思形成说不仅提出了建构的具体建议,而且也初步论证了这种建议的合理性。事实上,赞同意思形成说的学者对于股东会决议的完善建议大抵上也契合此种体系脉络(75)参见李志刚:《公司股东会撤销决议之诉的当事人:规范、法理与实践》,载《法学家》2018年第4期;陈雪萍:《程序正义视阈下公司决议规则优化之路径》,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1期;王湘淳:《股东会决议效力规范:诠释与完善》,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5页。,足见该学说的实践面向。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意思形成说不过是公司视角的研究范式在决议领域内的体现,可以与企业主体理论、公司实体理论等其他公司视角下的理论相衔接,形成体系效应。“公司法现代化改革的实践情况来看,‘体系化’思维的缺乏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多数情形下,理论界和实务界多专注于公司法具体规则的‘堵漏洞、补窟窿、打补丁’,对于公司法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和体系性不足却缺乏足够的重视。”(76)夏小雄:《公司法现代化:制度改革、体系再造与精神重塑》,载《北方法学》2019年第4期。因此,意思形成说下的股东会决议的诠释与完善,不过是公司法理论与规范体系融贯的一次迈步。基于公司视角,对公司法规范进行体系化诠释与完善,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更多的公司法学人为之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