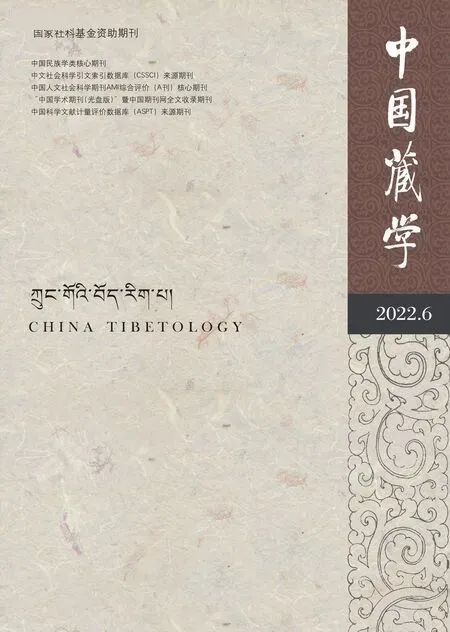炳灵寺第70窟南壁所见番僧身份考
赵 媛
炳灵寺第70窟坐西朝东,窟室进深约3.75米、宽度3.52米、高3.02米,①据笔者实地测量数据。略呈穹隆顶。洞窟主壁绘纵三世佛,南壁绘阿弥陀西方净土经变,北壁为格鲁派师徒三尊与宗喀巴传记壁画,东壁窟门南北两侧分别绘六臂怙主、阎摩法王②此二尊在格鲁派祖庭甘丹寺护法殿中即作为主尊九面四臂十六足大威德金刚的左右胁侍出现。参见普乔·阿旺强巴:《四大寺及上下密院史》(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19页。。窟顶中心为无量寿九尊曼荼罗,外圈环绕十六罗汉,窟室中央位置处存一身明塑十一面八臂观音立像。整窟结构为小型殿堂窟,窟室布局体现以纵三世佛信仰为主题的大乘显宗思想。此窟将宗喀巴作为北壁主尊,与南壁阿弥陀相对,是将宗喀巴视同于弥勒③贺世哲先生详述了唐以后敦煌三世佛造像出现的转变,即随着净土信仰的盛行,由释迦、弥勒与阿弥陀组成的三佛造像急剧增加。炳灵寺第70窟遵从敦煌传统,其西壁主尊为释迦,南壁绘阿弥陀,北壁绘宗喀巴,空间上亦是释迦、阿弥陀与弥勒三佛组合。详见贺世哲:《关于敦煌莫高窟的三世佛与三佛造像》,《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第84—87页。。该窟南壁阿弥陀西方净土经变图下方绘制有弘化寺番僧像,意在宣扬格鲁派宗喀巴大师创宗立派事迹,标榜格鲁派正统传承,兼有希望除障净罪、往生净土的意涵。
一、第70窟南壁番僧身份考
此窟南壁阿弥陀经变东侧最下方位置处,共绘制有三身番僧供养人形象。人物上方墨书其姓名,但因洞窟遭受了较为严重的烟熏变色、片状脱落等壁画病害,加之年久褪色等原因,致使个别字迹缺失或难以辨认。目前能看到的字迹从左至右 (观者视角)依次为:竹巴□□、锁南藏卜、忍巴□节 (图1、线图1),藏文可还原为①竹巴,意为能立,证成;修行,修习佛法等。见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616—617页。□□、②藏卜,常见人名,又作桑波、桑布、藏布。见陈观胜、安才旦主编:《常见藏语人名地名词典 (汉英藏对照)》,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年,第274页。此处“锁南”意为福泽、善报,“藏卜”意为善良、美好。见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第3050、2511页。、③忍巴,常见人名,也作日巴、柔巴。前揭《常见藏语人名地名词典 (汉英藏对照)》,第259页。此处 “忍巴”意为意识、智慧、理智,“□节”即为后文所见 “星吉”“星节”,意为狮子 。见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第2682、2933页。另,以上几处人名翻译原则参考仁增、傅利平、桑杰:《藏语人名汉译规范化研究》,《青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第31—40页。,从名字来看当为番僧无疑。3人中最右侧趺坐者 “忍巴□节”,身形较大,坐在穹帐下,绘头光,左手禅定印,面前摆放案桌,桌上放置烛台等供品。“锁南藏卜”位置稍低,双手合十侍立其后,“竹巴□□”侧立锁南藏卜身后。

图1

线图1
按“锁南藏卜”在《明实录》中共有23条同名记载,考虑到此窟壁画重绘年代当在宗喀巴大师(1357—1419)之后,即15世纪中晚期或16世纪,剔除时间与空间上不甚相干者,还余如下几位:洮州卫喇嘛、西宁卫禅师、河州卫白塔寺喇嘛、弘慈广善国师、灵藏禅师、临洮府番僧、妙胜禅师、岷州卫大崇教寺国师、朝定寺番僧、大慈恩寺国师、弘化寺番僧都纲、静觉寺国师和董卜韩胡进贡番僧等。通过梳理发现,这些“锁南藏卜”可分为两类:一类如西宁卫禅师锁南藏卜、河州卫白塔寺喇嘛锁南藏卜等,均是以个人或寺院名义远道来朝,目的是得到朝廷丰厚赏赐;另一类如弘慈广善国师锁南藏卜、灵藏禅师锁南藏卜等,属入朝纳贡并由朝廷赐给诰命,返回后继续守土一方,代朝廷“抚治番人”。
以上两类禅师或国师的出现年代多集中于明宣德至景泰时期,从属地、身份等信息中尚不能明确看出这些僧人与河州或炳灵寺之间发生联系的动因。相对而言,其中的岷州卫大崇教寺国师“锁南藏卜”的身份与第70窟所见番僧较为接近。《明实录》景泰五年 (1454)三月丙寅条记:“……陕西岷州大崇教寺国师锁南藏卜等各遣人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彩币等物有差。”景泰五年四月甲辰条记:“陕西岷州大崇教寺国师锁南藏卜遣番僧领占班丹……来朝,贡马。赐彩钞锭有差。”景泰七年 (1456)三月甲戌条记:“……陕西岷州卫大崇教寺弘慈广善国师锁南藏卜各遣人来朝,贡马。赐宴及钞、帛 (币)。”①顾祖成、王观容等编:《明实录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7—569页。可见此岷州卫大崇教寺国师锁南藏卜在短短3年间3次遣人入朝,且岷州距炳灵寺所在地河州相去不远,因此不排除此大崇教寺国师即为第70窟锁南藏卜的可能性。但疑点在于,大崇教寺乃大智法王班丹扎释 (1377—?)创建之寺院,②大崇教寺,甘肃岷州称其为“东寺”,今已不存。永乐十六年 (1414)班丹扎释40岁时回到故乡岷州修行,41岁在岷州开山造寺。“及寺将成,太宗文皇帝遣使驰驿,诏至大京,擢僧录司右阐教,及赐国师冠帽、袈裟、钞贯,仍命随驾京师,大兴国寺住坐。”见张润平、罗炤、苏航编著:《西天佛子源流录——文献与初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57页。系萨迦派传承,③见贾维维:《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北京活动及相关史事再考——以 〈西天佛子源流录〉为据》,载沈卫荣主编:《文本中的历史——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591—594页。另见安海燕:《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19年,第25页。而第70窟中北壁满屏绘制巨幅宗喀巴师徒三尊和宗喀巴传记主题壁画,说明重绘该窟的举动很可能是格鲁派弟子所为。
现藏炳灵寺明正德十二年 (1517)重修灵岩寺碑④灵岩寺即炳灵寺。此碑最初由冯国瑞先生 (1901—1963)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后由张思温先生 (1913—1996)将较为全面的录文收于其著作《积石录》,并作了初步考辨。其后的研究成果有吴景山、石劲松:《〈重修古刹灵岩寺碑记〉校读记》,《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3期,第158—170页;曹学文、黄兆宏:《炳灵寺大明碑若干问题研究》,《敦煌研究》2021年第1期,第37—46页;曹学文、黄兆宏:《炳灵寺石窟大明碑注释》,《丝绸之路》2021年第3期,第55—61页。本文涉及碑文内容仅在碑阴人名部分,此部分在众学者录文中均无甚出入。,也透露出一条重要信息。该碑碑文记载了明正德年间炳灵寺的一次重修活动,这是该寺继成化乙酉 (1465)、成化壬辰 (1472)和弘治庚戌(1490)年之后第四次较大规模的修造,其中碑阴所列重修灵岩寺功德主中有都指挥佥事、奉训大夫等地方官员,敕赐宝觉寺、钦差大能仁寺、钦差大护国保安寺、岷州法藏寺、弘化显庆二寺、金刚寺、法藏寺、澄阳庵等多地名寺名僧,⑤曹学文对碑文中提到的9处寺院进行过考证,见前揭曹学文、黄兆宏:《炳灵寺大明碑若干问题研究》。透露出明代中期以降此地崇佛活动日盛的情景。炳灵寺不仅吸引着来自河、洮、岷等地政教人士频繁往来,其影响力甚至远播京畿,可见藏传佛教在以炳灵寺为中心的河西走廊一带的影响力与辐射力,在当时不容小觑。上述碑文功德主名单中所录“弘化、显庆⑥“显庆寺,在河州城中,以其为弘化寺之下院也。”见 [明]龚景瀚编,李本源校:《循化厅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6页。二寺,灌顶大国师锁南藏卜”,基本能确定此“锁南藏卜”的身份,且其直接参与了炳灵寺的重修活动,则此人与第70窟内所见番僧锁南藏卜最有可能是同一人。
弘化、显庆二寺在明嘉靖本《河州志》中有载:“弘化寺,州西北百二十里,正统六年 (1441)奉敕建,规模壮丽、金碧交辉,有僧世袭,佛子常住。地百余顷,官军五十名守之,内有钦赐銮驾”,“显庆寺在州西南,旧系酥油厂,今属弘化寺下院”。⑦[明]吴祯著,马志勇校:《河州志校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另外,碑文中“弘化、显庆二寺灌顶大国师锁南藏卜”之踪迹亦与《明实录》载“弘化寺番僧都纲”条目吻合。《明实录》正德四年 (1509)九月庚子条记:“弘化等寺番僧都纲锁南藏卜等来朝,贡佛像、马、驼等方物。赐彩缎、钞锭有差。”正德十年 (1515)五月己丑条记:“陕西弘化显庆寺灌顶大国师锁南藏卜,以其师星吉藏卜旧赐山场地亩奏乞护敕。礼部驳奏,且请绳以法。特命给之,不为例。”①顾祖成、王观容等编:《明实录藏族史料》,第904、926页。由此可确定碑文中“锁南藏卜”与《明实录》中“锁南藏卜”二者确为一人。
但关于锁南藏卜的身份确认,还有另外一人可为佐证,此人就是壁画中坐在案桌旁的“忍巴□节”。翻找“忍巴”条目,《明实录》正统十三年十二月戊辰条赫然记:“岷州等府卫大崇教等寺番僧公葛坚参、剌麻速南藏卜②壁画中二人名字 “锁南藏卜”即对应 “速南藏卜”,藏文均可还原为。、忍巴星吉等……来朝,贡马及降香、佛像、舍利等物。赐彩币表里、钞锭有差。”③顾祖成、王观容等编:《明实录藏族史料》,第509页。至此,可确认壁画中出现的“锁南藏卜”正是《明实录》中记载的弘化寺番僧,而坐在案桌旁的僧人即为忍巴星吉 (忍巴□节)④忍巴星吉与忍巴星节藏文均可还原为前述。。
综上,我们可大致勾勒出这位弘化寺番僧锁南藏卜的一生:一、他于正统十三年与忍巴星吉首次向朝廷贡物,此时史料称其为番僧;二、于正德四年 (1509)再次向朝廷贡物,此时被称为“番僧都纲”;三、正德十年 (1515)他向朝廷“奏乞护敕”时,史料已呼其为“弘化显庆寺灌顶大国师”,及至正德十二年 (1517)他出现在《重修灵岩寺碑记》中依然沿用此称呼。
另在弘化寺旧址所出的一处残碑⑤该碑现藏于青海民和县转导乡弘化寺遗址。碑文为“□□□□□民诸色人等:□□□□已久,其教以空寂为本,以慈悲为心,化导众生,觉悟迷群。上以阴翊皇度,下以世之崇奉之者,亦岂有远迩之间哉。弘化、显庆二寺,乃至尊大慈法王塔院所在,地连河州、西宁两界,朝廷给□看守□□□□地亩,为香火之需。东至沙子口沟,南至川城,西至黑石山林,北至买的山止。乃拔军余民夫,□□□□□□□□□授妙善广济灌顶大国师,颁降□□,令其在寺提督官寺僧人,领众焚修,毋得怠忽。畀□□□□□□□□人耕占侵用,原拨看守人数与僧□□□照例应给。凡彼处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不许□□□□□□□□□其教者,必罪不宥。钦哉。故谕。”其落款有二则,首则为皇帝颁赐敕谕日期,即嘉靖七年;第二则为弘化显庆二寺事妙善广济灌顶大国师藏卜洛竹勒石日期,即嘉靖叁拾伍年。详见狄呈麟主编,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民和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31页。上,留有“嘉靖柒年拾贰月初四日、大明嘉靖叁拾伍年岁次丙辰柒月□日,钦差掌管弘化显庆二寺事妙善广济灌顶大国师藏卜洛竹建立”的落款,说明嘉靖七年(1528),弘化寺灌顶大国师之职已另易其主,可见锁南藏卜的大致活跃年代为1449—1517年,即15世纪中期至16世纪初。由此推论,炳灵寺第70窟的重绘年代大致也应在此时间范围内。
二、锁南藏卜与大慈法王关系稽考
炳灵寺第70窟所见锁南藏卜的身份既是弘化、显庆寺灌顶大国师,而弘化寺又是大慈法王圆寂后明廷为纪念他而敕建的寺院,因此大慈法王与锁南藏卜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师承关系,值得我们关注。
弘化寺所在地距炳灵寺仅50多公里,两地隔河相望。根据《明实录》记载,正统七年 (1442)八月辛亥敕谕河州、西宁等处官员军民等的诏书中,如是强调了弘化寺的特殊地位:“朕惟佛氏之道以空寂为 (宗),以普度为用,西土之人久事崇信。今以黑城子厂房地⑥黑城子厂房之地即藏文史传中所谓佐莫喀 地方,意为犏牛城,在今青海民和县转导乡红花村。赐大慈法王释迦也失造佛寺,赐名弘化,颁敕护持。本寺田地、山场、园林、财产、孳畜之类,所在官军人等不许侵占骚扰侮慢。若非本寺原有田地、山场等项,亦不许因而侵占扰害。军民敢有不遵命者,必论之以法。”①顾祖成、王观容等编:《明实录藏族史料》,第422页。可见弘化寺周边乃朝廷护敕之大慈法王领地,大慈法王圆寂后,弘化寺及其辖属田园寺产得到明廷的敕谕保护。
另在《重修显庆寺碑记》中载:“明初永乐中,尊崇释典,敕诏乌思藏大慈法王入讲。旋朝时,仍令住持奉命修理,太监侯显董其事,特造金粟迦叶十六像,金篦、上乘经二藏。宣德二年工竣,道场中有甘露隆松,祥光照水之瑞。督工者上其事,因赐名 ‘显庆’焉。”②[清]龚景瀚编,李本源校:《循化厅志》,第217页。可见先有显庆寺,后有弘化寺。显庆寺的创建亦和大慈法王有着密切联系。
前引正德十年五月己丑条载:“陕西③即陕西行都司。洪武七年 (1374),明廷在河州卫设立了西安行都司,次年改为陕西行都司,洪武十二年将治所迁于庄浪卫,洪武二十六年又西迁至甘州 (今甘肃张掖)。可参梁志胜:《洪武二十六年以前的陕西行都司》,《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期,第168页。弘化显庆寺灌顶大国师锁南藏卜,以其师星吉藏卜旧赐山场地亩奏乞护敕。礼部驳奏,且请绳以法。特命给之,不为例。”说的正是锁南藏卜因寺产事宜曾向朝廷“奏乞护敕”,意图让自己从“其师星吉藏卜”处得到的继承合法化,但遭到礼部驳奏,险些获罪,好在皇帝仁慈,“特命给之”,告诫下不为例。这条史料阐明了星吉藏卜与锁南藏卜二者的师徒关系,而星吉藏卜的身份在《循化志:卷四·族寨工屯》中非常明确:“明永乐十二年,差太监侯显诣乌思藏请大慈法王,路由河州,其从张星吉藏卜④陈楠教授考大慈法王第一次入朝时,路经河州,张星吉藏卜作为随从就一直跟随入京。此人出生于河州藏汉杂居地区,因随汉人习俗,也有汉姓,也不排除藏化汉人的可能。释迦也失在内地需要一位藏汉兼通的随从,而张星吉藏卜之徒裔后人也被封国师、禅师,并且住持弘化寺及其属寺显庆寺。见陈楠:《明代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在北京活动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96—97页。跟随入京。正统四年法王圆寂,敕建渗金铜塔,藏其佛骨,七年奉敕河州建寺赐名弘化,随给附近之高山穷谷永作香火之需,该管寺僧五十五名,诵经祝圣。其星吉藏卜之徒裔世给国师、禅师之职,世给山场以中茶马而供僧食。”⑤[清]龚景瀚:《循化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2页。
上述两条史料勾勒出清晰的人物师承关系,即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是张星吉藏卜师,(张)星吉藏卜是锁南藏卜师。很多传记说大慈法王圆寂后,由此森格桑布等人负责把灵骨运回“佐莫喀”,此森格桑布指的就是星吉藏卜。⑥拉巴平措:《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43页。至此,我们可以确认,炳灵寺第70窟南壁中出现的番僧锁南藏卜等人,正是大慈法王的后辈徒人。大慈法王作为宗喀巴大师的亲传弟子,多年服侍宗喀巴大师,并在大师近前听闻格鲁派显密教法,后受宗喀巴大师嘱托,奉召代师前往内地,可谓对汉藏民族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厥功至伟。以宗喀巴大师与大慈法王的师徒关系来看,炳灵寺第70窟北壁绘制巨幅宗喀巴大师生平传记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某种意义上,此举亦透露出功德主想要彰显自身为格鲁派正统传承的强烈意味。
三、由“锁南藏卜”看汉藏文化交融
事实上,以炳灵寺为中心进而辐射整个河西走廊的甘青涉藏地区,是15—16世纪以来沟通中央与西藏,联通汉藏交流的核心区域。谢继胜教授考证了京师大慈法王徒裔——番僧桑迦班丹于明正统己未年 (1439)在甘肃靖远法泉禅寺“始创大佛殿、次葺天王殿”等相关史实,指出这在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展史上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作为非常古老的汉传寺院的景云寺与法泉禅寺由番僧接管,这一事实也说明明代藏传佛教势力向内地的发展。①谢继胜:《宁夏固原须弥山圆光寺及相关番僧考》,《西夏研究》2013年第1期,第85页。另在成书于17世纪中叶,由夏尔·噶丹嘉措(1607—1677)所著的《安多地区佛法传播史略》中,也详细记录了近百年间格鲁派教法向甘青地区传播过程中创建的寺院。②达瓦拉措、拉先加:《〈安多地区佛法传播史略〉译考》,《中国藏学》2017年第4期,第185页。不难想象,从大慈法王进京③大慈法王76岁即宣德四年 (1429)由宣宗皇帝邀请到内地。此行是大慈法王第二次奉旨入京,随同金字使者一道,并在弟子阿木葛和索南西饶的陪同下,途径青海湖、宗喀、西宁、佐莫喀、瓜州、帕巴新股、洮州、岷州、西安、宝山 (河北)、山西、五台山,直至京城。由于这一原因,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大批三宝俱全的佛殿、金殿、大喇嘛仓、禅院等。见拉巴平措:《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第36、112页。时在沿途大力弘传格鲁派,到其后众多甘青地区格鲁派高僧从拉萨学成后,返乡弘法建寺,④如《安多政教史》中记载却吉嘉措 (1571—1636)生于赤嘎地方 (今青海贵德县),14岁时在三世达赖喇嘛座前出家,后前往卫藏甘丹寺求学,34岁返回,47岁时出任塔尔寺法台。见智贡巴·贡去乎丹巴绕布杰:《安多政教史》(藏文),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292页。使得甘青地区的寺院数量和发展规模至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已蔚成大观。⑤明代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创建寺院共计95座,建寺数量超过前两个时期总和的近一倍。从寺院创建的时间上看,洪武、永乐、万历三个时期寺院创建相对集中。若以有确切创建年代的寺院统计,这三个时期共创建寺院28座,占整个明代寺院的近31%。从创建寺院的教派上看,创建的格鲁派寺院数量最多,有46座,占整个明代寺院的44%;宁玛派寺院有33座,觉囊派寺院13座,萨迦派寺院2座,噶举派寺院1座。见李顺庆、卿希泰、吉宏忠、王联章、罗中枢编:《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6年,第161—162页。弘化寺、显庆寺、法泉禅寺及炳灵寺第70窟等一批寺院、石窟遗迹,皆是这一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当地初兴的生动写照。
不仅如此,通过明廷设置的朝贡制度,大量番僧如“锁南藏卜”等以朝贡之名,经由河西走廊络绎往来于藏地与朝廷之间。明廷对前来朝贡者回赐大量财物,优予市贡之利,以经济手段加强了西藏各实力派首领的政治凝聚,也直接促进了藏地寺院的发展。⑥石硕:《明朝西藏政策的内涵与西藏经济的东向性发展》,《西藏研究》1993年第2期,第70—73页。另通过护持颁赐制度以及僧号承袭制度等,使得大量赏赐用以兴建寺院,从而在制度上保障了寺院的利益。⑦胡箫白:《明朝政策与15世纪中期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的传播机制述论》,《中国藏学》2021年第3期,第50—51页。反观上述番僧锁南藏卜,可以说他就是明廷诸多施政策略受益者的一个缩影,他的身份也绝不仅仅是宗教意义上的“灌顶大国师”,更是沟通边疆地区与中央的文化交流使者。
简言之,本文通过梳理《明实录》《重修灵岩寺碑记》等史料中出现的番僧“锁南藏卜”的相关记载,发现炳灵寺第70窟南壁所绘僧人锁南藏卜和忍巴星吉二者与史料记载弘化寺番僧身份吻合,由此明确锁南藏卜的上师为大慈法王进京途中在河州所收弟子张星吉藏卜。继张星吉藏卜后,锁南藏卜成为弘化、显庆二寺灌顶大国师。以大慈法王第二次进京途径甘青各地传法作为契机,格鲁派教法在其后该派诸多弟子的推动下,在甘青地区形成规模拓展态势,炳灵寺第70窟即是在此机缘下由锁南藏卜等人于嘉靖年间重新主持绘制。此窟中所见相关弘化寺番僧,对我们理解明代治藏施政策略、汉藏民族文化交流、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及炳灵寺一带的传播发展等都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