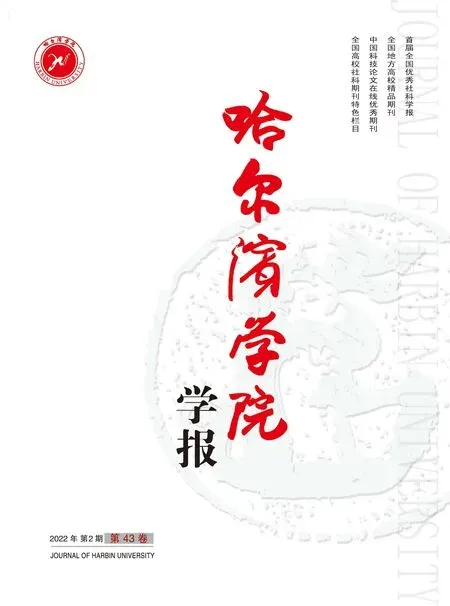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为入罪研究
陈 玲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国民的生命健康依赖于食品安全,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威胁到了国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呼声高涨。为此,我国在立法及司法解释方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做出了调整,相继出台了《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细化了负有监督管理食药安全责任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以及滥用职权行为,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呈现趋严的状况。学界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刑法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存在一些问题,提倡严密食品安全刑事法网,以完善对此类犯罪的治理。[1]在此背景下,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为应否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便具有了较大的理论探讨空间。
一、持有型犯罪行为方式的理论争议
持有是指行为人对特定物品或者财产进行支配、控制的一种状态。持有型犯罪,是以行为人持有特定物品或财产的不法状态为基本构成要素的犯罪。[2]关于持有型犯罪的行为方式,学界主要存在作为说、不作为说与独立行为说等三种理论学说。
作为说认为,持有型犯罪违反了禁止行为人取得特定物品的法律规范,处罚重点在于取得行为,不法状态是先前积极获取行为的自然延续,实质上属于事后不可罚。不作为说则认为,持有型犯罪存在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刑法将持有行为规定为犯罪,表明刑法禁止持有特定物品这种行为的存在。这一规定的隐含内容是当出现持有某种物品的状态时,行为人具有应将该物品上缴司法机关或其他部门结束该状态的法律义务。其违反了抽象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属于不作为。[3]独立行为说认为,持有型犯罪的行为方式,既有先前取得的作为特征,又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支配特定物品状态持续的特征,[4]很难将“持有”这一行为方式完全归属于作为或者不作为,因此被认为是同作为、不作为并列的独立行为方式。
笔者赞成持有属于作为方式,行为人持有特定物品,违反禁止规范属于不应为而为之。非法持有某种特定物品或者财产的状态来源通常来讲有三种:一是更为严重的先前犯罪行为的结果,例如非法持有大量不安全食品往往是生产有毒、有害食品或者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结果状态;二是后续衔接犯罪的过渡状态,例如持有大量不安全食品的后续犯罪行为可能是销售,持有毒品的后续衔接犯罪行为可能是贩卖等;三是可能是其他目的犯罪的预备状态,例如非法持有枪支可能是故意杀人罪的预备。由于行为人的持有行为往往较为隐蔽不易被发现、行为人故意销毁犯罪证据等各种原因,司法机关在抓捕犯罪分子、人赃并获后可能因无法收集到能够证明非法持有状态的来源与去处的足够证据且犯罪分子无法说明其来源,而无法以先前犯罪行为、后续衔接犯罪或者其他目的犯罪对行为人定罪处罚时,可以持有型犯罪定罪处罚。
二、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为的界定
不安全食品是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为的对象,其范围的明确界定是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为入罪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国刑法和食品安全法中均未使用“不安全食品”这一概念。对“不安全食品”做出明确规定的是2007年《食品召回规定》第3条和2015年《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2条,即不安全食品是指有关食品的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以及其他能够被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上述两条规定并未对不安全食品的范围做出具体的划定,因而实践中无法依据此规定确定某种食品是否属于不安全食品。
2015年《食品安全法》第150条规定,安全食品要求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并且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以此条规定的内容为参考反推知,不安全食品应当指的是食品有毒、有害,不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食品。其范围应该包括两种:一种是有毒、有害食品;另一种是虽不属于有毒、有害食品,但不符合应有的营养要求,食用后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食品。第二种不安全食品类型的确定,需要借助食品安全机构的检测和鉴定。
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为,指行为人客观上持有一定量的不安全食品,司法机关无法查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生产、销售或者其他目的,行为人也无法或不愿说明不安全食品的来源与流向的行为。[5]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为是食品安全犯罪的重要环节,贯穿整个食品的链条。对不安全食品的持有可能是生产某种有毒、有害食品前的贮存阶段,也可能是食品生产完成后发往销售点的运输阶段,同样也可以是销售前或者销售中的贮存阶段,这种运输和储存阶段均是对食品的持有行为。食品的持有状态在食品从生产者到销售者再到消费者这一完整的流转过程中是常见、频繁且持续时间较长的。这意味着,相比于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的行为,持有行为更容易被行政执法机关发现并查获。
将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为入罪不能忽略的问题是,如果在我国《刑法》中增设不安全食品的持有型犯罪,该罪名中的不安全食品范围与第143条和144条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两个罪名的犯罪对象之间的关系。从不安全食品、有毒有害食品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这三个概念所涵盖的范围来看,不安全食品和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认定与《食品安全法》衔接,两者的内涵一致。有毒、有害食品也属于不安全食品,因为其规制的范围最小,可视为最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被包含于不安全食品的概念中。在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层出不穷的背景下,有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法网较为疏漏,犯罪对象范围较窄。因此,笔者认为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入罪的对象应当以食品行政法规中的不安全食品范围为参考,以弥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对象较窄的问题,严密刑事法网。
三、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为入罪的必要性
我国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立法趋势表现为法益保护前置化、帮助行为正犯化、重视风险防控、注重保护民生。回顾我国对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从《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量刑方面的修改,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到《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罪的细化等内容可以看出,我国食品安全刑法保护呈现出介入时间提前、规制范围扩大与打击力度趋严等特点。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为入罪具有必要性:
第一,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持有不安全食品的行为是食品行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其通常是生产行为的结果状态、销售行为前或进行中的贮存状态抑或是食品安全犯罪中其他目的犯罪的预备状态。由于多种原因的存在,不安全食品暂时未能进入食品流转环节。不安全食品是有毒、有害食品或者其他能够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的食品。投入市场流通环节,容易危及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在工业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食品行业已经成为科学技术含量高、专业性强、操作精细化、链条化的领域,现代社会的食品通常是工业化大规模、批量化加工制造的。当含有不能食用的化工物质或者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制成的不安全食品经生产者、销售者流转到消费者手中时,通常会导致一定的不良后果,会对广大消费者造成伤害。例如我国曾出现的三聚氰胺事件,在该事件中使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奶而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食用奶粉流入市场,对众多婴幼儿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给无数家庭本来幸福的生活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其种类繁多,既包括不需要精细加工,从农田便直接进入市场的初级农产品,同时也包括了经过细致复杂的工业生产技术加工而成的食品。随着物流网络的大规模铺开,网络销售食品行业不断发展壮大,通过网络渠道销售的食品也日益成为国民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存在。从农产品的种植、养殖、销售到食品的生产、加工、运输、贮存、销售,链条上的每一环节都可能存在不安全因素。犯罪行为人在任一环节施加影响,都容易造成食品安全事件,损害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因此,将作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或者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先行行为或者后继行为的持有行为犯罪化,能更好的维护国家对食品的管理秩序,保护公共安全,严密我国食品安全刑事法网,发挥刑法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防线作用,意义重大。
第二,我国食品安全法网存在疏漏。首先是,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方式范围较窄,其他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相关行为未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例如,与食品生产、销售行为相关的产品进出口、相关记录制度的维持、产品召回以及持有相当量不安全食品等环节,尚未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其次是,根据我国目前《刑法》的规定,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行为方式限于社会危害性较为严重的生产、销售两种方式。而《食品安全法》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规定则覆盖了农产品的种植、养殖、供应等环节和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等一系列从“农田到餐桌”的相关活动。由于二者范围不一致,因而“两高”出台司法解释,针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补正:除食品的生产、销售环节以外,对于其他环节如提供资金、贷款、账号、证明、许可证件,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贮存、保管等行为的依照帮助共犯论处,扩大了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圈,算是对现有规制不完善的一个弥补。再次是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规制的对象与作为其前置行政法的中食品的范围不一致,食品安全法将规制的范围扩展到用于食品生产销售的工具、设备,例如食品添加剂、食品包装所用材料等诸多与食品相关的产品,而刑法中所规定的食品犯罪的行为对象不能囊括上述与食品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品。最后是,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主观罪过限于故意,事实上很多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并不是由于行为人的故意行为所致,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导致食品安全事故,同样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其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所造成的影响不低于故意行为。因此,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增设持有型犯罪,能在有毒、有害食品和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销售流入市场之前截断犯罪,保护法益,防止造成更严重的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的后果。
第三,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刑事政策的要求。现代化不断发展给国民日常生活和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制造了风险。不安全食品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往往不能立即被发现,具有潜伏性和隐蔽性等特征,工业社会的风险性决定了侧重积极预防成为我国食品安全刑事政策的重要体现之一。食品安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行政执法机关查获行为人运输或者储存了一定量不安全食品,当行政执法人员、司法人员能够查明或者行为人能够说明不安全食品的来源与去向时,可以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罪名定罪处罚;但当无法查明或行为人不能(愿)说明不安全食品的来源与流向,且无相关证据能够证明行为人有生产、销售的目的时,在此情况下难以用先前犯罪行为、后续衔接犯罪或者其他目的犯罪对行为人定罪处罚。在此情形下,因为持有型犯罪一般可以从持有的现状推定行为人具有持有的故意,适用持有型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公诉机关的证明责任, 有利于规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将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犯罪化符合严密我国食品安全刑事法网,以及我国食品安全刑事政策保障人民健康、侧重积极预防的要求。
四、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为罪名归属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侵害的是双重客体,哪一个客体是主要客体关系到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犯罪化后在我国刑法分则罪名体系中的归属。
学界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归属存在争议,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将食品安全犯罪归入我国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此观点认为,食品是国民的生活基础,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影响波及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应当将公众的健康与安全作为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客体。而且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罪,有利于实现刑法保护人民利益的目的,并有效规制犯罪。另一种观点主张,将食品安全犯罪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此观点认为刑法分则中的罪名体系放置,既要考虑侵犯的客体,也需要兼顾罪名间的关系以及立法技术问题。现行的立法模式,不仅考虑到了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经济属性,而且也是因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主要规制生产、销售环节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存在相似之处。[6]就此争议,高铭暄教授认为,曾有刑法修拟版本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设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下。现行刑法最终将该罪名归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专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罪的刑法立法价值取向偏重实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也是对广大消费者生命健康权利的保护。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主张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罪增设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罪名体系上归属于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在此仅对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罪的构成要件做出假设,宜参考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销售金额的设置,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构成本罪,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的,属于行政违法行为,由行政机关予以处罚,实现刑行有效衔接。在该罪的法定刑方面,宜设置短期自由刑和罚金。
至于增设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罪后,如何在立法层面上规定该罪的罪状,该罪的立案标准是以货值金额还是以销售金额为标准,该罪的法定刑该如何设置等问题较为复杂,需要结合我国食品安全司法实践、刑法分则罪名体系、国际食品安全犯罪刑罚轻缓化的特征以及其他持有型犯罪的规定进行深入研究。
五、结语
近年来我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呈现趋严的形势,但在司法实践中未取得明显效果,食品安全问题仍有增无减。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为是食品安全犯罪链条中的重要一环,通常衔接先前的生产行为以及后续的销售行为。大量的不安全食品流入市场,容易影响消费者的正常生活和市场经济秩序。我国食品安全犯罪行为方式范围较窄,缺少对持有行为的刑法规制,考虑将其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也是食品安全刑事政策的需要。食品安全问题是食品市场的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企业盲目追逐利益缺乏行业自律和底线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综合造成的。刑法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无法以一己之力解决由行为人逐利、企业管理不足等诸多原因导致的犯罪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监管、食品的生产经营者自律、公众监督等多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刑法最终应回归谦抑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