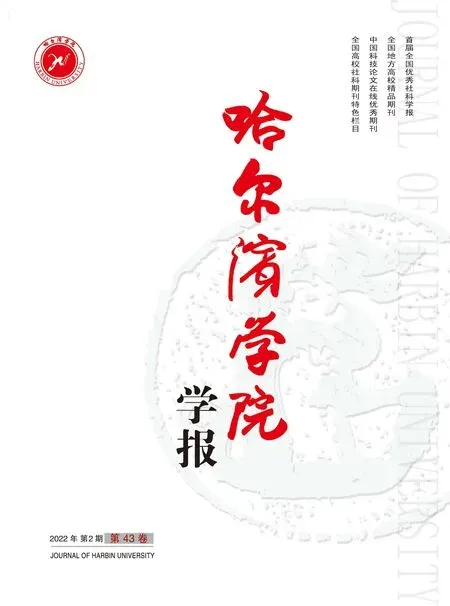平塚雷鸟与“新妇女协会”
宋庆丽,吴 玲
(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平塚雷鸟(1886—1971)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女性解放思想家、女权主义领袖、评论家、作家。1918—1919年,平塚和与谢野晶子围绕母性价值与育儿问题展开著名的“母性保护”之战,在论战中,平塚认同爱伦·凯“母性主义”思想,倡导“母性保护主义”。1920年3月以平塚为核心成立了“新妇女协会”,其杂志为《女性同盟》。本文围绕平塚的“母性保护主义”与“新妇女协会”,梳理、剖析平塚的女性解放思想的变化轨迹。解读平塚在女性解放思想中“母性保护主义”与女性之间的关联,并通过和与谢野晶子的对比,揭示平塚“母性保护主义”的特质。
一、平塚雷鸟及其“母性保护主义”
平塚雷鸟是家中次女,父亲平塚定二郎是政府会计检察院官员,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母亲饭岛光沢出身名门,是当时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中具有“贤妻良母”形象的传统女性。[1](P1-3)平塚受父亲影响,对西洋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有关女性思想解放的观点就是在西方文献和书籍的研究中受到的启发。
1890年日本颁布《教育敕语》与《集会及政社法》、1898年实施《明治民法》、1900年颁布《治安警察法》。1903年4月平塚不顾父亲反对进入日本女子大学,但是一年后,平塚发现学校标榜的新式教育核心依然是“贤妻良母主义”。平塚在家中也愈发排斥父亲的父权地位和自己被支配的角色,认为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从属地位严重阻碍了女性的才能与个性的发展,开始探寻内心世界。后来平塚通过参禅和大量阅读西方哲学书籍,形成了独特的哲学观与自我认识,认为女性应从内部出发探求人生。1907年平塚加入闺秀文学会,在这个面向年轻女子的研究会中认识了森田草坪,并与他在1908年3月21日晚上连夜出走。两人相约到盐原自杀徇死,但最后平塚被母亲带回家,此事件被称为“盐原事件”。[2](P60-65)森田草坪以“殉情自杀”为背景创作了小说《煤烟》。然而,平塚出走前留下的遗书中提到,“盐原事件”不是“殉情”,而是“殉道”,是她对当时社会压迫女性的反抗与挑战。此事件之后,平塚虽然背负“不贞”之女的恶名,但也成为当时“新女性”代表人物,并得到广泛关注,开启了自我觉醒意识,切识体会到封建家族制度与国家体制对女性正当权利的剥夺。后来,在生田长江的建议下,平塚联合当时日本新时代女性,着手创办日本第一个女性团体“青鞜社”,后来创建了女性文学《青鞜》杂志,全部由女性执笔的女性文学杂志《青鞜》,其目的是促使女性发挥各自的天赋。平塚在《青鞜》中表达出对现实中的贤妻良母主义、婚姻制度的质疑以及对法律制度不合理性的控诉,甚至因此遭到政府禁言。为了表示对婚姻制度的不满与对自由恋爱的支持,平塚与奥村博史长期同居并未登记结婚,孩子作为私生子,未随夫姓。1916年2月,由于家庭与社会压力,《青鞜》停刊,《青鞜》尽管存在时间短,却在日本近代女性史中具有自我觉醒的重大意义。新女性们在杂志上宣传西方先进的女性解放思想,批判封建家族制度,抵制旧道德、旧思想,不仅有力推动了女性思想解放运动,也开创了日本近代女性运动的先河。平塚后来倡导的“母性保护主义”是在“青鞜”时期自我觉醒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1913年,平塚翻译瑞典女性解放思想家爱伦·凯的著作《恋爱与结婚》,平塚颇为赞同爱伦·凯所说“女性生活”中心要素是“母亲”的观点。[3](P199)爱伦·凯认为女性最重要的角色是母亲,母亲最值得尊敬,强调将“母性”置于最重要的位置。[4](P128-138)平塚认为通过爱伦·凯使她得到了灵魂的复活,她从关注女性的自我觉醒上升到深入思考女性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相关问题。
平塚在阅读爱伦·凯著作《母性的复兴》后,与爱伦·凯在保护母亲、育儿方面产生共鸣。爱伦·凯主张社会为了下一代,应该对母亲进行保护和关怀,促进社会复兴。1918年,平塚将《母性的复兴》翻译成日文,并公开发行。平塚在经历婚姻、家庭、妊娠、生产等人生阶段后,认识到母性的意义与价值。平塚以爱伦·凯的“母性主义”为核心,呼吁政府在女性妊娠期、养育子女方面实施保护政策,即“母性保护主义”。平塚认为女性生活的幸福与国家的进步发展有重大关系,国家有义务保障女性在分娩、育儿期间的稳定生活。平塚认为母亲是生命的源泉,孩子的质量与国家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所以生育、培养孩子的“母亲”工作,已经不是个人工作,而是社会、国家的工作。由此可见,平塚把母亲的工作提升到关乎社会与国家利益的高度,认为母亲为了培养好孩子而倾注全部身心,代替国家承担了养育孩子的义务,从国家那里得到报酬是理所当然的。平塚希望通过国家权力促成女性团结,继而通过国家干预打破男性自古以来在家庭中经济、权利的垄断,以国家力量推动家庭关系的革命。日本女诗人与谢野晶子对这一观点持反对意见,她认为孩子是私有物,母亲的工作是私人事业,从母性价值角度出发批判平塚“母性保护主义”,认为母性价值是实现自我的关键。
与谢野晶子站在否定立场,责备“母性保护主义”是另类的“奴隶道德”“依赖主义”。她甚至公开呼吁“女子在没有获得经济独立之前,根本就不该结婚生子。”在《妇人公论》三号杂志上,与谢野晶子发表《紫影录》,由此掀起一场“母性保护主义等同于依赖主义”的母性保护论之争。与谢野晶子在文章中以“彻底的经济独立”为中心,认为“母性保护主义”把女性视为弱者,剥夺了女性经济独立的权利,是一种依赖主义。[5]不赞同对于妊娠期女性进行国家援助,认为男女应在物质生活、子女养育方面相互平等,互相援助,女性一旦结婚后经济上依赖男子,等同于残疾人或老人。[6](P22)与谢野晶子的这种观点,实际上与西方正统的女权主义比较接近,但对当时的日本而言,显得过于激进。虽然日本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但日本没有和西方一样的社会基础,日本的工业生产主要是家庭作坊式,女性正式工人占比相较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仍有差距,不存在大量的、正式女工群体。因此,与谢野晶子的观点很难在日本产生共鸣,相比之下,平塚的观点更容易被长期作为男性附庸的日本女性所接受,也更能让人们认识到女性的重要,以及为国家和社会的付出。通过强调性别差异,凸显女性价值,更有利于提升女性的地位以及在绝大多数被“贤妻良母”思想束缚的日本女性中产生共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平塚的观点虽然显得“离经叛道”,但在当时的日本,其更能促使女性的自我认知的觉醒,促进社会对男尊女卑观念的思考。
在1918—1919年的母性保护争论中,平塚认为,为了解决现实困难,亦为人类的将来考虑,国家应该保护母性,而与谢野晶子则主张女性“经济独立”,反对向国家寻求保护。平塚的“母性保护主义”更加注重女性生活与现实,而与谢野晶子的经济独立主张过于理想化,不符合当时日本社会的实际情况。与谢野晶子的主张是女权运动,平塚“母性保护主义”属于女权运动的补充。专门要求劳动权利忘却了母性保护是前者的缺陷,只关注母性保护而不提倡劳动权的后者也容易使女性独立陷入困境。母性保护的争论不仅起到了社会启蒙作用,而且加深了对日本现有家庭制度、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
二、创立“新妇女协会”,开展请愿运动
一战后,资本主义经济走向腾飞,产业构造巨变,日本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崛起,女工人数上涨,但女性劳动者明显受到社会的歧视与不公正待遇。平塚认为这不仅给作为母亲的女性和孩子带来不幸,也会对民族的未来造成损失。为了争取女性劳动者的权益,女性团体相继成立,女性劳工的相关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新闻杂志等对受压迫的女性现状进行公开报道。
1919年春,平塚最先开始尝试创建女性团体的实践。同年夏天,平塚参加名古屋报社和中京妇女会的夏季妇女讲习会演讲并视察爱知县纤维工厂。在名古屋目睹了女工艰苦劳作的平塚发出感叹:“这不是地狱,又是什么呢?”“我惊讶于在工厂的妇女劳动状态和健康状况,同时接触到这些女性,感觉她们的无知、无教育、无自觉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从此,平塚开始关注女性和儿童的劳动问题,开始致力于女性团体运动的实践。提出争取女性参政权、保障女性儿童合法权益、男女机会平等、改善女性劳动条件、组织女性团结起来共建女性同盟、鼓励女性受教育、设立女性劳动教育机构等以改造社会为目的主张。
1919年11月,在第一届关西女性联合会上,平塚发表《希望女性团结》的演讲,呼吁“我们女性应该团结起来集体活动,为了我们女性共同的宏大目标,为了我们的团结与解放,发动社会实践运动”。演讲会上,平塚与同样担任讲师的贺川豊彦、高梨(田中)孝子结识,她们都致力于将欧美社会文化理念引进日本。[7]平塚与两人进行了密切的交流,促使平塚产生了在关西设立“新妇女协会”的想法。[7]以平塚为首的这些新女性们,试图以“母性保护主义”为蓝本,从传统桎梏中逃脱出来。
1900年颁布的《治安警察法案》第五条明确规定:“女子没有加入政治社团的权力。”这从根本上剥夺了女性争取参政权的机会,呼吁修正该法案势在必行。对此,“新妇女协会”制定了以母性保护主义为核心,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治安警察法第五条修正》运动,开始了谋求政治参与权的漫长斗争之路。
1920年3月28日,“新妇女协会”正式成立,理事会成员有平塚雷鸟、市川房枝、奥梅子等人,机关杂志为《女性同盟》。在协会章程中,协会目的包含诸多内容:“为了废除对女性不利的各种法律制度、倡导女子高等教育、小学男女共学、妇女参政权、保护母性等要求,开始实际运动。”另外,第三条第九项还包括“设立事务所、女性共同寄宿所、女性简易食堂、娱乐场所、运动场、图书馆等”妇女会馆,体现出“母性保护主义”的具体要求。1921年,“新妇女协会”起草了修正请愿书,要求女性和男性一样参与政治生活,给予女性政治活动的自由。平塚认为《治安警察法》第五条的所有法文都是不必要的,“新妇女协会”这次提出的请愿,只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停止对女性禁止的要求,“女性必须加入政治结社,参加政治集会并获得自由,为了不久的将来,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并深入研究其方法,积极要求参政权”。[8](P172-187)平塚认为女性参政不是仅能和男性一样参与政治,还包括其他很多权利。
1922年《治安警察法》第五条第二项的修正案顺利通过。原条款内容是“女子及未成年人,不准旁听或议论当下政治形势,也不能作为时政研讨会的发起者”,经过“新妇女协会”的抗议与运动,修正案最终删掉条款中“女子”二字。虽然只是去掉了两个字,但在日本女性史上以及女性争取参政权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使女性参政运动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女性对参与社会政治的热情得以提升。女性参政权的获取冲击了旧家庭伦理体系,为当时封闭在家中的女性争取到了一定的权利,促进了平塚“母性保护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实践与发展。
《花柳病男子结婚限制法》是“新妇女协会”以“母性保护主义”为核心开展的另一项请愿运动。在男权主导的社会秩序中,很多男性性关系比较混乱,容易感染“花柳”病,很多无辜女性在婚后遭到传染,继而影响到儿童的健康成长。平塚等人围绕制定《花柳病男子结婚限制法》,组织了相关请愿运动。平塚认为“花柳”病的蔓延将危害到个人、社会、种族安全,主张《花柳病男子结婚限制法》不仅会保护作为未来母亲的女性,也会保护未来的孩子,谋求国民的实质性改善,是男女共同的义务和使命,是对整个日本民族未来的有力保障。这项请愿也是“新妇女协会”为贯彻“母性保护主义”最为突出的实践诉求。但该提案最终并未获得通过,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正处在男性为主导的家族制度下,法案实施时机尚未成熟,而且对未婚女子进行身体检查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当时社会难以支持提案的开展落实。可见在当时,“母性保护主义”理论尚不成熟,在实践中面临重重阻力。
三、“新妇女协会”的挫折及反思
1921年以后,“新妇女协会”内部矛盾重重,平塚不仅要照顾家庭和孩子,还要忙于工作,此刻的平塚身心疲惫已经无法继续留在协会工作。于是她决定去农村修养,不再参与政治生活。此时,以奥梅子为代表的协会成员对协会最初目的提出质疑,平塚还与市川房枝产生分歧。“新妇女协会”时期的市川认为,理想化的运动是“纸上谈兵”,一般多以“徒劳告终”。[9](P100)她认为社会改革运动就应该承认现在的社会状态,并立足于其上进行运动,表达出了市川对平塚“母性保护主义”的质疑。从此,“新妇女协会”的重心逐渐向市川倾斜,平塚和市川两人开始背道而驰,不久两人都脱离了协会的中枢。此外,伊藤野枝和山川菊容等社会主义新女性也开始批判平塚,这些都对“新妇女协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1922年12月平塚发布公告,宣告“新妇女协会”正式解散。
“青鞜”时代的平塚仅要求自我觉醒,确立自己的内在精神,明显缺少社会实践。“新妇女协会”的实践加深了平塚对女性解放的理解,而“新妇女协会”时期,其女性解放思想在确立自我精神基础上,将“母性保护主义”加以实践与巩固。可见这是她在经历为人妻、为人母之后体验出来的智慧结晶。虽然“新妇女协会”最终解散,但平塚“母性保护主义”在该协会实践活动中得以运用。“新妇女协会”是唯一一个在部分修改法律上成功的团体,也是“二战”前日本唯一一个成功获得女性政治权利的团体。然而,平塚的思想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她过于强调女性的本质等同于母性,夸大母性的绝对奉献精神,把女性的价值局限在了种族的繁衍,从而忽略了女性的个体的差异与自由。她还将母性“国家化”,寻求国家辅助母性的“母性保护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贤妻良母主义”,在明治政权的操纵下很容易成为维持天皇专制政治的工具,被“军国主义”利用,这显然无法实现女性的真正解放。了解平塚“母性保护主义”与“新妇女协会”,对于女性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