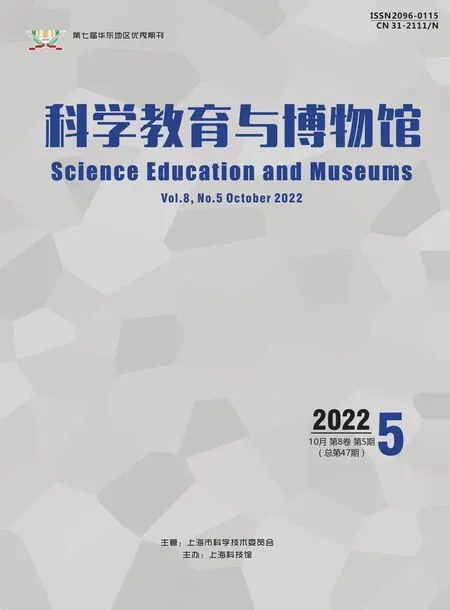怀旧与创新:景箱在自然博物馆展示的实践与反思
——以浙江自然博物院展陈为例
施波文
浙江自然博物院
0 引言
科学技术的进步影响着博物馆各个方面,如收藏、研究、展示、教育、文化等,进而对博物馆实体的形式、性质、关系等产生影响。因为博物馆主要是通过陈列展览向观众进行知识传播和公共教育,所以陈列展览是博物馆传播先进文化、发挥社会教育作用的主要手段,是博物馆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形式[1]。纵观自然博物馆发展历程,其专门的陈列展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多元,受到了社会发展、社会审美、社会教育、信息传播、博物馆与公众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这在博物馆展陈定位、内容表述、视觉呈现、功能实现和评价体系等方面均有所体现。生境景箱作为国内外自然博物馆最为经典的展陈方式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甚至与自然博物馆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本文以浙江自然博物院三次馆建陈列中的生境景箱展示为例,探析传统经典的景箱在新技术辅助下的展示新貌,以及在博物馆公众教育方面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1 Diorama 一词的定义与释义
Diorama 在博物馆语境下的中文译名,有“立体造景”[2]“全景模型”[3]“生态造景”[4]“生境景箱”“景箱”[5]等。英语词典中的解释是“用三维造型表现一个场景的模型,可以是微缩模型,也可以作为大型的博物馆展品”[6]。Diorama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展示方式,在当今博物馆展示中可以经常看到。普遍意义上的博物馆Diorama,是一种将实物和非实物展品置于背景为画面或构筑物的环境中,以展现某个自然或历史场景的三维组合装置。其组合展示特征为“景”与“物”相结合,“物”是主体,“景”是基于科学性和真实性对动物栖息地进行还原,它包含了一定体积的模型搭建而成的前景以及通常是二维绘画的背景,其背景一般巧妙利用透视法和弧形墙面以达到开阔景观的效果,而前景和背景共同组成了主体物存在和活动的场所[7]。有学者研究认为,欧美国家语境下的Diorama,在大陆博物馆学界,被赋予了符合中国博物馆特色的本土化定义,即“情景再现”[8]。如严建强教授观点,“复原”是陈列语言中最关键的概念,“通过对展品的复原性处理,消弭或缩小了展品与观众在时空上的距离,将观众象征性地置于‘现场’,从而理解了展品的意义及其相互间的关系”[9]。为了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张琰对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分析:情景再现实际上是实物展品与绘画、模型、雕塑、多媒体、互动体验设备等各类非实物展品的科学组合,它作为一种重要的展览叙述形式,从陈列语言的角度被提出,涵盖的形式范围更广。Diorama 是实现情景再现效果的其中一类构成元素相对固定、本身具有显著特征的展示装置,是实现情景再现效果的手段之一[10]。英国伦敦大学著名的科学教育专家苏·图尼克利(Sue Dale Tunnicliffe)对Diorama 及其社会教育功能做过专门研究,认为Diorama 既可以是玻璃橱窗形式,也可以是无玻璃阻隔的开放式结构[11]。原上海科技馆副馆长金杏宝博士在《博物馆展览——营造自主学习的开放空间》中,引用了苏·图尼克利的研究,将Diorama 和Panorama 分别译为生境景箱(景箱)和全景箱,认为这种展示方式揭示了特定地域内和生境中的各种生命独特的栖息状态和生存策略,它们与环境之间真实的依存关系,以及动植物区系的变迁[12]。鉴于此,依据Diorama 的特征和功用,顺应大陆博物馆语境下的表述习惯,本文采用了“生境景箱”(或简称“景箱”)为Diorama 的中文译名。
但是,中文译名“景箱”,亦给人们造成一些困惑,常常将其与“情景再现”混为一谈,认为Diorama仅限于三面或四面玻璃橱窗的景观箱,其实玻璃展柜只是Diorama 与博物馆结合的早期形式,随着国内外博物馆的长期实践,Diorama 的规模、设计和形式早已变得复杂多样,没有玻璃阻隔的开放空间同样可以表现Diorama。因此,采用玻璃展柜进行展示并不是判定博物馆Diorama 的唯一标准[13]。
2 生境景箱在自然博物馆发展历程中应运而生
2.1 景箱展示诞生的历史背景
自然博物馆的发展演变,其具有的收藏、展示、研究、教育等功能受到社会思潮、文化变迁与历史因素之深厚影响。16 至17 世纪,自然博物馆最为重视的是其研究功能,博物馆的收藏在当时主要为科学家提供研究物件。17 世纪,随着动物学标本处理技术获得新进展,博物馆开始使用高浓度酒精将标本以液体形式保留,运用火石玻璃便于观众观看液体标本,借助蜂蜡和水银使干制标本能够被展览[14]。到了18 世纪,林奈分类法使自然博物馆展览的内容结构步入类型学(typology)[15]。19 世纪中后期,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创始人阿凯西斯(Louis Agassiz)博士将一些标本搬至另一处楼房进行教学和展示,这种做法将教育和展示空间从原来的收藏空间独立开来[16],是博物馆经历的第一次分化式发展,为博物馆实施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提供了平台。到1851 年,英国伦敦举办万国博览会后,开始融入设计理念,开创了展示的新纪元,博物馆展示自此开始运用更多元的手法[17],包括对于展场的灯光、布置、装饰等,展示也因而变得更为生动、有趣。在19世纪到20 世纪之间,由于受到透视及全景图像的影响,背景画与博物馆中的生境展示密切结合,为呈现物件的脉络与背景提供了更多可能。尤其在19 世纪末,随着动物标本剥制技术的发展,促使动物标本可以在真实或虚拟的“自然”环境里进行展示,自然博物馆逐渐发展出所谓的生境景箱(Diorama)的展示手法。到20 世纪中后期,新博物馆学运动兴起,尽管各国因历史文化背景及综合国力的差异,博物馆建设不尽相同,但是人们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认识日趋丰富,因生境景箱代表了展览与教育的完美融合,逐渐被运用在自然史与民族学展示中,后来历史类展示也常运用此展示手法[18]。
2.2 景箱展示应运而生
早在19 世纪末,以“Diorama”命名的公共博物馆展示形式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在这之前,欧美博物馆中已多次出现了这种展示形式的雏形。博物馆景箱中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类型是“栖息地立体模型”(habitat diorama),最初在欧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崭露头角,它以1:1 的比例在模拟的栖息地环境中展示动物标本[19]。通常,生物组(biological group)、地理组(geographical group)、生境群(habitat group)等,都被看作是“栖息地立体模型”的早期形态。生物组和地理组大多用在欧洲早期博物馆对于物种及自然史的展示当中,生境群则较晚出现,主要在美国博物馆中保留了较为完整的发展脉络[20]。生物组和地理组的共同问题在于对自然环境的诠释很有限,而且缺乏艺术表现力,它们只是将标本和少量的仿真物简单地组合在一起。生境群被认为是栖息地立体模型的前身之一,它被定义为“按实物大小比例组合而成的三维装置,目的是在背景画所描绘的接近实际地理环境的场景中展示标本”[21]。“生境群”一词,由美国鸟类学家弗兰克·查普曼提出,他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展厅展示了北美鸟类及其生存环境。此后,一些较大型的哺乳动物开始被陈列在更为复杂的生态环境中,观众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现在看来,生境群展示手法并不复杂,展出的动物标本形态也比较呆板,呈现的环境也不具有明显的典型性和可识别性,但它改变了标本密集呆立于展柜中的情形。标本不再是一件孤立的认知对象,动物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被直观地展现在观众眼前,没有生命的标本一旦与自然景观摆放在一起,仿佛也焕发出一些生机。19 世纪末,随着动物标本剥制技术的发展,使动物可以在真实或虚拟的“自然”环境里进行展示,以期达到更好的教育意义。同时,受到当时社会盛行的透视及全景图像影响,在20 世纪初,生境群展示中的背景画与博物馆结合起来,自然博物馆逐渐发展出更接近于现今人们理解的博物馆生境景箱。但是,“Diorama”一词具体在何时何地取代生物组、地理群、生境群等词汇,并成为博物馆展示形式的名称,已经难以考证[22]。
历史上,被认为第一个制作生境景箱的人,是沃德自然科学研究所(Ward’s Natural Science Establishment)的卡尔·艾克里(Carl Akeley),他有着“现代标本剥制术之父”美誉[23]。1889 年,他在密尔沃基公共博物馆(Milwaukee Public Museum)制作的反映麝鼠的生活场景,现在依然还在。当时,由科学家、标本剥制师、画家等组成的团队远出实地考察,以求证景箱设计的科学精准。他将麝鼠标本安置在栩栩如生的沼泽栖息地生境中,尽可能地还原其真实生存状态。观众不仅可以看到姿态各异的麝鼠,还能从独特视角看到河流的水下截面,了解麝鼠的栖息状况。该景箱展示不仅展现了物种的外形,还清晰地呈现了麝鼠的生活方式与其环境的关系[24]。1936 年,卡尔·艾克里(Carl Akeley)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精心打造的非洲哺乳动物展厅对外开放,成了博物馆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
这些展示可以称作是现存最早的立体透视生境景箱,包含了主体、前景和背景三大要素,前景和背景共同组成了主体存在和活动的场所。现今,国内外自然博物馆的景箱,已经不再局限于空间狭小的玻璃展柜,其规模、形式和设计变得更为灵活多样,复杂精细,并逐渐被其他类型博物馆所借鉴。
2.3 生境景箱的价值与意义
当今自然博物馆在履行其自然教育使命的内容和方式手段上不断追求创新突破,自然教育的本质内涵渗透进博物馆工作的方方面面。博物馆学研究和自然教育的目标,并不只是了解众多与自然相关的知识,还包括积极的自然情感以及体验探索自然的能力[25]。自然博物馆中的景箱展示,作为发挥博物馆教育潜力的重要工具,它的出现实际上代表了收藏、展示和教育使命的完美结合。
2.3.1 生境景箱是展示物件及物件之间相互关系的最佳方式,阐释了主题的知识性、脉络性和系统性。一方面,在真实的自然环境中,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共同构成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各种典型的生态系统和系统内的物种,有着紧密的依存关系,如生物之间的捕食、竞争、共生与共栖等。单独的标本陈列,无法说明这种自然界相互依存的关系。而通过景箱,可以向观众直观清晰地展示生物群落与地理环境的互动性与适应性;另一方面,景箱既可以诠释物件的生态性,又能说明生物的栖居环境(habitat)特点,让展示的物件呈现出更为完整及脉络性的全貌[26]。自然博物馆中各种规格的生境景箱,使得展示物件的意义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意涵,而是与其他同一陈列展场的物件息息相关,呈现了彼此互相辅助与串联的展示脉络,有助于强化展示的教育目的,观众即使不具备相关背景知识,也可以通过观察来理解展示之内涵。
2.3.2 生境景箱有助于激发观众对话与思考,传递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理念。一方面,自然博物馆生境景箱可以展示各种典型的生态系统,包括珊瑚礁、红树林、针叶林、北美荒漠、稀树草原等,让观众不仅看到地球上生态系统的复杂多样性,也让人们发现不同的生态系统与系统内的物种之间,存在着重要的依存关系,而我们人类本身也是错综复杂的系统组成部分之一。各类主题的生境景箱展示,可以引发公众对自然的依存和责任感,理解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另一方面,优良的博物馆陈列展示,实际上是为观众营造一个自主学习的环境或氛围,观众可以通过多种感官体验来获取可靠的信息[27]。自然博物馆中常见的各类生境景箱展示,不论是玻璃橱窗式,还是无玻璃阻隔的开放式,通过逼真的生态环境营造,能激发人们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天性,使之成为学习和获取知识的内在动力,为博物馆参观体验带来更多的自主探索与乐趣。
3 传统景箱应用的灵活与创新
20 世纪以来,新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为博物馆展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博物馆展示,从一开始单一的物件陈列,进展到重视物件知识性的分类、设计概念的加入,再到展品脉络性的原始样貌呈现、打破城墙的博物馆环境营造,最后到多媒体数字技术、三维建模、物联网等技术的融合应用,展示趋向复杂化、互动化和虚拟化,为自然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注入活力。
浙江自然博物院有3 次大规模的场馆筹建与陈列布展,从这几十年的陈列展示发展来看,不论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标本为核心的教工路馆区陈列,还是新一代突出智性休闲的安吉馆区,都能见到生境景箱的应用。传统怀旧的景箱发展至今,随着新材料、新技术的引入创新,在兼具科学性、逻辑性的同时,又融入了观赏性、参与性和体验性。
3.1 以标本为核心的老馆区景箱展示
浙江自然博物院教工路老馆区,自1984 年从杭州西湖湖畔的浙江博物馆的自然之部分出单独建制后,囿于馆舍、经费等原因,无固定陈列场所,博物馆的功能运作一度受到制约,影响了社会教育功能的有效释放。后经多方努力,馆舍建设方面于1991 年建成库房业务楼,1998 年建成陈列馆,面积3 051 m2,基本陈列“恐龙与海洋动物陈列”荣获了1998 年度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当时,该陈列尝试打破传统的展柜标本陈列手法:在海洋动物陈列单元中,背景设计成蓝色海洋画面,人造珊瑚礁附近,立体空间里穿插悬挂着各式鱼类;恐龙陈列单元中,将恐龙骨架标本陈设在简易的古生态环境中,增强可视性和吸引力。展览推出后,颇受观众欢迎。教工路老馆时代,仍处于博物馆以物为核心的阶段,还没有系统完整建立起为观众阐释的想法,陈列思路和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研究的成果。但是当时能突破传统的标本陈列模式,将标本及标本生境信息一起展示,在今日看来,尽管细节制作略显粗糙,却也是陈列展示的一次重要提升。
3.2 以呈现科学、真实为核心的杭州馆景箱展示
浙江自然博物院西湖文化广场的杭州馆区,于2009 年建成开放,展陈面积5 200 m2,陈列主题为“自然·生命·人”,由“地球生命故事”“丰富奇异的生物世界”“绿色浙江”三个单元组成,各单元都有一定比例的景箱展示。展览将符合自然博物馆定义的“自然”“自然史”“自然与人类”三重内容融为一体,将观众引向对生物多样性及人与自然和谐重要性的思考,体现了自然历史的科学体系,也有助于增进人们对自然与生命的兴趣和责任感。
3.2.1 注重科学提炼,景箱的生境展示科学严谨,并适度引入简易互动装置。例如设计“浙江山地”展项,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赴浙江典型的丘陵山地考察,择取与指定生态系统景观相关的生境信息,包括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所在的具体地段环境及其他的生态因素,以及不同类型的景观要素或生态系统构成的景观,在空间结构、功能机制和时间动态方面的多样化信息,并进行模拟设计、高仿真翻模制作。相较于传统的静态景箱展示,引入互动概念,在观众驻足参观处,设有可旋转的抛物线探测器,方便观众自主操作,当瞄准场景中的某只鸟类标本后,可在设备中听到该种鸟类的鸣叫声。另外,立杆式摄像机让观众可以自由选定想观察的动物,在设备上便可观看该动物的相关视频。
3.2.2 采用新工艺,通过空间、色彩、造型等设计要素,在有限空间营造生动逼真且富有意境的立体生境。在各类辅助展品制作方面,如浙江山地的树木脱脂、防腐、树叶钢模翻制工艺,呈现了山林枝叶繁茂的效果;以浙江下渚湖湿地为模板的景箱中,亚克力水面雕模工艺使得水域呈现出波光粼粼的效果,水域的截面展示,便于观众观察该生态环境中的鱼虾、贝类等物种,新技艺的引入确保了时空场景和生态系统景观展示的质量和效果;在制作浙江海岛的岩石辅助展品中,应用岩石造型翻模技术,岛屿峭壁和背景画中的海岛连成一片,几近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为珍稀的中华凤头燕鸥等鸟类标本展示营造了良好的生境背景;浙江山地展示中,还应用了灯效控制、影音播放及机电一体化互动展项技术,观众可以感受晨曦光线变化中的山林,听到山林中栖居动物的叫声,看到各种动物身影,仿佛步入真实的大自然环境中。
3.3 注重主题阐释多维度、脉络性的安吉馆景箱展示
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区于2018 年12 月试开馆,后经半年多的整改提升和调试完善,2019 年10月正式开馆。作为亚洲单体建筑最大的自然博物馆,安吉馆区有地质馆、生态馆、贝林馆、恐龙馆、海洋馆和自然艺术馆6 个独立展馆,因展示技术的进步与迭代更新,安吉馆的展示形式多元丰富。除了艺术化的标本阵列,安吉馆设有51 个生境景箱,讲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涵盖地球科学与生命科学的相关主题故事。贝林馆、恐龙馆、地质馆的景箱设计各有侧重和特点,可以说是多维度地体现了景箱“自然之窗”的教育功能。
3.3.1 重视景箱中重要辅助展品的制作应用。贝林馆的景箱数目在6 个展馆中属最多。早在2016 年,肯尼斯·尤金·贝林(Kenneth E.Behring)先生捐赠了176 件标本用于筹建安吉馆区的贝林馆,捐赠的标本大部分来自非洲和北美洲。为了充分利用这批珍贵的标本,贝林馆设置了大小不一的各种生境景箱,其中最为主要的有北美沙漠、北美大草原、北美苔原、北美沼泽、浣熊、土拨鼠巢穴6 个主题故事景箱。贝林馆的景箱特点在于,仿真兽类模型在完整科学叙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贝林馆的展览内容中,除了展示非洲和北美洲的标本之外,还涉及很多澳洲、南美洲的有袋类标本。一些景箱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相关兽类标本无法获得的问题,原因是部分标本不在贝林先生的捐赠清单内,同时受到国际公约制约,或受到相关国家对动物标本出口的限制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征集到,这些标本的缺失将直接影响到展览主题的完整性和典型性,甚至影响展览的科学解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用高仿真兽类模型来替代无法征集到的兽类标本的方法,以完成景箱的完整叙事。兽类模型,就是应用其他材料模仿兽类动物本身,并通过特定的工艺制作而成的仿制品。制作一般先对兽类进行3D 建模,其关键之处在于对动物形体科学性的把握,再利用3D 打印技术制作动物假体,定制人工皮毛,最后对人工皮毛进行整形并着色。虽然仿真模型具有良好的展示效果,但与真实标本不可相比,不具备研究价值,从这个角度而言,仿真标本仅能在展览展示方面替代兽类动物标本[28]。例如北美沼泽湿地景箱中的星鼻鼹、美洲獾捕食的黑尾土拨鼠(美洲獾在洞口伺机捕食土拨鼠,土拨鼠被设计在洞穴内,光线较暗,观众无法看清细节,因此很好地掩盖了模型的不足,又不影响观众观看)等。
3.3.2 多媒体数字技术融入传统景箱展示。相较于杭州馆的景箱展示,安吉馆的景箱主题涵盖面更为广泛,不仅涵盖了生物学,在古生物、地质学方面也得到大量应用,并且辅之以新媒体数字技术,让景箱的叙事性与故事性更强。例如地质馆,既展示浙江的地质史专题,又展现从前寒武纪到第四纪地球结构、地质年代、生物演化等共性的地质学内容。因为时间跨度达数十亿年,信息量大且抽象,为将抽象的时间概念具象化,展厅中央设置了13 个微缩景箱,对应从前寒武纪至第四纪的13 个地质年代。在微缩景箱的背景画中设置了投影播放三维动画视频,各种外形奇特的古生物模型、化石与投影动画有机结合,生动地讲述了各时期生物群的典型生命特征,仿佛时间被凝固于咫尺之间,让人们在有限的展示空间中了解奇幻的远古世界。
又如恐龙馆,以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的时间顺序展出各种恐龙。其景箱展示大致分为两种:恐龙骨架所展现的生态造景与恐龙复原模型的全景式生态造景,二者皆生动直观且通俗易懂地让观众了解恐龙时代的生命景象及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等。在设计恐龙的生存环境时,在题材、情节的设定、表现形式的选择、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方面,都严格控制在科学研究的范畴之内。在介绍浙江的恐龙时,背景画都采用了传统的绘画形式,巨幅背景画前延伸开来的真实生态环境里,展出了白垩纪的丽水浙江龙、缙云甲龙、越龙、天台镰刀龙等,辅以幻影成像、光电玻璃等,模拟并塑造出远古时期恐龙的真实生活场景;而在早白垩世中国辽西地区的热河生物群展示中,辅以灯控、投影装置,对当时植被繁茂的生态环境做了细致还原,为观众了解该生物群铺垫了丰富的背景信息。
3.3.3 景箱制作材料考究、工艺精良。安吉馆的生境景箱制作,在相关材料的择选上紧随技术发展,注重品质。为达到良好的展示成效,丰富视觉效果,对细节的把控更为严格。对于一些封闭的玻璃橱窗式景箱,根据需要选择6 mm 至8 mm 的超白夹胶玻璃,透光率>97%,并精确计算倾斜角度以避免反光,降低环境光的干扰,让参观者拥有更舒适轻松的观看体验;对不同的景箱主题进行空间布局时,遵循科学研究的前提下注重艺术表现力,采用弧形结构对背景画和天顶进行搭建,例如恐龙馆,考虑到总高度12 m,有限的展示分区限制了观众的视点,在景箱制作时,为避免视觉变形,特意将背景画略微前倾15°,以减小透视变形;在绘制背景画时,依据观众平均身高,把握视平线高度,增强现场感,让背景画展现真实的自然景观无边无际的效果;注重场景的灯光照明,设置隐蔽的灯光布局,模拟自然光线,尽量提供自然真实的观看体验。
4 结语
自然博物馆属于一般大众能自主学习的场域,成为科学与一般大众之间的重要媒介。有着悠久历史的生境景箱,藉由背景的绘制与相关标本的摆饰,营造出真实逼真的生态景观,让观众更能容易地了解物件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是说明及解释展出物件的最佳方式之一。生境景箱有效结合了博物馆的展示与教育使命,在激发观众思考、促成自主学习、促进智识发展等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优越性。
从浙江自然博物院3 次馆建陈列来看,几十年的时间跨度下,传统经典的生境景箱在自然史的陈列展示中,依然处于重要地位。面临新技术、新材料的发展变革,传统景箱并不是一成不变,能及时融入更多创新元素,应用范围逐渐拓展,设计制作也逐渐走向成熟。生境景箱在诠释展示物件的原始环境样貌时,既有科学研究的细致严谨,又有艺术表现张力带来的情感渲染力,它们通过景箱知识性、系统性、脉络性的呈现,让观众得以深入观察、检视、欣赏、理解环境与该展示物件之间的各种主客观群聚关系,成为观众学习与物件相关知识的重要途径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