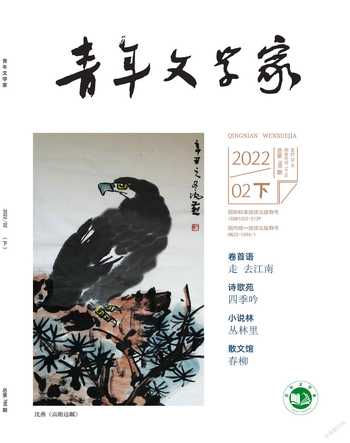张爱玲笔下的色彩书写研究
李想 刘红燕




张爱玲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女作家,她笔下华美的衣饰、精致的吃食、光怪陆离的城市景象历来为人所称道,成了20世纪40年代的一朵文学奇葩。然而,上述种种都离不开张爱玲对色彩的认真观察与精心描摹。在“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之中,我们感受着张爱玲用色彩书写成就的“荒凉绝望的底子上浮泛着俗世的欢乐”。
根据笔者统计,在《张爱玲全集》收录的二十八篇中短篇小说中,篇篇都有对色彩的书写,这些色彩可根据其自身属性划分为四大类和十四小类,笔者将在下文一一介绍。不仅如此,在张爱玲的散文中也不难寻觅色彩书写的痕迹,更在《谈画》等文章中表现出了其对色彩运用的独到见解。由此,色彩书写成为张爱玲文学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的深挖。
一、色彩斑斓的文本世界
七色光是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色彩组合样式,这也成为张爱玲色彩世界中的第一个大类。其下的七个子类自然就是红、橙、黄、绿、青、蓝、紫了。然而这七种颜色的运用频率及其各自内涵却大为不同,甚至出现了差异很大的情况,这实在值得我们再加以关注。
红色是张爱玲笔下最常用到的颜色之一。根据笔者统计,张爱玲的中短篇小说中篇篇有红色,红色更成了《年轻的时候》《多少恨》等小说开篇即首个运用的色彩。不仅如此,在这高频率的运用背后更蕴藏着丰富而深邃的内涵。首先,红色象征着喜庆与吉祥,这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亦十分常见。例如在《怨女》中,三朝回门时,店上“贴出一张红纸”,柴银娣穿着“大红百褶裙”,就连她残疾的丈夫也不忘被安排“瓜皮帽镶着红玉帽正”,一幅喜庆婚图顿时跃然纸上。即便是再冷心的读者,读到此时大概也会幻想:或许会有个好结局吧?虽然柴银娣的婚姻比骗局更不幸,但在走入富贵之时,柴银娣及她的兄嫂却都表现出了异样的渴望。然而,正与柴银娣不幸的人生类似,红色在张爱玲笔下往往是血色的代言词,由此衍生出了恐怖的内涵。同样是在《怨女》中,姚三爷为了不使自己的恶行败露而将一碗“深红色”的猪血抹在了脸上,原本喧闹的旅馆顿时充满了“一股子血腥气,像杀了人似的”,一阵恐怖、阴森的气氛令人不寒而栗。结合姚三爷此后的侥幸与不知收敛,一个荒唐而败落的大家族无需多言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另一方面,紅色在张爱玲笔下也与少女的羞涩直接相关,“红了脸”是张爱玲笔下常有的细节描写。在此基础上,张爱玲又巧用“红颜”这一惯用语,“然而她的确是非常红的‘红颜’”,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一个少女的美丽、懵懂、羞涩与心动。
相比起红色,橙色在张爱玲笔下所占的篇幅就少得多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本身介于红色与黄色之间,越是交界地带的事物其特征往往不易突出。另一方面,橙色是暖色系中最温暖的颜色,毫不费力地就能产生巨大的效果。然而,这些优点却在某些程度上与张爱玲小说的创作思路相抵牾。前者,张爱玲对温情人生持怀疑态度,后者则因张爱玲强调“安稳”而非“张扬”。于她而言,“巨大的力量”是危险的,是要远离的。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张爱玲对橙色的使用慎之又慎了。
黄色是四个心理学基色之一,亦是减法三原色之一,似乎它应当具备繁而又繁的内涵。然而,张爱玲对黄色的处理却简而又简。在张爱玲笔下,黄色首先以“黄包车”的形式出现。黄包车之所以将车身涂黄漆,是因为招揽生意方便,这自然而然地和底层人民,尤其是车夫所代表的力量产生了关联。在《年轻的时候》中,沁西亚“她的头发黄得没有劲道”,这原本是一句不合逻辑的描写,但在我们了解了张爱玲所赋予黄色的力量感之后,这句描写顿时就变得独到、精彩,一个生命力委顿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另一方面,黄色通常以“黄昏”的形式出现。这既可代表自然时令中一天的完结,也可抽象为一个人生命的临近终结。在小说《创世纪》的末尾,紫微在“发黄的纸上”阅读着文言童话。一个简单的“黄”字,既表达了过往时间的流逝,又巧妙地将时间凝滞在了这一刻上,将时间的流逝与永恒相对统一了起来,同时又暗示紫微其实已临近了生命的尽头,这是她人生中的一个“黄昏”,也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序曲。
绿色是自然界的主色调,其以绿叶、嫩草为代表而象征了生命、成长、清新、希望等含义。然而,在张爱玲笔下,绿色更多地代表了精神层面的生命力蓬勃生长,甚至于到了疯狂的程度。在《倾城之恋》中,当白流苏在香港送别范柳原,独自一人回到家时,张爱玲写道:“客室里门窗上的绿漆还没干,她用食指摸着试了一试,然后把那黏黏的指尖贴在墙上,一贴一个绿迹子。为什么不?这又不犯法?这是她的家!她笑了,索性在那蒲公英的粉墙上打了一个鲜明的绿手印。”在这一段貌似疯狂的描写中,张爱玲其实对白流苏的个性实行了一次彻底的大解放。白流苏的“疯狂”与曹七巧的“疯狂”是截然不同的。曹七巧是真正的病态人格,然而白流苏不是,她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压抑着自己的性格,即便是在一礼拜前,当她正式与范柳原确定关系时,她也依旧是“精刮”的。所以,在四下无人时,当“她该躲着人,人也该躲着她”的时候,在“绝对的静寂”时刻,她终于找到了机会来解放自己,释放自己压抑许久的天性。在这夸张的动作中,白流苏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个性张力。同样,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王娇蕊“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上便留着个绿迹子……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引发了佟振保近乎疯狂的幻想。张爱玲借用绿色而将笔触伸向人物内心深处,展现出了她运用弗洛伊德意识流、潜意识等相关手法时过人的技巧。
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青与蓝往往是同时出现的,或许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在张爱玲的小说里,青与蓝也成了一套“组合拳”。在《年轻的时候》《花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中,青与蓝依次出现,构成了张爱玲笔下色彩书写的一种惯性规律。除此之外,青与蓝又各有其特色。在张爱玲笔下,“青”首先象征着“年青”,也即“年轻”。在小说《第一炉香》的开篇,张爱玲即写道“园子里也有一排修剪得齐齐整整的长青树”,与“布置谨严”的花园一样,“长青树”也至少包括两层含义:正值青春年华的葛薇龙与试图留住青春的梁太太。两个女人如“两个花床”争夺着“长青树”般争夺着青春、爱情与财富。自然界中的竞争是残酷的,而现实人生之中的竞争又何尝不是呢?在《殷宝滟送花楼会》中,女主角殷宝滟穿着“青灰细呢旗袍”来找“爱玲”诉说自己的故事。故事尾声,她又不忘“低头看着青绸里子”,花影也“映在她袖子的青灰上”。在这个颇具象征与暗示意味的穿着中,张爱玲巧用色彩书写来交代出殷宝滟此时的真实心境。她与罗潜之的故事实在是她人生中极为重要的青春记忆,既可讲与他人,又需自己珍藏。由此,借助色彩书写,我们可以另辟蹊径地对人物心理做出合理的解释。
蓝色是光的三原色和心理四色之一,通常情况下,它首先代表着天空,其次是温柔、忧郁,最后则是永恒。在张爱玲的笔下,蓝色却成了贫穷和淡漠的象征。在《第一炉香》中,初入花花世界的葛薇龙穿着“翠蓝竹布衫”,如果说此时的她尚且能不以为意,那么当她见识过这个花花世界后,当她再度打量自家佣人的“簇新蓝竹布罩褂,浆得挺硬。人一窘,便在蓝布褂里打旋磨”时,蓝色无疑就成了贫穷的代言词,也就不怪她会觉得陈妈上不得台面了。不仅如此,在《小艾》中,一生贫困不幸的小艾也是常年穿着“蓝白芦席花纹的土布棉袄”“蓝布围裙”等象征意味很强的衣服—对于当时的底层群众而言,贫穷就像蓝天一样笼罩在他们的头顶,即便偶尔会飘过几朵幸福的白云,但幸福终究会像芦花一样飘散。久而久之,被贫穷折磨得麻木了的人就会对整个世界都变得淡漠起来。例如在《年轻的时候》中,潘汝良“过度的鄙夷与淡漠使他的眼睛变为淡蓝色的了”,而行至生命尽头的沁西亚更是“对于世上一切的漠视使她的淡蓝的眼睛变为没有颜色的”。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紫色是尊贵的颜色。同时,紫色又是极佳的刺激色。而在张爱玲笔下,紫色成了一种“幻想专用色”。这种“幻想”既指对现实层面的幻想,比如物质、性等,同时又指对过去或未来的幻想。前者以大量出现的紫色衣饰为代表,后者则以人名或小物件为主。在《年轻的时候》中,沁西亚的一件“玫瑰紫绒线衫是心跳的绒线衫”,它让潘汝良“觉得他的心跳”。这明显的幻想暗示了潘汝良与沁西亚之间的结局。而在《留情》中,杨太太“在家也披着一件假紫羔旧大衣”,作为淳于敦凤的昔日情敌,对于淳于敦凤和米晶尧的结婚结局,杨太太心中难免嫉妒,所以她陷入了幻想之中,但也正如她的大衣是“假”的一样,她的幻想也于事无补,最终只能“(杨太太)把假紫羔大衣向上耸了一耸……旁边没有男人,她把她那些活泼全部收了起来”。而在张爱玲的未完稿《创世纪》中,小说后半段忽然用大量笔墨记叙、描写“紫微”的过去。熟悉张爱玲的人都能从中找到关于张爱玲家族过去的蛛丝马迹。然而,即便是对张爱玲家族并不了解的读者,也依旧能从“紫微”这个名字中找到最直接的证据—紫色在张爱玲的笔下就意味着回忆。“紫微”之所以是“紫微”,就是因为她所要回忆的并不是平凡岁月,而是一个显赫家族的衰微史!这是一段高贵而又破败的回忆,所以她的名字中必须带有一个独特的意象来与之匹配,也即“紫”。所以,“紫微”只能是“紫微”,而非“采微”或别的什么名字。
白光曾被误认为是最纯净的光,直到三棱镜将其分解后,我们才得以了解白光(白色)的背后奥秘,白色也由此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在张爱玲笔下,白色是一种十分矛盾的颜色,它既可以代表纯洁、希望与美好,又可以代表病态、死亡与恐怖,这一特征在小说《花凋》中表现得格外明显。在对郑川嫦的描写中,张爱玲写道“尤其美的是那一双华美的白肩膀”,极力突出郑川嫦的健康与美丽。在恋爱对象章云藩的世界里,郑川嫦穿着“葱白素绸长袍”,虽并不合身,却别具诱惑性。此时,纯白无瑕的郑川嫦令章云藩心动,郑川嫦更是对未来充满希望,但在这希望中却已经包含了危险—“白手臂与白衣服之间没有界限”,纯白之中暗藏着苍白,这是作为医生的章云藩的本能发现。之后,郑川嫦一病不起,“穿着她母亲的白布褂子”,“她的脸像骨格子上绷着白缎子”,“她趴在李妈背上像一个冷而白的大白蜘蛛”。此时,“白”已经由希望变为了病态,及至死亡。《花凋》采用的是倒叙的手法,故而在小说开头,张爱玲就已经写道:“坟前添了个白大理石的天使……上上下下十来双白色的石头眼睛……翻飞着白石的头发,白石的裙褶子……乳白的肉冻子……”在这一片纯白的世界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希望,而是一种笼罩小说前后的恐怖氛围,在这恐怖气氛的笼罩下,郑川嫦的种种希望又何尝不是一种苍凉的讽刺呢?
与白色相对的是黑色。但在张爱玲的笔下,黑色与白色的内涵却并非是相对的,而是相似的。除黑暗、恐怖笼罩之含义外,黑色还多了“神秘”与贫穷之意。前者多表现在其笔下的人物所佩戴的黑色眼镜与各种不确定的“黑影”之上,后者则如《连环套》中,“广东的穷人终年穿黑的,抑郁的黑土布,黑拷绸。霓喜一辈子恨黑色,对于黑色有一种忌讳,因为它代表贫穷与磨折”。
金属色是张爱玲笔下色彩书写的第三大类。大多数的金属都因其外表光滑而自带色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金、银、铜,这些金属色也是频频出现于张爱玲的笔下,而且各有其深意。
金色在张爱玲笔下首先是富贵与美好的象征。在《鸿鸾禧》中,邱玉清在婚前买了“金织锦拖鞋,金珐琅粉镜”等物,因为“她认为一个女人一生就只有这一个任性的时候”。如果说这是富贵的象征,那么下文中“一团高兴为媳妇做花鞋”的娄太太就代表了对未来美好的向往,“娄太太那只平金鞋面还舍不得撒手”。同时,作为富贵与美好象征的金色也可以在精神层面引申为虔诚之意。在张爱玲笔下,神甫的衣饰常有金色,即便是胡须也是金黄的;神像也多为金,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正式。
银色与金色相似,都有富贵、美好之意,但通过张爱玲“科学化的银色的壶”的描写,银色就又多出了科学及纯净之意。而通过“银脆的绢花”等描写,银色又在特定的时候被赋予了易碎的特点,这当然是与其和“白”类似的特点有关。
上文未提及的颜色即为张爱玲笔下色彩书写的第四大类。具体颜色有粉色、灰色、棕色、栗色等。
粉色是深受年轻女性喜爱的颜色之一,它也因此成了可爱、温馨、娇嫩的代表。但在张爱玲笔下,粉色少了青春洋溢的快乐,反而多了油腻的庸俗之感。粉色被从年轻少女的世界中剥离出来,成了中年妇女们世故的代表,张爱玲借此将琐碎的生活日常直截了当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在《创世纪》中,紫微回忆着自己的过去,“传递着蛋形的大银粉盒,女人一个个挨次地往脸上拍粉,红粉扑子微带潮湿……”在这段并不美好的回忆中,我们感受不到紫微对于生命、生活的活力,而只是她的无奈与被折磨。
另一种被张爱玲大量运用的颜色是灰色。除了灰色的传统含义,张爱玲别出心裁地用灰色勾勒出了历史的色彩。在《创世纪》中,仅仅一句“还是一个灰灰的世界”,就将一个混乱、压抑、迷茫、贫穷的时代交代清楚,令紫微完成了时代看客的任务。
除此之外,在某些作品中,张爱玲所运用的不是某一种具体颜色,而是抽象的色彩代称,比如“泛了色”“五颜六色”“深色边”等。这多与描写对象的心情及情节需要相关。可以说,张爱玲笔下的色彩世界并不全是工笔细描,其中也有大面积的色彩堆积。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大面积色块的铺垫,某一具体的颜色才能色彩更艳丽,其特点也才能更鲜明。由此,张爱玲笔下的色彩书写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粗有细、主次分明,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不仅如此,张爱玲笔下还常用“喜色”“绝色”“脸色”等词语。其实严格说来,它们都不算颜色,但其中一个“色”字却令读者将其与色彩联系起来,甚至于它们本身就是颜色的引申义,好比丰富多样的脸谱般多彩又实用。
二、内蕴丰富的文学世界
近年来,色彩心理学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在心理学领域,所谓色彩心理学,也即由对色彩的经验积累而变成对色彩的心理规范。毫无疑问,张爱玲笔下的色彩书写与色彩心理学的关系密不可分。但是对张爱玲而言,产生心理规范的对象并非作品中的角色,而是现实世界中的读者。对于身为作者的张爱玲而言,巧用色彩书写可以免掉很多不必要的描写与抒情。一旦我们发现了这一规律,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一个“绿”就可以表现出白流苏的疯狂,一个“紫”就可以表现出紫微的回忆与幻想……由于视觉是人的第一感觉,色彩又是对视觉影响最大的因素,故而在人类日积月累的经验积累过程后,色彩不再只是带有颜色的物体,曾经的方块字也带上了“颜色”,这是人类阅读过程中十分隐蔽的心理过程。但其过程越是隐蔽,作家对其运用的效果就越是高明。张爱玲将文字的颜色最大化使用,不动声色地在心理学的层面上对读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读者进入情境中而不自知。可以说,在营造氛围方面,实在没有比这更巧妙的方法了。
在张爱玲笔下,色彩是身份、心理变化的外在体现,张爱玲符合场景、情节的需要而设置颜色,赋予并运用颜色的内涵。张爱玲用色彩勾勒角色,色彩就是角色的印象。不仅如此,张爱玲为了加强色彩对心理的规范作用,而直接采用了感觉与色彩直接搭配的方法,“痛楚的青、白、紫”,色彩的心理暗示与感官的直接信息接收使得事半功倍,快速地将读者引入了情境中。
另一方面,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直言,“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它像葱绿配桃红”。与同时代的其他大多数作家相比,张爱玲其实很少涉及文艺理论,为数不多的几次谈论也都是以自己的作品为中心。在解释自己的文艺理论时,张爱玲不忘运用色彩,仅用“葱绿”与“桃红”这两个颜色就将“参差的对照”这一理论解释清楚。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或许正是这种思维上的连贯性使得张爱玲在作品中时刻不忘色彩书写。
若说“参差的对照”,那么“红玫瑰与白玫瑰”之名可谓明证。红与白一强一柔,本是极强烈的反差,但在张爱玲的色彩书写中,红与白都有美好的一面,也都有令人感到恐怖的一面,这种内涵上的相通,使得两种色彩在心理学上达成了某种契合。同時,张爱玲将两种色彩赋予在同一事物之上,也即玫瑰,美丽的玫瑰花从心理上起到了缓和的作用,但玫瑰花的刺又会给读者猝不及防的痛感。在张爱玲笔下,很少有什么事物是绝对的,即便是红白二色也可以在经过调和后既崭露锋芒又不失美感,在这形象对比中,颜色的具象含义与抽象含义被完美结合了起来,形成了张爱玲最为推崇的“参差的对照”。
事实上,对于张爱玲而言,其“参差的对照”并不仅限于两种颜色,甚至于说,多种颜色的混合使用才更能发挥“参差的对照”的功用。在《第一炉香》中,在描写梁太太的花园时,张爱玲一口气连用了白、金、青、粉红、黄、虾子红、红、浓蓝这八种颜色。在这八种颜色中,同是红便有三种,其他颜色也是有冷有暖、有亮有暗、有浓有淡,彼此之间虽构成了对比,但又不失和谐,并未出现某种色彩“失控”的局面。在这种有同有异、同异之间构成对比,同、异又各自内部构成对比的色彩书写中,张爱玲更成功地完成了“参差的对照”。张爱玲无惧大篇幅使用颜色,在一句话中运用多个颜色的色彩叠用中,极力渲染并深化印象于读者。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对香港码头的描写可谓经典,“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张爱玲敢于让同一颜色反复出现,在相似中发现不同,更表现了她对“参差的对照”炉火纯青的运用,而最简便直接的运用方法自然就是运用色彩无疑了。
究其实质,张爱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展现其苍凉的艺术世界,“更喜欢苍凉”。张爱玲不追求刺激性而偏爱启发性,这自然与她所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也是因此,她才力求在文本世界中构筑一个氛围强于实际的世界。由此,张爱玲笔下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品味,其中的色彩便更是重中之重。了解张爱玲赋予色彩的独特含义,就能“走捷径”地了解到张爱玲的所思所想,进而品味出苍凉艺术世界的深厚力量。张爱玲无愧于“天才作家”的美誉,她敏锐地抓住了同时代作家所忽视的因素而构成了独特的色彩书写,并最终成了苍凉艺术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
纵观对张爱玲的研究,其作品中丰赡的细节历来被视为重中之重,从华美的衣饰到精致的饮食,从多变的场所到逼真的出行……可以说,张爱玲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蕴含了大量可供挖掘的信息。然而这些细节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点,也即色彩书写穿插其中。张爱玲的色彩书写既为其作品涂上了一层多彩的外衣,又暗合其作品的苍凉意味;既为读者提供了别样的阅读体验,又让作家张爱玲“省力”不少;既上承中国古代文学的绚丽世界,又呼应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合流的时代趋势。从这个角度而言,色彩书写无疑是张爱玲笔下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价值仍有待我们去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