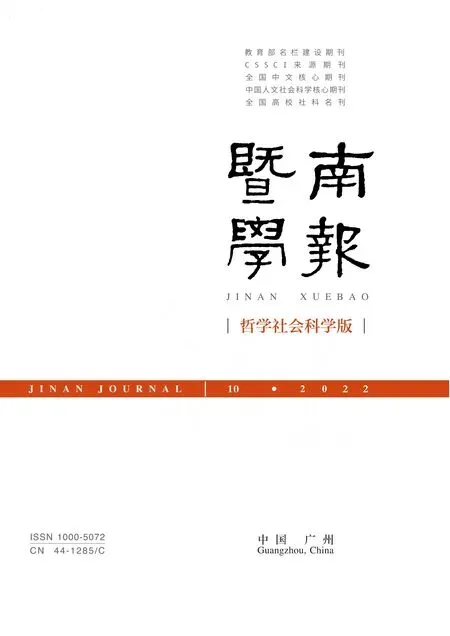“表见代表” 之虚与实
刘 骏
一、问题的提出
自原《合同法》颁布以来,学说多认为原《合同法》第五十条(现《民法典》第五百零四条)规定了表见代表制度,①若干代表性文献,参见温世扬、何平:《法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与 “表见代表” 规则》,《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李建华、许中缘:《表见代表及其适用—— 兼评〈合同法〉第50条》,《法律科学》2000年第6期;张学文:《董事越权代表公司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石一峰:《商事表见代表责任的类型与适用》,《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即代表人超越权限从事代表行为时,如第三人善意、有理由地相信其有权,该代表行为有效。即对代表权的法定限制可当然对抗第三人,而对代表权的非法定或内部限制,仅可对抗知情或应知情的恶意第三人。这一理解也延伸至《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三款。②参见杨代雄:《公司为他人担保的效力》,《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1期;梁慧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解读、评论和修改建议》,《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判例上表见代表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形:第一,不得以法定代表人超越对其权限的内部限制对抗善意相对人;③如最高人民法院(2019)民申4457号裁定书。第二,代表人滥用代表权,订立的法律行为不符合法人利益时,但相对人属善意的;④如最高人民法院(2017)民终313号判决书。第三,准许法定代表人缔约的公司决议嗣后出现瑕疵的,不得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特别是在公司对外担保领域。⑤如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56号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
表见理论适用以权利人对某一因素的认识错误为前提,然而相对人真的能够对法定代表人的权力发生认识错误吗?个别学者对此有所反思,①参见朱广新:《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中外法学》2012年第3期,其认为原《合同法》第五十条的基础不是权利外观理论,而是法人内、外部关系区分理论;刘骏:《〈合同法〉第50条解释论基础》,《民商法论丛》(第6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3页;崔建远:《关于制定〈民法总则〉的建议》,《财经法学》2015年第4期。后一篇文章认为应以 “越权行为” 替代 “表见代表” ,并引用法国公司法关于代表权的规定,其实法国这方面也是继受经理权的规定,详见下文。但尚未准确指出哪些情形属真正的表见代表。的确,代表人的权力是概括的而非具体的,涉及法人的所有营业事务,第三人很难对其权力认识错误。不过,第三人可因登记等外观措施对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发生认识错误,也就是误以为某人是法定代表人,而实际上其并非法人所选任的法定代表人。出于这些考虑,本文先揭示并无必要以表见理论分析所谓的 “超越代表权的行为” ,第三人很难对代表权发生认识错误,以及《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三款实际确认的是经理权规则。随后讨论真正的表见代表,②本文认为代表人属于权限范围被客观化的意定代理人,在法律行为归属方面,法定代表人并不区别于一般的委托代理人,因此不拘泥 “代表” 与 “代理” 之区分;参见刘骏:《揭开机关理论的面纱:区分 “代表” 与 “代理” 以及 “机关” 与 “雇员” 之无益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即第三人因登记不实或无权代表人的不实称述而对其身份发生认识错误。最后,明确真正的表见代表和非真正表见代表之区分意义。表见代表作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制度,在《民法典》解释适用的背景下厘清其适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非真正的表见代表——对代表人权力的认识
如前所述,针对法定代表人超越非法定或内部限制而完成的代表行为以及公司争议该行为的,学说和判例以属外观主义法理的表见代表制度来保护善意第三人。在追溯这一称谓的来源之后,我们在讨论《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三款时应以经理权而非表见代表法理来解释之。
(一) “表见代表” 之日本法启发
原《合同法》立法过程中,有学者在讨论董事越权代表公司时,认为表见代表是指董事虽超越权限代表公司,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董事具有权力的,该行为对公司有效,并以原《日本商法典》第二百六十二条③现《日本公司法》第三百五十四条。的表见代表董事制度为例证。④董峻峰:《董事越权代表公司法律问题研究》,《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合同法》颁布后,当时的主流观点继续受日本法上表见代表董事制度的启发,认为原《合同法》第五十条与原《日本商法典》第二百六十二条内容相同,该条从立法上承认了表见代表制度,⑤温 世扬、何平:《法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与 “表见代表” 规则》,《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李建华、许中缘:《表见代表及其适用—— 兼评〈合同法〉第50条》,《法律科学》2000年第6期;张学文:《董事越权代表公司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第109页;刘骏:《〈合同法〉第50条解释论基础》,《民商法论丛》(第6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75页。随后 “表见代表” 这一术语传播开来。当然,该称谓被广泛接受也与原《合同法》的条文安排不无关系,其在表见代理规则(第四十九条)之后紧接着规定越权代表,⑥合同法草案第三稿并未单独规定越权行为,而是使其准用表见代理,参见梁慧星:《关于中国统一合同法草案第三稿》,《法学》1997年第2期。两个条文皆旨在保护善意第三人,让人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皆是表见法理之体现。
然而日本法上表见代表董事制度是对代表人身份发生的认识错误,原《合同法》第五十条规范的是对代表权的认识。日本法上,公司可在董事中选择一人或数人担任 “代表董事” 作为常设代表机关(《日本公司法》第三百四十九条第三款、第三百六十三条),代表董事常常挂有 “社长、副社长、理事长” 等头衔。①[日]山本为三郎著,朱大明等译:《日本公司法精解,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页;[日]前田庸著,王作全译:《公司法入门》(第1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7页。所谓 “表见代表董事” ,是指如果公司将包括社长、副社长以及其他被普遍认为具有代表公司权限的名称授予代表董事之外的董事等人时,就该行为人以公司名义实施的行为,公司对善意第三人负外观责任。②[日]近藤光男著,梁爽译:《最新日本公司法》(第7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30页。在设置委员会的公司,也存在与表见代表董事制度类似的表见代表执行董事制度(《日本公司法》第四百二十一条)。另《日本商法典》第二十四条规定了 “表见经理人” ,参见刘成杰译注:《日本最新商法典译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关于新旧条文之变更,还可分别参见吴建斌编译:《日本公司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王书江、殷建平译:《日本商法》,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虽然真正的代表董事属于登记事项(《日本公司法》第九百一十一条第三款第十四项),但是在商事交易快节奏下,人们有时可不去详细查登记并信赖拥有社长、副社长等名称的人具备代表公司的权限;③[日]山本为三郎著,朱大明等译:《日本公司法精解》,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183页;[日]前田庸著,王作全译:《公司法入门》(第1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7页。特别是,不是代表董事或代表执行董事的事实并非登记事项。④[日]山本为三郎著,朱大明等译:《日本公司法精解》,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页。这一制度实际上是表见法理在商法的运用。表见代表董事制度与越权规范明显不同,一方面,日本法上股份公司代表人越权规范位于《日本公司法》第三百四十九条,其规定 “对代表权的限制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 ,基于代表权的不可限制性相对人很难对代表权之行使发生认识错误。另一方面,在表见代表董事制度中,相对人误以为不是代表董事的人有权代表公司,且这一信赖值得保护;或者说,表见代表董事不存在 “越权” ,其根本无权代表公司,与有权代表公司但违反内部权限限制的董事明显不同。
综上,日本法上表见代表董事制度是善意第三人对代表机关身份因外观等因素而发生的认识错误,错误地把不是代表机关的人当作代表机关,这与代表机关自身超越权限完全是两回事。问题在于,对代表人身份的认识错误与对其权力的认识能够等同吗?回答该问题之前,需明确《民法典》第六十一条之适用。
(二)《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三款并非 “表见代表”
在法律所规定的限制之内,法定代表人就法人的营业事务无须特别授权、拥有概括的签字权力。⑤刘俊海:《现代公司法》(上),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612页。从相反的角度来看,法定代表人的哪些行为不能够拘束公司?
第一,法定代表人不得违反法律对其权力的限制,违反法律关于法人内部机构的权力划分,如董事会、股东(大)会的职权。⑥关于《公司法》第十六条所规定的对外担保规则,本文倾向认为代表人的对外担保行为虽未经公司内部决议的授权仍可拘束公司,除非明显损害公司利益,鉴于问题的复杂性,此处不详细展开。《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三款这一规定位于总则编第三章 “法人” 第一节 “一般规定” 中,理论上适用于任何类型的法人。但区别于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具有自身的特性。一方面,非营利法人是否能够从事经营性活动具有争议,或者说其能力是否受必须从事非经营性活动的限制。《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允许基金会进行以保值和增值为目的的投资活动。相反,《社会团体法人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禁止社会团体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但该条的司法适用不一。在一起典型案例中,富登公司与湖南商会签订了《渠道合作协议书》,该协议的履行会导致湖南商会获得一定经济利益。一审法院认为,湖南商会不具备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资格,该协议未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也未违反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规定,应当有效;二审法院也未否认该协议的效力。①参见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4民终811号判决书。但是,也有法院基于非营利法人不能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或者通过认定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合同不能视为职务行为,②参 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湘民再271号判决书。或者通过认定其签订的联营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而直接无效。③参 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一中民终字第13050号判决书。我们认为,法律只是禁止非营利法人向其成员或设立人分配利润和剩余财产,并不禁止其从事营利活动,其经营所得应用于非营利事业。④参 见金锦萍:《论非营利法人从事商事活动的现实及其特殊规则》,《法律科学》2007第5期。社会团体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可承受相应公法上的不利后果,如责令整改、处罚等措施;私法上其从事经营活动而缔结合同的效力并不受影响。非营利法人为实现其目的,难免缔结给其带来利益的各种民商事合同,一概否认这些合同的效力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因此,非营利法人也可像营利法人那样从事经营性活动。另外,非营利法人的目的之范畴较营利法人更窄,具有特殊性,其代表人事实上也拥有概括代表权限,但相对人更应关注这类法人的目的。因为,这类法人章程所表达的目的同时也是法律对这类法人所要求的目的,而且在追求公益的法人利益和相对人利益之间,法律似不能完全侧重相对人利益和交易安全。例如,捐助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应该在设立章程规定的公益目的下行为,相对人应形式上核实代表行为是否符合捐助法人之目的。而在营利法人中,能够被纳入法人目的的代表人行为非常广泛,哪怕公司所作出的无偿行为,只要其直接或间接符合公司利益,都是有效的。
第二,法定代表人滥用权力且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其代表行为不可拘束公司。作为 “权力” ,代理权至少应该部分地为本人的利益而行使,而非独为了代理人自己的利益。⑤E .GAILLARD,Le pouvoir en droit privé,Paris,Economica,1985,pp.232-233.区别于主观权利, “权力” 行使的法效果及于他人的责任财产,而主观权利行使的法效果及于权利人自己的责任财产。⑥I bid.在法定代表人滥用权力时,同其他代理权滥用情形一样,为了平衡本人利益和第三人之保护,需要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力之滥用。滥用情形主要有 “双方代表行为” 以及代表人的行为明显损害法人利益等。
第三,法定代表人违反章程、内部决议以及内部规章对其权力的限制时,能否拘束公司?依据《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判例多认为章程以及决议等内部限制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后者的善意属推定。⑦参 见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终字第217号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浙商终字第57号判决书。问题是,第六十一条第三款只规定内部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而未言及这些内部限制是否限制代表权。在内部这些限制当然有效,代表人违反之可引起其对公司的责任;在外部,这些限制的效力如何呢?有两种解释:其一,主流学说认为,这些内部限制限制外部代表权,由于推定第三人不知或者不应知道这些限制,代表行为有效,反之,如果第三人知情则为无效。⑧参 见朱广新:《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中外法学》2012年第3期;王浩:《论 “代理权滥用法理” 之滥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其二,这些内部限制不限制代表权,哪怕第三人知道这些限制的存在也是善意的,只要没有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即 “简单知情” 并不等于 “恶意” 。⑨刘骏:《再论意定代理权授权行为之无因性》,《交大法学》2020年第2期。多数学说似乎没意识到二者的区别。0这一解释选择需要0例外是,吴越:《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行为效力再审》,《政法论坛》2017年第5期。就越权担保合同效力区分,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如果说 “善意有效” 、 “恶意串通无效” 没有疑问的话,仍可能出现第三种情形 “不为善意仍有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即相对人知情但不为恶意;但是该作者没注意到这实际上是经理权规则之适用,他所引用的《英国公司法》相关规定也是继受 “欧共体公司法第一指令” 。追问该条的比较法来源。
立法者可能没有意识到,《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三款实际上是受比较法上的经理权规则(Prokura)影响。在法定代表人是法人的唯一签字人且享有概括的代表权限这一前提下,《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三款的表达相比第五百零四条,更接近经理权规则。①张舫、李先映:《论商法中的经理权》,《河北法学》2007年第5期。经理人(Prokurist)是商人的另一个 “自我” ,其在不违反法定限制的情况下,就营业事务享有全部的权限,商人对经理权的内部限制不可对抗第三人。②参见《德国商法典》第四十九条及其以下;后来这一制度也适用于公司代表机关,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和《股份有限公司法》第八十二条,参见[德]托马斯·莱赛尔、吕迪格·法伊尔著,高旭军等译:《德国资合公司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530页。后来被 “欧共体公司法第一指令” (First Council Directive of9March 1968,68/151/EEC)第九条所借鉴,随后被其他国家转化。在经理权规则下,相对人对非法定限制的简单知情无碍代理行为之有效性。③B.Stauder, “L'abusdu pouvoir de représentation en droitcivilet commercial allemand” ,in Travaux de l'Association HenriCapitant,L'abus de pouvoirs ou de fonctions(Journées Grecques),Tome XXVIII,1977,Paris,Economica,1980,p.285;P.Le Cannu et B.Dondero,Droit des sociétés,6eéd.,LGDJ,2015,n°504,p.334.因为,关键问题在于权力是否为了本人的利益而行使,是否构成滥用,而非纠结代理行为是否违反章程或内部决议等内部限制。首先,这些限制不属于一般登记事项,④《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八条。不具外部公示性,第三人很难知情。而且,某一限制代表权的条款是否真正地在公司内部发生着效力,外部第三人也无从知晓。若承认意定的公司章程等可限制代表权,会损害相对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甚至会出现如下悖论:查询了章程等内部文件的谨慎第三人比根本未查询的第三人更不易得到保护。不同于授权范围多特定的一般委托代理权,代表权范围概括,对其权力的法定限制主要是法律所确定的法人内部各机构权力之划分。另外,体系地观察,早在《民法总则》制定之前,其他立法中已经有经理权规则的类似表达,如《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九条、《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条。
对于我们提倡的表见代表与经理权之区分,有学者可能反驳道:我国适用表见代表已经较长时间,也未见对交易安全有致命障碍。确实二者功能上类似,经理权机制着眼于外部,即面向外部的代理权不可被限制,例外地当代理权滥用时代理行为才有瑕疵。而表见代表则着眼于内部,认为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可以限制代理权,法定代表人违反内部限制的属于越权代表,但是第三人的善意和权限外观弥补了内部权限的缺失,进而产生有权代表的效果。然而确定的是,相比表见代表机制,经理权更优越。
首先,经理权机制在保护第三人和交易安全方面更占优势,依逻辑推演,表见代表规则并不能当然得出 “简单知情并不等于恶意” ,其忽略了如果交易符合正常市场条件或第三人可合理忽视对代表权的内部限制,第三人对内部限制的简单知情并不影响代表行为的效力。其次,关于表见代表,有学者受表见代理之影响,认为第三人可选择性地主张适用表见代表,⑤余延满、冉克平等:《企业法人目的范围外行为新探》,《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4年第1期。而在概括性的代理权视角之下,一旦第三人与代理人缔结法律行为,无论是第三人抑或被代理人都不可单方主张代理人违反某种内部限制,进而质疑代理行为的效力,这更符合代表权的运作机制。最后, “表见代表” 这一称谓容易使人联想到,法人被代表行为拘束是由于第三人的善意或者权利外观;而在概括代理权视角之下,是由于代表人享有概括的、实在的权限才拘束法人,这更符合逻辑和事理,认为法定代表人就某一营业事项没有权限实属拟制。⑥关于代表人与一般代理人的区分,还可参见李宇:《民法总则要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页;他认为,《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三款的法理虽与表见代理有近似之处,但仍有重要区别,因为代表权依法律规定产生无须法人特别授予,无须考察有无授权外观,这间接否定了所谓的表见代表。
此外,特别法人,诸如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也适用《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三款、第五百零四条。应注意的是,其并不都以从事经营活动为主,对交易安全保护的需求并不强烈,与《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三款、第五百零四条之适用关系较远,例如机关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属于行政机关,主要履行公共管理等职能。而且从实践角度来看,在北大法宝依据原《合同法》第五十条和原《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进行检索,案例几乎都是与公司有关的。①检索日期:2022年6月20日。如果实践中出现营利法人之外的法定代表人不遵循章程或其他内部限制,也应注意相对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行为损害法人的利益,这一评定可结合法律对代表权行使的提示和交易时的具体情形等因素。
综上,应以经理权而非表见代表理论来解释《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三款,代表人享有权力之实在,而非权利之外观。第六十一条第三款所确认的经理权规则虽可适用于全部法人,但以营利性法人为主。非营利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也拥有概括代表权,非营利法人也可从事经营活动。在讨论完我国法上所谓 “表见代表” 的实际运作之后,我们来看真正的表见代表理论。
三、真正的表见代表——对代表人身份的认识错误
(一)因登记不实的表见代表
表见代表可因法定代表人选任或离任登记不及时而引起,由于法定代表人选任或离任的生效与其外部公示之间必然会出现时间差。此外,法定代表人任命过程中的瑕疵也会造成登记不实。这一问题的探讨,需要先讨论法定代表人之选任和离任以及相应公示措施,再讨论登记的效力。考虑到公司法人的典型性,此处只讨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类型法人可类推适用之。
1.法定代表人的登记
由于单一的法定代表人制,新选任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一般伴随着前任的离任登记,即涂销登记。因此,我们主要以法定代表人的选任登记作为讨论对象。
(1)法定代表人之选任和离任
关于法定代表人之选任,首先在公司设立时,申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设立登记申请书,其中包括法定代表人的名称。②原《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八条、第十六条。可见, “法定代表人” 是由公司发起人提前共同指定的,被指定的人在公司法人取得人格的同时成为代表人。
其次,在公司设立后,公司变更其法定代表人的,应进行变更登记。但法定代表人究竟是由哪些机构选举出来的呢?依据《公司法》第十三条之规定,董事长、经理和执行董事都可担任法定代表人,考察法定代表人之选任,必先考虑这三种职务的选任。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由董事会过半数选举出来(第一百零九条),当然章程可另行规定;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之产生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第四十四条),如果公司章程无特别规定,应可由董事会过半数选举。当然在国有独资公司,董事长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在董事们中指定(第六十七条)。在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可只设执行董事,其产生办法可由公司章程规定,没有规定时,应由股东会过半数选举。关于公司经理,其由董事会聘任和解聘。
另依《公司法》第二十五条和第八十二条之规定,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章程的必要记载事项,更换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修改公司章程,进而需要三分之二的决议,在实践中很有争议。有人认为股东会罢免法定代表人属于特别决议,也有人认为这属于普通决议,半数即可。①参见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衡中法民二终字第79号判决书;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2010)石民二初字第1l号判决书;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沈行终字第15号判决书。后一种观点值得赞同,前一观点属于形式化理解公司法,还会引起公司两个权力机构之间就法定代表人选任一事产生争执,不利于公司良好地运转。公司法将选任法定代表人的权力交给上述机构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股东(大)会应尊重其决定,避免后者架空前述机构的这一权力。
同《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三条规范的委托代理终止情形类似,法定代表人离任事由包括:辞职、聘任合同届期、被解职、死亡和行为能力丧失等。
(2)登记措施
关于登记措施,依据新通过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八条之规定,公司设立时法定代表人属于法定登记事项,同时记载在营业执照中。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管理部门变更登记处相关材料的记载,同时换发营业执照。另外,依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为了让第三人知情,营业执照应悬挂在公司住所或者分公司营业场所醒目的位置。自2014年年末后,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六条之规定,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信息还需要二十个工作日内在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上公示,任何人皆可网上查阅。以上三种方式中,哪一种方式决定法定代表人的选任公示得以对抗第三人的时点呢?我们认为,工商管理部门的记载属于最原始信息,可信度最高,但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簿的记载和法人营业执照的记载相比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属于公示性较弱的措施,第三人也不便于查询,应以后者为依据来判断法定代表人之选任对抗第三人的时点。②类似观点,参见邹学庚:《〈民法典〉第65条商事登记公示效力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不同观点,参见石一峰:《论商事登记第三人效力》,《法商研究》2018年第6期。立法论层面,可将传统的工商登记作为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前置环节,逐步以后者为中心构建企业信息公示体系,比如可考虑将公司章程和法定代表人的记载信息及时反映在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中,例如将这些材料扫描成pdf上传系统或设置超链接引导公众阅读这些材料。
综上,视情形,法定代表人选任取决于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决议行为,离任事由包括辞职、聘任合同届满和死亡等。明确了法定代表人之选任和离任以及相应的登记措施之后,我们继续讨论代表人登记的效力。
2.登记的效力
关于法定代表人登记之效力,我国法经历了若干变迁。最初,依据《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三条、《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的代表企业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是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也就是说,法定代表人之资格取决于是否经核准登记。最高法院曾适用这一规定,认为被解职的法定代表人,在未经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前仍可代表公司。③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四终字第13号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1期,第20页。即将法定代表人变更这一私法行为的效力取决于行政行为之作出,这一适用是可争议的,该案中的代表行为还涉及 “双方代表” 。具体行政行为只是备案法人依据意思自治作出的代表人变动,并不能决定其私法效力。随后,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登记事项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民法典》第六十五条则进一步明确,法人不得以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实际情况对抗善意相对人。但这两个规定过于笼统,反倒是最高法院的判例逐步明确了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效力的具体规则。
第一,法定代表人的选任和离任自生效之日起即发生效力,但经登记后,才可对抗第三人,除非法人举证第三人之前就已知情。④类似规定参见《法国商法典》第L210-9条第2款,《比利时公司和社团法典》第2:18条第1款。法定代表人之选任系私法行为,自相关决议行为成立时起发生效力,其效力不取决于行政部门的许可。代表人之离任既可因法律行为(如辞职)也可因自然事实(如死亡)而引起,也是自其成立或发生时生效。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以及考虑到制定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等当中的相关规定与《公司法》、《民法典》有关规定相冲突,《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将其彻底废除。法定代表人选任和离任自有关决议行为作出等相关法律事实发生时生效,相应的登记或变更登记只是行政备案性质。①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审三商申字第0247号裁定书。
出于权力的公示和交易安全维护,法定代表人之选任和离任未经登记,不可对抗外部第三人。②关于登记后立即得对抗第三人的例外,参见下文。作为补充,只有善意第三人才值得保护。因此,如果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才离职,这一离职虽未经登记仍可对抗之,该第三人与离职的法定代表人缔结合同的不值得保护。当然应由公司来举证第三人不值得保护。在判例方面,法院认为,公司不能以其法定代表人被公司内部停止职务(未变更登记)否认代表行为的效力,代表人身份应以工商登记为主。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提字第76号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年第11期。随后在另一案件中,最高法院明确区分代表人变更的外部效力和内部效力:第一,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如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而产生的外部争议,应以工商登记为准;第二,公司与股东之间因法定代表人任免产生的内部争议,则应以有效的股东会任免决议为准。由此确认了法定代表人一经任命即发生效力,公司内部人都应予以遵守,但在外部应以登记为准。④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四终字第20号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8期。在另一起案件中,又明确了相对人善意之要件,该案中最高法院认为,法定代表人职务随免除决议生效之日即刻免除,凡知道该法定代表人职务免除事实却仍接受其代表行为的,该代表行为应为无效。⑤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四再字第1号判决书。
如何理解 “第三人” 范围?原则上,选任法定代表人的机关和代表人之外的人都属于第三人。但一概认为公司其他内部人员(例如监事会成员等)不属于第三人不甚合理。对此,在个案认定时,权衡公司利益和交易安全,可有两种途径:或认为公司其他内部人员应当知情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并非第三人,或认为他们不为善意。
第二,未经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之选任或离任,第三人也可主张之。为确保交易安全,第三人最好选择与经登记的法定代表人缔约。当然,如果经有效任命但未经登记的代表人与第三人缔约的,第三人可选择与其缔约而不顾登记情况。此时,公司和第三人都不得以代表人未被登记为理由,主张不被合同拘束。第三人承担的风险在于,若该代表人的声称不真实,则其可能得不到保护。理由很简单,同其他任何法律行为一样,依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法定代表人之选任不直接拘束公司和代表人之外的其他人,但其他人应该尊重当事人的这一意思安排,特别是其他人可主张某一法律行为以证明一件法律事实。⑥J.Flour,J. -L.,Aubert,E.Savaux,Les obligations,L'acte juridique,16eéd.,Sirey,2014,n°432,pp.448-449.这一规则早存在于诉讼行为领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6号)第五十条的规定,法院可接受未经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参与诉讼。只要后者经公司选任即是有效的,而且严格要求参加诉讼的法定代表人必须与登记相符合,未免过于形式主义,也不利于迅速解决纠纷。值得注意的是,当登记事实与客观事实不一致时,如果相对人和代表人缔约构成表见代理的,相对人不享有选择权,即选择无权代理,比如善意相对人与登记的法定代表人缔约,而后者已辞职尚未变更登记。⑦相反观点,参见邹学庚:《〈民法典〉第65条商事登记公示效力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167页。这也符合我国对表见代理适用的通常理解。⑧纪海龙:《〈合同法〉第48条(无权代理规则)评注》,《法学家》2017年第4期。
第三,法定代表人任命之瑕疵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①类似规定参见《欧盟委员会和欧盟议会2017年6月14日与公司法有关的指令(Directive(UE)2017/1132)》第八条,该指令是欧盟对其及其前身 “欧洲共同体” 自1968年以来颁布的若干公司法指令的编纂。法定代表人任命中的瑕疵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方面,考虑到公司债权人利益之维护和交易安全,法律②参见《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了哪些人不应被任命为法定代表人,违反这些规定所作出的任命即是有瑕疵的,应予撤销。另一方面,任命法定代表人的决议行为会出现瑕疵,比如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任命法定代表人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程序等有瑕疵,嗣后被其他利益相关人争议之。这些瑕疵影响法定代表人之登记效力吗?进而影响法定代表人与第三人订立的法律行为吗?回答都是否定的。《民法典》第八十五条和判例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提字第48号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3期。都确立了决议行为的效力瑕疵不影响与外部善意第三人形成的法律关系。基于工商登记的公信力,第三人有理由相信登记在册的法定代表人就是真实的,尽管这一外观事实上不符合真实情况。例外地,如果公司证明第三人知情这些瑕疵仍与代表人交易,则第三人属恶意、不值得保护。既然公司不能向被推定为善意的第三人主张法定代表人任命之瑕疵,那么反过来,第三人能否向公司主张该瑕疵以逃避已经缔结的债务或撤销已缔结的合同呢?考虑到交易安全,第三人无论善意与否,不能以法定代表人任命之瑕疵撤销已经与其订立的合同;而且允许公司主张这一瑕疵或任命法律行为的相对无效是为了保护其利益,第三人自无利益主张这一瑕疵。
反观第一个和第三个规则,它们实质上是表见法理在法定代表人身份领域的反映。内部已经生效的法定代表人选任或离职需要进行相应的公示后才可对抗外部第三人,未经公示的,若离任的代表人仍以公司名义行为的,即为无权代表人,可有表见理论之适用。实际上,代表人的权限都是概括的,第三人判断其是否有代理权限,不是依据授权委托书或其他授权表示,而是依据工商登记,即公司告知第三人其代表人身份的方式是工商登记,有此身份必有概括权限。而普通委托代理中,委托人告知相对人代理人身份和权力的方式主要是出具授权委托书或对相对人表示,代理人身份和权力需分别、个体地分析;同理,委托人在撤回委托或终止委托时,他应收回委托书,必要时采取相应的公示措施或通知潜在的、可能受该撤回影响的第三人;否则,可有表见代理之适用。
关于法定代表人之选任瑕疵,跟普通代理人委托授权的瑕疵一样,授权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不影响代理人所缔结行为的效力,在善意第三人合理相信任命或登记这一表象时,可有表见理论之适用。
综上,在法人内部代表人一经任命或被解任,立即发生效力,但在外部须经登记后才可对抗第三人。选任或解任从其生效之日至其经正式登记之间,可有表见代理之适用。立法论上,可整合《民法典》第六十五条和相关判例作如下规定:第一, “法定代表人的选任和离任经登记后才可对抗第三人,除非公司证明第三人之前已知情或应当知情” ; “第三人可主张未经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之选任或离任” ;第二, “任命法定代表人过程中的瑕疵不得对抗第三人,除非公司证明第三人知情或应当知情” 。除因登记不实引起表见代表适用外,后者还可能因无权代表人之伪称而引起。
(二)因伪称而引起的表见代表
因伪称而引起的表见代表是指某人宣称自己是法定代表人但实际上并不是,或者从来不是代表人,或者权力已经终止并经登记,④如果权力终止但未予以外部登记的,可归于前述 “因登记不实的表见代表” 类型。而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是有代表权的。⑤杨代雄将这种情况称为 “无权代表” ,将其归属于表见代表两种类型之一,参见杨代雄:《〈民法总则〉中的代理制度重大争议问题》,《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原则上在与法定代表人交易时,第三人应该确认其身份,由于我国实行单一的代表人制度以及电子化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之设立,伪称代表情形下第三人应被保护的不多。这可能解释了相比登记不实的表见代表,实践中该类型案件稀少。
在一起典型案例中,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316号判决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晋民终字第282号判决书。由于股权变更引起法定代表人变更后,虽经变更登记,原法定代表人王某仍利用其担任职务期间私自刻制的公章和其他信息继续以公司名义签订抵押合同,法院认为善意第三人可主张表见代理。在归责性层面,法院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方面,该公章曾在工商年检时进行了工商备案,并以此办理过公司有关业务,而且在之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该公章仍被王某使用;受让股权的公司和该公司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后,未及时收回旧公章并进行相应的公示措施,具有过错。另一方面,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12月16日变更登记,而系争抵押合同签订于同月25日,法院没有严格拘束于变更登记的即时对抗效力,而是认为要求相对人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审查到王某无权签订抵押合同未免苛刻。这一判决值得称道,实际上,无论是登记不实还是由于伪称引起的表见代表,皆只是表见代理在代表权领域的适用,需要考察相对人的善意和被代理人的归责性问题。
原则上,法定代表人的任命和变更自进行登记后即可对抗第三人,但在快捷的商事交易中,很难要求第三人时刻关注登记,②这与前述日本法上表见代表董事的制度逻辑有共通之处。例如在相对人与法定代表人经常交易情况下,在某一阶段后者突然被停职,而公司在变更登记后没有及时告知相关第三人的,此时善意第三人值得保护。对此,比较法上多缓和 “登记后立即对抗第三人” 这一规则,规定在有关代表人之任命或变更登记发生后15日内,该代表人以公司名义订立的行为仍有效,只要第三人证明其不可能知情这一登记。③参见《欧盟委员会和欧盟议会2017年6月14日与公司法有关的指令(Directive(UE)2017/1132)》第十六条第六款。当然,代表人的选任经登记后,应由第三人来举证其不可能知情或者其信赖是合理的。这区别于上面我们所提到的,代表人的任命或离任在经登记之前,应由公司来证明第三人已经知情,第三人在这两种情形下的举证负担是不同的,由第三人来主张其不可能知情这一消极事实明显较重。这一规定也是表见代理之具体适用。换而言之,将工商登记的 “绝对” 对抗效力延长到登记事项被登记之后的若干天内,同时让相对人对其在此期间的善意负举证责任,可兼顾善意相对人保护和公司利益,避免登记事项登记后的立即对抗力之机械适用。从立法论角度,我们可在将来商事主体登记规范完善时,吸收判例和比较法经验规定: “法定代表人在其离任登记后十五日内缔结的法律行为有效,只要第三人证明其不可能知情该离任事实” 。
概言之,第三人可因登记不实或代表人的伪称表示而合理相信其相对人有权代理法人,引起对法定代表人身份的认识错误,进而可有表见代理之适用。当然,这两种情形对第三人的善意要件有不同要求。法定代表人选任或离任之生效与登记公示不可避免地有一定时间差,在引起表见代理适用时,法人应该承担这一经营风险,但其可向无权代表人追偿。接下来我们追问区别表见代表和经理权有何意义呢?
(三)区分真正的表见代表与经理权的意义
区分真正的表见代表和非真正的表见代表,即对代表人身份的认识与对代表人权力本身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在范围具体的委托代理权视角之下,代理人的实际授权和其对外所展现出的外观可能有所差异,造成第三人对其权力发生认识错误。而从事理上看,在尊重其他机构法定职权的前提下,代表人对公司营业事务享有全部概括的权限,第三人很难就代表权与合议制的且定期聚会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有效沟通。在概括代表权视角之下,很难对代表权范围发生认识错误,甚至可以说很难出现 “越权” ,更多的则是 “滥权” ,这是法定代表人区分于一般意定代理人的关键。 “越权” 需要客观比对被授予的权力和代理人已完成的法律行为,①刘骏:《法国新债法的代理制度与我国民法总则代理之比较》,《交大法学》2017年第2期。而 “滥权” 之认定并不满足于代理行为形式上违反了章程或某内部规定,而需实质判断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代理行为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本人举证代理人 “滥权” 比举证其 “越权” 更难。
第二,相对人 “善意” 之界定和效果在这两种情况下有着明显的区分。在真正的表见代表中,同无权代理行为一样,在第三人知情或应当知情有关代表人的登记状况与实际不一致时,无权代表人的行为未经授权,是违背法人意志和损害法人利益的,其效力待定。相反,当代表人不遵守对其权力的内部限制进行代表行为时,由于核心是考察代表人的行为是否违背法人利益以及相对人是否应该知情这一违反,导致相对人对代表人违反内部限制的简单知情并不足够认定其恶意,该代表行为原则上有效。不加区分地对待经理权和真正的表见代表会危害交易安全,会不加区别地扩大 “恶意” 相对人的范围。
或有质疑观点认为,《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三款、第五百零四条也可适用于真正表见代表的情形,即可规范对代表权身份的认识错误,进而质疑区分真正表见代表和非真正表见代表的意义。这一观点值得商榷,首先,真正表见代表实乃表见法理的适用,适用《民法典》第六十五条或类推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等规定即可,无须辗转适用第五百零四条、第六十一条第三款。其次,自原《合同法》第五十条制定以来,立法机关相关材料解读②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解读》(上),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49页。、学说论述和案例适用并未将对代表人身份认识错误作为该条或第六十一条第三款的涵射对象。最后,在真正表见代表机制下,第三人的善意之认定应区分是因登记不实引起的抑或因代表人伪称而引起的,而这一区分评价融入《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三款、第五百零四条适用之中会带来不必要的困难,在适用这些条款时,相对人的简单知情并不当然被认定为恶意。
第三,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类似于委任合同关系,代表人之选任属意定;而《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三款事实上承认了代表人一经任命即享有概括和法定的权限,其权力不应在合同的视角下进行分析,某种程度上该权力被 “客观化” 或 “法定化” 了,即代表人是权力被客观化的意定代理人。甚至可以说,各公司法定代表人权力都是类似的。相反,在普通委托代理人情况下,无论其身份还是权力皆在合同这一视角之下进行分析,只是例外地在表见代理的情况下代理人的权力不由个体 “意思” 来决定而是由客观 “外观” 来确定。
第四,适用范围之差别,真正的表见代表实乃表见法理之具体化,可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法人,还可包括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市场主体,在这些情形下,都可能出现第三人因登记等外观措施而对代表人或业务执行人的身份发生认识错误。或者说,对团体对外表达机关的有效授权和该授权的公示之间常有不一致,可引起表见代理的适用。而非真正的表见代表即经理权规则主要适用于对交易安全有强烈保护需求的营利法人,相对人不可能对其概括权力发生认识错误,其适用于非营利法人时需要同时考虑这类法人的目的。
因此,无论是从代理权的基本概念还是从交易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区分对代表人身份的认识和对其权力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结 论
综上所述,受日本法上表见代表董事制度和原《合同法》条文安排的影响,主流观点将规范越权行为的原《合同法》第五十条解读为 “表见代表” ,表见代表董事制度是指相对人合理信赖不是代表董事的人有权代表公司。由此混淆了对代表人身份的认识和对其权力的认识,如果说相对人可能对代表人身份因登记或代表人伪称而发生认识错误,其不可能对代表人的概括权力发生认识错误。代表权涉及法人所有营业事务,且对其权力的内部限制不得对抗第三人,第三人如何能对该权力发生认识错误?在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违反章程或其他非法定限制时,代表行为对公司有效,第三人的对这些内部限制的简单知情并不构成恶意,而需实质性判断该行为是否损害法人利益。区分这两种认识具有重要意义。立法论上,可整合有关真正表见代表的判例和比较法相关经验,明确以下规则: “法定代表人的选任和离任经登记后才可对抗第三人,除非公司证明第三人之前已知情或应当知情” ; “第三人可主张未经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之选任或离任” ; “法定代表人在其离任登记后十五日内缔结的法律行为有效,只要第三人证明其不可能知情该离任事实” ; “任命法定代表人过程中的瑕疵不得对抗第三人,除非公司证明第三人对此知情或应当知情” 。
-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论处分限制与宅基地三权分置
- 也论土地承包权的性质
- 利义统合观与明代商人的经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