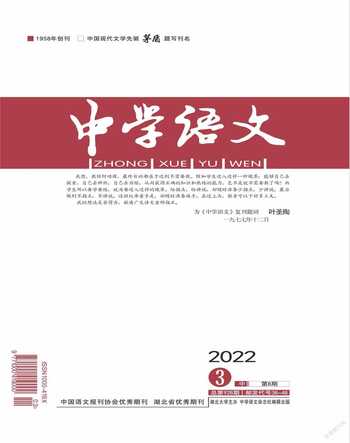从美学看语文教育
马振伟
关键词美学 语文教育 审美心胸 审美能力
年底,笔者整理资料,蓦然看到了半期试卷上的一篇文章——朱光潜的《诗的境界》。笔者曾给学生上过两学期的美学课,喜欢朱光潜,他的这篇文章以前也读过,有今年一番经历,再读,感慨颇多。
人们外感万物,内觉神明,全在一“见”字,朱光潜将之析为“直觉”与“知觉”。知觉见之于事物的内部联系,是科学发生的基础。而对于艺术,美在意象,无直觉则难见其意象,难感其“美”。诗歌是文学艺术的精华,对“直觉”的依赖更深更紧,朱光潜所谓“如果不能在直觉中成为独立自足的意象,那就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形象,就还不成为诗的境界。一首诗如果不能令人当作独立自足的意象来看,那还有芜杂凑塞或空虚的毛病,就不能算是好诗”,意即如此。钟嵘:“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此非虚言。因此,诗歌教学乃至语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应在于培养学生对文学美语言美的直觉能力。
朱光潜举例道:比如说读崔颢《长干行》,你必须在一顷刻中把它所写的情境看成一幅新鲜的图画,或是一幕生动的戏剧,让它笼罩住你的全部意识,使你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玩味它,以至于把它以外的一切事物都暂时忘去。在这一顷刻中你不能同时起“它是—首唐人五绝”、“它用平声韵”、“横塘是某处地名”之类的联想。这些联想一发生,你就从诗的境界迁到名理世界和实际世界了。
很遗憾,我们的语文课堂好像反着来的,语多文少,理多美少,知识多文化少。
究其原因,语自外入,是世界在内心的异质同构,容易把握和量化,文自心生,是情感的寄托与投射,难以把握,更不易量化,故人们舍后就前,舍难就易,这是一种心理惰性,也是一种心理惯性,更是时势使然。
似乎,我们的语文教育是失败的,至少是低效的。
失败,源于我们被这种惰性、惯性和时势所打败。低效,源于知觉和直觉可以互相转化,即朱光潜所谓“直觉的知常进为名理的知,名理的知亦可酿成直觉的知”,但这种转化是有损耗的,是低效的,是玉石不分的,如大浪淘沙,但也会淘去金石,又如面对音乐绘画,大多数人只觉悦耳悦目,能感悦心悦意的就很少了,悦神悦志的就更寥寥了。
记得在高中时笔者读沈从文的《边城》,只觉语言绵软俚俗,叙事不清不楚,颇感无聊。后来到了大学,图书馆里,一杯清茶,两畔微风,捧上《边城》再读,一下子就被其出尘脱俗的桃源之美所折服了。
心境变了,高中的浮躁功利,大学的轻松自在,同样一篇《边城》也就成了两个世界。
无独有偶。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里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很多人在读这篇文章时都会忽略这一句话,直接跳到对“美景”的分析上,其实此句话正是“美景”之源,正因为内心空明澄澈,那“日日走过的荷塘”才会明亮起来,才能行诸于笔端,呈现于读者面前。
李清照的《如梦令》,面对“雨疏风骤”后的海棠花,丫鬟答道:“海棠依旧”。李清照则言:“绿肥红瘦”,这真真印证了一句话:世界上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心胸)。
心胸的空明澄澈并不等于空无,它需要审美主体的积极参与和资禀,胸有河山古今,才能视通万里,思接千载,所以引导学生多读、多感、多悟,也就非常重要。心胸虚静,亦无须一定要摒弃日常生活的功利琐碎,陶渊明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意即此意,当然此种修为更多要靠学生自己了。
可以说,审美心胸直接决定了“美”的有无厚薄,如何营造塑造学生的审美心胸,这应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文艺教育工作者应思考的问题。
美在意象,这是美学的核心要义。
何谓意象?“莲花”本身不是,周敦颐自己也不是,周心中“君子者也”的莲花才是,即意象是寄寓了人的心灵旨趣的物的形象,柳宗元“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即是此意。
美在意象,培养学生的语文审美能力的重点也就是在培养学生对意象的感知能力了。
在所有的文体中,最富于意象的莫过于诗歌了。
诗主情,限于篇幅和韵律,它和小说、戏剧、散文等往往借事抒情不同,而是长于借物抒情。作者将感情外移于景物,读者将景物内化为感情,如此在审美的两端便实现了感情的宣泄与享受,唤起了心灵的共鸣。正因为这样,每当我们做出或读到一首好诗,我们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就不奇怪了。
朱光潜曾言:“一部好小說或是一部好戏剧,都可以当一首诗看。诗比别类文学较谨严,较纯粹,较精微。如果对诗没有兴趣,对小说、戏剧、杂文等等的佳妙处,也终不免有些隔膜。不爱好诗而爱好小说、戏剧的人,大都在小说和戏剧中可能只是见到最粗浅的一部分,就是故事。”
持之以恒的坚持诗歌教学是培养学生语文审美能力最重要也最便捷的途径了。
似乎,我们现在的语文教材诗歌少了点。
在每次分析完课文或考试后,往往都会有学生跟上来问:“老师,作者写作时真的想到这些了吗?”
似乎每次高考后,也都会有作家甚至是选文作者跃跃欲试,去做一下题目,完后面对“奇怪”的正确答案惊呼:“我当时没这么想啊!”
难道我们都错了?
其实,一个公开的作品,自作者画上句号的那一刻便是一个独立的展现在读者面前供其鉴赏的艺术品了,读者调动自己的审美感知能力对其进行阐释、解读。在此过程中,读者会不可避免的带有自己的主观色彩,惟其如此,才会有此与彼心灵的共鸣、契合,才会有“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精彩,才会有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才会有美。
换句话说,对作品阐释时有原作者“没这么想”的部分是很正常的。
阐释没错,甚至过度阐释也没错,错的是出题者将自己对文本的阐释强加给学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完全消泯、无视学生的理解和阐释,学生也只好费尽心机去揣摩出题者的意图,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可能会有创新精神和想象能力呢?
更可怕的问题在于阐释的模式化,提到诗歌,离愁别绪,爱恨情仇;提到文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提到小说,痛斥腐朽,弘扬正义……。如此种种,以至于上课枯燥,没人愿听,考试机械,堆砌术语。语文的审美性、抒情性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一堆堆题型术语和答题技巧。
如此种种,原因你懂的。至于办法,谁知道呢?但我们将努力“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