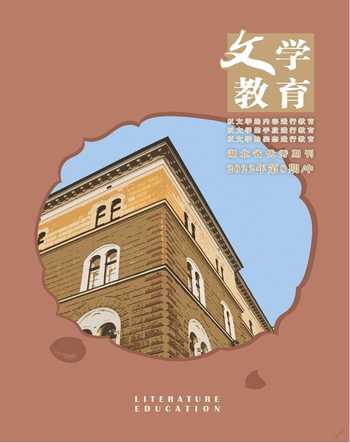父亲去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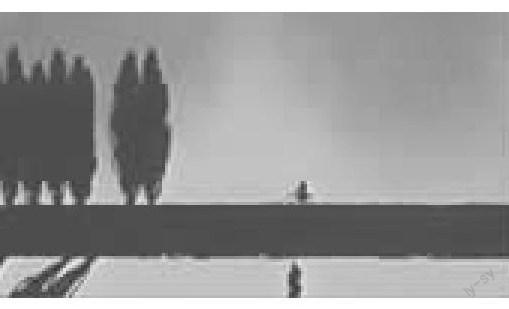
举水河从宋埠镇两边环城而过。南边的河道宽些,叫大河;北边的河道窄点,叫小河。小河边有条街,是城镇与码头连接的通道。街道上铺满石板,石板上刻着深深车辙。与城里的大街相比,这条街很小,叫小街。小街约一丈多宽,有三四十户人家,大部分做小生意。
我家住在小街北头,紧挨着河堤。河堤上绿草葱茏,沿着河堤,两边有许多参差不齐的新坟旧墓,掩映在树木和野草之中。堤下的壕沟,伸向望不到头的远方。
四岁那年的一天,我与坤伢一起,在屋后壕沟里玩。坤伢是对门王奶奶的长孙,与我年龄相仿。壕沟是小街后面倒垃圾和排污水的地方,在壕沟与小街之间,有一块块面积不大、田埂很窄的菜地。正是油菜开花时节,地里一片金黄,一股清香。
好些天没下雨,积水和苔藓都晒干了。霉臭刺鼻的壕沟里,野草灌木绿成一片,把一堆堆垃圾掩藏其中。垃圾堆上爬满绿头苍蝇,叽叽喳喳的麻雀在灌木中扑腾,惊得苍蝇不时“嗡”地飞起。两只铜钱大小的黄蝶,在草丛间忽上忽下。
我与坤伢穿着土布褂和开裆裤,屁股翘老高,趴在沟底玩。三月的太阳已有些灼人,烘热的恶臭直往鼻孔里钻。但我俩注意力全在泥地上,那里露出个骷髅的头骨,枯黄枯黄的,黑洞洞的眼眶塞满泥巴。我找了块巴掌大的瓦片,坤伢捡了根鸡蛋粗的树枝。我们费力地掘开腐臭的泥土,将头骨挖了出来。
头骨出土后,碎成好几块。我们发现那个头盖骨很像锅,就用三块石头支个灶,将头盖骨放在石头上,用瓦片铲了点泥沙放里面,又丢几片马齿苋叶进去,学着大人炒菜的样子,用小木棍在头盖骨中搅拌。这个游戏,姐把它叫做“嫁姑娘”。时近中午,我们如痴如醉,一脸泥点,鼻子上渗出了汗珠。
耳边传来姐的喊声。我站起身,只见姐穿件白底蓝格衬衣,颈上系着红领巾,站在后门外大叫。
“宪宪,快回来。妈要我们跟她一起出去。”姐向我招着手。
我出生时,正逢国家发布第一部宪法,所以父亲为我取名建宪。那年头很看重宪法,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只要名字中有个“宪”,准是这年出生的。
我从壕沟爬出来,向家中走了几步,有点不舍地回头看了看自己的“锅”。忽然,我发现那个骷髅头的下半截,被我们甩在一旁的两排弧形齿骨,还有连着鼻骨的两个黑眼眶,像一个没有脸的怪人,就要笑出声来的样子,吓得我的心扑通乱跳。
家中有些异样。奶奶坐在圆靠椅上,歪着身子,用围兜不断擦眼泪。她穿着大襟黑褂,满头白发梳成个柿子大的鬏髻,盘在脑后。妈穿着宽大的蓝衫,挺着大肚子,一脸消瘦,眼圈红红的,站在奶奶旁边。
“不是我不开通。我一辈子生了十一个,只有这个断肠儿还活在世上,叫我么样舍得!”我听到奶奶在说活,她的眼泪不断线地哗哗往下掉。
我和姐一进门,妈就把我拉到天井旁,拿起葫芦瓢,从石臼中舀出一瓢水,冲洗脏兮兮的小手。洗完手,妈用天井里挂着的粗布毛巾,擦了擦我的脸,脱下沾满泥土的小褂和裤子,扔进天井边的脚盆,从里屋拿出一套干净裤褂,给我换上。天井里长满绿苔,散发着霉味。
妈低头给我扣扣,鼻孔里喘着粗气,两个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在我脸上擦来擦去。她的手冰凉,右手大拇指分了叉,长着一大一小两个指头,这使她扣起扣子来很不方便,弄了好几下才扣好。
“奶,我们去送送他。车子在车站要停一下,我们在爷爷店里吃饭。”妈挺着大肚子,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姐,对奶奶说。走到门口,她又回头说:“奶,您莫太伤心。他说了,过一两年就能调回来。”
奶奶没抬头,扬手轻轻挥了一下。
出门左拐,上了大堤。我问妈去哪儿,妈说:“车站。送你爸去新疆。”
爸爸在外工作,很少回家,對我来说,他去哪儿都一样。我感兴趣的是去爷爷店里吃饭,每次在那里总会有点好东西吃。
下了大堤,沿公路走一小段路,远远望见爷爷的茶馆。茶馆挤在公路边一排灰蒙蒙的房子中间,门前吊着个很大的黄灯笼,灯笼上写着个“茶”字。
茶馆里一大群人站着,有老有小,把爷爷围在中间,杂乱地叫喊声传了出来:“来一个!来一个!”一个20来岁、光着上身、剃个平头的小伙子,笑嘻嘻地跑出茶馆,从门外抱进一块大青砖。这种青砖是修城墙专用的,有三四十斤重,生铁般坚硬。小平头呼哧呼哧地将青砖抱进茶馆,人墙闪开一条路。只见粗矮壮实的爷爷,光着头,从黑色对襟夹衣中脱出一只右手,挽了挽袖子,露出青筋突起的粗胳膊。他深深吐纳了几口气,站直了,将右手高举,大吼一声:“嘿——!”只见那只手变成掌刀,电光石火般切在小平头双手抱着的青砖上,“咔嚓”一声,青砖断成两块,从小平头手上掉下去,差点砸在他的脚上。人群一声欢呼,鼓起掌来。
爷爷收回右手,伸进袖筒之中,得意洋洋地笑着:“喝茶!喝茶!”
人群围上茶桌。爷爷没有去筛茶,而是向茶馆门口走了过来。
“小邋遢,早看见你了!”爷爷把我抱起,看了看我的袖口,“今天没用袖子擦鼻涕?”
“妈给我换了衣服。”我说。
“难怪这干净。”爷爷笑着。扭头对妈说:“幼香,我买了菜。你把桶里那条鱼杀一下,还是活的。”
妈的大名叫李幼华,幼香是她的乳名。除大姨和二姨外,只有爷爷和奶奶把妈叫“幼香”。
妈没说话,挽了挽袖子,挺着大肚子,一扭一扭走向后边的灶屋,拿起围裙系在身上。
姐姐跑向车站。“妈,我去接爸爸。”
“我要看鱼。”我对爷爷说。爷爷把我放了下来,我跑到灶屋,蹲在木桶旁,桶底果然有条半尺多长的鲫鱼,鼓着眼睛瞪我。
爷爷走进灶屋,从一个有大人那么高的铜茶罐中,向小茶壶里倒茶。那个小茶壶也是黄铜的,壶嘴又长又尖。
“爹,你么答应他去那远的地方。”妈的声音,“奶昨天哭了一夜。”
“领导要他去,有么办法!”爷爷说。
妈没说话,在铜盆里哗啦哗啦洗菜。爷爷走向堂屋,给坐在条凳上的茶客们筛茶。回到灶屋,爷爷拿起烟管,一股呛人的烟雾飘了过来。
不一会,姐的声音传来:“妈,爸爸下车了!”
一辆绿色的敞蓬大卡车,停在车站不远处的公路边,车上的人手攀着挡板往下爬。姐牵着爸爸的手,从公路边走过来。爸爸穿件没领章的退色灰军衣,胸口插着支钢笔,又黑又瘦。
爷爷放下烟袋,迎了出去。我跑在爷爷前面,扑向爸爸。
爸爸把我抱起来,绕过堂屋里喝茶的人们,径直走进灶屋,坐在灶前烧火的小板凳上。
“爸,计划改了。我们到三岔路吃饭,车子在这里只加油。”爸爸对爷爷说。又把头转向妈,“幼华,小玲没来?”
“她睡了。”妈没好气地答,把白菜从铜盆往筲箕里捞。
爷爷拿起烟管长吸一口,对爸爸说:“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你这一去新疆,几年不能回,家里么辦?”
“昨天副县长找我谈了话,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爸爸望了望灶屋外,低声说,“他还说,去新疆的人都涨工资,比这里多一倍。”
爷爷望了望妈。妈把头转向一边,咬着嘴唇,不做声。
“内地去的都有提拔。我现在是县援疆团的参谋。”爸爸对爷爷说,眼睛却看着妈。
“参谋是多大的官?”爷爷问,“过了团长就是你?”
爸爸略为犹豫了一下,轻声说:“差不多吧。”
妈突然从水桶中捞起那条鲫鱼,“啪”的一声,重重摔在地上。响声很大,堂屋里喝茶的人都转过头来,朝灶屋里看。鲫鱼弯曲着身子,张着口,在地上痛苦地扭动着。妈绷着脸,挺着大肚子,费力地弯下腰,把还未断气的鲫鱼捡起来,放在案板上,一手用抹布按着鱼头,一手拿起菜刀,刮起鱼鳞来。
茶馆内外,所有人都没说话。只有妈的菜刀,在鱼身上发出嘶拉嘶拉的声音。
公路上“轰”的驶过一辆汽车,一团灰尘和一股汽油味扑进茶馆。
“爸,我也想去新疆。”姐姐忽然说。
“爸,我要当团长。”我歪着头,大声说。
大家都笑了。这时,车站那边有人喊:
“陈兆,上车了!”
“来了。”爸爸应答着。妈放下菜刀,在围裙上揩了揩手,从爸爸手上把我抱过来,放在地上。爸爸站起来走出茶馆,妈牵着我,爷爷牵着姐跟在后面。
到了卡车边,爸爸回头对妈说:“我一到那里就写信来。”
妈转过头,不看往车斗中攀爬的爸爸。有几滴冰凉的水,落在我头上。
卡车开动了。
“爸爸再见!”姐姐扬着手喊。爷爷向汽车挥手。
妈把背对着汽车,低着头,咬着牙,脸色蜡黄。她撇开腿,挺着肚子吃力地站着,眼睛朝向金黄的油菜地。
卡车上传来一阵激昂的歌声:
再见吧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
汽车被路上扬起的灰尘淹没,歌声越来越远。不一会,灰尘和歌声消失得无影无踪,公路边,只剩下老人、孩子和挺着大肚子的瘦削女人。
父亲在日记里记载,这一天是1959年3月18日。
陈芝麻,本名陈建宪,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